- +1
葉兆言專欄:志同道合,契若金蘭
光緒三十四年是1908年,這一年,光緒皇帝37歲,生命已到盡頭。大清朝的氣數基本完了,再過三年,便是轟轟烈烈辛亥革命。有人把中國封建時代結束,歸罪為取消科舉,這話題有些突兀,也有些自說自話,但是肯定有它的道理。對于廣大老百姓來說,科舉從來都是唯一出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跟今天的高考一樣,陽光大道也好,獨木小橋也好,有它你可能會抱怨,沒它還真有些麻煩。
應付科舉也和高考一樣,有什么樣的科舉,就有什么樣的對策。譬如在唐朝,科目雖繁多,最看重的還是詩詞歌賦,后人有一個“文起八代之衰”之說,然而誰都知道,因為朝廷看重詩賦,看重名人推薦,因此當時的高考學子,清一色文學青年,揣著自己詩集到處亂竄,到處拜碼頭見老爺子,李白李賀都這么干過。那些藏懷里的詩集又叫行卷,有關行卷的研究,程千帆老先生最有發言權。
又譬如在明清,絕對八股文的天下。喜歡不喜歡八股文是一回事,會不會八股文又是一回事。關于八股文,有種種非議種種不堪,不過說老實話,我還真有點喜歡八股。從相對公平的角度看,還是八股靠譜,畢竟這玩意有板有眼,很輕易看出好壞。唐人以詩賦取士,看走眼乃平常事,杜甫被后人稱為詩圣,當年也就二本水平,或許連二本分數線都夠不上。八股文的好處是比較容易操作,有法可依,有評判標準。還有書法的嚴格要求,要又黑又光又亮,我見過康有為的考卷,小楷規規矩矩,全無寫大字的霸氣。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有所好,下必其焉。科舉不是說取消就取消,也有個過程,經過一系列改革。1898年開始考理科內容,加考經濟特科,嚴禁憑楷法優劣定高下。記得最后一次科舉殿試,譚延闿的文章便是談西藏問題。對科舉的挑戰事實上早已開始,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參加科舉,就公然不寫八股文,用的是散文體。還有一位叫柳詒徵更不像話,干脆用篆字書寫,簡直是視科舉為游戲。
廢科舉是個進步,這么做,顯然更有利于官二代和富二代,畢竟進新式的大學,要出國留學,得有銀子才行。規則改變了,新學開始流行,平民百姓最多只能跟著起起哄。當時有個說法,小學畢業相當童生,中學畢業便是舉人,但凡家中有點余錢,都會讓小孩去新學堂。也就是在這時候,蘇州府所屬三個縣,一口氣竟然合辦了四十所小學。1907年,草橋蘇州公立中學開始招生,招了五六十號人,按考試成績分成一二年級兩班。有趣的是,雖然形式上分兩個年級,最后畢業仍然還是同一天。
我祖父是草橋中學第一期的學生,過去常聽家人說起他當時的同學,有顧頡剛,有王伯祥,還有吳湖帆,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好像隨便扯個出來都能是個角兒。事實上,這批學生畢業,已是1912年的1月,這時候,大清不復存在,已經是民國,所謂中學畢業相當于舉人身份,完全是一句笑話。這時候,不要說舉人,就算是賜同進士出身又怎么樣。祖父他們這一代人能夠有幸成材,草橋中學的這段歷史固然重要,后來的用功也不可抹殺。說到底,一個良好開始,未必就一定會有輝煌結局。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一百多年前,中學剛畢業那陣,未能繼續上大學的祖父,心情一定會有些壓抑,難免羨慕嫉妒恨。從草橋中學走出去,繼續深造上大學是常事,他的同學有好多都去了北大。后來的一些好友,如朱自清,如俞平伯,也都是北大出身。祖父生前經常提醒我們,上不上大學并不重要,過去一直以為這么說,是因為他自己學歷不過硬說氣話,后來才明白,其實是在鼓勵我們小輩。能上大學當然是好事,我高中畢業沒大學可上,祖父希望我們不要因此荒廢學業,后來有機會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他又擔心我會自滿,不能老老實實做學問。
今年12月到蘇州參加會議,有位喜歡收藏的朋友給我看了一個圖片,是祖父中學時代與同學袁封百的“金蘭譜”。耳聞不如目睹,過去也經常聽說,武俠小說上似乎瞄過一兩眼,基本上沒往心上去。這次卻完全不一樣,看了以后,覺得很好玩,真的很好玩,立刻有要與讀者一起分享的念頭。大家可以看實物圖片,為便于閱讀,我把上面文字抄點下來,先抄中間這一段。
以意氣相投而結為異姓兄弟者,古時常有之。然求其始終如一,安樂相共,危難相濟者已百無二三,況進此者乎。后世之風,更趨于下,每邂逅相遇,傾心一談,遽結為兄弟。安知其所言非虛乎。以致初則親如骨肉,后則疏若路人,始也刎頸,終致切齒。觀晏平仲久而敬之之句,得無赧赧乎。
袁君與余同學已二年,各人意氣相投,因而結為異姓手足,非邂逅相遇而結為兄弟者可比。以道義相交,以學問相友,深恥若輩所為。爰各作盟誓,以各示己志,始得始終如一,不致首鼠兩端,以貽人笑。議其誓曰:
道義相交,學問相友。有侮共御,有過相規。富貴共之,貧賤同之。終始守恃,弗背弗忘。謂予不信,有如河漢。

不管怎么說,小孩子的話用不著太當真。在我伯父寫的那本厚厚的祖父傳記上,甚至都沒提到這位袁封百先生。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從草橋中學畢業,袁去了北京大學,然后就是在東吳大學教書,擅長書法篆刻,與畫家吳湖帆交往頗多。袁家是世家,顧頡剛和俞平伯的家世都很有來頭,和他們相比,出于平民百姓之家的祖父根本沒錢去念大學,他是完全靠自學成才。
志同道合,契若金蘭,金蘭譜的格式很有意思,不看實物不知道,看了恍然大悟。最有意思的當然還是前面自我介紹,如實填寫交待家族四代人的姓名,祖父的父親竟然娶過三個妻子。我們只知道有個與祖父一樣長壽的姑奶奶,不知道祖父還有早年過世的胞兄和胞妹。
除了這個金蘭譜,袁家還保存著當時互相送的照片,照片背后有祖父的題字:
同學經年,意氣相投,蒙不棄結為兄弟,無有為信,聊以小影表微情。封百兄收存,至若家世里居,盟誓之言,則詳于蘭譜不贅。如弟葉紹鈞持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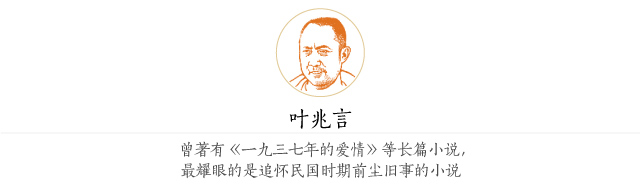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