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吳鴻:川菜因包容受歡迎,蒼蠅館子永不會消失
在成都的街邊有很多小飯館,里面的食客往往是形形色色的,既有周圍小區的居民,也有特意來尋覓美食的食客,門口有時還會停著豪車。其實在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小飯館,例如香港早年的大排檔,但是四川人比較詼諧,稱這些小飯館為“蒼蠅館子”,它們在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的生活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蒼蠅館子”早年得名于那些衛生條件不好、蒼蠅亂飛的路邊攤,而現在四川人仍用它來稱呼所有的小餐館,不過其中“蒼蠅”的意味發生了變化,這些飯館里沒有了蒼蠅,但是食客自己卻像蒼蠅一樣四處尋找美食。
不像那些高大上的餐館,“蒼蠅館子”是四川普通老百姓日常餐飲的備選,它們不僅味道好,又經濟實惠。和那些由資本注入、以謀取投資回報的連鎖餐飲店不同,“蒼蠅館子”往往是家庭作坊式,一家人的生存要依靠一家小餐館,因此他們需要使出渾身解數,在味道上做足功夫,以招攬和留住客人。
但隨著城市規劃帶來的拆遷,有些蒼蠅館子不得不搬遷甚至停業,不管對于店家還是食客,都是一種損失。資深出版人吳鴻長年居住在成都,他多年來一直在體驗蒼蠅館子的生活,而他也為蒼蠅館子的這種現狀感到擔憂,因此記錄下了他和朋友們在蒼蠅館子的覓食生活,結集成冊出版,名為《舌尖上的四川蒼蠅館子》。
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了作者吳鴻,請他談談蒼蠅館子的發展歷史與未來以及川菜廣受歡迎的原因。

澎湃新聞:之所以稱“蒼蠅館子”,是因為它的衛生條件比較差,我看到另外有說法是指食客像蒼蠅似的找美食?
吳鴻:最早的餐館,我想環境應該普遍都是比較差的,有幾只蒼蠅飛來飛去,十分正常。蒼蠅無孔不入,就算是在高大上的餐館里,也會不時有蒼蠅的出現。但我書名取的“蒼蠅館子”不是這意思,這是我們四川人,特別是成都人對一切小餐館的統稱,這些小餐館面積不大,設施簡陋,衛生條件差一些,但也不至于蒼蠅亂飛。流沙河先生在給我的序中說,現在的市政設施完善,陽溝死凼都沒有了,哪里還會有蒼蠅,他還詼諧地說,何況現在的空氣有霾水有毒,蠅蛆想活也難,蒼蠅早就沒有了,但蒼蠅館子卻要永恒下去。
我在后記中總結了幾條蒼蠅館子的特點,一是形容蒼蠅館子的多,遍布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就像蒼蠅散落在市區;二是說蒼蠅館子確實有些簡陋,條件差些;三是說成都人好吃,無論餐館開得多么的隱蔽,都能像蒼蠅一樣找到自己心儀的去處。這就有些類似你說的“食客像蒼蠅似的找美食”。四是,大多數蒼蠅館子都是為求生存而開的,生活不易,老板總是使出渾身解數把味道做好,用味道來留住客人,因此,在成都,蒼蠅館子又是“好味道”的代名詞。好味道的餐館往往客人很多,人多說話聲音就大就嘈雜,嗡嗡之聲就像蒼蠅飛來飛去,這就是蒼蠅館子來歷的又一個引申。
澎湃新聞:其他城市的這種小館子也能叫做蒼蠅館子嗎?
吳鴻:把小餐館叫做蒼蠅館子,只有四川人才這么叫,其他省份的人不這么稱呼。一般就叫小店、路邊店或大排檔等。但我們四川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叫這些小餐館為蒼蠅館子。如果大家對我的這本《舌尖上的四川蒼蠅館子》認可度高的話,相信以后全國所有城市的人都會叫小館子是“蒼蠅館子”的。

澎湃新聞:為什么成都人那么喜歡蒼蠅館子?
吳鴻:其實不只是成都,每個地方都會有很多人喜歡這種小餐館,它能夠代表當地的一種生活狀態,是市井生活的一種反映。
我當初寫這本書的時候,流沙河先生說他非常贊同,說蒼蠅館子就是成都人生活最真實的形態表現,不像5A景區,全國到處都差不多。成都人愛去蒼蠅館子消費,是成都人生活的常態。好吃是成都人的天性,尋找自己喜歡的蒼蠅館子去滿足口腹之欲,是成都人生活中的樂趣。很多成都人不愿意把時間浪費在家里,做兩小時飯菜,半小時不到就吃完了,還要洗鍋洗碗,麻煩。他們寧愿把時間花在吃蒼蠅館子上,既是享受,其中也跟朋友交流了,增進了友誼,說不定在飯桌上還整合了資源,成就了一單業務。
成都現在是個不夜城,24小時都能找到很多好吃的蒼蠅館子,能成一個成都人是上天的厚愛。
澎湃新聞:但現在人們好像越來越注重餐廳飲食衛生,蒼蠅館子的生意會受影響嗎?
吳鴻:蒼蠅館子的說法是成都人的諧謔,流沙河先生說是“自占地步,不讓你來貶損”,并不是說餐館不衛生,人們的衛生意識強了,要求高了,當然是很好,但應該不會影響到蒼蠅館子的生意的。
在四川特別是在成都地區,蒼蠅館子的稱謂已經是廣泛地被接受了,大家從來不避諱。人們經常可以看到開著寶馬、奔馳車的人去吃好味道的蒼蠅館子。對于那些開好車就是講身份的其他城市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成都不是的,成都飲食非常大眾化、市井化。
“蒼蠅館子”這個名字,如果不了解的人,聽到后可能會產生惡心感。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反對和支持的意見都很多,反對的說一聽到“蒼蠅”二字就好惡心啊,但支持我的人說,這是地道的四川味道和成都味道,是四川獨一無二的文化啊。所以我權衡再三,仍把名字定為“四川蒼蠅館子”。據說拍攝《舌尖上的中國》的陳曉卿到了四川以后,也特別喜歡蒼蠅館子,他認為真正的美食只有在這些民間的館子才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所以他也為我這本書寫了推薦語。
澎湃新聞:在成都如何找到這種蒼蠅館子,是靠大家口口相傳,遇到好吃的人才能吃到,還是有其他方式?
吳鴻:口口相傳的推薦是最值得信賴的推薦,所以到一座城市,最好交幾個好吃的朋友,大家趣味相投,有了他們的引導,那真是不一樣的體驗。前不久我到重慶去,就是當地資深的好吃嘴朋友帶我去吃與成都不一樣的蹄花和豆花,記憶深刻,那樣偏僻的地方美食,不是一個外來客人能找得到的。
現在到成都體驗蒼蠅館子的方法有很多,電視臺、電臺和當地的紙媒都設有欄目推薦,但這種推廣大多是廣告行為,“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這些推廣大多不可信,我試過幾家,無一讓我滿意的——當然,“食無定味,適者為珍”,不滿意只是不合我口味而已。還有就是微信朋友圈的分享,當地飲食達人的推薦也不少,上網查查會很多,不過這相當于自己做考題,選擇起來麻煩。
所以到成都來,最好有朋友的推薦,那才可以真正嘗到成都地道的美食,歡迎你到成都來,我給你當導游。
我這本書里寫的并不都是好吃的,有的只是我認為有特點而已。加上我的體驗是重要的一環,這里面有文化的,有我與文化人的交游的,也有我與餐館老板交流等等,有的餐館的老板還交成了朋友。剛才我還接到雙流勝利鎮劉鱔仁飯莊老板的電話,因為和他已經交成朋友了,他說冬至那天要宰一只羊,要親自下廚,叫我帶朋友去他家品嘗。
我記錄的大部分館子的味道都很好,是我反復吃過、反復體驗過,并帶不同的朋友去之后達成共識的。我把我吃過的、經歷過的寫出來分享給大家,也是給好吃嘴們一個途徑,希望大家看了我這本書后再來成都體驗,說不定也會有很好的收獲。
澎湃新聞:有網友反映,有些蒼蠅館子有霸道條款,比如如果不用一次性碗,就要自己洗碗,那么在您的經歷中有沒有遇到過這種霸王條款?
吳鴻:這樣的霸王條款好像在蒼蠅館子不多見,但是很多餐館的特色就是霸道,說霸道是因為客人太多,照顧不過來的,或是有一套自己認為的有效安排管理方式。書中寫的“浣花北路鄉村菜”就是,中午11點半開始營業,到下午1點多就不賣了。客人不能自由地選擇座位,必須經由店家安排位子。晚上賣饅頭,每人限吃一個,吃多不賣給你。其他人沒有去破壞過這個規矩,我去試了試,而且我成功了。其實我撒了一個謊,說我的一個朋友是回民,他不能吃其他東西,只能吃饅頭,然后在這種情況下,老板把別人的饅頭多分了一個給我。
還有很多蒼蠅館子有這樣那樣的“霸王”行為,形成他們的經營特點,客人們不以為怪,反而津津樂道。
像你說的這種強制使用一次性餐具的霸王條款,在成都高檔的餐館里卻是常見的,收專門的筷子費、包間費和明令禁止的開瓶費等,讓人心里很是不爽。他們的態度就是你愛吃不吃,四川的餐飲業非常發達,他們不愁沒人來吃飯,所以這種霸王條款和霸王行為在成都很普遍。
澎湃新聞:那您為什么要去挑戰他們的霸王條款?
吳鴻:說不上是挑戰,最多是好玩嘛,看看他們會不會變通。有的餐館是一種經營行為,故意這么做。我說的那家鄉村菜,因味道好去的人太多,他們的蒸籠有限,不可能滿足每個人多吃的要求。如果每個人都因為饅頭好吃而多吃了,其他菜就會少點,其他東西吃得少了,饅頭的價又低,生意就不劃算了,當然要控制饅頭的量了。我“挑戰”了一下,發現他們遇到特殊情況,還是可以變通的。對于那些高檔餐館的霸王行為,只有無可奈何了,挑什么戰也沒有用的,背后有一大群的利益鏈。
澎湃新聞:我看您在書里講到城市拆遷導致蒼蠅館子搬家的問題,那么城市的發展會影響蒼蠅館子的經營嗎?
吳鴻:肯定會影響的,說老實話,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很大部分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一個城市的變遷一定會讓很多有特色的手工勞作或者餐館消亡的。因為“吃”這個東西很奇怪的,它不像其他東西,就算是同一家館子,因拆遷換一個地方去經營了,盡管還是那幫廚師,還是那些作料與做法,客人多少會發生變化,人們的感覺都會發生變化,覺得不如從前,我這本書里寫到的一些蒼蠅館子,也有因為城市的變遷而不復存在了。
美食是世界上最短暫的一門藝術。一個畫家的一幅畫作,幾百年以后仍會源遠流長,任由世人評說欣賞;一部文學作品可以流芳百世,給讀者心靈以滋養。但沒有一道菜可能保留多年而不變味的,上一頓吃過的,下一頓的味道就沒有人愿意接受了,而美食跟所有藝術一樣,給人以美的享受而回味無窮。在我看來,沒有一家蒼蠅館子會成為百年老店的,對食物的享受,人們總是喜新厭舊的。珍惜現在,留住當下,就是我寫這本書的本意。
澎湃新聞:那比如說像成都這種城市,它現在已經慢慢國際化,也有很高檔的地方,而且現在大城市都會遇到這種境況,像在上海這種城市,蒼蠅館子就沒那么流行,那么它們會在全球化、標準化以及大量連鎖店這種浪潮中消失嗎?
吳鴻:蒼蠅館子是永遠不可能消失的,不管怎么樣的國際化、現代化,都不可能讓人人都很“高檔”,只要共產主義沒有實現,就不可能人人都住大別墅,個個都吃五星級六星級。這個社會注定了生活在底層的人會是大多數,開小餐館討生活的、吃小餐館過緊日子的人一定還是大多數。“蒼蠅館子”可以在形式上發生變化,但內容上不會變的。成都很多小餐館已經變得很有個性,很有特點了,但不管怎么變,在四川人眼里它的名字還是“蒼蠅館子”。
標準化、國際化的連鎖店,是一種現代生產手段,需要高智慧的管理才能生存,像肯德基、麥當勞這樣的連鎖店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的消費主流。味道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鄉愁,鄉愁是要講個性差異的。所以解鄉愁就是要講究秘籍,各家有各家的拿手滋味。蒼蠅館子不會因為社會發展了就消亡了,而應該是更有個性地發展。
澎湃新聞:那他們的生存會更困難嗎?比如說現在蒼蠅館子的數量在減少嗎?
吳鴻:所有的生存都是艱難的,蒼蠅館子的生存肯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生存的困難是一方面,競爭激烈嘛。就算生意很好的蒼蠅館子,也會存在發展的困難,困難不可怕,解決了就好。
在我看來餐飲業在現在是最繁榮最發達的時期,這跟當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相對穩定有關,也與生活節奏有關。生活節奏不快的地方,可能會在自己家里做飯,這是自得其樂;生存壓力大的地方,也可能自己在家里做飯,因為在家里做便宜么。
像成都這種休閑城市,在家里做和在外面吃,差別不大。而且成都人的生活豐富多彩,在口味上也喜歡多樣化,自己在家里做,口味相對比較單一,久了也會生厭,所以喜歡時不時地在外面消費。
在現階段我沒有看到蒼蠅館子的數量在減少,而是在增加,現在講萬眾創業,開家蒼蠅館子可能是成本較低、門檻較低的創業途徑吧。
澎湃新聞:可能每個蒼蠅館子對食客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那么他們會開連鎖店嗎?
吳鴻:成都很多蒼蠅館子開了連鎖店,但我的書里沒有寫,因為“連鎖”是以賺錢為目的的,管理也好、做菜也好,都會程序化。程序化不是不好,但程序化了,個性就少,到處都能吃到像肯德基這樣的食物時,尋味的樂趣就會少很多。程序化的廚師都不會全面,可能做一道菜可以爐火純青,如果老板炒他魷魚了,他就沒法生存,其他的菜都不會做。我的書里面很少關注這樣的店,我關注的是那種獨一無二求生存的店,他們本身非常喜歡做餐飲,愿意花很多心思和心血做這件事,是真心實意為顧客好的,我主要寫這樣的館子。
夢想發財、愿意開連鎖店的蒼蠅館子想來也會很多,但我相信都不會有好結果的,我不相信開蒼蠅館子的人會有管理連鎖店的本領,那是另一種技能了。

澎湃新聞:其實川菜本身在全國就蠻受歡迎的,各個地方的川菜館子都很多。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歡川菜?
吳鴻:川菜為什么能被各個地方的人接受,我想是和川菜的文化有關。四川是個移民的省份,自秦漢以來全國有幾次大的移民到四川,影響最大的就是清代的所謂“湖廣填四川”。明末張獻忠剿四川,把四川原住民消滅得差不多了,留下的土著很少。湖廣填四川,全國有十多個省份的人都往這個地方移民。不同省份的移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飲食的差異也就很大。川菜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結果,肯定是各個省份移民的生活習慣在不停地對抗、不斷地融合后形成的,這個融合的過程是很漫長的,最終融合成為川菜的獨特口味,其中有中原的味道,也有江浙的特點等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認為川菜的精髓就是它的那種包容性,現代的川菜有幾十種味型,是全國四大菜系中味道最豐富的菜系,來源于全國各省移民口味的混合。我想為什么全國人民都能接受川菜,是不是川菜里都有自己故鄉的味兒在里面呢?
我有一個觀點,可能說出來別人會罵我的,為什么川菜能夠被人接受,我認為這可能與它的辛辣有關。人的味覺是很脆弱的,吃慣了清淡的東西,只要吃過幾次重口味,比如辣的、麻的以后,就漸漸會依賴這個東西,味覺的恢復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誰會去忍受那么久?所以寧愿去接受更刺激的食物。我曾跟深圳的一些美食家交流過,他們覺得我說的多多少少還有些道理。川菜的重口味部分對味覺的破壞性極強,使人們加重了對川菜的依賴,也就是說是對川菜的喜歡吧。
澎湃新聞:川菜到其他地方會有一些改良,比如到南方就沒那么辣了,您怎么看待這種改良?
吳鴻:其他地方怎么改良川菜我不知道,這個改良可能就是跟我剛才說的那種包容性有關,現代所有具規模的城市,都可以說是移民城市了,這是現代文明使然,文明發展到今天,地球都變成了一個村子,人口流動的頻繁,各地的文化交融必然要具有包容性。川菜到南方去沒有那么辣了(其實并不是所有的川菜都辣味的),跟其他菜系到四川后都變辣了一樣,是一種融合行為。

澎湃新聞:我還聽到一種說法,說川菜普及跟它的成本低有關,這有道理嗎?
吳鴻:我走過很多地方,川菜的消費確是比較便宜。便宜跟成本有關,但在我看來也未必盡然。現在各個地方的食材價格相差不會有多大,全國各地相對比較均衡。
不知道你在四川生活過沒有,在四川,特別是在成都,生活是非常方便的。我們到自由市場買菜,攤主都會按你的需求加工得很精致。比如你要買魚,他們會問你是蒸、是炒、是燒、是燉,然后按你的需求給砍塊或是切成片,大小相宜、厚薄均勻,回去后自己就不用太麻煩了。按理說這是增值服務,在其他地方都會收費的,但在四川、在成都都是免費的。白送給你了,是順水人情。顧客既節約了時間也節約了金錢,這種服務也就自然會刺激消費,量上去了,利薄一點,收益也會得到保證,何樂而不為。
說一個相反的例子。有一次到天津,我與朋友去一驢肉店吃飯,覺得味淡了,需要一碟醬油,叫了很多次后,店家才很不情愿地給了我們一袋袋裝的醬油。我們也沒有隨身帶剪子之類的東西,讓他剪開醬油的塑料袋,用碟子裝起來。他們都不愿意,還說:“難道你們在家也不會開袋子嗎?”讓我們哭笑不得。在成都,不管你有什么要求,他們都非常愿意和非常客氣,讓你覺得你就跟他們是親人一般。還有很多的店為了節約成本,比較小器,舍不得給輔料,我們四川人出差就餐,往往會讓店家多放些辣椒花椒什么的,不少的店都不情愿。天再熱再冷都不愿意開空調,說是空調壞了,長此下去,客人自然會少,哪來生意?提價是必然。
川菜便宜,或許跟大量的增值服務不計成本有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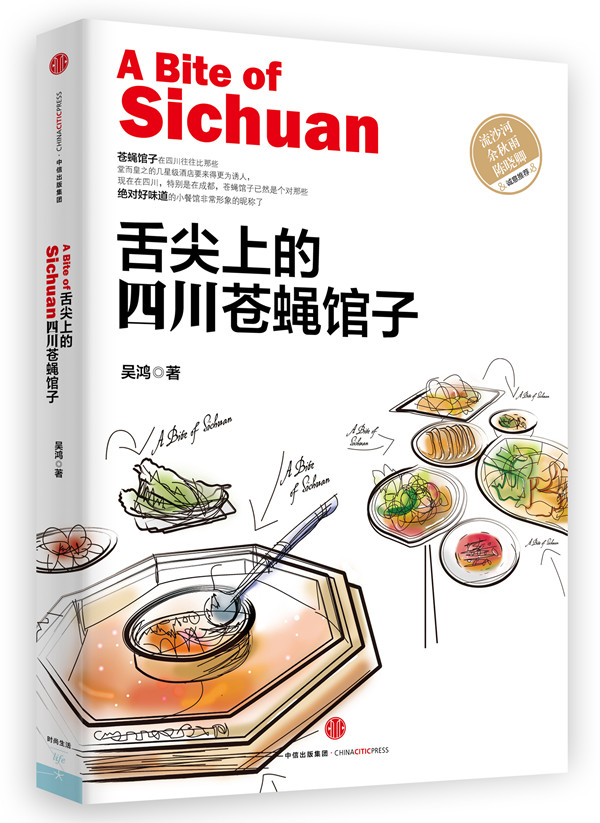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