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孔教的突圍?——評干春松《保教立國》
辛亥革命之后,在章太炎所開國學會中聽講的顧頡剛受到章氏的深刻影響,繼承其反孔教的立場。他原先以為“孔教原是國學的一部分”,現在才發現“今文學家竟是這樣的妄人”,“真氣急了”,“深惡痛絕”,他堅信孔教是“一班無聊的今文學家”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興妖作怪”(《古史辨》第一冊,24頁)。
當然,在大陸新儒學蓬勃復興,尤其是今文學家突然遍地開花、野蠻生長的今天,這些說法很可能被視為科學主義的迷妄。事實上,干春松就在其新著《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略》(以下省略書名,只注頁碼)中認為,“胡適基于科學主義的方式去求孔教之‘真’更是緣木求魚之舉”(44頁)。也許需要多說一句的是,顧頡剛不僅是章太炎的學生,而且也是胡適的學生。他的疑古方法就是胡適的科學方法運用到古史研究去的結果。所以干春松這話其實連顧頡剛也一并批評了。何況何謂科學主義,在干氏之作中也未得到基本說明。現在似乎很多大陸新儒家都會貼標簽,一旦有人批評儒學,就會被認為陷入了反傳統的窠臼。可是,傳統如果有不好之處,反一反又如何?
但顧頡剛的確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就是,在科學昌明的時代,孔教如何突圍?不過,有趣的是,干氏新作《保教立國》從某種角度看又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干春松劈頭就指出,“按一般的說法,康有為建立孔教的設想來自鴉片戰爭之后應對因治外法權而得到迅速傳播的基督教的沖擊。在康有為看來,依托一個組織化的孔教組織,一方面可以將宗教事務和政治事務進行剝離,杜絕西方列強借用宗教原因來對中國進行政治上的勒索;另一方面,建立儒家的宗教團體可以遏制基督教有組織地在民間社會進行傳播。”(14-15頁)
從論述孔教章的謀篇布局來看,干春松雖然認為以上看法屬于“一般的說法”,但實際上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他的補充是,“如果將康氏的孔教設計僅僅理解為基于宗教爭奪的原因,恐怕亦有未周處”(21頁),因為孔子的神圣化本來就是儒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方面,這點尤其表現在神秘化色彩比較濃厚的漢代讖緯思想和公羊學系統中。干春松的這個觀點無疑揭示了孔教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一面,如果我們聯系從“侯外廬學派”開始,經任繼愈先生傳承,由李申教授敷衍篇章的“儒教說”,那么還可以獲得更多的證據。不過,在現代中國,孔教的一個指向就是應對基督教的沖擊。
需要補充的不是在中國歷史上孔子的神圣化、神秘化從什么時候開始,而是在其他地方:康有為究竟為什么提出孔教說?同樣是大陸新儒家的唐文明明確指出,“學界流傳甚廣的一個說法是認為康有為提出制度化的孔教是在模仿基督教,這一說法至少就康有為早期的孔教建制主張而言是很不妥當的。”(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76頁)
在康有為思想中,孔教說究竟提出于何時?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一個原因是,這關涉到康有為的孔教說有多少種形態,關涉到孔教說能否成立,因此不得不察。值得注意的是,在干氏《保教立國》一書中,孔教思想的出現最早在1895年,而且還是作為基督教的對立面隱約出現的。不過,唐文明認為,“孔教”二字在康有為著作中的首次出現,是寫作于1886年的《康子內外篇》,但是,孔教思想的提出在文獻上卻在早于《康子內外篇》的《教學通義》。他敏銳地注意到,梁啟超寫于1901年的《南海康先生傳》明確單列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在其中提及《教學通義》中孔教思想的萌芽:“先生所著書,關于孔教者,尚有《教學通義》一書,為少年之作,今已棄去。”唐文明認為,在此書中康有為的孔教主張還是在師法上古、三代而恢復敷教之制。這個意義上的教指的是廣義的宗教,用康有為的說法是順乎人性的“陽教”,而不是狹義的宗教(“陰教”),其內涵是:“其立國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士、農、工、商之業,鬼、神、巫、祝之俗,詩、書、禮、樂之教,蔬、果、魚、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傳也。反地球之內,靡能外之。”(《康有為全集》第一集,103頁)
這種對孔教的理解,當然可以有效應對孔教的一個頑強對手——章太炎的批評。章太炎認為,中國素來沒有(狹義的)宗教,因此平白無故勘定孔教,有如在完好的身體上剜肉補瘡,毫無必要;而且由于宗教慣有的狹隘性,容易激起沖突,“十字軍之禍生于東方矣”!問題在于,一來,廣義的孔教其實就是人倫日用,將吃飯喝茶都稱之為孔教,未免過于寬泛;二來,如此理解的孔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磨了孔教的一個積極作用,畢竟康有為還是想利用孔教做一點應對基督教的事業的,這點干春松的著作言之甚詳。
孔教能否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標志?
干春松認為,“孔教會所要承擔的功能主要有兩個:一是對于傳統價值和生活習俗的繼承;二是提供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孔教凝聚了歷史和文化甚至民意上的合法性資源。”(53頁)竊以為,如果孔教會發揮的是第一個功能,那倒和一般的國學研究會之類差別不大,但那又何必創造一個新名詞,妄生事端?祥林嫂搞起祭祀來是一把好手,但她是否會自認為孔教會成員?但無疑,這個意義上的孔教之教是廣義的,指的是儒家文化。
值得討論的是第二個意義上的孔教。麻煩在于,這個意義上的孔教既可以指狹義的宗教,也可以指一般性的歷史文化,確切地說是儒家文化能否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標志?
對這個問題,狹義的宗教意義上的孔教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國近代史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康有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因為表面上這似乎違背現代國家政教分離,不立某一具體宗教為國教、主張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則,但是,“孔子之道,敷教在寬,故能兼容他教而無礙,不似他教必定于一尊,不能不黨同伐異也。故以他教為國教,勢不能不嚴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國以儒教為國教,二千年矣,聽佛道回并行其中,實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則尊孔子教,與信教自由何礙焉?”(《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7頁)
但是,仔細辨析之下我們還是能發現問題:某一宗教的特性是寬容的,是否就賦予它被尊為國教的合法性?其實新文化運動諸人早就認識到,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現代國家應當奉持信教自由的原則,而不可確定一尊。陳獨秀所言甚明:“政教分途,已成公例,憲法乃系法律性質,全國從同,萬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有出入依違之余地。”(陳獨秀:《再論孔教問題》)他還說:“與其主張將尊崇孔教加入憲法,不如爽快討論中華國體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那么,廣義上的孔教也即作為歷史文化乃至民意凝結的儒學能否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干春松指出,對這個問題的忽視是陳獨秀等人的一個嚴重不足:“遺憾的是,反對者并沒有從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康有為對于孔教與國家意識和國民精神培養之間,以及文化傳統與政治之間復雜關系的思考,這些在抱持政治理想主義的陳獨秀眼里一并被認為是中國接受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障礙。”(72頁)
“文化民族主義”在此是一個不恰當的詞語。按照這句話的下半句,這里干春松要說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但文化民族主義的要點恰恰在于暫時撇除政治的因素來考慮文化的民族主義價值;甚至有學者反對文化民族主義這種提法,因為什么不是文化呢?一個太廣的概念或許就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源于莉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和筆者的談話)。
在此,更加確切的提法是政治民族主義,指向的就是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以此為背景,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人民主權”已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國原則。換言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是內部的人民對現代政治原則的認同,至于人民在文化上認同的是哪一種,則是其次的問題。如果將文化作為民族國家的建設原則,那仍然難以避免內部的分裂和沖突。從這個角度看,陳獨秀等人一再追問孔教和專制之間的聯系,絕非單純出于激進主義、理想主義,也絕非由于歷史的偶然(如張勛復辟捎上了康有為),而是對國家基本建設原則的取舍。
從這個角度看,廣義的孔教試圖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根基,一方面似乎過于看重自己,有意無意忽略了中國歷史上其他類型的文化傳統的存在;另一方面似乎忘卻了要進行現代轉換。而轉換之后的孔教是否還是傳統文化,那是需要辨析的:更加精確的說法是,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變遷,已經接受了現代性的洗禮,當然也包含著與現代性的對話。
孔教的德性化與禮儀化
看來,孔教是否能夠成為基督教類型的宗教,這個問題本身在大陸新儒家那里就存在爭論;孔教(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能否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也頗存疑問。那么,孔教的出路何在?干春松認為,德性化與禮儀化或許是可以考慮的。
所謂德性化是筆者的概括,干春松的說法是將孔教“公民宗教”化。他認為,“康有為虛君共和的設想并非是要維持帝制,而是希望借助帝王的名號來維護傳統的道德,這與盧梭和貝拉建立公民宗教的目的有一致之處”(74頁),而這正是“以舍棄教會組織和權力參與的方式來構建儒教的未來形態”(76頁)。干春松指出,無論是楊鳳崗還是陳明對公民宗教的設計,都旨在充分發揮儒家思想對于道德風俗重建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把這種進路稱之為孔教的德性化。
于是我們發現,去除“公民宗教”這種提法比較玄乎的成分,這種做法的實質還是讓儒學發揮道德建設的積極作用。對此我們也是熱望的。當然,這么一來,另一位大陸新儒家唐文明未必同意,他認為重提孔教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經過科學的方法論的過濾,“只剩下一副干癟的道德主義面孔”的儒教,恢復“原本貫通天地、具有終極面相、意在全盤生活計劃的儒教思想”形象(唐文明:《敷教在寬》,第6頁)。但儒家的道德意義已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以“公民宗教”稱之,是否又會增加無盡的爭端?
干春松對作為公民宗教的儒教的設計,當然有其新意:“我個人認為將儒教設計成一種公民宗教有一個很可行的路徑,就是在禮儀資源十分缺乏的當下中國,通過儀式和禮儀的重建來重構中國人的道德意識和神圣性維度。”(80頁)
在此,干春松對儒教的理解已經不限于道德建設,而是意在回應中國國家文化符號缺失的現狀,“通過一些超越具體宗教派別的符號來強化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81頁),這個設想很好,只是筆者不知這些國家符號為何一定要來自儒家?自稱孔教、儒教的儒學如何超越具體的宗教派別?我們絕不否認“傳統儒家在公共禮儀和日常禮儀建設方面的文化積累”(81頁),傳統具有繼承和借鑒意義,但現代的創獲也是值得珍視的。對此,康有為本人或許在無意間為我們提供了論證。比如,在《教學通義》中,他建議將古代的射禮改為燒搶禮。因為“射之義在武備,今之武備在槍炮,則今之射即燒搶也”(《康有為全集》第一集,52頁)。
孔教能以何種形象突圍?宗教、國家認同的符號、道德培養的資源,還是神圣化的禮儀制度,抑或其他?隨著行文的展開,我們發現,其背景已然不單純是科學昌明,而且也是民主盛行。孔教何去何從,國人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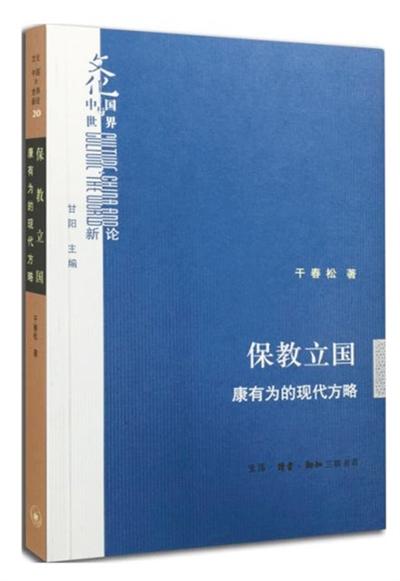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