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強牛津訪書記(完結篇):用不必出的書建條高速公路
7月5日星期日 牛津
除了之前提到的兩冊《愛麗絲》,我還有如下珍藏——
一、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亭尼爾插圖四十二幅,1866年美國初版一刷。倫敦書商Peter Harrington 擁有的“切爾西裝幀坊”(The Chelsea Bindery)裝幀。棗紅色全摩洛哥皮。六格竹節書脊。第一、四、五、六格,單線金絲框內燙金印(瘋狂茶會中的)制帽匠;三張撲克牌;(給愛麗絲嚇跑的)大白兔背影;(給愛麗絲、渡渡鳥、貓頭鷹等講故事的)老鼠;第二格燙金印書名;第三格燙金印作者名。第六格底端燙金印出版年代1866。封面單線金絲邊框:中心三圈金線圈出的同心圓中燙金印愛麗絲懷抱豬娃圖案;封底單線金絲邊框:中心三圈金線圈出的同心圓中燙金印空中現形的柴郡貓齜牙咧嘴的正面頭像。鵝黃色配紅色主調大理石紋蝴蝶頁。書頁頂口底三邊燙金。

三、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London: Macmillan & Co.,亭尼爾插圖五十幅,1872年英國初版一刷。英國阿特金森斯裝幀坊(Atkinsons of Salisbury)裝幀。二分之一拋光深綠色牛皮包草綠色紙板精裝。六格竹節書脊。竹節格內燙金印書中角色:第一、六格印特維德頓;第二格印書名;第三、五格印制帽匠;第四格印作者名;第六格底端特維德頓之下印年代1872。大理石紋蝴蝶頁。封面封底未印圖案,僅以暗線作書脊皮邊及封面封底皮包角邊的邊飾。書頁頂口底三邊刷大理石紋。入藏此冊的理由在于:真正的初版一刷——第21頁“胡言亂語”詩第一節第二行最后一字“wabe”誤印成“wade”,第98頁漏印頁碼;至為難得的是,書封內里貼亭尼爾后來簽名題贈的卡片一幀,以其喜愛的紫色墨水書寫:With J Tenniel's compliments, Dec 1. 1891(亭尼爾題贈,1891年12月1日);此外,書中尚夾有依此書改編,倫敦1934年至1938年演出的舞臺劇“貴賓席入場券”(Privilege ticket)一張。
四、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倫敦:William Heinemann, 1907年賴格姆(Arthur Rackham)插圖初版。手工紙。毛邊。書頂燙金。賴格姆畫貼紙板彩圖十三幅, 素描十五幅。此版印一千一百三十冊,其中編號一至一千一百用于出售;編號一千一百零一至一千一百三十留為贈書。我新近入藏的此冊,編號三百八十,是英國書籍裝幀家克里斯朵夫·肖(Christopher Shaw)的重裝作品。肖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書籍裝幀家協會會員(fellow of Designer Bookbinders)。他于1982年成立的裝幀坊C. Shaw Bookbinder位于牛津附近。過去十幾年里,他的書籍設計和裝幀屢屢獲獎,并為大英圖書館和德國漢諾威的威廉·布施博物館(Wilhelm Busch Museum)收藏。此冊《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完成于2011年,之后選送參加了當年的英國書籍裝幀家協會作品展。肖的此冊裝幀,使用深紅色優質山羊皮作外封,選用淺一個色調的J & J Jeffery的花飾貼紙作蝴蝶頁。他借助半圓鑿和線,用其獨特的傳統方式滾壓燙金,在深紅色的真皮上創造出畫感筆觸十分逼真的圖案:占據幾乎整個版面的賴格姆的撲克牌“小精怪”(the playing card imp)從書封跨過書脊活靈活現地將腿腳伸展至另一面的封底底端,自然如蔓藤纏繞,靈動得令人過目難忘。

五、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真愛麗絲”(the Original Alice)Alice Hargreaves 簽名本(愛麗絲1880年嫁給Reginald Hargreaves后改為夫姓)。兩冊。紐約:限印版本俱樂部 “百年紀念版”(the Centennial Editions)。《愛麗絲漫游奇境記》,1932年初版。這一年,愛麗絲年屆八旬。她罕見地打破禁忌,答應哥倫比亞大學的盛邀,在卡羅爾百年誕辰慶典上,接受專為她設立的榮譽博士學位。《鏡中世界》,1935年初版。此冊的簽名,當是愛麗絲1934年辭世前為出版商事先完成的。兩冊分別為出版商原裝紅色和藍色全摩洛哥皮。書脊書封書底花飾燙金,分裝于藍色和紅色硬紙版書匣。Frederick Warde 裝幀設計。此套兩冊均限印一千五百冊。入藏的此套兩冊,編號均為五百七十五。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巧合。兩冊又均有“真愛麗絲”筆跡色澤不同的簽名更為難得。因為,兩冊書的初版年代不在同一年,加之Alice Hargreaves簽了一千兩百冊的《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卻只簽了五百冊的《鏡中世界》。


六、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初版;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初版。兩冊尺寸近對開本。James R. Kincaid作序及注釋。柏利·摩瑟(Barry Moser)設計并插圖。兩冊的書名頁文字以藍色、黑色和紅色套色印出。正文黑墨,邊注朱墨。插圖、文字、邊注的整體版式設計美輪美奐。此兩冊加州大學版系“流通本”。之前,摩瑟在麻省西哈特菲爾德(West Hatfield)他自營的“普列薄荷書坊”(Pennyroyal Press)分別推出了簽名限印本。年近八旬的摩瑟,蛋殼頭、禿頂、花白胡子,是美國當代最受歡迎的插畫家。他的版畫木刻,線條細膩,想象大膽,氣勢磅礴里透著一種神秘的深邃。他設計并插圖的《愛麗絲漫游奇境記》1983年獲美國國家圖書設計與插圖獎(National Book Award for Design and Illustration)。他設計并插圖二百二十九幅木刻的《普列薄荷書坊版圣經》(Pennyroyal Caxton Bible)氣質華貴,是藏家競相追逐的精品。這是繼畫家多雷之后,唯一一部全部插圖均由一位藝術家獨立完成的《圣經》。此版《圣經》加州大學也出了“流通本”,可惜我尚無緣入藏。但稍覺寬慰的是,除入藏他這兩冊《愛麗絲》,我還入藏了一冊他設計并插圖的加州大學“流通本”《白鯨》,是洛克維爾·肯特版之后的又一插圖力作。
我尤為珍視這兩冊“流通本”《愛麗絲》,因為它們是經美國“后極簡主義”代表人物、畫家、雕塑家、書籍裝幀家塔特爾(Richard Tuttle)設計并皮裝的。皮裝的雕塑感似乎暗示著此著的不朽性。棕色皮裝封面封底的內外面,鑲嵌了大量小愛麗絲的珍貴照片。此裝幀本身即是過目難忘的藝術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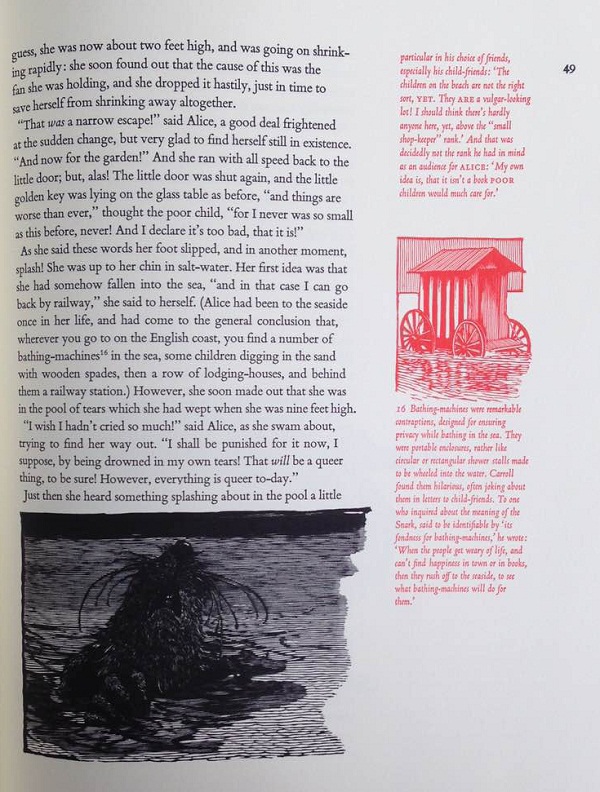

三十年來,我集藏作品的準繩,依考量的順序排列:一、品相;二、英文;三、經典;四、裝幀。前面談及的是收藏《愛麗絲》之“一”、“二” 與 “四”。現在不妨談談收藏《愛麗絲》之“三”。
錢鍾書曾提到“經典”的兩個內在特質:“可讀性”(readability)與“可再讀性”(re-readability)。前者指的是文本敘述“雅俗共賞,長幼皆宜”;后者指的是文本意義“讀之不盡,思之不竭”。
英國人前赴后繼熱愛集藏作為“經典”的《愛麗絲》,自有不同于外人的根由。倍克夫人(May Lamberton Becker)在她1936年出版的文集《閱讀的首次歷險》(First Adventures in Reading: Introducing Children to Book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中,評說的角度甚為獨特。她說:“(《愛麗絲漫游奇境記》)這類經典長銷不衰,那是因為它們嚴格講屬于‘階層文學’(class literature)。它們不是為一般意義的兒童寫的,而是為那些衣食無憂家境里精心養育的兒童寫的。這一階層的兒童,在他們的環境里,永遠不需要長大成人。無論時代如何巨變,這一階層的一代又一代很少受到變遷的沖擊。” 此說也許有道理。但她下面的分析,才算是點到了我所期待的問題的癥結:“英格蘭的空氣中存在著某種東西——或許是北部灣流氣候令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霧氣濛濛,晦暝晦暗——這使得英國人形成結論或訴諸行動時,更多靠的是觸覺而不是視覺,著意避開拉丁邏輯所固有的尖銳清晰的輪廓。英國人抵達真理的方法是‘實用主義的’(pragmatic)。他自然而然,通過嘗試和錯誤不斷前行,極為耐心地將他獲得的經驗整合在一起,而這些經驗是他從真真實實直面他所置身的事物總體的生命與靈魂那兒獲得的。當他說自己‘在笨手笨腳地摸索’(muddles through),他指的不是他遭遇到的困惑;而是這種‘憑感覺’而非‘憑精細策劃’一步步推進的行動……從事物的本質方面說,這恰恰是兒童與他們生活的世界互動的方式,只要大人們允許他們不必長大。”
然而,時間的長軸上,令《愛麗絲漫游奇境記》跨越年齡、跨越階層乃至跨越國界,吸引更大范圍的世界讀者的“文學不朽性”卻極大仰仗了它那通篇文字傳達出的“沒有意思的意味”。
二十世紀初,兩位中國文人敏銳注意到了《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沒有意思的意味”對人的精神成長的必要性和重大價值。
1922年,趙元任翻譯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譯序里談及所謂“沒有意思的意味”時提到兩層意思:其一,創作不涉任何“主義”而是純當“美術品來做的”;其二,“沒有意思”即是“不通”(Nonsense),而“不通”的妙處正在于“聽聽好像成一句話,其實不成話說,看看好像成一件事,其實不成事體……要看不通派的笑話也是要先自己有了不通的態度,才能嘗到那不通的笑味”。 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建立在兩塊基石上:一塊是“兒童本位的”,另一塊是“文學本位的”。基于這樣的文學觀,他引德·昆西的話評商務版趙譯《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只是有異常的才能的人,才能寫沒有意思的作品。”“兒童大抵是天才的詩人,所以他們獨能賞鑒這些東西。”“就兒童本身上說,在他想象力發展的時代確有這種空想作品的需要……人間所同具的智與情應該平勻發達才是,否則便是精神的畸形……對于精神的中毒(按:即此文前面所謂學者毫無人性人情的“化學化”),空想——體會與同情之母)的文學正是一服對癥的解藥。”(《自己的園地·阿麗思漫游奇境記》)
越來越多的現當代西方研究者從不朽的《愛麗絲》和它“無意義的意味”中不斷汲取著思考的廣度和深度。
George Pitcher在《維特根斯坦、無意義及劉易斯·卡羅爾》(Wittgenstein, Nonsense, and Lewis Carroll)一文中借力“無意義”打通了哲學與文學間的壁壘:“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過去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關注著無意義。與他早期著作相比,他后期的著作更多體現出了這點。在《邏輯哲學論》中,無意義是按照狹義的技術層面理解的:詞語的某種組合若不可能被理解,它就是無意義的。因為沒有意義被或者能夠被(除了微不足道者)附著于它……他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找到并且確立一種方法,能夠把意義同無意義區分開來。這樣,后者才會被,也應該被,丟棄給沉默。無意義因而被視為哲學家手中殺傷性武器瞄準的主要目標。”“維特根斯坦一如既往,試圖驅魔般將無意義逐出哲學;他想把我們從產生于我們靈魂深處的那種大困惑,那種深深的不安中拯救回來。當然他現在也用無意義來充當療治我們擺脫無意義的疫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English Literature and British Philosophy, 1971)
Alison Rieke 深受《愛麗絲漫游奇境記》的啟迪。她研究喬伊斯、格特魯德·斯坦、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路易斯·祖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四位現代派作家的專著《無意義的諸意義》得出這樣的結論: 他們的“實驗性”寫作,蔑視語言的意義制造功能。他們是在人們通常理解的意義邊緣甚至之外寫作的。他們各自以自己獨立的方式,公然挑戰語言的邊界,挑戰這樣一種觀念,即探究的目的一定是條理分明的有邏輯的意義并且意義一定是語言的目標與結果。(愛荷華大學出版社:The Senses of Nonsense, 1992)
牛津消夏,享受的是書,憂郁的亦是書。這不難理解。吾生也有涯,而書也無涯。往昔的典籍尚無法征服,未來滔滔的文字又洶涌澎湃而至。抵擋文字泥沙俱下的洪流帶來的無奈,我力所能及的唯一辦法就是,越來越挑剔地選擇與越來越果斷地揚棄。因為,只有真真正正的文字才配短暫的人生消受。
明天就要離開“學問之都”牛津了。戀戀不舍中心有不甘。臺燈的柔光下,從打好的行裝里又抽出一冊平裝書《牛津析地志》(Isolarion)。書是幾天前逛“牛津大學出版社”商店偶然購得的。
2007年,倫敦從事藝術出版的James Attlee 寫了這部近四百頁的“另類牛津游記”。一查手上新印的此冊,已是第五版了,可見此著生命力之頑強。一頁頁翻讀,見作者緊緊聚焦于牛津的一條主干道 (Cowley Road),所記所思所憶,今古交錯,視角獨到。有點兒黃仁宇,有點兒布羅代爾。頗值一讀。書中有篇不長的文字,題為“談書與瀝青”。表面看,雖與學問淵藪的牛津毫無瓜葛,說它是由飽藏真正人類典籍的牛津刺激出來,對時下魚龍混雜的出版現狀發出的辛辣妙評,大致不太離譜。
身在靜靜的牛津宿舍,隨手譯兩段出來,權作一個書蠹告別牛津消夏時的一次另類回饋。畢竟,對人類生產的文字哪些值得讀,哪些值得藏,我的感受分明正是作者的感受,只是他表達得更犀利,也更趣味盎然:
事實上,想象著用文字來建筑一條高速公路并不完全愚蠢。英國每年出版的新書達十二萬種, 一本書一印動輒成千上萬,加上境外出版進口到英國的書,這些印刷品堆疊起的大山高過了人的想象。信息之多令讀者無法消化。面對這么多新書,報紙專欄有限的版面評不勝評;書商們的書架即使長而再長,這么多新書也存不勝存。其中絕大部分根本沒人要讀。它們來到世間本身就大錯特錯。像遺棄的孤兒或者街上無家可歸的野孩子,它們剛一出生,就被拋棄到閱讀公眾視線之外的幽冥國度,進入半衰期。它們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去, 沒有專注的讀者會意識到它們存在,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已淪為尷尬,茍延殘喘著證明賭注下錯了。那么,該拿這些書怎么辦?讓它們呆在倉庫里慢慢腐爛不是個辦法。它們會阻塞出版業硬化的動脈,那動脈總在渴望著新鮮血液。專賣積壓書的書店沒法兒甩賣它們。它們自有自己的市場,一點不假,那里的人們喜歡讀的,不過是酗酒的橄欖球員或者乳房大得離譜的小角色女藝人的傳記。這些傳記全是他人捉刀寫出的。只要名聲的燭光暫時還未熄滅,這些傳主總能找到讀他們的人。另外那些書怎么辦?希望渺茫的第一部小說,默默無聞的醫學課本,沒人記起的政客的回憶錄,電視上捆綁銷售而無人問津的課程?把它們化為紙漿太不經濟。成本只能徒增它們原已淪為負數的凈資產。
必須想出個解決辦法。有人突發奇想,把所有沒必要的多余之書同瀝青攪拌在一起用來鋪設公路;而且還推算出,每英里的路大致需用書籍四萬五千冊。這該會產生出多少開心的玩笑。受夠某個作者鳥氣的編輯,開著她的車,在那段用忍無可忍的怪胎的杰作鋪成的路上碾來碾去,終于報仇雪恨。言情小說筑成的路段一遇炎熱即會下沉,就像爛泥巴時伸時縮。情色小說會令路面凹凸不平。不一而足。盡管如此,這些精神的公路上面——那由白日夢、學識、抱負、想象力和貪婪構筑而成的公路——照樣疾駛著一輛輛運貨卡車,車上載滿了緊趕慢趕必須按時送達的下一季將出的新書。目空一切的矜持和自我循環構成了這樣一個共生系統。不過說到底,出版商們還是可以自詡,他們為英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總是操心來操心去書出得太多,我們豈不成了杞人憂天?
譯畢最后一句,文中跑在虛幻的路上或是真實的路上的車輪,倒讓我想起下午出乎意料發生的一幕。同去的嘯宇興沖沖打算去還幾天前租來的兩輛山地自行車。來到學院大門旁,他無奈地發現,鎖在停車架上的自行車只剩了一輛。另外一輛,除留下一只輪子,整個車架不翼而飛。
太陽下,見人高馬大的他,有些滑稽地手提一只車輪一籌莫展,我靈機一動,隨口改了句耳熟能詳的英文諺語扔給他,逗得他抱緊輪子,哈哈大笑:Where there's a wheel, there's a way——留得輪子在,還怕無路行!
牛津消夏最后一天,連竊賊都以如此書卷氣的勵志方式來為我們餞行。 ■
(《書蠹牛津消夏記》至此連載完結)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