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虛構為榮的紀錄片:赫爾佐格不要會計的真實,要狂喜的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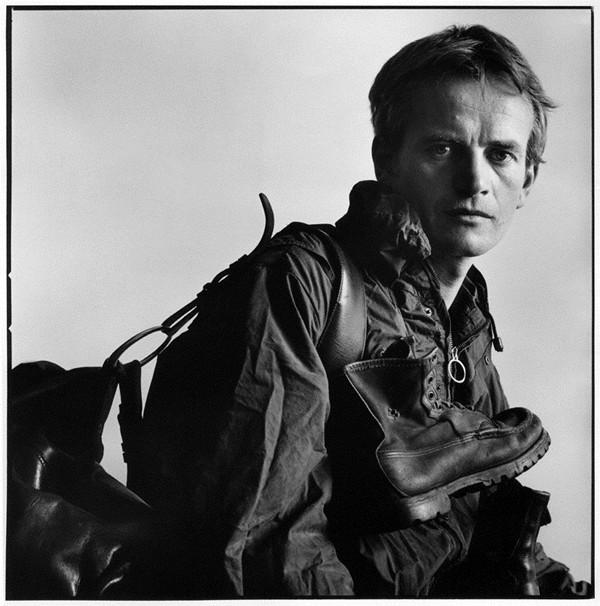
蘇珊娜·克拉普(Susannah Clapp)在寫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的回憶錄中講了這么一個故事:查特文去世前病得很重,他住在倫敦利茲酒店的房間里接待客人。許多前來探望的人都會得到一份禮物。其中一位得到了一個鋸齒狀的小物件,查特文說這是澳洲土著成年禮時用來割開尿道的割禮小刀。查特文在澳大利亞的灌木叢里撿到這東西,身為鑒賞家的他一眼就看出其價值:“它明顯是用某種歐泊寶石做的。色澤美麗,幾乎是查特酒的淡黃綠色。”不久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館長在滿懷感激得到這禮物的人家里看到了這個小物件,他拿起來對著光看了看,喃喃自語:“嗯……土著能把一個舊啤酒瓶碎片做成這么個東西,可真了不起。”
查特文有種粉飾現實的天才,如阿拉丁的神燈般,能夠講出極其魅惑神秘的故事。他是神話制造者,也是能將平庸事實變成詩的寓言家。若去質疑他故事的真實性,那是不得要領。他既非記者也非學者,而是最高級別的講故事大師。這種寫作的美妙之處在于完美的隱喻,能夠啟示現實表象之下的東西。該類型的另一位大師是波蘭人雷沙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ciński),他記錄了第三世界的暴君和政變。他的《皇帝》一書詩意地描述了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的宮廷生活,時常被解讀為隱喻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波蘭——但作者一直否認這種說法。

德國電影導演沃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是查特文和卡普欽斯基的朋友。他把查特文的一本書拍成了電影《眼鏡蛇》(Cobra Verde,肯定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講述一個半瘋的巴西奴隸販子在西非的故事,由半瘋的克勞斯·金斯基扮演。這樣的搭配是自然而然的,因為赫爾佐格也是一位偉大的寓言家、虛構者。在他接受的無數次采訪中(對于一個號稱自己寧愿像中世紀工匠那樣默默無聞工作的人來說,數量未免太多),他時常將自己與摩洛哥馬拉喀什市集中講故事的說書人比較。與查特文和卡普欽斯基一樣,赫爾佐格也極受“熱帶巴洛克”(遙遠、荒蕪的國度或是茂密的亞馬遜叢林)的吸引。像他們一樣,赫爾佐格也愛說可怕的困境、與大難擦肩而過的故事:骯臟的非洲監獄、秘魯的洪災、墨西哥橫沖直撞的野牛(當然赫爾佐格很謙虛,好像自己的故事其實沒什么要緊似的)。赫爾佐格在洛杉磯的一次BBC電視采訪中,正用他那低沉、魅惑的嗓音說德國已經沒人要看他的電影,這時突然聽到一聲巨響,赫爾佐格彎下了腰,他被一支氣槍擊中,留下了一個可怕的傷口。“這根本不重要”,他面無表情,嗓音低沉依舊,“我被打死也不奇怪。”這一時刻是如此的赫爾佐格,簡直叫人懷疑是不是他自己策劃了這一切。
這種懷疑并非捕風捉影,因為赫爾佐格對字面上的真相不僅毫無興趣,甚至鄙視之。“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強調捕捉真實,時常用手提攝影機跟蹤拍攝,赫爾佐格斥之為“會計的真實”。雷沙德·卡普欽斯基總說自己是記者,否認為了詩意或隱喻效果去編造故事,而赫爾佐格毫不諱言自己在拍紀錄片時虛構場景,甚至以此為招牌。事實上,他并不認為自己拍的紀錄片和虛構影片有什么區別。在精彩好書《赫爾佐格談赫爾佐格》中,他對保羅·克羅寧說:“雖然《來自深處的鐘聲》和《五種死亡的聲音》通常被歸入‘紀錄片’,但我覺得這是誤導人的。它們只是偽裝成紀錄片而已。”至于劇情片《陸上行舟》,講的是十九世紀末的橡膠男爵菲茨卡拉多(克勞斯·金斯基飾)夢想在秘魯叢林中建造一座歌劇院,還把一艘大船拖過一座山的故事,赫爾佐格認為這是他最成功的紀錄片。
在赫爾佐格看來,“會計的真實”的對立面是“狂喜的真實”。他在紐約公立圖書館參加活動時說:“我追求的東西更接近狂喜的真實,那種我們超越了自身的東西,那種有時會在宗教中出現的東西,比如中世紀的奧秘派。”《來自深處的鐘聲》達到了這種奇妙的效果,該片講述俄羅斯的信仰和迷信——西伯利亞的耶穌形象等等,查特文對此也相當著迷。影片開頭的場景極其迷幻,一群人在冰湖表面匍匐爬行,透過冰層張望,好像祈禱者在尋找看不見的上帝。赫爾佐格在旁白中說,實際上他們在尋找偉大的失落之城基德希(Kitezh),傳說這城就埋在無底的湖冰之下。韃靼侵略者洗劫該城時,上帝曾派大天使救贖居民,賜他們安居在深深的海底,唱唱贊美詩、敲敲鐘。
的確有這傳說,畫面也美輪美奐讓人過目不忘。但影片完全是擺拍的。赫爾佐格從當地村莊的酒館里找了幾個醉鬼,付錢讓他們躺在冰上。他在旁白中說:“其中一個臉貼著冰,看起來陷入深度冥想中。用‘會計的真實’描述是:他爛醉如泥,我們得在拍完后叫醒他。”這是騙人嗎?赫爾佐格說不是,因為“只有通過創作、編造和戲劇表演,你才能達到一種更為劇烈的真實,別無他法”。
查特文的崇拜者會說一模一樣的話。我得承認我也是其中一員,但并非完全沒有矛盾之感。影像的力量肯定會被放大——如果你相信那些人是真正的朝圣者而非拿了錢假裝朝圣者的醉漢。如果一部電影或一本書是被當作準確事實而推出的,觀眾或讀者肯定對之有相當程度的信任,這與暫且擱置懷疑還不太一樣。一旦你知道了未經修飾的真實故事,魔力就會部分消散,至少我是這樣。不過赫爾佐格作為影像演說家的天才在于,他的紀錄片即便當成虛構作品看也一樣動人。若要為他的獨特風格辯護,我們可以說他用虛構不是為了偽造真實,而是為了加劇、提升真實,使之更生動。他最愛用的手法之一是為人物編造夢境或幻覺,雖然這些都不是真的,但卻顯得十分真實,因為都與人物內在貼合。他選擇拍攝的對象都是一些他個人感到親近的怪人。某種意義上說,赫爾佐格電影里的主人公,都是他自己的各種變體。

赫爾佐格出生于戰時的慕尼黑,在巴伐利亞州阿爾卑斯山區的一個遙遠小村莊里長大,沒有電話,也沒有電影院。他小時候夢想成為一個跳臺滑雪運動員,挑戰地心引力、想飛翔成為他電影中不斷出現的主題,不管是滑雪板、熱氣球,還是噴氣戰斗機。1974年他拍了一部紀錄片《木雕家斯坦納的狂喜》,就是講一個奧地利跳臺滑雪運動員。斯坦納是典型的赫爾佐格式人物,一個獨來獨往的偏執狂,將自己推到極限,以駕馭對死亡和隔絕的恐懼。用赫爾佐格的話來說,斯坦納和“菲茨卡拉多形同手足,菲茨卡拉多把一艘大船拖過大山也是挑戰引力之舉”。
1971年赫爾佐格拍了他最驚人的紀錄片之一,講述另一種最極端形式的隔絕——眼盲耳聾之人。《沉默與黑暗的世界》中的主人公芬妮·斯特勞賓格是一位極有勇氣的德國中年婦女,她只能通過在別人的手心里敲一種盲文來交流。她在少女時代遭遇事故后雙目失明,所以依然有視覺記憶,她記憶中最鮮活的形象就是跳臺滑雪運動員在空中翱翔時臉上的迷醉表情。實際上斯特勞賓格從沒見過跳臺滑雪運動員。赫爾佐格為她寫了這些臺詞,因為他覺得“這是能夠代表芬妮內心和孤獨的偉大形象”。
這樣會消解影片,或歪曲芬妮·斯特勞賓格的真實嗎(哪怕她同意讀那些臺詞)?我們很難給出明確的答案。是,這是一種歪曲,因為它是虛構的。但它并不會消解影片,因為赫爾佐格令它看上去很可信。而且,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得知芬妮·斯特勞賓格或任何其他人的內心。赫爾佐格做的是去想象她的內心。跳臺滑雪運動員的故事是他如何看待芬妮的一部分。在他看來,這個故事能照亮她的性格。這是另外一種真實,是肖像畫家的真實。
赫爾佐格喜歡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藝術的檻外人,在危險的邊緣上獨自飛翔。不過從許多方面來說,他在挖掘的是一種豐裕的傳統。渴望狂喜、在荒野上獨自一人、更深層的真實、中世紀神秘主義者,所有這些都帶著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腔調。赫爾佐格頻繁使用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比如講述第一次海灣戰爭后科威特燃燒油井的《黑暗之課》),時常表達對荷爾德林詩歌的喜愛,這些都說明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浪漫主義趣味。他厭惡“技術文明”,美化游牧生活以及一切尚未被現代文明摧殘的生活方式,也與浪漫主義同調。他有時道德感十足,甚至達到清教徒的刻板程度。“旅游是罪”,1999年他在《明尼蘇達宣言》中宣布,“徒步是美德”。消費文化至上的二十世紀是“巨大的災難性錯誤”。他在歌德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說,冥想的西藏僧侶是好的,但冥想的加利福尼亞主婦則“令人作嘔”。為什么?他沒說。我猜是因為他覺得加州主婦都是為了趕生活方式的時髦,不是真的信徒。
和許多浪漫主義藝術家一樣,赫爾佐格很看重風景,這是他努力獲得視覺本真性的一部分。很少有導演能夠達到他的高度,去描繪叢林的可怕繁殖力、沙漠的駭人荒涼,或是高山的莊嚴巍峨。他從不把風景當成布景,風景是有性格的。他評價叢林“真正關乎我們的理想、我們最深的情感、我們的夢魘。它不是一個處所,而是我們心靈的狀態。它擁有幾乎全部人類特質。它是人物內心風景中的關鍵部分”。赫爾佐格崇拜的藝術家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從來沒畫過叢林,但把這描述放在他的其他畫作上也毫無違和感,比如孤獨的人凝視著狂風暴雨中的波羅的海,或是站在雪峰頂端凝望腳下的云層。弗里德里希將風景視為上帝的顯現。赫爾佐格經歷過一段“戲劇性的宗教階段”,少年時改信天主教,“在我的一些作品中看到了宗教的回聲”。
戰后的德國人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有時會對這種浪漫主義的神圣觀感到不適。它太容易讓人聯想到第三帝國吹噓宣揚的偽德國精神。也許這解釋了為何赫爾佐格的影片往往在國外更容易被接受(現在他住在洛杉磯,他喜歡這城市因為它有“集體夢想”)。事實上,赫爾佐格對祖國曾經釋放出的野蠻主義有極端敏感的體察。他說過:“我甚至看殺蟲劑廣告都會憂慮,知道從殺蟲到種族滅絕僅一步之遙。”赫爾佐格從未把玩過納粹美學。他做的要有趣得多:他虛構出一種被納粹給濫用并粗俗化了的傳統。比如萊尼·里芬斯塔爾自導自演的那種登山片,充滿了狂喜和死亡,在戰后很快不再流行,正如赫爾佐格所言,它們“與納粹意識形態步調一致”。于是赫爾佐格著手創作“一種全新的、當代形式的登山片”。
對我而言,看赫爾佐格的影片帶來一種全然不同的、在希特勒之前已經長久存在的、更受歡迎的浪漫主義:好像卡爾·麥的小說描寫無畏的德國獵人去美國西部探險。麥筆下最受歡迎的主人公是老沙特漢德,和印第安土著阿帕切族的“結拜兄弟”威尼圖(典型的十九世紀高貴野蠻人形象)一起漫游在西部大草原上。除了來復槍,老沙特漢德與一切技術文明劃清界限。他全靠機智在危險的自然中生存。卡爾·麥于1890年代寫下這些西部小說時從未去過美國,他的描寫全憑虛構,小說中充盈的真實細節都來自地圖、旅行記錄和人類學研究。

在所有赫爾佐格的主人公中(無論虛構與否),與老沙特漢德最接近的不是一般人以為的那些執迷不悔的幻想家(通常由克勞斯·金斯基扮演)——尋找黃金國的西班牙人阿吉雷,或是菲茨卡拉多;也不是《灰熊人》中的蒂莫西·特萊德威爾,這位鐘情灰熊的美國人以為自己能在阿拉斯加的寒冷野外活下來,只要灰熊對他的愛有所回應就成,結果灰熊把他給吃了。老沙特漢德不會對自然如此多愁善感,他懂得其中的兇險。
不,更像卡爾·麥筆下人物的是戰斗機飛行員迪特爾·登格勒(Dieter Dengler)。登格勒出生于德國的黑森林區,后來入美國籍,因為二戰結束時每當美國戰斗機飛過他家屋頂,他就渴望飛上藍天。由于戰后德國無法滿足他的心愿,他先當了鐘表匠學徒,然后揣著三十美分登上了一艘開往紐約的船。他加入美國空軍后有好幾年都在廚房里削土豆,然后才意識到得有大學文憑,于是他住在加州的一輛大巴士里艱苦生活,同時考出了文憑。終于他如愿以償開始接受戰斗機飛行員的訓練,很快被送去越南參戰。在一次老撾的秘密任務中,他的戰斗機被擊中了。他被巴特寮俘虜,送去叢林深處的俘虜營,經常被拷打折磨。這些牢頭喜歡把他倒吊起來,讓他的臉埋在螞蟻穴里,或是讓公牛拖他,要么就是用竹簽刺他的皮膚。
和他一同關在俘虜營的還有別的美國人、泰國人,牢飯是生蛆的米粥,他不得不從茅坑里抓些老鼠和蛇生吃以補充營養。靠著技術達人的機智以及超乎人類的生存技能,登格勒和同伴杜恩·馬丁越獄了。他們赤腳穿過雨季的叢林,朝泰國邊境的湄公河前進。在碰到一群敵方村民后,杜恩被村民用大砍刀斬首。不久后,已經瘦成骷髏的登格勒被一個美國飛行員發現,救了回來,這全是運氣。如果有人問他怎么能忍受這么多苦難,他會說:“這是我生命中的有趣部分。”
赫爾佐格容易受強壯之人的吸引,但他很快會加一句,說那不等于健美先生。在他看來,健美先生淺薄之至,像那些冥想的加州主婦一樣假惺惺,“令人作嘔”。赫爾佐格二十歲時拍了電影處女作《赫拉克勒斯》(1962),將車禍、轟炸和健美先生的形象拼接在一起,批評無意義的男性氣概。一個赫爾佐格式的強人也可以是女強人,比如芬妮·斯特勞賓格或尤莉婭妮·薛普克,后者是一次智利空難的唯一幸存者,1999年赫爾佐格拍攝《希望之翼》講述了她的故事。赫爾佐格式的強人不光要體魄健壯,還要有堅強的意志,知道如何險中求勝。
如果迪特爾·登格勒沒有活下來,赫爾佐格也會編造故事。登格勒是完美的赫爾佐格式強人,也是赫氏最佳紀錄片之一《小迪特爾想要飛》(1997)的主人公。其中第一個鏡頭已是創作:我們看到迪特爾走進舊金山的一家紋身館,假意要在背上紋上野馬駕著死神的形象。但他決定反對這想法,他說絕不會要這樣一個紋身,因為瀕死時他覺得“天堂之門開啟”,他看到的不是野馬而是天使:“死神不想要我。”
事實上迪特爾根本就沒想過要紋身。赫爾佐格拍這個場景是為了表現迪特爾的九死一生。下一個場景是拍迪特爾開著敞篷車回舊金山北部的家。沿途風景怪異地讓人想起戰前德國的登山片:霧蒙蒙,高遠,似乎遠離人類文明。迪特爾開關車門好幾次,有點兒強迫癥,然后又開關了好幾次前門,其實根本沒鎖。他說有人會覺得這習慣有點兒怪,但這是被俘時養成的。開關門會給他一種自由感。
在現實中,迪特爾并沒有把門開開關關的怪習慣,就像他沒想過要紋身一樣,雖然他墻上掛著一套油畫,主題是各種開著的門。他只是按照赫爾佐格設計的場景去表演。影片后面我們還會聽到迪特爾不斷重現的夢境:在戰俘營里,美國海軍派船來救他,但與他擦肩而過,他只能拼命向船揮手。這也是虛構。不過在看完《小迪特爾想要飛》之后,我們會強烈感受到一個像老沙特漢德般的德國英雄的內心肖像被轉接到了迪特爾身上,他以高效、有紀律、技術高超之類的“典型德國精神”超越了美國同胞。迪特爾本人也是高明的敘述者,他的德國口音和赫爾佐格的旁白有趣地融為一體,幾乎無法區分。這個例子不單單是導演認同他的拍攝對象,他幾乎變成了迪特爾。

赫爾佐格拍電影的許多天賦中,還有一樣是對音樂的驚人運用。科威特油井燃燒時配上瓦格納的《眾神的黃昏》可能太明顯了,不過戰斗機從航母上起飛時配上卡洛斯·加德爾的探戈音樂也十分有效果。轟炸越南村莊時配的是一個蒙古呼麥歌手,產生的混合效果既可怕又美麗。迪特爾講述瀕死經歷時,瓦格納又出現了。迪特爾站在一個巨大的水族館前,藍色水母在他身后怪怪地漂著,好像無數降落傘。迪特爾說,這就是死亡的樣子,背景音樂是瓦格納的《愛之死》。當然,水母又是赫爾佐格的主意,不是迪特爾想出來的,但無可置疑這形象十分有力。
事實上只要你問赫爾佐格,他從不諱言這些虛構,但并不能完全驅散人們對這類影片的疑問。如果這么多東西是虛構的,到頭來我們怎么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說不定迪特爾·登格勒的飛機從來沒在老撾被擊落過。說不定他根本不存在。說不定這,說不定那。我能說的是,作為赫爾佐格作品的仰慕者,我相信他對拍攝對象的誠意。所有那些虛構——門、水母、夢境——都不會改變迪特爾敘述的親身經歷。它們只是隱喻,不是事實。而且迪特爾本人也明白這些虛構的作用。
最好的例子出現在電影結尾處。后半部分迪特爾和赫爾佐格及拍攝組回到了東南亞叢林,他再次赤腳走過灌木,又被村民綁了起來(當然是赫爾佐格雇來的),他回憶了如何逃脫以及朋友杜恩被殺的具體細節。我們還看到了他在黑森林的老家,他講述了祖父是村中唯一拒絕追隨納粹的人。我們還看到了他回到美國,和救了他的美國飛行員吉恩·迪特里克一起吃一只巨大的感恩節火雞。所有這些鏡頭過后,在收場白(迪特爾在阿靈頓公墓的葬禮——他死于漸凍癥)之前,我們看到他在亞利桑那州圖森軍用機場的空曠休息區蕩來蕩去。攝像機掃過一排又一排報廢的戰斗機、直升機、轟炸機,迪特爾說他來到了飛行員的天堂。
這個場景也是赫爾佐格的發明。迪特爾沒想過去亞利桑那的圖森。不過他在片中的徜徉看上去很真實。開飛機是他畢生的迷戀,他需要飛翔,所以不管是誰安排他去瞻仰飛機的墳墓,小迪特爾看上去真的像在天堂一樣。

鑒于這部紀錄片取得的巨大成功,再拍一部同題材劇情片的想法可能聽上去很怪。迪特爾喜歡這主意,也可能只是想從中賺大錢而已(可惜他在影片完成之前就去世了)。赫爾佐格明顯被這個人和他的故事迷住了,無法放棄。于是他又拍了一部好萊塢小片《拯救黎明》(Rescue Dawn),把攝制組和演員送去泰國,其中包括兩個年輕男明星:克里斯蒂安·貝爾飾演迪特爾,斯蒂夫·贊恩飾演杜恩。此片遭受了司空見慣的赫爾佐格式困擾:無休止的爭吵、憤怒的制片人、不上心的攝制組、和當地官員的矛盾。對演員來說還有不尋常的困難:克里斯蒂安·貝爾為了演迪特爾掉了一身肉,看上去真的像是叢林煉獄里逃出來一樣。為了達到逼真的效果,他還被迫吃了看上去極惡心的昆蟲和蛇。
演員都相當不錯,特別是配角。杰瑞米·戴維斯飾演的吉恩尤其棒,他是抵制迪特爾逃跑計劃的一個美國俘虜。赫爾佐格捕捉大自然之美麗恐怖的眼光也從不失色。然而使得《小迪特爾想要飛》成為杰作的東西在劇情片里丟失了。首先是登格勒本人。劇情片里重演他的故事,不知怎地就沒有紀錄片里的那些火花。劇情片看上去很俗套,甚至扁平。迪特爾完全成了一個美國人(現實中并非如此),即便他比影片中的其他人都要堅強、機智。劇情片的結尾處倒是與事實更接近,登格勒被救回海軍戰艦,戰友迎接,但比起紀錄片里圖森的飛機墳墓那縈繞不去的形象,劇情片只是好萊塢式感傷催淚而已。
我覺得這其中的區別,關乎赫爾佐格對幻想的運用。在紀錄片里,他的方法更接近小說家。《拯救黎明》則緊緊跟隨登格勒的故事,沒有太多背景鋪墊,更別說他的內心世界了。它看上去就像制作精良的文獻片。然而在紀錄片中,正是那些家庭歷史、夢境形象、個人怪癖的拼接,加上真實的信息,使得迪特爾·登格勒成為一個豐滿的人物。這不是說劇情片里沒法達到同樣的效果,而是表示赫爾佐格愿意在突破體裁的路上走多遠,將常識中的紀錄片看成“影片而已”(“just films”)。因為沒有更好的詞,只能將就用這個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