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應奇:我與錢永祥先生的交往
記憶中第一次得見錢永祥先生夫子真身,當是十余年前在麗娃河畔的那次“公共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研討會上。既然是這樣主題的會議,作為彼岸“舊時代”之“見證者”、“新時代”之“催生者”之一的永祥先生自然是少不了要到場壓陣的。那時候大陸的“錢粉”可能還遠沒有后來和現在那么多,不過隨著《縱欲與虛無之上》簡體字版在三聯的推出,他“老”也一定已是名滿此岸之士林學界了。這不,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在會議間歇“見縫插針”地逮到機會向他請教,所談的也無非是我讀《之上》一書的感受,特別是其中關于羅爾斯、社群主義以及自由主義政治觀和平等觀的篇章。只記得永祥先生靜靜地聽我講,最后的“反饋”很“簡約”:“你把握得很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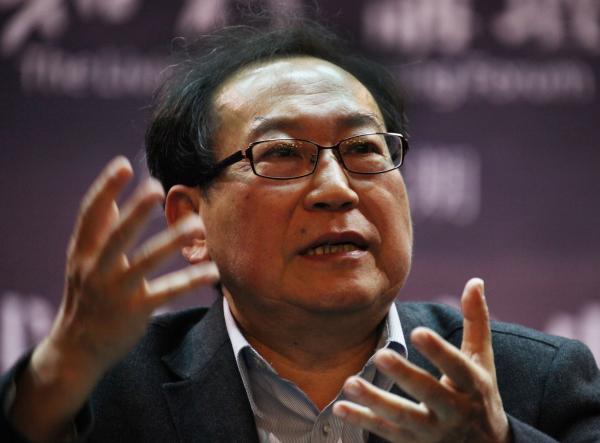
除了從同樣與會的陳來教授處得知余英時先生“近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之“消息”,那次會議也還有兩個情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其間的某個晚上,一眾人到其時剛落成不久的新天地“泡吧”,初次謀面的馮克利先生見我“侃侃而談”,忽然很“質樸”地發出一句:“你(小子)讀書不少啊!”不意我不假思索就回了句:“要不然我成天在家里空呆著干啥啊?”聞聽我言,也是初次見面的、可是見過八十年代的“大世面”的王焱老哥發出了不知是“齒冷”別人還是讓別人“齒冷”的“狡黠”淺笑,雖然他后來明確否認那笑里有什么“微言大義”。二是會議閉幕的大會上,在自由發言和辯論的階段,永祥先生批評了“中研院”前院長在“前總統”選舉上的表現,謂智識人應當慎用自己的“權威”,避免在其自身知識范圍外的議題上“誤導”大眾。永祥先生話音剛落,閉幕式主持人就立即站起來“商榷”了,其意謂身在那種“位階”的智識人似也有其“不得已”處——這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話題,頗可以引出很多復雜精深的辨析,遺憾的是大概因為那個場合的關系,并沒有能夠深入地討論下去。
固然和那次會議沒有什么“內在”聯系,但確是從那次會議之后,我就踏上了編書的“不歸路”:從“編年史”的意義上,我最早開始張羅的叢書是在人民出版社的劉麗華女士支持下在東方出版社推出的“當代實踐哲學譯叢”,那也許可以反映些我在“學問”上的“旨趣”;但是比較“狹義”而“專業”地聚焦在政治哲學上,則仍然要算在時任副總編輯的佘江濤先生支持下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創設的“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讀本系列”,也是通過那套叢書,我和永祥先生建立了電郵聯系——主要是為了給叢書壯聲威,我請永祥先生、石元康先生還有佩蒂特和金里卡中外一共四位“大咖”擔任叢書的學術顧問。洋人當然是來免費“站臺”的,但我記得石先生在看到他那時在中正文學院的秘書為他打印出來的我為叢書撰寫的序言后,還來信表示“贊賞”,而永祥先生更是沒有閑著,我記不得他有沒有為讀本中的某冊做推薦了,不過我記得他很欣賞我在為拙編《自由主義中立性及其批評者》撰寫的作者“小傳”中把Seyla Benhabib的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這個書名中的Reluctant一詞譯為“欲迎還拒”,以為頗有“風姿”;他也很贊賞我把呂增奎小友編的那冊柯亨文集命名為《馬克思與諾齊克之間》——據增奎告訴我,柯亨教授本人也對此書名極為稱賞——得知這個消息,我都不好意思說,我其實并沒有對柯亨下過任何功夫,我只記得曾在心里默默地把他的一篇文章標題中譯為《何以馬克思主義者會對諾齊克對羅爾斯的批評無動于衷?》。
2007年3月至5月間,我在宜蘭佛光大學客座。我的臺灣朋友本就很少的,于是自然早早地行前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永祥先生,記得他回信告訴我:四五月份正是南臺灣最美的時節。其意似乎在為我能夠在那時到訪臺灣而高興抑或替我“慶幸”——他說得并沒有錯,當我五月初參加完中正的德沃金研討會并造訪印順法師在那里“安住”的妙云蘭若之后獨自一人上到阿里山,雖然那里的櫻花幾乎已經凋落殆盡,但我仍然必須說,在其山巔可以遠眺臺灣最高峰玉山的阿里山所看到的日出,確實是我平生看過的日出中最為甜蜜也最為憂傷的。
有些出乎我以及邀我訪臺的張培倫兄意外的是,在我到佛光后的某天,永祥先生忽然來信,說是要請我在臺大附近的金華路(街?)上共餐——于是培倫兄二話沒說就慷慨地載我一起到臺北“赴宴”。就正如陳來先生某次“稱道”在下乃是“筆勝舌”。我確是記不得那次我們都聊了些啥了,只記得我把自己編譯的幾本書面呈給他,永祥先生則為我們點了一瓶金門高粱,而我本就是“好酒無量”的,再說——不好意思啊,永祥先生——餐桌上也沒有什么可下酒的菜,于是我們三人都沒有喝完那瓶酒。永祥先生很客氣,說是讓我們把那小半瓶酒帶走,大概我們走得匆忙,終究還是把那個酒瓶忘記在那家小餐館了。
過了十天半個月,在得知我將到他供職的“人社中心”演講后,永祥先生特意寫信來,告訴我他將參加我的演講會,但因為當晚另有安排,他向我抱歉不能參加招待我的晚宴了。不過當我后來到“人社中心”查找資料時,永祥先生還是在他的研究室里接待了我,記得他坐在一張書桌前的轉椅上,似乎又是面帶歉意地告訴我他沒有什么書可以送給我,于是指著一本關于動物倫理的書,問我有沒有興趣。當得知我似乎對新儒家更有“興趣”后,他表示對后者的“情懷”頗有同情,但始終不太清楚他們在哲學上可以說得清楚的“貢獻”到底在哪里。我也是“事后”才想起,他那時大概已經在醞釀甚或已經寫完那篇《如何理解儒家的“道德內在說”》。
在“人社中心”找資料還有個意外的收獲,我竟然發現了永祥先生早年(大概是在英國期間)所撰一篇關于維特根斯坦的論文,于是回到宜蘭的某晚,我就把那種有點兒興奮的心情寫信告訴給他,因為那天在資料室剛巧“偶遇”蕭高彥教授,我于是把那封信也抄送給了蕭教授。永祥先生的回信照例很客氣,大意是雖然并不悔少作,但仍然自嘆在哲學上才具不夠,所以后來就只能做點兒形而下的社會政治哲學。不想高彥教授回說:“可是永祥您已經是一位很好的哲學家了啊!”呵呵,其“惺惺相惜”一至于此,讓我想起在赴臺前夕,永祥先生還曾告訴我:“本組蕭高彥先生于共和主義研究精深,兄來臺后不妨與之好好切磋!”
同年6月間,我趁“人社中心”政治思想史組諸同仁到上海華東師大開會之際,順邀他們來杭州參加一個我“炮制”的主題為“中文語境下如何做政治哲學”的座談會。在會后征集書面發言稿時,永祥先生慮及在下畢竟曾為“地主”,就要求我也提供一篇稿子“充數”。于是我就果真本著“濫竽”其間的精神,把剛殺青的《中立性》“編序”做了一番增寫發給了他。我心想他大概會是不甚滿意于我的文稿“質量”的,但估摸同樣是念在“地主”分上,我的稿子竟也在《思想》上與海內外讀者見面了。
那年秋天到轉年初夏,我在普林斯頓訪問,異鄉客居未免寂寞,于是每每在“工余”制作些閑散文字前去叨擾包括永祥先生在內的諸位高僧大德。他對我還是很客氣,說是很喜歡我的訪書記,我當然只是把這話作為一種鼓勵的了,竟至于后來真還“系統地”把我的訪書經歷給寫出來了。雖然我一直并沒有機緣把那冊小冊子呈送給他,其實那種“寫作”在我也只不過是代表一種懷舊的心情罷了。
這些年我也還是有機會在自己參加不多的幾次會議上見到永祥先生。記得那年沙田中文大學保松君籌辦的會議他是從紐約飛過來參加的,我很奇怪那樣的長途旅行,他還帶著好多期他所主編的《思想》,記得他一邊疲倦地坐在酒店外面的長椅上“倒時差”,一邊要把其中幾期《思想》送給我。那時候我的精神狀態也很差,竟是淡漠地從他手里接過了在我眼中“花花綠綠”的那幾期《思想》,至今想來都還有些慚愧;三年前在清華的伯林會上,在自由發言階段,我記得他結合費希特的自由理論談到伯林之區分自由與成就的重要意義,我在感嘆他對于伯林之精熟有得的同時,再次非常具象地感受到自由派的理論原也是可以很淵深的,自由派的理論家原也是可以很博學的!不過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三年多前在人民大學周濂君的那次會議上,我追著他討論在中文世界由他首先引入探討的自由的價值問題,看著我喋喋不休繞彎子嘀嘀咕咕不罷休的樣子,他突然來了句:“你老兄為什么非得要證明自由是有價值的呢?!”
近三年我徹底地“淡出江湖”,幾乎沒有出去開過會了,而自從得到永祥先生那次“棒喝”后,我也似乎覺得再沒有什么政治哲學的疑難問題要向他請教了。除了今年春夏時節某天在光影變幻的玉泉老和山上從隨身攜帶的鄭鴻生的《青春之歌》上看到永祥先生當年在建國中學和臺大初期那帥呆了的青春“魅影”,我只是偶然在這樣那樣的郵件組中“見到”他那“翩若驚鴻矯若游龍”的“身影”,抑或“聽聞”他那“顧盼自雄婉約多姿”的“話音”。記得一次我們談到了黑格爾最重要的中文譯者賀麟先生“天翻地覆慨而慷”前后思想的變化以及怎樣評價這種變化,似乎我們對相關人士及人事的觀感和意見并不是很一致。在這種閑談中大家似乎都沒有較真地想要說服對方,但我一直還是對那一段的議論留有很深的印象。不久前,我“心血來潮”寫下了關于賀麟先生的得意弟子、目前國內最重要的黑格爾譯者薛華先生的一則“段子”,因為與曾經的“議題”有些“關聯”,永祥先生收到了這個“段子”。他沒有什么評論,只是回復說:“我今年春天出了本書,請告知你的地址,我可以寄給你。”因為我的那則段子題為《“等待”之“等待”》,我于是玩笑回說:“原來‘等待’也還是有效果的啊!”
昨天是每周一次的撒米娜時間,這學期我在和自己的學生一起閱讀John McDowell的Mind and World,用的是北大韓林合教授剛出的重譯本。在課程的間歇,我打開自己的信箱,見永祥先生新著已到——聯經學習牛津劍橋的做派,初版書還是精裝的!翻看目錄,大部分篇什我其實都是比較熟悉的,當初在各式場合見到時也曾大致學習過,但是“熟知并非真知”,而且我確實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好好讀讀永祥先生了,雖然正如我許多年前在楓林晚和丁丁“同臺”時說過的,我再讀汪丁丁也不會變成汪丁丁,“所以”我再讀永祥先生也不會變成永祥先生。但是人生不易,讀到耐讀的書更是不易,所以就正如葉秀山先生多年前一篇文章的標題:我們總還是得“讀那總是有讀頭的書”!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