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黃進興、李孝悌、葛兆光談思想史研究的趨向
2015年9月,黃進興、李孝悌、葛兆光三位教授在復(fù)旦大學(xué)文史研究院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講座,探討思想史、文化史在西方和中文學(xué)術(shù)脈絡(luò)中的嬗變和消長,對思想史在多種語境中面臨的挑戰(zhàn)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澎湃新聞?wù)砹诉@次講座的內(nèi)容與讀者分享。
黃進興,臺灣“中研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學(xué)理論。著有《皇帝、儒生與孔廟》《優(yōu)入圣域》《圣賢與圣徒》《后現(xiàn)代主義與史學(xué)研究》等。

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xué)中國文化中心主任、中文及歷史系主任。研究方向為明清社會與文化史、城市生活史。著有《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昨日到城市:中國近世的逸樂與宗教》等。
葛兆光,復(fù)旦大學(xué)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研究領(lǐng)域為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宅茲中國:重建有關(guān)“中國”的歷史論述》等。

葛兆光:今天的對談,我們先從黃進興所長開始。我記得黃所長在2009年寄給我一篇文章,叫《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xué)觀點的考察》(收入《中國學(xué)術(shù)》總第二十九輯,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出版),收到文章的時候,我正要去美國訪問,在普林斯頓的演講主題就是思想史在中國大陸為什么很興盛;而這篇文章是講,思想史在西方不興盛了。黃老師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美國名將麥克阿瑟的話,“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用這個話來形容思想史。當然,他又有一個轉(zhuǎn)語補充道,“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鳳凰”。
所以,我想請黃所長先講一下從這篇文章中引出來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大陸的思想史研究蠻熱鬧的,為什么西方的思想史研究逐漸凋零,能否談?wù)勎鞣降乃枷胧费芯壳闆r?第二個問題,您提到“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鳳凰”,這是為什么?第三個問題,您能否介紹下臺灣的思想史研究情況?前幾年,臺灣還專門出了一個《思想史》集刊,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到第四輯了。那么,為什么要專門辦這樣一本雜志呢,這是否說明臺灣的思想史還蠻興盛的?

黃進興:謝謝葛老師,謝謝大家。我想,最重要的是,每一個社會的思想文化狀況都不同,思想史比起其他歷史研究,是比較晚起的。從西方的學(xué)術(shù)脈絡(luò)來講,大約是十九世紀末才發(fā)展起來。而且思想史特別容易風(fēng)吹草動,因為它往往要借助其他學(xué)科的理論,所以它的穩(wěn)定性比較差。
簡單來說,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思想史研究,既有歐陸的脈絡(luò),也有美國的脈絡(luò),他們的研究取向不太一樣。從歐陸來講,是德國歷史學(xué)派影響下的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還有卡西爾(Ernst Cassirer)的系統(tǒng);在美國,是勒夫喬(A. O. Lovejoy)所構(gòu)筑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我們現(xiàn)在籠統(tǒng)地稱之為思想史,但是它們的基本運作原則,從理論到方法都非常不一樣。粗淺地講,像邁涅克和卡西爾這些,都是見其大,希望抓住整個時代的氛圍,從方法論上來說,是整體論的取向。而勒夫喬基本上是分析的取向,透過對觀念單元的分析,受到化學(xué)的啟示較多。他認為,研究一個人的思想,就像研究一個人的思想的質(zhì)素,如同化學(xué)分析一樣。所以,表面上我們可以看到浪漫主義、民族主義、極權(quán)主義等等,事實上是各個思想元素不同組合的結(jié)果。勒夫喬的這個學(xué)說影響了將近四十年之久,因為他有一個類似機關(guān)報的雜志,今天還存在,叫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等于自己成立了一個俱樂部。所以你看,他的構(gòu)想之所以能夠?qū)嵺`,是有人、有基地、有機關(guān)報,跟年鑒學(xué)派是一樣的。這一派是采取內(nèi)在理路的方式,關(guān)注思想本身的因素。他最出名的著作,當然是《存在的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從柏拉圖一直談到十八十九世紀。
這種做法,后來受到了一些批評。第一個就是,觀念本身變成有它自己的生命,但他不考慮時間的跳躍,現(xiàn)在講的“存在”與幾百年前的“存在”還一樣嗎?就像朱熹講的“性即理”,跟戴震講的“性”是一樣的嗎?我們似乎很少去想,“心即理”的“心”,跟孟子講的“心”、陸象山講的“心”、王陽明講的“心”一樣嗎?我們都把它們等同為一,用德里達的話來批評,就是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兩千年來的“心”字真的都是一樣的嗎,它的本質(zhì)都不會變嗎?做哲學(xué)史的人,比較容易犯這個毛病。到1950年左右,勒夫喬的說法受到很大的挑戰(zhàn),有些人批評他只關(guān)注精英分子、思想家、哲學(xué)家,這也是新文化史提出來的挑戰(zhàn),新文化史強調(diào)群眾、外在的因素。勒夫喬所研究的觀念、概念,好像有它自己的生命,也不需要經(jīng)濟、社會的基礎(chǔ),就會自己傳承。所以在1950-1970年代,比較盛行的是social history of thought,“思想的社會史”,針對的就是勒夫喬的觀念史。
這之后,情況對思想史比較不利。從西方史學(xué)史的發(fā)展來看,有社會史、新政治史、文化史,都是從外緣因素來談思想,單就思想本身來談思想是被質(zhì)疑的。極端的例子,普林斯頓曾經(jīng)有一位本來是教思想史的教授,甚至在研究室外面貼上海報:不要跟我談思想史,我絕對不是教思想史的。在這個風(fēng)潮影響下,做思想史好像是很不名譽的事情。在當下西方學(xué)界,說對方做思想史,是有點貶義的,一般大家都要走向李孝悌先生所闡揚的新文化史,這才是堂堂正道。現(xiàn)在一說到思想史,好像就是落后、封建。

以上是西方的脈絡(luò),我想在大陸和臺灣有點不一樣,西方是隨著思潮而快速變化,使人目不暇接、跟不上,就像孫悟空翻跟斗一樣。在西方享有大名的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曾提出“思想史的語言轉(zhuǎn)向”,但在中文世界,這種語言的研究方法就難以操作。就我淺薄的了解來看,“語言轉(zhuǎn)向”在中文世界并沒有很大的回響,但大家都會談到,斯金納是西方思想史發(fā)展的階段性里程碑。這是很特殊的情況。西方學(xué)術(shù)變化很快,基本上十五年就有一個“圣人”,根本來不及追上,就像夸父逐日。因此最重要的,我想還是要站在自己的文化和傳統(tǒng)上,對中文的文本解讀下功夫,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
關(guān)于“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鳳凰”這個問題,是李孝悌老師的看家本領(lǐng),我就不掠人之美了,等一下聽李老師談。我稍微來談一下臺灣的思想史研究狀況。思想史研究在臺灣,最重要的是1970年代的中期,也就是1975年左右開始,當時有我的老師輩余英時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當然,他們的研究取向不一樣,林先生的研究有一個標識,叫“分析式的思想史”,他不滿意于以前的思想史只是敘述性的,多少跟勒夫喬比較接近。而余先生那段時間所做的研究,最出名的就是對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釋,所標榜出來的是“內(nèi)在理路”。他們兩位也有互通。后來余先生卻有變化。“內(nèi)在理路”對早期清代思想史,尤其是考據(jù)學(xué)的興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在余先生之前,大家都是從政治上,例如文字獄的箝制思想等來解釋考據(jù)學(xué)等問題。而余先生與他們的區(qū)隔在于,余先生認為,考據(jù)學(xué)是義理學(xué)最后逼出來的結(jié)果。就是,必須從義理學(xué)、宋明之間的辯證互動入手。當時這個說法一出來,影響非常大,不限于文史哲領(lǐng)域。隨后將近二十年,大家都在這個思路下做研究,大陸叫范式,臺灣叫典范(paradigm)。后來,余先生又有蛻變,覺察到思想的外延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等。所以,余先生并不是完全走“內(nèi)在理路”的做法。我和孝悌那時候都受之影響很深,因此我們會走上思想史研究這條路。到1990年代以后,余先生比較脫離了“內(nèi)在理路”的操作方式。你去看《朱熹的歷史世界》,烘托出來的完全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從思想所處的政治、社會情況來談,這本書又成了一個新典范。所以,余先生已經(jīng)翻了好幾翻了,許多人還是到廟里拜著原來的偶像,不過原來的塑像已經(jīng)跑掉了。
這就牽涉到葛教授剛才提到的《思想史》雜志,雖然思想史在臺灣不能算完全的沒落,文史哲都有人在做,但歷史系做思想史的的確比較少,中文系、哲學(xué)系比較多。但為什么會有這個雜志呢?它主要是由一群有點老、但不太老的人在辦,基本上是四十歲到五十歲,可以算是我們的學(xué)生輩。我們現(xiàn)在講,出版文化很重要,這個雜志背后,是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在支持,其中的關(guān)鍵人物便是林載爵先生。讀書的時候,林載爵和我是同一屆的,所以他年齡跟我相仿。因此,可能他活在以前的世界里,仍然認為思想史很重要。這個雜志現(xiàn)在還在努力中,但常常會稿源不繼,因為事實上做的人少。就臺灣學(xué)界主流來看,現(xiàn)在當?shù)赖氖俏幕贰⒆诮淌罚绕涫轻t(yī)療史,大陸學(xué)界我比較陌生,不太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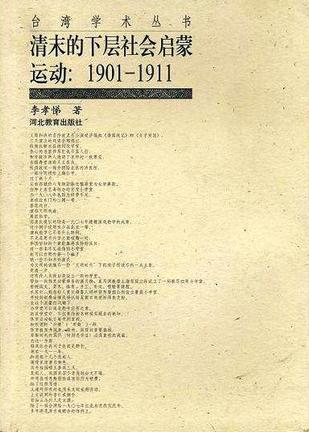
葛兆光:剛才黃所長沒有講“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鳳凰”這個問題,待會請李孝悌先生接著講。咱們都知道,李孝悌教授很早就出版過一本書,叫《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顯然那個時候,他是眼光向下的,關(guān)注社會、文化。但是后來呢,他寫了好幾本有關(guān)城市的書,比如《戀戀紅塵》《昨日到城市》,有點像彼得·伯克講的,從布克哈特式的經(jīng)典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轉(zhuǎn)換。所以,我一直比較好奇的是,經(jīng)典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差異究竟在哪里?
而且,我還想問一下李孝悌先生,為什么現(xiàn)在這么關(guān)心城市?昨晚他還跟我講,他對南京具有極大的興趣。今年夏天,我去巴黎之前,看了好幾本洋人寫的關(guān)于巴黎的書,那真是新文化史的典范之作。我也知道,李教授的朋友費絲言也研究南京,美國的羅威廉做過漢口研究,王笛研究成都,那么,新文化史在研究城市文化時,背后有什么樣的背景和理論?比如我們以前知道,羅威廉研究漢口曾經(jīng)用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那么現(xiàn)在呢?這些著作會描寫城市里面的吃喝玩樂、聲色犬馬,這也是新文化史的一種趨向嗎?最近,大陸有些人在討論,因為文化史一下子把題目變得很多,各種資料開始大量出現(xiàn),比如圖像、聲音、下層文本和社會調(diào)查,亂七八糟的什么都來了,歷史圖景會不會出現(xiàn)碎片化的問題。我看大陸有的朋友批評得最兇的就說,你們天天研究的是奇技淫巧、聲色犬馬,茶啦、酒啦、麻將啦,都是這些東西,會不會把歷史碎片化?所以,近來大陸有個有趣的趨勢就是,有人號召重提政治史。他們覺得,政治史比較能夠提供一個比較宏觀的歷史全景,而新文化史會不會使得這個圖景碎片化?
另外,我還要向大家介紹一下李孝悌先生最近的一些研究計劃,比如研究沿海城市,并與其他國家的沿海城市相比較,構(gòu)成一個沿海城市圈的文化比較研究,您是不是也可以介紹一下?
李孝悌:謝謝。兩位杰出的思想史家都認為我在做文化史,我還是要做一些補充。我先自報家門吧,我從1985年開始在哈佛讀了四年書,花的時間最多也最受影響的是西方思想史,從十八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從啟蒙運動、反實證主義,到存在主義,到后現(xiàn)代。一直到現(xiàn)在,這些思想在各方面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包括做學(xué)問和個人關(guān)懷。西方近代思想史對我影響最大。另一方面,我跟隨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讀書。我景仰的老師還有史華慈先生,他從古代一直做到近代的嚴復(fù)。孔飛力老師的第一本書,寫得有點枯燥,我當時讀沒進入狀況,后來過了很多年,才知道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最后,我對社會史是有極大極大的興趣的,這個興趣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忘,雖然我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做文化史。我在過去十年,一直參與兩岸研習(xí)營的工作,特別是前面幾年,帶著臺灣學(xué)生去福建、廣東做田野調(diào)查,我在哈佛所受的社會史訓(xùn)練,全部又回來了。我最佩服廈門大學(xué)的鄭振滿教授,讓我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的鄉(xiāng)村和基層社會。如果將來還有精力,我想去做一個關(guān)于叛亂的案例,當然我不會去搞叛亂。之所以講這些,是想說,我對社會史并沒有忘懷。最近在寫的一本書我還是試圖處理下層,把社會史和文化史放在一起談。
至于經(jīng)典文化史,大概從1800年代到1910年代最為興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然就是布克哈特和他的文藝復(fù)興史研究;此外還有荷蘭史學(xué)家貝辛加。我有幾年在臺大教史學(xué)方法,讀過一些對經(jīng)典文化史的介紹。如果大家讀過布克哈特,可以知道,經(jīng)典文化史處理的是文學(xué)、藝術(shù)和科學(xué)、哲學(xué)的經(jīng)典作品。我很好奇的一點是,經(jīng)典文化史和后來的社會史,都很強調(diào)模式、formula、schema,不太好翻譯,就是說,它不是在處理一個簡單的東西,它要處理更深層的東西。剛好跟蘭克的政治史是對立的,它不是要處理單獨的事件,它是要處理不斷循環(huán)的模式。我要強調(diào),經(jīng)典文化史到現(xiàn)在都沒有死亡,影響還是很大。有一個名詞,叫“布克哈特的重返”,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卡爾·休斯克(Carl Schorske)就是當代的代表性學(xué)者。
如果要用一句話簡單地來講新文化史與經(jīng)典文化史的差別,那就是新文化史受到后現(xiàn)代的影響,強調(diào)建構(gòu),這是我自己的理解。一切都是建構(gòu)和再現(xiàn),當然這跟福柯所說的“權(quán)力”有很大的關(guān)系。可是要把新文化史看得比較復(fù)雜。我覺得社會史跟文化史,或者說社會跟文化,是二十世紀最曖昧的兩個名詞,也是最神秘的兩個名詞,因此衍生出來的社會史與文化史都是無所不包的。所以,你現(xiàn)在問我什么是新文化史,是沒有辦法界定的。剛才葛老師提到什么是邊界,沒有邊界。
我可以簡單講一下社會史和文化史的關(guān)系。文化史在相當程度上是對社會史的反動。社會史大概在1950-1970年代蓬勃發(fā)展,一方面承續(xù)了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三人或三個學(xué)術(shù)流派的影響,一方面開始批判現(xiàn)代史觀。但社會史不同于文化史的地方,在于還承認有一個共同的基礎(chǔ)與預(yù)設(shè)。一方面,社會史家開始使用統(tǒng)計學(xué)、社會科學(xué)(社會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追蹤行為模式和理論。規(guī)范、模式、過程、結(jié)構(gòu)、組織成為社會史最常出現(xiàn)的詞匯。另一方面,在光輝、正面的歷史之外,社會史家開始描述挫折、失敗、掙扎的人與事。移民、女性、黑人、新族群、階級等課題開始受到重視。研究課題從精英轉(zhuǎn)向下層。
新文化史則因為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洗禮,在很多方面是反啟蒙的,而啟蒙運動要處理的是理性、科學(xué),要找一套訴諸四海而不變的準則。孔德的實證主義是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做新文化史,跟研究者的出身成分很有關(guān),他們最討厭訴諸四海而不變的universal rule,強調(diào)獨特性和個人的差異,反對律則。所以,只要有了解構(gòu),everything is possible。因此,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出現(xiàn),是對社會史的一種反動。他們旗幟鮮明,像洪水猛獸一樣,總算可以把那個不變的律則推翻了。他們不要律則,要處理每一個個別的情況。這就是剛才葛老師講的,他們?yōu)槭裁慈菀捉o人一種瑣碎化的印象。
可是我想提醒一點,不是只有新文化史可能瑣碎化。至少在歷史學(xué)的每一個次領(lǐng)域,甚至是每一個學(xué)科,都可能極端地瑣碎化。我們不滿意的政治、外交史,可以極端極端地細瑣化。我們熟悉的思想史,做宋明理學(xué)也可以問出極端無聊的問題,什么理、氣,根本就是自己想象出來的game,跟實際社會或宇宙秩序的運作完全沒有對應(yīng),是一個最大的Intellectual game。所以,每一個歷史領(lǐng)域都可能細瑣化,沒有大的意義。當然,我想,有的時候,小東西是有意義的。小跟細瑣不一定有關(guān)系,小可能是大的基石,是重要的磚頭。我原來很討厭十八世紀的考據(jù)學(xué),覺得真沒意思,開始做城市史后,研究冒襄、王士禎,但王士禎的詩幾乎都看不懂,完全是透過惠棟的《漁洋山人精華錄訓(xùn)纂》,才得以一窺堂奧,所以對惠棟佩服極了。對考據(jù)學(xué)家的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也開始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細小的東西,對我們文化史來說,有時可能是極其重要的。細瑣化當然是一個問題,但單單以這個來責怪新文化史,未必公平。而且西方新文化史有極強的反省能力,他們大概做了十年,開始反省我們真的能把社會史留下的偉大傳統(tǒng),或者把社會史問的大問題,完全丟掉嗎?這個時候,他們覺得必須要回頭,重新把社會史找回來。
后現(xiàn)代是新文化史的理論源頭之一,如果大家熟悉新文化史的發(fā)展,會知道它在美國的重鎮(zhèn)是普林斯頓大學(xué),有幾位代表性人物,像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其實他們受到人類學(xué)極大的影響。在此,思想史和文化史有相當類似之處,即它們對文本非常重視,強調(diào)意義的闡釋。當然達恩頓寫過很多書,其中比較有名的包括講百科全書流傳的《啟蒙運動的生意》,和啟蒙運動時期流行的地下書籍。后來我特別喜歡的,就是《屠貓記》。有一次我把《屠貓記》和孔飛力的《叫魂》放在一起比較。《屠貓記》是一部小小的作品,好像很瑣碎,幾個前現(xiàn)代工人殺幾只貓,看起來無聊至極。但如果仔細看,知道他其實受到人類學(xué)儀式研究的影響,把一個看起來非常無聊的儀式背后的意義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剝出來。貓有各種意涵,是邪惡的象征,殺貓等于強暴了女主人,或給主人家?guī)矶蜻\。分析到最后,作者其實是要處理一個重大的課題,要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是不成立的。無產(chǎn)階級對資本主義的反動,或者說無產(chǎn)階級意識的出現(xiàn),不是工業(yè)革命之后的產(chǎn)物,而是在此之前,在里昂等法國大城市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下層的工人也不需要階級斗爭的觀念,他們從小就從鄉(xiāng)村社會學(xué)到人與人之間的對待關(guān)系,知道人與人應(yīng)該如何相處,不必等到十八十九世紀,也不必等到工業(yè)革命。此書試圖證明,在前現(xiàn)代之前,在里昂這些大城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工人,出現(xiàn)了階級意識。我老師的第一本書寫的是枯澀至極的制度史,后來的《叫魂》則有極強的文化史傾向。孔飛力是一個極端自負的人,他覺得他是一個白人,又在哈佛教書,干嘛要去拾同行的牙慧,套用別人的理論。可是我覺得,他的書都有極強的理論意涵。《叫魂》跟《屠貓記》一樣,看起來要處理的是一些怪力亂神的民間信仰和儀式。大家讀過就知道,它其實和《屠貓記》一樣,都有一層一層的意涵,直到最后,孔飛力寫到十八世紀整個江南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以龐大的時代背景為其最終的關(guān)懷。當然,孔飛力不會簡單地承認自己是新文化史家,社會史、文化史、制度史層層交織成堅實的“深描”。
其實我覺得,好的文化史跟思想史一樣,對文本非常重視,會一層一層地解析文本的深意。當然,文化史有許多理論為其張目,每個人的說法也不盡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后現(xiàn)代主義、人類學(xué),布迪厄的品味的“區(qū)隔”、場域和文化資本、象征資本等理論,都有極大的影響。我?guī)孜蛔龀鞘惺返耐戮褪艿讲嫉隙虻膯l(fā)。也有人認為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伊利亞斯研究餐桌禮儀、文明化進程,巴赫金的狂歡、嘉年華、荒誕,和懷特文學(xué)批評的影響。總之,文化史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曖昧的、神秘的東西。它的理論來源是多元的,它處理的主題也是多元的。
另外,我想回應(yīng)一下,我們所做的衣食住行、逸樂的研究,剛才葛老師說在大陸頗受批評。可是我覺得,個別的研究看起來可能瑣碎,沒有意義,但是如果我們把晚明所有文化史的細小研究合而觀之,它就會透露出一個極大的思想史意義,或極大的命題。這個大的課題是晚明十六世紀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促成了情欲的解放,也顛覆了主流的理學(xué)體系。當然,我還要進一步強調(diào),即使這種研究沒有反映出時代的動脈,衣食住行、逸樂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的課題,這些都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可以仔細想一想,政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是為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信念、一些意識形態(tài)而服務(wù),還是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如果你們認為,政治的功能是照顧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中什么最重要,不就是衣食住行、逸樂、耽情縱欲嗎?雖然耽情縱欲是有危險的。所以,即使這些研究沒有顯現(xiàn)出更大的意義,本身就是重要的價值。所以我在一本書的序言里,特別提出,逸樂作為一種價值。而在儒家價值體系中,逸樂從不被正面看待。我記得以前讀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啟蒙的主題當然是理性,可是十八世紀的哲學(xué)家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激情,他們覺得激情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了激情,很多東西都不存在了。我覺得,我們研究的逸樂,跟十八世紀法國哲學(xué)家處理的激情,是一樣的。逸樂為什么要被抹殺,逸樂為什么不能變成一個重要的價值?文化史研究在這一方面,就會重新促使我們?nèi)ニ伎肌?/p>
剛才葛老師問我為何會去研究城市,這一方面是對我過去的下層研究的“反動”,因為做下層研究,每天讀白話報,或半文不白的報紙,覺得很沒有學(xué)問、沒有營養(yǎng),我想不能一輩子做這些沒有學(xué)問的東西吧,所以決定去讀上層的東西。于是,我開始讀詩詞,但我發(fā)現(xiàn)我連王士禎的詩詞都讀不懂。就這個意義來說,我做的其實不是新文化史,因為我沒有用后現(xiàn)代的觀念,沒有談解構(gòu),我是在重構(gòu),而且做的是上層的東西。我對精英文化充滿了景仰,文字的魅力簡直如魔幻一般,讓我著迷。這是我做明清城市史的原因之一,讀《桃花扇》覺得多了不起呀,自己的感情可以得到投射。
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思想史和社會史影響最大,那個時候文化史剛剛出現(xiàn),影響很大的幾本書,特別是西蒙·沙瑪(Simon Schama)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對我做城市史影響最大。西蒙·沙瑪?shù)臅土硪晃还鸱ㄕZ系教授帕特里斯·伊戈內(nèi)(Patrice Higonnet)寫的《巴黎:世界之都》(Paris: Capital of the World)有些共同的特色:第一,他們的書都寫得很厚;第二,都用了大量的圖像。西蒙·沙瑪寫了兩本大書,一本是講荷蘭的《財富的尷尬:黃金時代荷蘭文化解析》(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一個是法國大革命兩百年編年史《公民:法國大革命紀年》(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八九百頁書里面,有四五百頁是圖像,而且他不是簡單地把畫作為附錄,他對藝術(shù)史的圖像有極深的了解。如果你要問我佩服的文化史家,當然娜塔莉·戴維斯和達恩頓都包括在內(nèi),可是讀起來最賞心悅目的還是西蒙·沙瑪寫的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史。它的背后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財政背景,討論當時經(jīng)濟是否要對外開放的辯論。開放的結(jié)果,受害最大的是農(nóng)民,這是法國大革命中農(nóng)民造反的主因。所以,先有這個大的財政背景,然后處理了國王的飲食、色情狂的皇后、被流放的哲學(xué)家、走上巴黎街頭攻打巴士底獄的男女市民,還有關(guān)在巴士底獄的色情狂薩德,真是波瀾壯闊,風(fēng)起云涌,讓人讀了愛不釋手。書中看不到后現(xiàn)代主義和人類學(xué),反而受到傳統(tǒng)敘事史的影響。可是所處理的各種課題,又不是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化史會去處理的,它用的一些史料,比如圖像、食譜、漫畫之類,都是文化史會用的。從研究課題方面來說,新文化史貢獻良多。
至于葛老師提到的疆界,我覺得沒有疆界,因為文化史跟社會史一樣,都是變形蟲。一些重要的課題,比如宗教朝圣、旅行、博物館的收藏,還有現(xiàn)在風(fēng)行一時的出版史、閱讀史,都受到文化史家的關(guān)注。還有很多作品在處理回憶、再現(xiàn),虛無縹緲的感覺,欲望、恐懼、暴力、身體等,這都是以前歷史學(xué)不會觸碰的范疇。當然更不用說物質(zhì)文化這個流行而重要的課題了。文化史可說是方興未艾,它有各種理論和意涵。雖然我對理論有極大的興趣,但自己在做研究時,不太受理論的影響和束縛。但我知道我選擇的題目,不是傳統(tǒng)歷史學(xué)所做的,有許多可以歸到文化史的范疇。
葛兆光:關(guān)于思想史和文化史,我有一些想法。我也不認為新文化史只是處理碎片化的東西,只是做聲色犬馬的研究。其實,文化史的很多先驅(qū),他們做的一些看似非常具體的題目,背后都有非常大的關(guān)懷,要解決非常大的問題。比如早期研究印刷史,其目的是要講清楚歐洲的知識普及,知識是如何超越教會,從而形成獨立的知識階層,最終知識超越了神學(xué),真理取代了宗教。再比如,有的學(xué)者研究火藥在歐洲的使用,反映的是歐洲的國王軍隊越來越強大,大到足以與教皇相對抗。我還看到有人研究羅盤,講的是大航海時代,如何使歐洲逐漸走出中世紀,并且引起人類文化知識的擴張。所以,很多枝節(jié)的問題,也能提升為一個大的主題,反映出大的歷史背景。剛才,李教授有一點講得非常好,如果我們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議題,那么它本身就有很大的關(guān)懷。
我想回到經(jīng)典文化史這個話題。我一方面贊成李孝悌教授說的,作為文化史的研究,不必畫地為牢,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天象地理,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要說,如果打算寫一部文化史,就無法漫天撒大網(wǎng)了。大家可能都記得,無論是臺灣,還是大陸,都出過好多套叫作“中國文化史”的書,這些書從形式上說,大概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分門別類的平行敘述,就是梁啟超所說的,有點兒像正史里的書志,按文化類別來的,就像《食貨志》《藝文志》,各種文化分門別類,這是名為文化史的“(中國)文化常識”,其重心落在“文化”二字上,像我的老師陰法魯先生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就是這樣的;還有一類呢,是以時間為綱的縱向敘述,順著歷史(或王朝)寫各個文化領(lǐng)域的轉(zhuǎn)變,就像以前日本高桑駒吉做的《支那文化史》,是按時代順序來的,重心在“歷史”。可是,這兩類寫法都有點問題。首先,什么是文化?以前的文化史無所不包,我當年讀大學(xué)的時候,上過一門超級豪華的課,就叫“中國文化常識”,是當時一批最頂尖的學(xué)者給我們上的,包括已經(jīng)過世的鄧廣銘、王力、史樹青、劉乃和、陰法魯?shù)龋F(xiàn)在看起來都是明星級學(xué)者。這門課講的是什么呢?包括職官、科舉、地理、天文、歷法、繪畫、音樂,分門別類。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當這些東西都是“文化”的時候,什么不是“文化”,那么,文化史是不是把所有歷史都包含進來了?因此,我們現(xiàn)在看很多文化史著作,是無所不包的,那你要寫一部中國文化史,它的邊界在哪里?第二呢,它始終不處理“什么是中國”這個問題。因為中國是在不斷變化的,邊界也在不斷伸縮,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反過來用現(xiàn)代中國的疆界去倒推歷史的話,那什么都可以擱進去了。中國文化史這個名字,就名不副實了。所以,我以前曾講過,當然我做不到,要想想怎么給中國文化史瘦身,讓它有邊界,讓它有目標,讓它有一個主要的軸心脈絡(luò)。經(jīng)典文化史也得重新想想它自己的困境。
回到思想史的問題。2009年黃進興教授寄給我那篇文章的時候,他要講的是西方思想史逐漸衰落和邊緣化,可是,我那年去普林斯頓作第一講,主題是講思想史為什么在現(xiàn)代中國還很重要。當然,思想史在中國到現(xiàn)在還方興未艾,吸引了很多學(xué)者,來自不同學(xué)科的學(xué)者都聲稱自己做思想史。原因很簡單,一方面,這跟它處理的歷史問題一定和現(xiàn)實問題有關(guān),這是思想史仍然興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它表面上要處理的是歷史問題,但其實背后呢,又有很多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要對現(xiàn)在的思想世界追根溯源,找到現(xiàn)代觀念問題的來龍去脈,這使得很多人對思想史感興趣,所以,大陸很多學(xué)者都在說自己做思想史。另一方面,原來的思想史表述方式有變化,過去的思想史和哲學(xué)史過度抽離歷史語境,使得思想史變得很抽象、很形而上,可是現(xiàn)在受到各個方面的刺激,比如“語境中的思想”,原來是知識史、社會史、文化史種種背景,都和思想史相關(guān)聯(lián),使得思想史可以豐富多彩起來,所以也讓它活躍和生動了;當然,最重要的是前一點,談?wù)撍枷胧罚冀K跟現(xiàn)代中國思想問題的復(fù)雜性和尖銳性有關(guān)。林毓生先生曾經(jīng)講過,中國習(xí)慣用思想文化來最終解決問題。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一個人要是寫進史書的文苑傳,雖然很榮耀,但是不如列入儒林傳,列入儒林傳,似乎又不如列入道學(xué)傳更為重要。所以,在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系譜里,文學(xué)、歷史好像都不如思想來得重要。
雖然我一再說,思想史在當代中國還是很興盛,但我們也看到了它的問題和它面臨的挑戰(zhàn)。其中,第一個挑戰(zhàn)就是新文化史,它眼光向底層、向邊緣,也逐漸討論一些物質(zhì)化的問題,對純粹的思想觀念研究,有很大的沖擊。現(xiàn)在,新文化史在大陸也很興盛。不光是醫(yī)療、印刷、飲食,很多東西都在往新文化史上靠,甚至就連歐洲學(xué)者研究的什么恐懼、死亡、童年經(jīng)驗等,這些都在中國被引進來,用中國資料來照貓畫虎。第二個挑戰(zhàn)當然就是后現(xiàn)代、后殖民理論。諸如權(quán)力、話語、系譜、知識考古、東方主義,包括現(xiàn)在流行的反向東方主義。稍微解釋一下,什么是反向的東方主義?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是說,西方想象了一個奇風(fēng)異俗、充滿異域情調(diào)的東方,用來貶低東方,現(xiàn)在反向的東方主義,干脆承認自己就是“異邦”,用它來形塑一個與西方對峙的東方,強調(diào)自己超越了普世文明的傳統(tǒng),然后書寫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系統(tǒng)。當然這種嘗試也很有趣。那么,第三個挑戰(zhàn)是對邊緣的關(guān)注,不再集中于原來占主流的、經(jīng)典的、精英的思想上,大家去發(fā)掘各種邊緣的資料、邊緣的區(qū)域、邊緣的思想等等。
在這里,我想特別討論一下來自“國際思想史”的挑戰(zhàn)。前面我們提到的《思想史》雜志在臺北剛剛創(chuàng)刊的時候,發(fā)表了大衛(wèi)·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多回應(yīng)。阿米蒂奇是哈佛大學(xué)歷史系的教授,是最近非常有影響的學(xué)者。他始終在提倡思想史的國際轉(zhuǎn)向,或者說國際思想史的轉(zhuǎn)向。應(yīng)該說,阿米蒂奇是一個非常有創(chuàng)造力和挑戰(zhàn)性的學(xué)者,他是昆廷·斯金納的學(xué)生。2000年,他在劍橋大學(xué)出了一本《大英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起源》;2007年,出版了一本《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2013年,出版了另外一本書《現(xiàn)代國際思想的基礎(chǔ)》;特別是2014年,他和霍普金斯大學(xué)的一個學(xué)者合著了一本《歷史學(xué)宣言》,挺轟動的,這本書是劍橋出的。我看到今年《美國歷史評論》第二期居然組織了一幫人在討論這個宣言。他顯然是要改變這個歷史學(xué),尤其是改變思想史。
所以,我覺得,對于思想史的一個很重要的挑戰(zhàn),或者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出路,是不是我們也要追隨阿米蒂奇的思路,做國際思想史?我不反對在有條件的時候,討論國際的思想史,可是我又有些疑問,比如他提出的思想,像啟蒙、文明、自然、包容等等,這些被用來分析的關(guān)鍵性觀念,實際上那個時代主要在歐洲各個國家流傳與通行,所以他提出說,思想史不僅要考慮什么是思想,而且要考慮思想在什么地方,他認為要把這些都連起來。可是,我跟他的想法有點不一樣,我當時也寫了一篇文章參與討論。我說,我們確實應(yīng)該考慮什么是重要的思想,也應(yīng)該考慮思想在什么地方,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討論思想在這個地方和在那個地方,到底有什么差異。所以,一個思想、一個觀念或一個事件,在這個國家和在那個國家,為什么在理解和實踐上會有差異?你就不得不考慮思想如何被各個國家的政治、宗教、文化力量所解釋、所形塑、所改造。
我舉個例子,我最近觀察歐洲文藝復(fù)興在日本和中國的影響。一個歐洲的“文藝復(fù)興”,在日本的解釋,跟歐洲原來的歷史趨向就不太一樣,他們曾經(jīng)翻譯了很多歐洲歷史著作,但是他們讀這些書,對于文藝復(fù)興的理解、復(fù)述和借鑒,重心就很不一樣,包括在明治中葉,它也會引起像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往回走,強調(diào)日本民族性、提倡國粹主義。同樣,“文藝復(fù)興”在中國的影響也不一樣,它也引起了兩種反應(yīng),一種是黃節(jié)、鄧實、劉師培他們講的“古學(xué)復(fù)興”,這就要重新回到經(jīng)典,發(fā)掘傳統(tǒng),接續(xù)文化;另一種呢,則引起了胡適講的“啟蒙運動”,用白話重新塑造國語,通過教育塑造國民。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把各個國家的思想串聯(lián)起來,成為一個“國際思想史”,但是我們更應(yīng)該看到,在不同的國家,由于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的特殊性,思想會發(fā)生變異。阿米蒂奇是做歐洲思想史的,歐洲思想有很多共通性和連帶性,因為啟蒙時代它有一個超越國境的知識分子群體和思想平臺,所以,他更容易看到各個國家的思想的聯(lián)系性。但是對我而言,在東亞這種國家力量相當強大的區(qū)域,更容易看到思想的差異性。以前有段時間,我常常讀鮑默(Franklin L. Baumer)的《現(xiàn)代歐洲思想》(Modern European Though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1600-1950),他用五個詞貫穿了歐洲思想:上帝、自然、人、社會、歷史。可是,我們能用這五個詞來貫穿中國思想嗎?好像不行。在中國,就要選另外一些關(guān)鍵詞。所以呢,有些東西,我們要接受,比如“思想史的國際轉(zhuǎn)向”,我們要學(xué)習(xí)其超越國境的研究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站在中國的角度,考慮中國的特殊語境,希望還是有一些研究,能夠說明這個歷史上一直過于強大的國家力量,在歷史上如何限制、影響和形塑了思想的特殊性。
再把話題說回來吧。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之間,我一直在想找到一條把兩者溝通起來的道路。現(xiàn)在有個很籠統(tǒng)的說法叫“思想文化史”。這個詞當然很好,能把兩者捏在一起,但有時候搞思想史的還是做思想史,搞文化史的還是做文化史。剛才黃所長說,在臺灣,中文系、哲學(xué)系做思想史研究比歷史系多,這是因為臺灣的中文系有一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傳統(tǒng),除了西方學(xué)科中的文學(xué),它還有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xué)和小學(xué),因此,使得很多人也自稱為思想史,但是它的儒家,或者理學(xué)家的色彩很濃。哲學(xué)系的話,因為思想、觀念屬于哲學(xué)嘛,也要做思想史研究,但是它的形而上色彩很濃。可是,在歷史學(xué)領(lǐng)域里討論思想史,就像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樣,是要把思想放在一個非常復(fù)雜的、活動的語境里,這點跟斯金納所說的“語境”(context)有接近的地方。所以,歷史學(xué)家在做思想史研究的時候,會盡可能選擇一個有語境的、有背景的、有文化的思想史,或者說,是“文化史背景中的思想史”或者“政治史背景下的思想史”,這樣才能真的把兩者溝通起來。當然,這樣做,關(guān)鍵也需要找到著力點,也就是說要找到合適的“語境”和“焦點”,不然的話,那個“背景”會很虛很空。我舉個例子,我一直覺得宋元以后,思想史應(yīng)該關(guān)注“中人”——比如地方士紳、私塾的塾師、幫人打官司的訟師、發(fā)家的“土豪”、邊緣知識分子就是鄉(xiāng)秀才之類、破落大家的子弟——這些人的思想世界,其實有可能影響甚至左右整個社會的思潮。大家也許注意到,雖然古代比如從劉邦起,就是這種身份的人在左右歷史,到了現(xiàn)代更是如此,如果從現(xiàn)代中國的情況倒推回去的話,真正在現(xiàn)代中國起巨大作用的,恰恰是這批中人,而不是精英。無論是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是中間階層來的,不是貴族知識分子,也不是大字不識的土豪。其實這層人,很容易在歷史上起很大作用。如果我們能夠研究這批人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身份是浮動的,他們的觀念是游離于舊傳統(tǒng)和新價值之間的,他們的態(tài)度是非常實用的,而且,他們能夠串聯(lián)上面和下面。對這群人的研究,既可以作為政治史研究,也可以作為文化史研究,也可以作為思想史研究。此外,也可以變成“國際思想史”呀,因為它需要與德川時代日本的“武士”、李朝朝鮮的“中人”進行比較,看看這些人是否也是后來政治的新力量。
我過去總是講,思想史太過于重視精英的思想,可是不太注意到“中人”,但是另一方面,民眾的、世俗的、下層的那些東西,怎么樣能夠上升到精英的、官方的、思想的東西,研究也不夠。所以,我覺得“中人”是貫通高低、串聯(lián)上下的,一旦他上升,就成為精英,一旦下降,他就成為民眾。如果我們將這一階層作為研究重心的話,思想史和文化史或許就能溝通起來。當然,我這只是舉一個例子,怎樣研究,還需要很深入的考慮和摸索。
我覺得,現(xiàn)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學(xué)者都在自我反思,然后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出路,否則的話,光憑思想史在大陸曾經(jīng)盛行的余威,未來如何繼續(xù)做研究?也不能說,光憑著現(xiàn)在新文化史漸漸興盛的勢頭,就去做新文化史?如果沒有一個自己的問題、方法和角度,思想史和文化史都不能成為這個學(xué)界真正關(guān)心的領(lǐng)域,也提不出新問題、做出新結(jié)論。說老實話,今天我們?nèi)齻€人談這個問題,不是在解決問題,而只是想提出問題。
(石偉杰根據(jù)講座錄音整理,經(jīng)過三位教授補充修訂)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