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清代官場的仕途疏堵與滿漢對抗
中國有句俗語說,大家都做官去了,誰來抬轎子。它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士人熱衷官場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了官場的擁擠程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似乎官場從來都是僧多粥少,人才擁擠不堪,競爭黑暗無比,但是人們對此“醬缸”卻絲毫不懼,前赴后繼。清代官場較之前朝,同樣存在人滿為患的通病。士人大多一方面覺得自身才干欠缺,另一方面又責怪上天不公,崇尚迷信。對于清代最高統(tǒng)治者來說,他們需要對整個仕途的晉升通道定時清理,促使整個官僚體系有效運作,乃至勉強維持,這就不得不考慮仕途擁擠的問題。

侍衛(wèi)挑選與入仕別途
清代官場中,滿漢士人升遷的顯著差異是旗人入仕不必限定科舉渠道。從八旗子弟入仕的歷史軌跡來看,清初,科舉往往不為八旗士人重視,后來才越發(fā)重要,乃至成為主流。清代前期,戰(zhàn)事不少,崇尚武治天下,因而皇帝進行侍衛(wèi)挑選,進而補充官僚體系,亦是清代國家人才成長的重要通道。隨著時局發(fā)展,特別是選材整體格局中出現(xiàn)重文輕武的發(fā)展趨勢,這一通道日漸狹窄。但是,這一通道從未關閉,乾隆晚期權臣和珅即起家于侍衛(wèi),可見侍衛(wèi)入仕仍是八旗子弟的重要選擇之一。
在侍衛(wèi)挑選中,距離皇帝較近的拜唐阿侍衛(wèi)挑選更是緊要。然而,即使如此重要的人才挑選機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乾隆中期,大批八旗子弟不愿入侍衛(wèi)之選,而是熱衷科舉或者其他入仕渠道。乾隆帝為了維持這一傳統(tǒng)選材渠道,特意頒布了相關的上諭,建立五年一選的制度。當然,此種侍衛(wèi)挑選制度,同樣借鑒了科舉制度的成功經(jīng)驗。有所不同的是,它更集中體現(xiàn)了皇帝的自我判斷,而不是相對客觀的評價標準。侍衛(wèi)挑選是皇帝親自主持的一次面試。
嘉道時期,這項制度的實施遭遇到不少危機,情況并不樂觀。嘉慶十年十一月,軍機大臣翻出乾隆五十年諭旨所訂立的挑選侍衛(wèi)拜唐阿制度,請求重新實施,從八旗內(nèi)外文武大員子弟中挑選侍衛(wèi)拜唐阿,五年一屆。此請得到嘉慶帝大力支持:“揀挑侍衛(wèi)拜唐阿,溯自乾隆五十年遵旨查辦以來,惟于乾隆五十年查辦一次,乾隆五十五年查辦一次,乾隆六十年、嘉慶五年,屆期均未辦理,今已越十五年,自應遵照原奉諭旨查辦。著八旗及內(nèi)務府三旗,即照前辦成例,將在京文武大員、外任知府以上大員及歲子弟,查明分造清冊,咨送軍機處匯奏,候朕指出帶領引見。嗣后五年一次,照此查辦。”
同年十二月,嘉慶帝對于挑選的范圍進行詳細說明,規(guī)定相應品級的官員子弟才有資格參選:“嗣后大員兄弟子孫揀挑侍衛(wèi),仍照前次辦理,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世職公侯伯以上,外省文職知府以上,武職總兵以上及新疆辦事大臣之兄弟子孫應行咨送者,俱著查明造冊,咨送軍機處,照例繕寫清單呈覽。”對于大員子弟的年齡等限制也有說明:“此項大員兄弟子孫,年及十八歲之六品以下文武人員,無論補缺與否,俱著查送。其候補五品文武人員及未經(jīng)引見之五品蔭生,亦著造冊咨送,至實缺五品文武官員,俱毋庸開送。”
盡管朝廷對此制度的維護頗下功夫,但八旗子弟對此并不買賬,效果越來越差。道光十五年,朝廷發(fā)現(xiàn)挑選侍衛(wèi)拜唐阿遭遇諸多挑戰(zhàn):“自道光十一年查辦以來,迄今又屆查辦之時,該大員子弟,或身軀單薄,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驟難學習弓馬,自應酌量變通。”朝廷不得不對官員子弟的登記有所讓步,一些確實才品不行者允許缺席挑選:“嗣后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在外文職由總督至臬司,武職由將軍提督至總兵,子弟內(nèi)如有及歲情愿送挑者,仍照從前咨報本旗,由旗咨送軍機處匯奏,候朕指出引見。儻身軀單薄,及有殘疾,或弓馬平常,不堪送挑者,即據(jù)實報明,聽其自便,用示朕曲成旗仆,因材器使之至意。”
鑒于此項挑選制度實施效果不佳:“自道光二十一年查辦后,迄今已及五年,又屆應行查辦之時。惟念該大員子弟內(nèi),亦有不同,或身體單弱,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一時不及習學騎射,似此即挑取侍衛(wèi)拜唐阿,又何能得力,自應酌量變通辦理。”道光二十五年,朝廷再次修改制度設計,要求大臣報名挑選:“嗣后在京文職自三品以上,武職自二品以上,在外文職自總督至按察使,武職自將軍提督至總兵,該大員兄弟子孫內(nèi),如有年已及歲,可以充當侍衛(wèi)拜唐阿差使者,俟五年查辦之際,該大臣等仍照上次呈報本旗,由該旗造冊咨送軍機處會總具奏,俟朕指出,帶領引見。”對于那些不愿參加的大臣,道光帝也是給予較大的自由:“如身體單弱,或有殘疾,抑或弓馬平常者,著該大臣即據(jù)實報明該旗,轉(zhuǎn)行軍機處,均聽其便。該旗亦毋庸催取其名,以示朕作養(yǎng)器使旗仆之意。”
自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五年,整整十年之間,拜唐阿侍衛(wèi)的挑選始終不容樂觀。道光帝對于整個高級官僚子弟的教育,也不是很滿意。不過這一制度的實施,在某種意義上,仍是在延續(xù)和保持八旗子弟的入仕優(yōu)勢,在通往清代政治權力核心圈的征途上為他們開辟了另外一個通道。這也表明,八旗子弟仍是道光帝等人信任的主體和核心圈。但侍衛(wèi)挑選本身的窘境,充分說明了清代官場的擁擠、官職的貶值和各種選材通道的競爭,展示了清代原有權力分配體系的整體性溶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清代官場日益擁擠的境況下,侍衛(wèi)的挑選得到清朝統(tǒng)治者的重視。這一方面固然是延續(xù)傳統(tǒng),有制度慣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是在科舉選材越發(fā)占據(jù)主流的情況下,另開別途,保持八旗子弟對核心權力掌控與占有的方式。這無疑是清代官場高層權力職位流傳與沿襲的一種自救性措施,可惜的是效果不盡如人意。
舉人大挑與制度慣性
清代仕途的疏通,一方面要確保八旗士人的優(yōu)先特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兼顧滿漢兩大勢力之間的平衡。舉人大挑是乾隆朝選材制度的創(chuàng)新,對于維護科舉制度的健康發(fā)展以及捐納制度的持續(xù)實施,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一是從仕途的疏通來看,舉人群體出路的解決,不僅有利于下層監(jiān)生等群體的持續(xù)涌入,同時也可緩解上層進士群體的錄取壓力,可謂承上啟下的關鍵之舉。二是從捐納的交易維護來看,舉人群體的持續(xù)與穩(wěn)定更有利于監(jiān)生等名額的捐納,這才使得捐監(jiān)這一捐納形式自乾隆初年至光緒年間都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資金籌措功能。三是從官員素質(zhì)和銓選機制來看,舉人群體充實到地方基層官吏,可以提高地方官吏的整體素質(zhì),為基層官僚體系注入新的血液。
自乾隆朝以來,舉人大挑受到士人極大關注,競爭越來越殘酷。關于挑選的程序,嘉慶朝不少大臣提出了修改意見,試圖改革。嘉慶六年,御史濟蘭上奏酌改大挑舉人章程的諸多建議,主要內(nèi)容有三。一是擔心挑選考官個人專斷。二是要求大臣匿名提交考選意見:“令派出之王大臣,于名冊內(nèi)各注記號,挑畢后,另派親信大臣,會同拆看,始定去留,挑額不敷,再將此記圓圈,彼記尖圈之舉人,另傳復看。”三是參加面試的人數(shù)不設限制。對此,嘉慶帝結(jié)合自身參與舉人大挑經(jīng)驗,給予詳細回復。在嘉慶帝看來,朝廷應該充分相信考官素質(zhì):“朕在藩邸時,曾蒙皇考閑派,與成親王永瑆及大學士阿桂、劉墉等,一同挑選。彼時朕與成親王坐位在前,即系與眾大臣公同商酌,以定去取,從無獨出意見之事。目今派出之王大臣等,自不敢意存專擅。如果挑選時,派出居首之一二人,并不與他人參酌,現(xiàn)有御史在旁,原可據(jù)實參奏。儻竟有聽受囑托情事,訪查得實,亦無難列入彈章,何必更易舊規(guī),始能剔弊。”同時,對于大臣意見匿名核對,嘉慶帝認為程序煩瑣。而對于面試人數(shù)的限制,嘉慶帝認為是便于考試管理。對于嘉慶帝來說,舉人大挑的選擇標準更多是舉人的年齡和精力,而不是文采:“至大挑舉人,原為疏通寒畯,以免淹滯,其中年力精壯者,自應列為一等,俾得及鋒而試,即年齒稍長,而精力未衰,亦可與民社之選。若年力近衰之人,則應列為二等,俾膺司鐸,以遂其讀書上進之愿。惟在派出之王大臣等,仰體朕意,秉公挑選,自必輿論翕然。”
對于舉人大挑,嘉慶帝深有體會。在乾隆帝的安排下,他曾兩次親自參與挑選,對其中內(nèi)幕十分了解。“朕與成親王于乾隆五十二年、六十年曾兩與其事,溯自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已蒙皇考密緘朕名,纘承大寶,而丁未、乙卯兩次大挑,俱蒙皇考閑派,仰見圣心于此一事,委任至為慎重,乃彼時即有人將與挑舉子,托言私宅賓友,竟敢在朕前呈遞名條者。”但是,對于舉人大挑的積極作用,嘉慶帝還是高度肯定:“大挑舉人,原為疏通寒畯,俾免淹滯。挑選時并不試以文藝,只就其人年貌,分別去取,立法遵行已久,亦斷無復行考試之理。”
對于嘉慶帝來說,舉人大挑本身是一項優(yōu)良的人才選拔制度,關鍵是官員的執(zhí)行問題。因此,他對考試的管理十分重視,要求官員潔身自好、公正無私:“此次大挑,經(jīng)朕派出王大臣等,諒不敢為受賄營私之事,而徇情聽囑,實不能保其必無。即有謹飭自愛者,面為拒絕,亦未必肯將囑托名條,遽行陳奏。但此等夤緣舞弊之徒,若不嚴辦一二,不足示儆。”
但制度的運作與國家治理的大環(huán)境息息相關,嘉慶朝的舉人大挑也很難解決仕途壅積的大問題。因為嘉慶年間的科場和官場本已十分擁擠,大挑的舉人很難分發(fā),后來不得不減少挑選的名額。嘉慶十三年三月,到京挑選的全國舉人有3000多人,朝廷不得不再次商量對策。此次由通政使司副使閻泰和奏請,建議酌量變通大挑程序,核心內(nèi)容是一等名額減少,歸入二等。于此,嘉慶帝還是憑借個人經(jīng)驗,確定一等、二等名額比例:“朕于藩邸時,兩次親理挑務,其分別一二等舊額,向所稔知,所有此次大挑舉人,著于每兩班二十人內(nèi)挑取一等三名、二等九名,以示體恤寒畯之至意。”
嘉慶朝的官場人才擁擠程度遠超朝廷估計,此后一段時間內(nèi),舉人大挑的人員始終無法得到有效使用,朝廷不得不停止大挑,謀求進一步改革。嘉慶十八年八月,朝廷宣布暫緩舉人大挑,改為每四科挑選一次。“各省舉人,從前皇考高宗純皇帝加恩寒畯,特予大挑,俾多士及時自效。朕親政以來,每閱六年,按次舉行,惟現(xiàn)在分發(fā)各直省者,為數(shù)過多,該舉人等挑選以后,補缺無期,省垣需次,資斧惟艱。此次若再照例挑選發(fā)往,更形壅滯,轉(zhuǎn)非所以體恤寒士之意。所有明歲大挑,著暫緩一科,于丁丑科會試后舉行,并著嗣后每屆四科奏請大挑一次,仍照例扣除近三科舉人,俟各省挑往人員漸次疏通,該部即奏明再行照舊辦理。”
但四年之后,嘉慶帝再次面對挑選舉人無處安置的境況,不得不另起爐灶,將部分舉人挑選為河工人員:“大挑舉人,原以疏通寒畯。近來各省分發(fā)人員漸覺壅滯,昨經(jīng)大學士會同吏部酌議章程,量加調(diào)劑。朕思南河、東河、北河三處河工,亦需員差委,若于此項大挑一等人員內(nèi)分發(fā)試用,俾之學習河務,以河工之繁閑,定人數(shù)之多寡,既可策勵人材,亦可疏通額缺。”隨后,吏部秉承圣意,挑選河務人員60名,一年試用期滿,以知縣注冊試用。對于吏部此舉,嘉慶帝認同挑選整體方案,但對試用期提出質(zhì)疑:“此項大挑一等分發(fā)河工人員,著定為試用二年,經(jīng)歷六汛后甄別。該河督秉公察看,其能通曉河務者,留于河工,照新定章程分別補用。如河務不能諳習,而才具尚堪膺民社者,奏明改撥地方,仍以知縣補用。其才識迂拘者,以教職改補。”

道光帝對于舉人大挑,沒有嘉慶帝如此深刻的個人體驗,也很少發(fā)表個人意見,更多參考大臣的意見。而且從朝局發(fā)展來看,道光朝仕途壅滯現(xiàn)象并無緩解之態(tài)。道光帝對此也十分苦惱。但是,生性謹慎的道光帝對于祖宗之法不敢過多修改,仕途擁擠之窘境遂很難改變。道光三年七月,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和江蘇等省,先后奏請停止分發(fā)佐雜人員,原因是各省人浮于缺,仕途阻塞。基于各省實情,朝廷先后允許。但是御史趙柄提出異議,要求各省督撫設法調(diào)劑,不得停止分發(fā)。道光帝站在吏部立場,批評趙氏建議:“若如該御史所奏,令各督撫設法調(diào)劑,不得請停分發(fā),是佐雜等選期本屬遙遠,分發(fā)到省,又復擁擠至數(shù)百人之多,守候至數(shù)十年之久,旅進旅退,得缺無期,甚非所以恤微末而權銓政也,所奏著毋庸議。”在道光帝看來,只有限制選拔的數(shù)量,才能解決現(xiàn)有的官場人員眾多的擁堵問題。
道光初年,各省吏治疲軟,仕途晉升壓力巨大,江蘇官場頗有代表性。道光五年,道光帝委派能干的江蘇巡撫陶澍整治江南吏治,希望其能徹底振奮官場。陶澍到省后,發(fā)現(xiàn)官場人多于缺,進階太雜:“蘇省大挑等班,知縣輪補無期,現(xiàn)在六十八州縣中,由捐班補、由佐貳升者不少。而沿河各縣,以縣丞署理者十居其七,雖甲科捐納人本原無區(qū)別,然進階太雜,難免幸進之輩濫廁其間,始基未立,安望其留心民事,有益地方?此吏治之不可不亟為整頓者。”
各省缺少人多,中央各部同樣位置緊缺,僧多粥少。道光十二年六月,給事中孫善寶奏請飭查各衙門缺分,吏部回奏調(diào)查結(jié)果:“現(xiàn)查六部各項主事,共三百二十一員,內(nèi)分部進士一百八十八員,補缺未免太遲。查各部郎中本系三年截取,嗣于嘉慶八年,改為二年截取,蓋以升途稍寬,則主事可無壅滯。查知府選例,雙月一內(nèi)班、一外班、一捐班,單月一應補、一捐納、一京升,內(nèi)班、京升二項,皆郎中與御史相間輪用,現(xiàn)在各部郎中二年截取后,又非四五年不能得選,占缺既久,故主事仍形擁擠。”由此可見,連京城六部主事也是人滿為患,不得不縮短選拔輪期,這又進一步加大了現(xiàn)有官員群體的升遷難度。
道光朝官場的這種擁擠之勢,從上到下,俱有明顯的滯礙表現(xiàn)。地方各省的教職保舉,也遭遇到名額危機。道光二十年五月,給事中巫宜禊奏報教職保舉知縣班次壅滯,要求酌議疏通,得到道光帝的大力支持,吏部修改選拔教職期限:“原奏請照教習之例,自俸滿引見日起,扣足三年,呈請分發(fā),簽掣各省補用,應如所奏辦理。”同年五月,給事中周春祺奏請捐納人員補缺,要求盡先保奏:“不準全占升調(diào)、丁憂、終養(yǎng)、參劾改補各缺,并兼三兼四題缺捐。”對此,吏部給予積極回應:“查委用試用道府等官,只補升調(diào)遺缺。該給事中請補告病、病故、休致之缺,系屬錯誤,請嗣后捐納道府分發(fā)試用人員,保奏先補、即補者,于本班到班之前先用,準補升調(diào)所遺選缺。如該省并無題調(diào)缺分,遇有告病、病故、休致三項選缺,亦準扣留題補。”
道光年間,隨著國家財力的衰弱、自然災害的增多,捐納開始更為廣泛地開展,特別是捐納從原來的禁止民間力量廣泛參與,逐漸轉(zhuǎn)變?yōu)閲覐娖然蛘邉訂T民間力量進行捐輸,國家與士人的交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乾隆年間,朝廷為了疏通仕途制定了諸多有效的措施,或舉人大挑,或侍衛(wèi)廷選,或控制捐納,等等。這些措施雖然不能達到朝廷的理想效果,但還是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科舉制度和捐納制度得以維持較長時期的健康發(fā)展。但是,伴隨著鎮(zhèn)壓白蓮教起義等系列軍事行動,國家耗費巨大,國庫日漸空虛,捐納呈現(xiàn)出了從力圖控制到難以控制的發(fā)展態(tài)勢。與此同時,科舉制度持續(xù)發(fā)展,滿漢士人的不斷涌入讓本就擁擠的科場和仕途都更加擁堵。宗室科考的發(fā)展從一個側(cè)面可以反映出科舉發(fā)展的迅速和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同樣,拜唐阿侍衛(wèi)的遴選,一方面顯示出清朝照顧八旗、選拔人才的多渠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非科舉選材渠道的尷尬。
值得注意的是,滿漢的消長在制度的實踐中發(fā)生了難以察覺的變化。從絕對數(shù)量上來看,滿漢士人的科舉都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包括內(nèi)務府的官學都在不斷興建。八旗科舉相比此前也得到更大的發(fā)展,特別是允許駐防八旗考試,以及后來的翻譯考試,都表明進入科場和仕途的八旗士人的絕對數(shù)量在不斷增加,而且其增加的幅度和數(shù)量,都是漢人群體無法比擬的。但是,從滿漢的絕對比較優(yōu)勢來看,滿漢的隱性對抗越來越有利于漢族士人,因為在長時段對抗中,增長的滿族士人仍是整個士人群體中的少數(shù),無法改變整個滿漢消長的趨勢。
(本文選摘自《清代捐納與國家治理》,吳四伍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轉(zhuǎn)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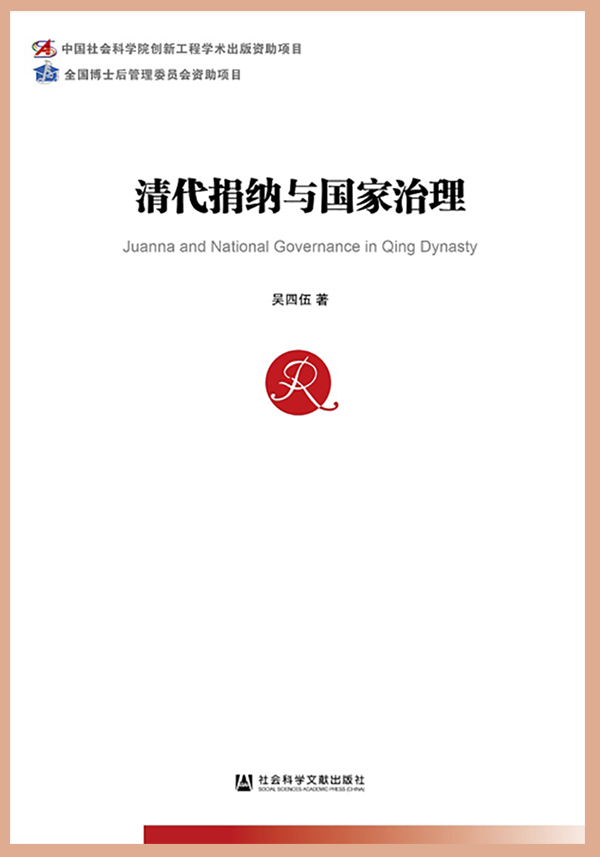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