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王希:美國民主走入了死胡同?
自從2000年出版以來,《原則與妥協(xié):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這本書已經(jīng)有了三個版本,影響了不止一代學(xué)人,成為美國憲政史及美國史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在2014年出版的最新版增加了二十萬字,聚焦于新世紀(2000年)以來,一直到2014年美國憲政秩序的發(fā)展和變化。其中包含了很多重要議題,如司法的活躍、立法與行政的對峙、黨派政治的強化、民主制的危機、反恐戰(zhàn)爭中公民自由與政府權(quán)威間的平衡、種族平權(quán)、性別平權(quán)、公民的福利訴求以及醫(yī)療保障平權(quán)。所有這些議題,可說包括了美國政治的最為重要的方面,而它們都統(tǒng)攝在美國憲政這個大的框架之下。本書作者、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希對這些核心議題一直保持深入的關(guān)注和了解,故而能做出全面、詳盡的分析。讓他遺憾的是,這本書的出版早了一年,“如果2015年出的話,又可以增加不少精彩內(nèi)容了”。看來,修訂還會不斷持續(xù)下去。

美國憲政的“變”與“不變”
澎湃新聞:您在《原則與妥協(xié)》這本書當(dāng)中關(guān)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美國憲法為什么會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我讀后的感想是,由于種種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法律體系本身的機制存在,美國憲法能夠很好地處理“變”與“不變”之間的關(guān)系,對此您怎么看?
王希: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也很關(guān)鍵,首先涉及我們?nèi)绾慰创龖椃ㄒ约皯椃ǖ氖褂谩椃仁且环N關(guān)于國家組織和國家政治的文本,也是一種制度和文化。所謂“憲政”,也就是實踐中的憲法,就是由憲法文本、制度體系和憲法文化構(gòu)成的。換句話說,憲法只有用得上,才有生命力,才不至于成為一種擺設(shè),但憲法的有效性不光是靠文本的存在,還需要制度、文化的支撐與維系。
關(guān)于美國憲法的“變”與“不變”的關(guān)系,可以從憲法原則和原則的實踐兩個層面來理解。我們一般的印象是,原則是由憲法文本來陳述的,而憲法文本——尤其是美國憲法的文本——似乎一直不變;但事實上,實踐中的憲法原則是變化的,這是因為對憲法原則的詮釋或解讀在不斷變化。
舉個例子。美國憲法的序言提到,美國人立憲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完善的聯(lián)邦,樹立正義,確保國內(nèi)安寧,提供共同防務(wù),促進公共福利,并保障我們自己及后代得享自由之恩賜”。這里面提到的“樹立正義”(establish justice),可以說是立憲的一個重要原則,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美國人對“正義”的理解和解釋可以說非常不同。內(nèi)戰(zhàn)前,保護奴隸主的財產(chǎn)權(quán)是“正義”的內(nèi)容之一;內(nèi)戰(zhàn)中,解放奴隸成為“正義”的行動;重建時期,將前奴隸變成公民和選民成為美國憲法的“正義”原則的核心內(nèi)容。“促進公共福利”(promote general welfare)也是如此。十八世紀末立憲的“公共福利”指十三個州的共同利益;今天看來,則是指聯(lián)邦國家的利益和全體美國公民的權(quán)利。所以,不同時代對憲法原則的解讀是不同的,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舉不勝舉。
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兩點,一是憲法原則需要得到實施,需要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依循的根本;只有這樣,所謂“原則”才能轉(zhuǎn)化成為普通人能夠觸摸的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他們也才可以有理由、有機會參與到憲政中來,包括參與對憲法原則的解讀。而對憲法原則的解讀,不光是通過立法、執(zhí)法、司法等國家渠道,也通過公民的集體和個人行動。二是允許不同的解讀的存在。這是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美國在這方面的處理也不始終是順利的或成功的。處在不同時代的人對同一原則有不同的解讀,同一時代處在不同背景和地位的人對同一原則更有不同的解讀。美國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圍繞憲法原則爭論的的歷史,有些爭論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誰的解讀能夠勝出,這就需要制度的規(guī)范,但僅有制度是不夠的,還需有憲政文化的支持。新的憲政原則會通過法律來體現(xiàn),立法過程必須是開放的,但一旦形成法律之后,就必須得到尊重和遵守,直到新一輪的、對原則進行重新解讀的博弈開始并產(chǎn)生新的結(jié)果。
我尤其強調(diào)立法過程中的“開放”性,因為這是所謂“變”與“不變”博弈的主要戰(zhàn)場。就像當(dāng)下的移民法改革,奧巴馬總統(tǒng)想要否定某些過時的法律,但國會共和黨人因為種種理由卻要堅決阻止,雙方都竭盡全力,訴諸各種可以利用的體制力量。我想,最終的結(jié)果應(yīng)該是有得有失。美國憲法的“變”與“不變”通常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
補充一句,博弈之后達成的共識成為新的憲法原則,究其實質(zhì),“新原則”并不是一切推倒重來,而更多的是對原有原則的重新解讀或延伸,看似不同的原則之間其實存在邏輯上的連續(xù)性和一致性,能夠幫助化解“變”與“不變”之間的張力。
澎湃新聞:新世紀以來,美國憲政出現(xiàn)了哪些重大變化?
王希:第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司法權(quán)特別活躍。“9·11”事件之后,司法權(quán)變得空前活躍,介入了很多問題。這跟第二個重大變化有關(guān):2000年以后,公民權(quán)利問題日益凸顯。公眾越來越關(guān)心公民應(yīng)該享有什么樣的權(quán)利,而公民權(quán)利也越來越多元化、細化。當(dāng)今的權(quán)利訴求與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quán)運動有著明顯區(qū)別。民權(quán)運動追求的是以種族、膚色和性別為基礎(chǔ)的群體權(quán)利(group rights),因為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土著美國人、婦女等曾長期在歷史上受到法律的歧視。現(xiàn)在的公民權(quán)利訴求是跨種族、跨性別、跨年齡甚至是跨黨派的活動,比如對同性婚姻平等權(quán)的追求。

第三個重大變化也是美國憲政目前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即黨派政治對國家權(quán)力機構(gòu)的高度滲透和影響,造成了立法權(quán)與行政權(quán)之間的無法妥協(xié)的對峙,經(jīng)常出現(xiàn)政治僵局,這在奧巴馬任職期間尤其如此。奧巴馬總統(tǒng)是民主黨人,但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占有多數(shù),雖然不是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shù)(因此不能推翻總統(tǒng)的否決),但至少可以拒絕與總統(tǒng)合作,阻撓總統(tǒng)希望推動的政策或改革,這就造成了僵局。美國歷史上的關(guān)鍵改革之所以發(fā)生,要么是總統(tǒng)非常的強勢,要么是國會非常的團結(jié)或與總統(tǒng)有良好的配合。二十世紀的“新政”和“偉大時代”改革之所以得以推進,在于有體制上的優(yōu)勢:總統(tǒng)強勢,又有國會的配合。奧巴馬的個人能力是優(yōu)秀的,也有很強的民意支持,但他卻無法成為一個像羅斯福或約翰遜那樣的強勢總統(tǒng),因為他受到的牽制太多。他目前采取的辦法是利用行政權(quán)來推行他的改革政策,按理說,這是不正常的,而且時效性有限,他一下臺,很多政策可能被逆轉(zhuǎn)。最高法院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自由派和保守派大法官的力量勢均力敵,自由派大法官們還可以利用微弱、但不確定的多數(shù)來推動他們追求的社會正義,但如果自由派大法官退休,新的保守派大法官被任命,最高法院內(nèi)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例就會發(fā)生變化,這也會影響關(guān)于公民權(quán)利的司法判決的走向。所以,我們看到,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公民通過選舉的程序來表達意見、影響政治的道路已經(jīng)越走越窄。
澎湃新聞:所以,有些批評家說,美國民主走入了死胡同。
王希:我倒沒這么悲觀,但覺得這的確是個嚴重的問題。美國學(xué)界也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且有嚴肅的批評和討論。究竟如何解決,還沒有形成共識。黨派政治還對立法、司法、行政三權(quán)的平衡形成了沖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現(xiàn)在越來越政治化,權(quán)利政治(politics of rights)和權(quán)力政治(politics of power)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大家都懂,有了權(quán)力(power),才會有權(quán)利(rights),只有在政治上處于有利地位,權(quán)利才能得到擴張。
澎湃新聞:這種僵局有沒有可能化解?或者美國的憲政體系有沒有可能消化容納這些變化?
王希:通常的辦法是靠定期選舉來重新洗牌,改變國會中黨派力量的組合。但因為選舉主要靠政黨來主持,在很多選區(qū),某一黨派的勢力始終是多數(shù),少數(shù)黨幾乎不做努力,因為努力了也是白費。這跟選民的心理和政治習(xí)慣有關(guān)。像南加州這樣的地方,不管共和黨的政策多么不接地氣,大部分選民還是會基于傳統(tǒng)去支持共和黨。真正具有競爭性的選區(qū)實際上是為數(shù)不多的。民主、共和兩黨對競爭性選區(qū)有大量的精細研究,會去那里爭取“搖擺票”,而且隨著選民成分和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情況的變化,選舉的結(jié)果也不是政黨能夠為所欲為任意決定的。換句話說,選舉仍然是有效的,仍然能夠改變黨派力量在權(quán)力政治中的平衡,仍然是美國的一種“常態(tài)政治”。
澎湃新聞:除了“常態(tài)政治”之外的“非常態(tài)”情況是什么呢?
王希:還有就是國家遇到重大危機的時候,黨派對峙的僵局會被打破。比如1929年胡佛當(dāng)選的時候,很多人是支持共和黨的,但是當(dāng)選之后不久美國遭遇大蕭條,1932年選舉時,民主黨人羅斯福就翻盤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quán)運動時期,美國也面臨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南部白人保守派多為民主黨人,但當(dāng)同樣是民主黨人的約翰遜總統(tǒng)選擇站在支持黑人民權(quán)這一邊,他們就轉(zhuǎn)向支持共和黨了,而重新獲得選舉權(quán)的南部黑人則成為了民主黨的中堅力量。這也是一種重新洗牌。
歷史不是個人可以左右的,政策要順應(yīng)歷史的潮流。美國人現(xiàn)在雖然有危機感,而且比前幾年更加強烈,但危機感還沒有大到讓他們覺得自己的日常利益和總體利益受到了“清楚的和即時的威脅”(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地步。到了那個時候,他們會采取行動的——因為他們手中握有選票。
當(dāng)然,很多人對選舉也不抱任何希望,尤其是年輕人,有人可能因此認為選舉民主是無效的。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覺得這里有一個選民如何和為什么運用投票權(quán)的問題。比如地方學(xué)區(qū)委員會的選舉,大部分的人不關(guān)心,甚至不投票,但那些關(guān)心自己孩子教育質(zhì)量的家長會去投票和參與競爭。加州在2008年就同性婚姻問題舉辦過一次全民公決,投票率是相當(dāng)高的,因為許多人覺得這是涉及自身和社區(qū)的道德價值觀的問題,相當(dāng)于一種“危機”狀況。

2000年總統(tǒng)選舉和“9·11”事件
澎湃新聞:關(guān)于2000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聯(lián)邦最高法院裁決小布什勝出,不少人視之為美國制度優(yōu)越性的體現(xiàn)。而您對此卻持保留意見,指出這一裁決不僅打破了美國憲政中的三權(quán)分立,而且引入了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機制,降低了總統(tǒng)選舉的民主性。十五年過去,回看這場大選,能否請您談?wù)劊谑裁捶矫妗⒍啻蟪潭壬蠈γ绹鴳椪难葑儙碛绊懀瑢γ绹偨y(tǒng)選舉程序又造成了怎樣的改變呢?
王希: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我當(dāng)時說最高法院的決定打破了三權(quán)分立的原則,并不是否定最高法院的決定,而更多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探討這一特殊現(xiàn)象,即由最高法院來決定總統(tǒng)大選的結(jié)果。總統(tǒng)大選出現(xiàn)難局,在2000年之前至少有三次,但由最高法院單獨裁決,這是第一次。1800年杰斐遜的當(dāng)選是由眾議院投票決定的。1824年約翰·昆西·亞當(dāng)斯的當(dāng)選也是如此。1876年海斯的當(dāng)選則是由國會兩院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共同組成的裁決委員會投票決定的。2000年最高法院為解決布什與戈爾的爭執(zhí)兩次投票,一次的結(jié)果是七比二,但最關(guān)鍵的第二次投票是五比四,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在這次投票中的立場是鮮明對立的。
從程序上看,由最高法院來解決這場難局似乎是順利成章的,因為布什和戈爾兩人在佛羅里達都是通過法院渠道來訴諸裁決。我感興趣的是“政治”——或者說“政黨政治”——在這個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最高法院要求佛羅里達州停止人工計票,是擔(dān)心后患無窮。如果佛羅里達要重新計票,全國可能都要重新計票。停止重新計票的要求是布什提出來的,而從人工計票一開始,布什的多數(shù)優(yōu)勢就在減少,到最后只剩下一百多張選票的優(yōu)勢,而計票還遠遠沒有結(jié)束。可以說,是最高法院的命令保住了布什的優(yōu)勢,讓2000年大選的真正贏家成為一個永久的無解之謎。
但問題是,最終投票要求停止人工計票的五名大法官都是由共和黨總統(tǒng)任命,并在處理墮胎、民權(quán)問題上采取與共和黨主流思想一致的立場,他們判布什勝訴,也等于為布什就任之后提名新的大法官人選準備了機會,而大法官的加入可以改變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tài)結(jié)構(gòu)。最高法院的介入,從程序上來看也許是正義的,但大法官的決定本身是帶有政治性的,投票的結(jié)果可以看到黨派政治的作用。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2000年總統(tǒng)大選是通過“非民主”的方式化解了總統(tǒng)選舉的憲政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民主制并不是我們理想中的百分之百的民主制度——即所有人都訴諸每個人完全平等的做決定的權(quán)利。更準確地說,美國民主制中同時含有“民主”和“非民主”的機制和內(nèi)容,甚至有些時候還要加上“反民主”的建制和成分。這種混雜的制度一直伴隨美國憲政的歷史進程。但我們不能說,因為有“非民主”的內(nèi)容,整個制度就不再具有“民主性”,關(guān)鍵在于最核心的內(nèi)容和最根本的機制是不是“民主”的,或者說,這個制度產(chǎn)生的政策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文化是否有利于“民主”。
2000年總統(tǒng)選舉帶來了兩個重要的結(jié)果,一是布什當(dāng)選總統(tǒng)后得到任命兩名大法官的機會:一名是現(xiàn)任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另外一名是阿里托大法官。我在《原則與妥協(xié)》新增章節(jié)中對兩人的立場都有很多討論。如果2000年是戈爾當(dāng)選總統(tǒng),我們可以想象,他會任命兩名自由派大法官,而如果在他之后,奧巴馬能夠接著當(dāng)選,現(xiàn)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比例可能就是自由派占到七票以上,不像現(xiàn)在是四比四,決定票往往掌握在“獨立”的肯尼迪大法官手中。
另外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它幫助推動了美國各地的選舉設(shè)備的現(xiàn)代化。選舉的具體操作是由地方政府組織的。美國公民在選舉日那天是針對很多內(nèi)容投票,包括選舉總統(tǒng)、國會議員、州長、州議員、地方官員等,都必須在同一天投票選舉出來。一張選票上往往列有十幾項內(nèi)容。有的時候還包括重要的立法決定,比如要不要允許本州實施同性婚姻平等,要不要允許州政府征收新稅等。選票投票機器出問題的話,“民主”就無法運作和實現(xiàn)。

澎湃新聞:2000年那次總統(tǒng)大選之后,美國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9·11”事件了,您能具體談?wù)勊鼘γ绹鴳椪纬傻奶魬?zhàn)嗎?
王希:總的來說,“9·11”事件有這么幾個挑戰(zhàn)。
首先是對美國傳統(tǒng)的國土安全概念形成了挑戰(zhàn)。“9·11”事件以后,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本土已經(jīng)不再安全,恐怖襲擊隨時隨地可能發(fā)生。
第二個挑戰(zhàn)是公民權(quán)利的保護和運用受到新的挑戰(zhàn),不再是一種不可侵犯的領(lǐng)域。“9·11”事件和反恐戰(zhàn)爭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加入敵人陣營的公民(被稱之為“敵人公民”enemy citizens)的權(quán)利到底應(yīng)不應(yīng)該繼續(xù)受到聯(lián)邦政府的保護?美國人一向認為,所有美國人都是愛國的,盡管歷史上有過為他國充當(dāng)間諜或出賣情報的,這些被視為叛國行為或叛國罪。但現(xiàn)在是有美國公民——雖然人數(shù)不多——跑到阿富汗、伊拉克去加入塔利班或其他實施恐怖主義的組織。他們被抓回來,關(guān)在關(guān)塔那摩之中。他們的公民權(quán)利要不要得到尊重?他們不是去加入敵國,而聲稱是為信仰而戰(zhàn)。
另一個方面就是政府對公民信息的控制和監(jiān)督。“9·11”事件之后,只要你被鎖定為潛在的恐怖分子,你的郵件隨時可能被查看,在你上班的時候,政府反恐人員可以隨時到你家里搜查,而在以前這一定是需要法院的批準。大學(xué)雇用教授,需要審查你的所有犯罪記錄,哪怕是一些小罪,也得說清楚,以前這是沒有的事。換句話說,為了享受自由,你必須承擔(dān)更多的責(zé)任,付出更多的代價。
還有一個大的沖擊是總統(tǒng)權(quán)力的擴張。比如,小布什總統(tǒng)為了展示美國反恐的決心,要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他要求國會給他支持,并讓國務(wù)卿鮑威爾到聯(lián)合國去作證說伊拉克掌握了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戰(zhàn)爭打響之后,沒有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鮑威爾覺得很丟臉,在全世界面前撒了謊。但這場耗資巨大的反恐戰(zhàn)爭也再度引發(fā)關(guān)于總統(tǒng)權(quán)力的討論,并牽涉到大型軍工企業(yè)與政府國防合同之間經(jīng)濟利益的勾連。比如,制造飛機、導(dǎo)彈的軍工企業(yè)是否進行了大量的游說?反恐是否與這些企業(yè)的經(jīng)濟利益有關(guān)?如果這個問題真的存在,那么情況就非常嚴重。事實上,“9·11”事件之后,國會兩院對布什的支持非常一致。參議院只有大概一兩個人對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一事投反對票,眾議院也是絕大部分人都表示支持,非常一致。這也說明,在遇到國家重大危機的時候,在捍衛(wèi)國家的價值觀的時候,美國人會迅速地團結(jié)起來。

“肯定性行動”的歷史困境
澎湃新聞:您的書里提到“肯定性行動”(Affimative Action)政策和選舉中的種族政治。如您所言,這些指向了美國的根本性問題:種族問題。從發(fā)端于1960年代的“肯定性行動”政策到首位黑人總統(tǒng)奧巴馬當(dāng)選,再到進入2010年以來圍繞肯定性行動的新的判例,種族問題一直和美國憲政如影隨形。作為長期生活、工作在美國的亞裔學(xué)者,能否請您談?wù)劮N族問題對新世紀以來美國憲政秩序的影響?
王希: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那我就從亞裔談起吧。亞裔曾在美國歷史上長期遭受種族歧視,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間很長。1868年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生效之后,出生地公民權(quán)和平等法律保護的原則建立起來,但國會在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進入美國。與此同時,那些已經(jīng)在美國的中國勞工也不能加入美國國籍,在很多州不能擁有土地財產(chǎn)。類似的限制在十九世紀末又擴展到日本人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從亞洲去美國的移民本來就不多,有了這些限制之后,移民美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幾乎為零。這就是亞裔在美國人數(shù)相對較少的主要原因。1943年,因中美在二戰(zhàn)中是盟友關(guān)系,羅斯福政府廢除了《排華法案》。1965年,借助民權(quán)運動的動力,美國實施了移民法改革,廢除了以移民人口的原國籍為基礎(chǔ)的移民配額法,亞裔才開始獲得了較為平等的機會進入美國。
如今五十年過去了,亞裔美國人的數(shù)量急速增長,是增長最快的族裔人群之一。無論是來自日本、印度、韓國、中國大陸還是臺灣地區(qū)的移民,在美國都非常努力,這大概是因為歷史文化的緣故,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在美國算是高的,受教育的程度也很高,所以被認為是“模范少數(shù)族裔”。這在某種意義上是真實的,但也掩蓋了另外一種真實,即很多亞裔是工薪階層,他們的生活狀況很少得到報道。我是八十年代中期去的美國,親眼看見很多偷渡去美國的華人,他們沒有護照,被稱為undocumented aliens(無證外國人),去了之后,只能打黑工,埋頭掙錢,等待大赦把自己洗白,成為合法移民。
成為中產(chǎn)階級的亞裔往往非常反感“肯定性行動”政策,殊不知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是這項政策的受益者。“肯定性行動”政策從二十世紀六十代開始實施,本意是幫助少數(shù)族裔和女性在就業(yè)、就學(xué)和競爭政府商業(yè)合同方面獲得資格平等上的優(yōu)先考慮。為什么有這樣的規(guī)定呢?因為這些群體在歷史上曾因為種族、族裔和性別的原因長期遭受了歧視,沒有積累,沒有基礎(chǔ),形不成群體效應(yīng),無法在政治、經(jīng)濟、商業(y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里與白人進行平等的競爭,始終落在后面。
澎湃新聞:但這項政策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很多人對它不滿。
王希:因為獲得這項政策幫助的往往是那些事先有準備的人,或者說是少數(shù)族裔中的精英分子。而且各地的實施情況不同。加州的亞裔人口多,在入學(xué)方面,可能就不算是少數(shù)族裔。有些亞裔也可能認為自己很優(yōu)秀,不用“肯定性行動”政策,也能進好大學(xué)(事實也的確如此,很多學(xué)校因為亞裔的考試成績太好,而不得不采取更多元的錄取考量標準)。所以,他們在申請大學(xué)時更希望是憑才能(merit),比如憑考試成績或高中的畢業(yè)排名等。但美國不能這樣做,因為美國種族問題的根源源于奴隸制,種族歧視的法律、意識形態(tài)、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都與奴隸制和種族主義有關(guān),或者是由奴隸制衍生出來的。所以,非裔美國人的權(quán)利和地位是美國種族關(guān)系中的核心問題。這就是為什么在美國一談到種族主義,大家就會聯(lián)想到對黑人的歧視。事實上,對亞裔的種族歧視也是存在的,現(xiàn)在所有少數(shù)族裔享有的許多權(quán)利,是非裔美國人通過數(shù)代人艱苦奮斗而爭取來的。亞裔在這方面應(yīng)該感謝非裔美國人的堅強不屈的努力。
這里我要提一下,很多在美國的亞裔,包括來自中國的留學(xué)生,對黑人和美國的歷史不甚了解,對黑人帶有很深的偏見。我不是說非裔美國人是完美的,但如果認為他們只是偷盜搶劫,坐享其成,好吃懶做,享受福利,這是不對的。我在國內(nèi)教書的時候,經(jīng)常遇到的一種情況是,大家不覺得黑人史是美國史,更不覺得亞裔美國人的歷史是美國史。其實這些都是美國史,而且是當(dāng)今最“地道”的美國史。

澎湃新聞:好多人都認為,奧巴馬2008年就任總統(tǒng)標志著美國的種族問題不再是一個問題。
王希:其實不是這樣。前面你用“如影隨形”形容種族問題跟美國憲政的關(guān)系,很恰當(dāng)。前一陣子,幾個城市的警察對黑人公民施行過度暴力,反映了在社會和心理層次上種族偏見仍然深深地根植在美國的社會生活,而且還會長期存在下去。我相信,如果沒有當(dāng)年的黑人民權(quán)運動創(chuàng)造的政治條件,奧巴馬不會當(dāng)選美國總統(tǒng)的。但奧巴馬之所以當(dāng)選,絕不僅僅因為他是黑人——事實上,有些非裔美國人不認為他是真正的黑人——一來是因為他父親的關(guān)系,二來是因為他提倡的價值觀并不是一種專屬黑人的價值觀。這其實很好理解,他是在競選美國總統(tǒng),而不是競選美國黑人的總統(tǒng),就像希拉里·克林頓競選的是美國總統(tǒng),而不是美國女性的總統(tǒng)。
對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shù)族裔的歧視與膚色的關(guān)系不像過去那么大了,更多的是與少數(shù)族裔所處的經(jīng)濟和社會地位有關(guān)。黑人之所以受到歧視,是因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在經(jīng)濟上仍然處于低下水平,他們想要進入主流社會的路仍然十分漫長。進入中產(chǎn)階級社會,需要教育,需要家庭的支持,需要經(jīng)驗、知識和財富的積累,不是說今天你受到“肯定性行動”政策的恩惠,明天你立馬就能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的高級軟件工程師或大學(xué)教授。很多的積累與經(jīng)濟有關(guān)系。“肯定性行動”的理念是非常值得欣賞的,但實際提供的幫助非常有限。我覺得美國各級政府實際上是花了很大的力氣來推動“肯定性行動”政策,比如州立和私立大學(xué)都會給來自非常貧窮的少數(shù)族裔居住區(qū)的學(xué)生獎學(xué)金,幫助他們上大學(xué)。但我們都知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長期的經(jīng)濟不平等造成的惡性循環(huán)不會輕易消除。
澎湃新聞: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肯定性行動”政策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但是美國大學(xué)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花了很多心思的。
王希:“肯定性行動”政策實際上與“色盲的憲法”(colorblind Constitution)的原則是相悖的。這條原則是說,在憲法面前人人平等,不以膚色或性別論地位。但“肯定性行動”政策包含的是另外一個憲法價值,即社會正義的原則。也就是說,美國歷史的種族歧視剝奪了黑人的權(quán)利和機會,造成了延續(xù)至今的問題,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國家有責(zé)任幫助他們站起來。
很多人不愿意把這種努力看成是一種“補償”,包括很多優(yōu)秀的黑人。他們不愿意被人當(dāng)做是沾了“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光才進大學(xué)讀書、或到大學(xué)任教、或進入公司管理階層的。我在書里提到的很多關(guān)于“肯定性行動”的爭論其實都很微妙(subtle)。一所大學(xué)只是象征性地招一兩個黑人學(xué)生來裝點門面是不行的,一定要招足夠多的少數(shù)族裔,讓他們擁有一個“關(guān)鍵體積”,從而可以自然而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不會感到被孤立,并充滿自信地與白人社會融合在一起。美國大學(xué)在這方面是非常用心的。但因為美國無法做到中央政府一紙命令,各地高校貫徹落實。推行這樣的政策,需要國會、總統(tǒng)和最高法院的支持,還需要白人民眾的支持。處于中下階層的白人認為“肯定性行動”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尤其是當(dāng)美國正在經(jīng)歷經(jīng)濟轉(zhuǎn)型,他們也失去了工作,有的也生活在貧困線下,但卻得不到黑人那樣的待遇。他們認為自己被美國社會被拋棄了,反對“逆向種族歧視”,要求回歸到不分膚色的憲政秩序中。
澎湃新聞:說到種族問題,之前亨廷頓曾在《我們是誰》中擔(dān)憂過,隨著美國社會少數(shù)族裔的不斷增多,盎格魯·撒克遜傳統(tǒng)會逐漸衰亡,從而從根本上沖擊瓦解盎-撒精英引以為傲的美國制度。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亨廷頓的擔(dān)憂會成為現(xiàn)實嗎?
王希: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中主要談的是國內(nèi)政治,他擔(dān)心國內(nèi)政治被不同的族裔、種族和宗教等利益肢解和分化。具體來說,就是不同國家的移民到了美國之后,還繼續(xù)保留對母國政府的忠誠、對母國文化的依戀以及對母國文化價值觀的推崇,雖然人生活在美國,但拒絕融入美國文化,等于生活在美國的外國人,而且這些人還會利用美國相對開放的體制,把“非美國”(non-American)的價值觀帶入美國生活之中,甚至組成強大的游說集團,影響美國政治。
舉個例子,美國東部和西部的華人居住區(qū),大辦各種考試復(fù)習(xí)班,一下把美國鄰居弄得很焦慮。美國中小學(xué)生的單詞拼寫比賽,得冠軍的是印度裔孩子。這些都是細小的變化,但給人的啟示很深。
說到價值觀,我覺得,價值觀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還跟生活方式和個人選擇有關(guān)系。亨廷頓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但他有點焦慮過頭了。我的看法是,第一,美國制度本身是變化的,根基可能來自于英國和歐洲,這個國家的“基本原則”(founding principals)——包括對理性政治的追求,對法治的崇尚,對權(quán)力的限制,對個人權(quán)利的尊重等——實際上一直是在變化的。方納教授那本《美國自由的故事》講的就是這樣一個道理,即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的內(nèi)容本身是在變化的,而且處在不同地位、不同階層的人的抗爭極大地豐富了美國價值觀的內(nèi)涵。所以,美國的根本原則是不會改變的,并仍然將是吸引人們前往美國的主流價值觀,而且也是可以共享的。
第二,也許如同人口學(xué)家預(yù)測的,美國所謂有色人種在本世紀中葉會在數(shù)量上超過白人,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加速變成美國人。對第一代移民來說,同化也許比較困難,他們可能欣賞美國的價值觀,但要徹底改變生活方式和心理習(xí)慣是困難的。移民的后代則肯定會是美國人。中國人把出生在美國的年輕美籍華人稱為“香蕉人”,聽上去有些負面,其實這恰恰說明,他們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有的美籍華人或許會有自我認同的危機,有的就完全沒有,尤其是現(xiàn)在,他們完全可能為自己是美國人感到自豪。我前些日子剛在北大上完一門國際學(xué)生暑期課,選課的學(xué)生有一部分是海外出生的華裔,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好奇感,卻很難分享中國人擁有的那種情懷。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他們沒有在中國出生和長大的背景。我想說的是,不要低估了美國文化和美國生活的同化能力。
第三,我想問一個問題,什么是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如果說美國價值觀起源于歐洲,就一定只能是以歐洲或西方為基礎(chǔ)的價值觀,未免有點過于武斷。美國的價值觀為什么不能是美國式的呢?為什么不能與歐洲價值觀有很大區(qū)別,就如同與中國價值觀有很大區(qū)別的呢?構(gòu)建美國價值觀的人也不限于歐洲人或崇尚歐洲的人。在美國的知識構(gòu)建者中,也有相當(dāng)多的非歐洲裔的人在崛起,中東學(xué)者、非洲裔學(xué)者、華裔學(xué)者、印度裔學(xué)者等。美國擁有來自世各地界的智識資源,有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傳統(tǒng)的知識人,可不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完全屬于美國的價值觀,而不必一定死守歐洲傳統(tǒng)呢?所謂美國價值觀,可不可以是美國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價值觀的濃縮和綜合?美國人有沒有勇氣和胸懷來這樣看待美國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實際上是更有力量的。
亨廷頓對美國文化的消化能力和再生能力有些低估。美國的價值觀應(yīng)該是美國歷史的寫照,不同族群的經(jīng)歷對此都有貢獻。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有一些美國歷史學(xué)家提出,不管美國人內(nèi)部有多大多深的階級劃分,所有美國人都分享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觀,包括法治政府、追求正義、個人權(quán)利、保護私有財產(chǎn)、推崇自由民主等。不妨設(shè)想一下,如果今天美國仍然實行種族歧視,從法律上將黑人、華人界定為次等種族,美國對中國人還會有吸引力嗎?亨廷頓憂慮的要害在于,他想堅持的是哪一種美國價值觀?是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僵硬不變的的美國價值觀,還是一種開放的、允許變化的、富有包容性的價值觀?比如,對有些人來說,同性戀者之間的婚姻是無法想象的。在過去那種清教的氛圍下,同性戀還能結(jié)婚?簡直不可思議!所以,這里有兩個問題:什么是美國價值觀,誰來定義美國的價值觀?我想一定不是單由白人社會來定義的,而應(yīng)該是由美國內(nèi)部多族裔來共同定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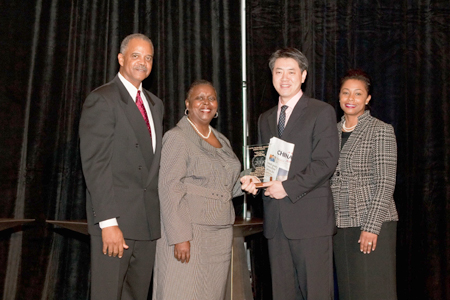
同性婚姻背后的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
澎湃新聞:說到同性戀婚姻,最高法院判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已經(jīng)轟動世界,也引發(fā)了美國國內(nèi)國外、網(wǎng)上網(wǎng)下的巨大爭議。撇開為數(shù)眾多的肯定的意見不看,有人認為,這是聯(lián)邦權(quán)對州權(quán)的侵犯,還有人認為,這是司法部門替代立法部門主導(dǎo)社會改革,因而是對美國憲政的破壞。對此您怎么看?我們應(yīng)該怎么評價這一事件?
王希:的確,今年6月底宣布的奧伯格費爾訴霍杰斯案(Obergefell et al. v. Hodges)是一樁同時涉及“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的案例。毫無疑問,這將是同性婚姻平等權(quán)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判例。就權(quán)利而言,同性婚姻所涉及的是公民的婚姻權(quán)和福利權(quán)問題,也涉及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的問題。這里說的“自由”,不是人身的自由,而是選擇性取向、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就權(quán)力而言,該案涉及的是雙重權(quán)力的劃分:聯(lián)邦立法權(quán)與司法權(quán)的界限,州權(quán)與聯(lián)邦權(quán)的劃分。后者是一個關(guān)于聯(lián)邦制的問題,與聯(lián)邦制本身一樣的古老。
我想指出的是,這個案例實際上是2013年宣布的溫莎訴美國案(在《原則與妥協(xié)》第十三章中討論)判決的繼續(xù)。不同的是,在溫莎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利用第五條憲法修正案和聯(lián)邦制的一條原則(即州有權(quán)管轄本州公民的婚姻),宣布聯(lián)邦的《捍衛(wèi)婚姻法》違憲,變相地承認了同性婚姻在紐約州的合法性。而在奧伯格費爾案中,最高法院內(nèi)同樣的多數(shù)派借助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和聯(lián)邦制的另外一條原則(一州公民的合法權(quán)益必須得到他州的尊重)將同性婚姻權(quán)變成一種各州都必須承認的公民權(quán)利,也就是使這一權(quán)利全國化了。
肯尼迪大法官在判決意見里非常巧妙地構(gòu)建了這個最新的美國公民權(quán)利。他指出,對婚姻方式的選擇是一種表現(xiàn)個人自主的權(quán)利;婚姻權(quán)是一種基本的權(quán)利,受到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保護;婚姻權(quán)為子女和家庭提供保護,并與撫養(yǎng)、生育和教育子女的權(quán)利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一州拒絕承認同性婚姻,等于將同性婚姻伴侶及其家庭、子女排斥在州法律的保護之外。從憲法原則的使用上,肯尼迪的判決應(yīng)該是無懈可擊的。當(dāng)然,對反對者來說,這項判決推翻了傳統(tǒng)的婚姻定義,創(chuàng)造了一種荒唐的“新權(quán)利”。來自保守派大法官的指責(zé)是,多數(shù)派利用最高法院的法壇,用司法審判代替了立法,同時也剝奪了州對公民權(quán)利的保護,是對州權(quán)的侵犯。他們認為,同性婚姻是否應(yīng)該成為合法婚姻,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應(yīng)該由人民通過國會或州議會來決定,而不能由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說了算。
這項決定是不是對美國憲政的破壞?我覺得要看站在哪個立場上。

我可以具體舉幾個相關(guān)的案例,比較一下。
一個是1857年的斯科特案。作為奴隸的斯科特以自己在自由州居住過為理由,要求獲得自由,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代表的多數(shù)派判他永遠不能獲得自由,因為他是非洲人的后裔,永遠不能成為美國公民,即便出生在美國也不行。此案的潛臺詞等于是說,奴隸制可以無限制地蔓延到西部未建州的領(lǐng)土上去。這個判決對林肯這樣的共和黨人來說絕對不能接受,因為西部的領(lǐng)土是要留給自由的白人移民的。所以,林肯提出,關(guān)于斯科特案的判決是一個要自由還是要奴隸制的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應(yīng)該由最高法院來決定,而應(yīng)該由國會來決定。斯科特判決激發(fā)了林肯去競選1860年的總統(tǒng),而內(nèi)戰(zhàn)后制定的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則建立了出生地公民權(quán)原則,推翻了斯科特案的判決。
另外一個例子是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說服所有的大法官,與他站在一起,在判決中推翻了南部各州實行的種族隔離教育制。他引用的原則是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護,但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里面并沒有說公民有接受平等的教育的權(quán)利。沃倫大法官也是以教育與塑造良好公民的關(guān)系為由“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公民權(quán)利。他訴諸的不是先例,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要求。這項判決也是一種“政治”決定,也是跳過了聯(lián)邦和州議會的立法程序,但沃倫避開這些問題,指出種族隔離教育給黑人兒童的心理造成了不可修復(fù)的自卑感,并以此為由,要求州廢除歧視性的種族隔離教育。這項判決幫助開啟了二十世紀后半葉的民權(quán)革命。
肯尼迪大法官在奧伯格費爾案的做法,與沃倫大法官在布朗案的策略幾乎完全一樣,使用的也是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中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目的也是對權(quán)利和利益受到傷害的公民(同性婚姻伴侶)進行補救。他舉的三個案例都是與婚姻權(quán)利和由婚姻產(chǎn)生的福利和權(quán)益有關(guān)。一位起訴者的同性伴侶去世之后,他不能在伴侶的死亡證明上簽字,僅僅因為他們是同性戀者。另外一對伴侶,在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可以享有婚姻權(quán)益,但到了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州,便喪失了所有的婚姻權(quán)益(包括醫(yī)療保險),等于限制了他們的遷徙自由。領(lǐng)養(yǎng)孩子的同性伴侶中只有一人可以作為家長,即便在孩子遇到緊急情況需要家長簽字的時候,另一人也不能代替(雖然他每天都如同家長一樣與孩子生活在一起),而異性夫婦中的任何一人均可平等地行使家長的權(quán)利。肯尼迪利用這些例子來說明,同性戀者因為其對婚姻形式的選擇而受到法律的懲罰,享受不到應(yīng)有的公民權(quán)利和權(quán)益。他將同性婚姻的問題轉(zhuǎn)化成了公民的權(quán)利問題,權(quán)利問題則是憲法問題,是最高法院可以而且必須過問的。
至于司法代替立法的指責(zé),從自由派大法官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并不存在,因為同性婚姻權(quán)已經(jīng)存在,只是同性婚姻者的權(quán)利沒有得到尊重,法院需要對他們進行補救,承認他們的權(quán)利。
澎湃新聞:這個問題在國內(nèi)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王希:這很出乎我的意料,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迅速站隊,但好像反對者居多。不過,我認為,關(guān)注就是一個進步,以前我們連這個問題都忌諱提到。必須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一場革命,《芝加哥論壇報》用過一個非常漂亮的標題,稱其為一場“無聲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馬薩諸塞州是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州,時間是2004年。十年之后,也就是2014年,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達到三十多個。到2015年,通過奧伯格費爾案,同性婚姻就在全國合法化了。而美國黑人在爭取民權(quán)平等方面經(jīng)過了整整一百年,婦女爭取選舉權(quán)經(jīng)過了將近八十年的奮斗。2004年支持同性戀的人數(shù)是極少數(shù),百分之一二十而已,現(xiàn)在已經(jīng)百分之六十了。我也曾與美國同事聊過此事,得到的印象是,大家認為這是一種個人選擇的權(quán)利問題。在我看來,這是美國社會越來越包容的一種體現(xiàn)。
追求社會福利與保守主義憲政
澎湃新聞:同婚平權(quán)是您在書中討論的三種爭議較大的權(quán)利訴求之一。此外還有福利權(quán)和醫(yī)療健康保障權(quán)。談及福利權(quán),往往帶有強烈的左翼色彩,而美國的憲政秩序某種程度上遵循的就是強大的保守主義邏輯,帶有鮮明的右翼色彩,那么,保守主義的憲政如何與要求福利的權(quán)利訴求相兼容呢?
王希:就像我前面說的,美國進行福利社會的建設(shè),是不得已而為之。上世紀三十年代,面臨巨大的危機,羅斯福總統(tǒng)推行新政,既有經(jīng)濟方面的考慮,也有社會正義方面的考慮。經(jīng)濟方面的考慮是,為了刺激消費,必須給予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讓他們老有所依。社會正義方面的考慮是,在遭遇重大的經(jīng)濟危機時,政府必須承擔(dān)責(zé)任,幫助人民從失業(yè)和貧窮的狀態(tài)中擺脫出來。
新政時期,羅斯福受到很多攻擊。他的改革力度太大,來自左右的壓力也很大,最高法院與他的關(guān)系也非常緊張,曾經(jīng)宣布他的重要法律違憲。羅斯福在1936年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后,利用威脅的手段,強迫最高法院改變了做法,新政才得以繼續(xù)下去。正因如此,人們指責(zé)他破壞了美國的憲政秩序。前不久有一個美國學(xué)者在演講時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說,新政時期的反羅斯福主義就是后來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起源。里根時代的保守主義是對新政自由主義的一次清算。里根認為福利社會將敗壞美國社會的道德觀,懶惰的人政府要養(yǎng)起來,勤勞的人反而要交稅,這不公平。在歐洲人的眼中,美國沒有真正的福利社會。但我個人認為還是有的,只不過與歐洲的福利社會不同,處在比較初級的層次而已。
至于美國憲政本身,很難講到底是激進主義的還是保守主義的,很多對美國憲政懷著虔誠信仰的保守主義政治家,具體操作的時候,也會比較靈活。比如,小布什是里根之后又一個奉行保守主義的總統(tǒng),但是他也沒有全盤否定美國的福利體制,只是提出其運作的方式要變化,不要讓政府過多插手和介入。當(dāng)然,這樣就涉及一個問題:政府對福利體制的介入的邊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政府完全不介入,肯定不行,如果完全由政府來推進,負擔(dān)又無法承受。
比如,奧巴馬的醫(yī)改方案強制沒有醫(yī)療保險的人都要去買保險,共和黨人認為這是一種政府的強制行為。事實上,奧巴馬推出的醫(yī)改法已經(jīng)與他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樣了,在與保守主義的談判中棱角被削掉不少。他當(dāng)然希望能像羅斯福和約翰遜一樣,在美國福利社會構(gòu)建的歷史上留下英名。羅斯福有《社會保障法》,約翰遜有醫(yī)療保障法和醫(yī)療補助法,這些都是美國福利政策的經(jīng)典內(nèi)容,也一直為美國人所銘記。奧巴馬想推行全民醫(yī)保,但他的醫(yī)改法與理想差距太大。

澎湃新聞:正好您提到醫(yī)療問題,咱們接著往下聊。您曾經(jīng)說過,醫(yī)療健康保障權(quán)這類新的權(quán)利訴求超越了民主、共和兩黨的意識形態(tài),也跨越了性別和地域的分野。現(xiàn)實當(dāng)中,民主、共和兩黨大有為了全民醫(yī)保而鬧得水火不容之勢。甚至還有人畫漫畫說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要把美國轉(zhuǎn)變?yōu)樯鐣髁x國家。我們對此應(yīng)該作何理解呢?
王希:其實,民主、共和兩黨現(xiàn)在爭的倒不是應(yīng)不應(yīng)該有醫(yī)療健康保險的問題,而是醫(yī)保應(yīng)該由誰來主持、監(jiān)管和運作的問題,是交給市場,還是由政府來主持。美國人很講究有沒有保險,因為醫(yī)療費用實在是高得離譜。民主黨人認為,所有人都應(yīng)該有起碼的醫(yī)保,沒有醫(yī)療保險的人,要想辦法讓他買醫(yī)療保險,甚至采用強制的手段。共和黨也主張這些人應(yīng)該買醫(yī)療保險,但反對使用強制手段。共和黨人認為奧巴馬的醫(yī)改立法里面有很多不合理之處。比如,其中有一條規(guī)定是,擁有二十五個雇員以上的公司,老板必須給員工買醫(yī)療保險,他們認為這樣的規(guī)定實際上強迫雇主進行財政轉(zhuǎn)移支付,將導(dǎo)致公司輕易不敢雇用員工,從而影響就業(yè)。
至于說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這只能理解為是反對黨的政治說辭。跟其他的歐洲國家比,奧巴馬推行的政策與真正的“左”離得很遠。如果非要說他搞的是社會主義,那只能是最不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美國的鄰居加拿大的醫(yī)療體制倒是有點社會主義的味道,政府包辦,全民覆蓋。但美國不是加拿大。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