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別再自責了,為社會突發新聞感到憂慮不是你的過錯
本周 Editor's Pick 當班編輯殷佳琦,
她推薦的書是學者弗朗西斯·奧戈爾曼的
作品《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
單讀實習生殷佳琦的推薦語:
最近,我們的情緒不斷被社會上的突發新聞牽動著,恐懼、不安、焦慮、擔憂如洪水般涌來。盡管這些負面情緒的表征因人而異,但我們對此都有相似的糾結:既渴望被理解、被傾聽、被治愈,又不愿將自己的脆弱輕易示人。于是,我們一邊在社交媒體上匿名吐槽生活中的各種煩心事,一邊把正念冥想或心理療愈類的書籍加進購物車,以備不時之需。我們在另一個時空里“求醫問藥”,默默宣泄著自己的情緒,哪怕彼此難有交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憂慮成為了你我共有的秘密。
心理學上通常認為,憂慮源于不合理的自我信念,所以如果選擇積極的認知行為模式,就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緒和感受。但事實上,接受一套外在強加的理論并非易事,這樣帶來的挫敗感只會讓人們陷入更深的憂慮。如此看來,憂慮作為一種難以測量的情緒狀態,還有很多與之相關的話題值得追問。比如,從文化意義上看,什么樣的情緒可以稱為憂慮?它于何時何地出現?什么阻礙了它被公開講述和談論?難道憂慮的出現只是個體差異帶來的結果嗎?針對這些問題,愛丁堡大學英語文學教授弗朗西斯·奧戈爾曼從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哲學和美學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01 尋找同病相憐的創作者,追溯憂慮的存在條件
盡管作者通過文學和歷史討論“憂慮文化”,但這并不是一本晦澀、枯燥的學術書籍。作為飽嘗憂慮之苦的“資深患者”,作者在真誠坦率地剖析自身經歷的基礎上,從小說、詩歌、繪畫、音樂等作品中,探索憂慮和憂慮著的創作者存在的蛛絲馬跡,分析憂慮得以存在的條件。
作者選用莎翁戲劇中的臺詞作為章節的標題,減輕了話題本身的沉重感。比如在第一章中,他借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場“可是哎,你近來這樣多病”引入話題,表現出憂慮者與哈姆雷特一樣,有著不被外人理解的苦悶。第三章 “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同樣來自莎翁的作品,作者由此感慨憂慮的產生有著荒誕的歷史原因。

電影版《哈姆雷特》,1996 年
02 質疑“啟蒙理性敘事”,從自我責備的泥潭中探出頭
我們似乎理所當然地相信:人類可以通過理性的思考和判斷做出正確選擇,也可以經由自己的意愿,過上幸福生活。但實際上,美好的愿景也往往是幻象,我們時常因自己的失誤而陷入“思考—憂慮—自我責備”的惡性循環中。與韓炳哲等當代哲學家一樣,奧戈爾曼在書中質疑了這套“啟蒙理性敘事”的合理性,從情感文化史的角度延續著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他幫我們從自我責備的泥潭中探出頭,冷靜地想想,誰該為這一當代集體情緒負責?
在他看來,我們無形中被這種強大的文化敘事規訓了,啟蒙理性不但沒有把我們引向應有的美好未來,相反,它讓我們備受選擇困難之苦。更糟的是,個體也完全承擔著因選擇錯誤而帶來的道德負罪感。換句話說,憂慮是人類文化轉變之際的產物,當我們把獨立思考的權利從上帝手中奪回時,在歡呼著人成長為 “完整的人”之際,憂慮、孤獨、抑郁、存在主義危機等精神困境也隨之而來。而這種自我道德譴責如果無止境地發展,則會讓人們忽視了對社會結構性問題的關注和反思。
03 在“歷史規律”中,發現抵抗憂慮的希望
在正念的理論中,有效緩解憂慮的方式之一就是與它保持距離——適當離開自己才能觀察自己。讀完這本書,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我們不僅需要與“憂慮”保持物理空間的距離,還要與它維持時間上的距離感。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作者要將憂慮置入歷史脈絡中考察。憂慮不是一個有明確界定的實體,而是一種流動開放的狀態,是人類普遍而永恒的困境。因而,我們能被不同際遇下人們的煩悶、不安、憂慮擊中,在文學作品中找到了彼此。也正是在“歷史規律”中,我們發現了抵抗憂慮的希望。
很遺憾,對于抵抗憂慮,這本書似乎沒有明確的實操性和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作者提示我們,如果憂慮源于“思慮過多”,那我們也能以自我思考的方式識別困境、調整內在感受。這與他人代勞是截然不同的,因為經由此,我們能把憂慮送回它的來處。
當下次感到憂慮時,請為充滿愧疚的自己松一口氣,也許不是我們選擇了憂慮,而是我們“別無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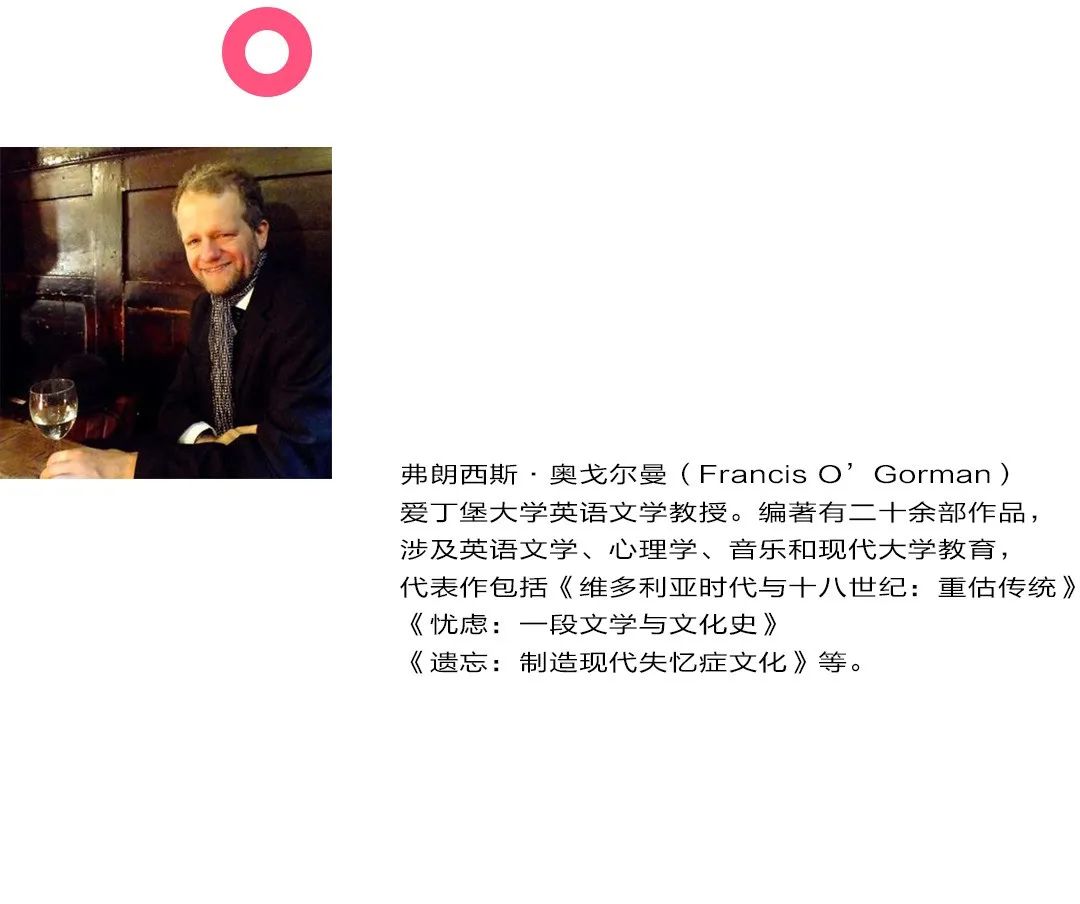
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場
撰文:弗朗西斯·奧戈爾曼
人們相信在憂慮這一“幕”結束之后,理性會隨之上演。從這個角度講,憂慮也許和眾多理性活動的形式相似—— 瞻前顧后,試圖追上早些時候發生的感覺、信念和直覺。的確,人在經歷憂慮時,心中的信念與推理之間的沖突可能更長久也更棘手。撇開其他不說,將憂慮捆綁于信念之上,這種矛盾可能是宗教信仰被取代的后果之一。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ren Kierkegaard,1813—1855)認為宗教生活的最高境界本就是一種精神持續焦慮的狀態,虔誠的信徒始終在內心欲望和所信仰的絕對命令間徘徊。這種分裂是引發焦慮的最深層原因的一部分,是自我欲望和對更高的善的認知之間的張力。
更準確地說,引發憂慮的深層原因之一,并非個人欲望與對更高的善的感知之間的沖突,而在于我們能理性分析自己的欲望。當我開始思考我們的現代信念,即我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有一些權利來滿足或至少考慮個人欲望時, 我便發現,似乎有更多麻煩事出現了。當代世界告訴我們要為自己做選擇,這是當代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其一大成就,但它不僅僅只有成就。本章講的是我們如何繼承了一個理性優先,且將其視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決定性特征的世界(盡管上一章對這一看法的謬誤之處已有所提及)。問題在于,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加上了一系列有關“自由” 思考與選擇的假設,而這也勢必會催生比以往更多的憂慮。
作為一種思維活動,憂慮只能存在于一個有選擇可言的世界。它甚至可能因為人們覺得自己有能力乃至有權利為自己做出選擇而更加頻發。憂慮是我們堅信自己掌握自主選擇權的衍生品,它的出現不可避免。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其內容豐富的《走出憂郁》(The Noonday Demon: An Anatomy of Depression,2001)一書中說:“憂郁是愛的缺陷。”而另一方面,憂慮是理性的缺陷。它是理性不利的一面,是理性的副作用。粗略而言,憂慮誕生于人類文化轉變之際:人們從無條件地信仰無所不能的力量轉為開始對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進行思考或推理。盡管此前我說了很多關于信仰和憂慮的話題,但毋庸置疑, 人類從信仰超自然存在的絕對掌控,到相信自身思維的力量及其思考事物的能力,憂慮確實是這一觀念轉變過程中意外的、不受歡迎的產物,是從神到人的轉向中誕生的不幸的孩子。在某種程度上,它產生于人類文化之巨大轉變:從心靈轉向思維,從對抽象命運的信仰轉向人類自我選擇的世界,從信仰時代走向啟蒙時代,從理想走入現實,從天上墜入凡間。

只有當人們相信一切并非由某個神秘莫測的神明預先決定,憂慮才成為可能;當奧林匹斯只不過是一座山,人類要自食其力,憂慮才成為可能。當人們相信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能夠通過理性評估來做出抉擇,而這一評估試圖將一切納入考量,憂慮就瘋狂滋長;當我們認為對于未來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我們要使用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依靠神圣權威來辨識它,憂慮就瘋狂滋長。當理性評估試圖將一切納入考量,以盡量調節我們作為人類的感受, 開始解決如何在情感上獲得安全感、平靜和快樂的問題時, 憂慮更是站穩了腳跟。這種“把一切納入考量”的計算, 幾乎總是要求“理性”不僅考慮邏輯論證,還要考慮非理性的、超出理性的因素。我們的心靈被攤派了太多工作。所有這些試圖平衡各種利益以做出最佳選擇的嘗試,造成了無數個無眠之夜。如果從 20 世紀初憂慮才開始在語言中出現的角度來看,它有一段“簡史”或“地方史”,但憂慮本身的歷史其實是源遠流長的。
人類思維史,以及塑造了今日人類的智識變遷歷程, 其最重要的特點只能通過象征史,通過與人類起源有關的神話才能探知一二。憂慮誕生于什么時刻,這是一個極具誘惑性的問題:憂慮在彼時、彼處發生。我當然也很想知道潘多拉究竟在何時何地打開了她那滿盛煩惱的盒子。我還很想知道,那個惱人的盒子的底部還有什么,究竟是“希望”還是更令人憂慮的“預期”?當然,“預期”可以是令人快樂的,但也可以令人心生恐懼。
事情的“起源”或“轉折”這類概念,對于歷史的敘述方式來說很有吸引力。英國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就很明白起源的吸引力,明白能夠提出“這樣的態度由此產生”或“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發源于此” 是多么迷人。她非常著迷于研究允許或限制人類選擇的各種力量間的相互作用,也曾睿智地說:“若不虛構一個起源, 人們將寸步難行。”此外,若沒有將起源與當下聯系起來的敘事,人們同樣寸步難行。尋找起點的誘惑乃是創造起源神話的誘惑,也是塑造只提供要素,而非經驗真理之象征的誘惑。將某些節點看作起源的做法之所以誘人,是因為我們假定歷史總是依循一種有序的、連續的、發展的或進步的方式運作。虛構起源不僅涉及一個起點的神話,更關系到整個故事性歷史的神話:歷史中容不下任何隨機的、不一致的、破碎的、意外的、無法解釋的事物。憂慮及其歷史也不例外,況且關于“思想的誕生”之神話式的想象本就無窮。

古希臘人挾其精妙的哲學推理,盡管在中世紀被長久遺忘,現在仍可稱為當代“思考之心靈”的設計師。作為西方哲學之父,希臘人很容易被想象為思想斗士,反對無知,反對僅僅相信全能神明統治世界而盲目摸索。這是思想的起源嗎?英國首相兼荷馬學者 W. E. 格拉德斯通(W.E. Gladstone,1809—1898)不僅宣稱荷馬史詩是“人類智識生活的開端”,還認為歐洲中世紀的終結和文藝復興的興起是離我們更近,也更為人所知的“思想的(重新)誕生”時刻,常遭迫害的理性在此前已透出微光。“文藝復興人文主義”(Renaissance Humanism)、對亞里士多德的重新發現,以及文藝復興藝術家對世俗世界的關切——用透視法強調人類而非上帝的視角,都使這個觀點更加清晰。18 世紀法國的哲學家、百科全書派,以及歐洲整個啟蒙運動,組成了所謂現代世界誕生的一些標志,建立了反對“非理性”信仰的思維模式,反對相信不要求亦不鼓勵思考的冥冥之力。相應地,“科學方法”在 19 世紀進一步得到鞏固,人們拋棄了信仰高于思考的模式,代之以新的世俗科學, 其中具代表性的是 1859 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發表,以及定義了那個時代人類智識生活的實證主義研究。啟蒙運動似乎已全竟其功。
反駁以上每條論述都有充足理由。首先,我們有理由反對這種對思想轉變時刻的指認,因為顯然,歷史并非如此發展。若這還不夠的話,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道德評判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但這些轉變的象征性時刻確實有著強烈的意義,哪怕它們不是“真的”或證實為真,也仍然很重要。這就好比我們明知道照片里不是自己真實的樣子, 但仍然無法離開它。換作喬治·艾略特,她無疑會說,我們無法丟棄這些虛構之物,因為無法放棄它們的象征意義。有些東西太重要了,以至于難以校正。這些神話式的歷史敘述早已根植于我們作為人類,尤其是現代人的意識中, 僅僅質疑其真實性是沒用的。從無須思索的信仰世界到獨立思考的世界的轉變,確實是當代人類歷史的一大解釋性神話,即使我們無法將其精準描繪,或在任何簡單意義上稱其為正確。從信仰到理性的轉向,是關于我們“走向自我” 的偉大西方故事,是關于個體性誕生的宏偉神話,是具有撫慰功能的敘事:關于自我的重要性以及正當的、完整的為自己著想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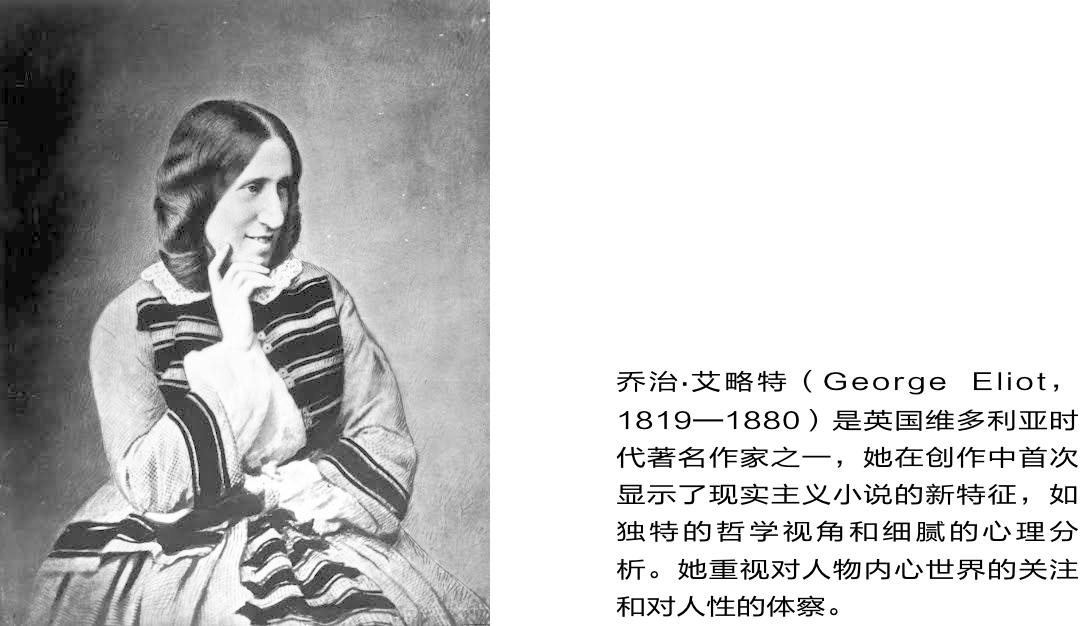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根據思維能力的不同,把真實存在者與其他人劃分開來,留下了現代史上最著名的(在我看來也是最傲慢的)哲學命題之一——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他試圖區分人類和動物,還質疑了“不思考”的宗教信徒。他也不無象征意味地解釋了一些術語,而正是通過它們,憂慮在世俗的、思考的心靈中滋生。在評估各個選項時承認思考至上,相當于在我們的心智中戳出一個針眼,細小、灰暗的憂慮就這樣滑了進來,因為獨立思考必然會有出錯的可能。顯而易見,笛卡爾借助思維的推理過程否認了信仰。他的名言抓住了——或是重新抓住了——憂慮得以存在的條件。也許,他本應該說:“我憂故我在。”不過我認為兩者說到底是大同小異的。
人逐漸從“盲目”信仰走向理性,相信可以通過思考為自己選擇,以及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做事,這一虛構卻又必要的觀念,甚至能影響我們敘述自己歷史的方式。擁有獨立思想和自由思考的特權是一種如此強大的文化敘事, 很容易變成字面意義的自傳。
現在,如要我回想自己第一次真正獨立而自由地思考某事的時刻,我腦中會出現一個清晰的片段。(當然,我說服自己相信這份記憶分毫不差。) 我那時十七歲。至于那之前,我到底是如何全然不用腦子就通過會考的,暫且不管。只記得在那之前自己沒真正思考過,別人說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別人給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天我正穿過伍爾弗漢普頓的一條馬路,附近街道臟亂不堪,只有幾家勉強維持的破舊小店,而我正在為一篇高中課文犯愁,那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夠諷刺的是,這部戲劇無關理性行為。當時我正在“思考”老師可能會讓我們對某個特定問題做出怎樣的解釋。突然間,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本身就有誤導性。我想了想,試圖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它,在腦海里搜集了一些與老師問題背后的假設并不一致的臺詞。接著我突然意識到我在做些什么,在既無警示牌也無充足準備的情況下,我就站在了懸崖邊,站在了看不見的渾濁水池上方。我處在質疑被告知的事情的邊緣:若繼續下去,我可能會陷入多么可怕的混亂!我產生了模糊但強烈的恐懼,意識到自己能夠獨立思考會導致個人的、智識的,無疑還有道德上的混亂狀態。或許獨立思考的能力一直就是老師希望我擁有的,但在那一刻,這樣的自我意識就好像一種可怕的反叛行為,一種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的企圖,所以我不得不到此為止,到若干年后才重新開啟這樣的能力。
我認為這個故事是真實的。在我為了寫這本書而想到它之前,我從未質疑過它的真實性。但現在我想知道,我這樣說是不是因為被宏大的文化敘事說服,它已經為我灌輸了“作為人重要的是什么”的理念。那我是不是也成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證明擺脫那種關于理性起源的敘事—— 講述不僅是作為物種,而且是作為個體,在成長中發生的激動人心、嶄新又珍貴的事件——有多么困難?我為獨立理性思考能力的萌生而歡呼雀躍,是否僅僅因為我自己內化了在上文中探討的文化敘事?或許我也只是一個心甘情愿的同謀,這個故事看似真實、自然,但實際上只是這個時代為我所寫的故事。我的故事微縮模仿了智識生活中最重要的敘述:獨立思想的萌生,“自由”的人的概念,人的價值和尊嚴就在于其意識到可以“為自己”做決定。但對我來說,復述自認為的自己的歷史,顯然就跟意識到自己能獨立思考一樣令人不安。

幻想一個不僅沒有憂慮,甚至連它出現的可能性都不存在的古代社會并不難。這可以是一個堅信命運的文化,一切事物的結果都不受凡人掌控,因此人們免于恐懼。在古希臘人眼中,主宰人類命運的手是確鑿存在的。那就是命運三女神:克洛托為每個人紡織生命之線,拉切西斯負責丈量其長度,而阿特洛波斯則掌管人的未來,因為她決定何時切斷生命之線。斷線之際,就意味著一個人生命的終結。對于我們憂慮者來說,那無疑是不復存在的好時光。那時的人們哪怕不能從憂慮中解脫出來,至少也沒有任何理由去憂慮。既然眾神掌控著蕓蕓眾生,我們何須焦躁?若沒有能力改變神靈定下(或即將定下)的宿命,我們緣何焦慮不安?因為別無選擇,我們最好享受當下,直至命運女神前來切斷生命之線。
但我覺得,我們無法證明這樣一個社會在何時何地真實存在過。當我反復推敲古代文學的遺存,以及近年來出現的可見的證據時,不禁一次次為同一顯見的事實所沖擊:一旦一個人能夠思考——用自己的頭腦來處理信息、考慮、裁決和思索,即便是在最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下——困難就出現了。憂慮正是從人們的反省、評估、權衡、懷疑能力之中誕生的。令人傷感的是,做一個現代的憂慮者(從囊括所有史料的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講),其實不過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老舊標志。Je m’inquiète donc je suis:我憂故我在。
(上文摘自《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由新民說 | 廣西師大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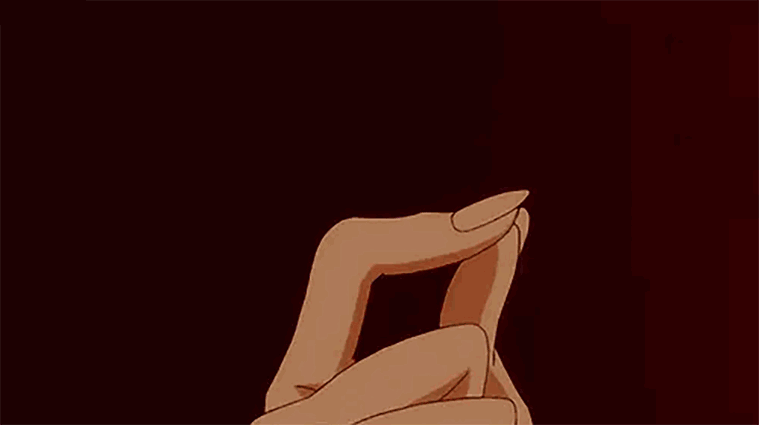
原標題:《別再自責了,感到憂慮不是你的過錯 | Editor's Pick》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