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學星期五︱生物學沒有種族概念,為何人類難以克服種族成見

最近兩周,兩則毫無關聯的事件一同燃起了網絡上關于種族的討論。第一則是一位世界冠軍的宣言。在喀山游泳世錦賽中奪冠的“小鮮肉”寧澤濤,在賽后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是黃種人,我是中國人,今天我做到了!”第二則是來自涼山彝族女孩的“世界上最悲傷的作文”。這篇寫下了父母相繼死去的短文迅速引發了關于大涼山為何長期貧困的討論。而這討論,不幸地,又快速轉向了種族是否部分導致了大涼山的長期貧困。
在生物學家那里,“種族”概念不存在
一如既往,本文并不著眼于社會評論。從科學的角度而言,“種族”是一個有趣的概念。生物學家們,眾口一詞,沒有例外:種族不存在——要知道,這個結論可是在天天吵架、你挑我刺、我捅你刀的學界,但在日常生活中,“種族”概念卻無處不在。我們不但時時按照白人、黑人、黃種人或其他種族來劃分人群,而且我們相信,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內在特質。他們有的勤勞,有的懶惰。有的善于創造,有的墨守成規。“種族”這個概念幾乎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僅僅是因為生物學普及不夠,導致日常的概念出現了偏差嗎?說來,倒還真沒有這么簡單。下面就讓我們詳細說說為什么。
先說生物學家。生物學家們的態度統一而又堅決。大家都認為“種族”這個概念背后所蘊藏的關于生物、遺傳的假設完全站不住腳,“種族”這個概念也不指向任何自然的分類。一本經典的生物人類學教科書指出,常見的“種族”的概念包含以下三點:
1.整個人類物種可以被自然地劃分到幾個數量有限、互相區分(并且有明確的外貌,特別是膚色標記)的種族中去,比如說白人、黑人、黃種人等等。
2.不同種族之間的基因差異巨大,并且形成了相應的種族特質。比如說,我們認為出于基因的差異,有的種族特別擅長數學,而有的種族特別擅長運動。
3.種族身份和種族的特質差異是通過遺傳繼承的。比如說我們認為黃種人和黃種人的后代也是黃種人,并且黃種人后代繼承了黃種人先祖的種族特質。
這三條在當今的科學研究之下,早就不值一駁。限于篇幅,讓我們簡單看一下第二條。大量生物學家和生物人類學家把大樣本的受訪人群按照種族、語言或者國籍等各色各樣的種群維度進行分類,結果發現,種群之內的基因多樣性,比種群之間的多樣性,要大得多得多。平均而言,種群之內的基因多樣性,占到整個人類種族的基因多樣性的85%。
這個結論可以用來自同一本教科書的假想小故事來解釋:假想有一天外星人入侵。他們準備把所有人類從地球上抹除,只留下一個種群,以備送進外星動物園以供觀賞。無論他們怎么挑選——黑人、美國人、說俄羅斯語的人——隨便挑,他們都能保留下平均而言整個人類種族約85%的基因多樣性。
而另外一種研究顯示,在同一個種族里隨機挑選出兩人,也從不同的兩個種族里隨機挑選出兩人,前一組內部的基因相似程度高于后一組內部的基因相似程度的概率僅僅比50%(也就是翻硬幣的概率)高一點或者幾乎沒有差別。這也就是說,按照種族劃分并不是一種區分或者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基因差異的良好劃分方法。反過來說,告訴你一個人的種族,我們也不能得到很多有用的基因信息。
因為上述三點沒有一點成立,生物學家們一般就很直接地表示:種族并不存在。既然種族在生物層面上并不存在,為什么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無處不見“種族”這個大標簽呢?僅僅是缺乏足夠的生物教育和相關知識普及嗎?倒還真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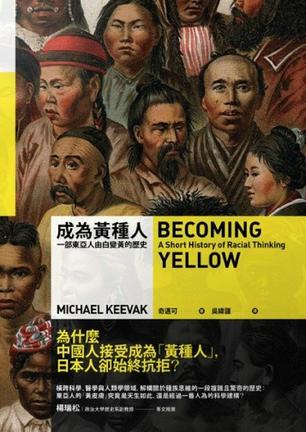
沒有種族識別基因的人類,為什么會演化出專有的種族識別機制?
很多研究顯示,人類會高度關注、迅速識別種族信息。大量研究顯示,我們看到一個人的時候,往往最先也是最快注意到他們的性別、年齡和種族。我們識別之快,開始識別的年歲之早,都讓人懷疑我們是不是進化出了相應的、專有的識別機制。我們擁有專有的、識別性別和年齡的機制并不令人意外——迅速注意到對方的性別和年齡對于生存和繁衍可以有很多好處。
那么,種族呢?首先,不少研究者認為人類不可能演化形成專有的種族識別機制。為什么?因為我們萬年前的遠祖主要依靠步行。終其一生,他們的日常生活范圍半徑平均不超過65公里。65公里才多遠啊!這也就是說,我們的遠祖們絕不可能經常和外貌,特別是膚色完全不同的其他人類接觸。既然,我們遠祖都不和,按照我們現代定義,“其他種族”的人類接觸,那么我們很難想象為什么人類會演化出專有的種族識別機制。
按照目下流行的假說,很有可能是我們其他的認知機制,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被應用到了種族識別上。具體的假說有好多種,讓我挑兩種頗為流行的。
我個人最喜歡的解釋,是來自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Tooby和Cosmides教授夫婦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們提出的假說。他們認為,我們日常迅速識別種族的機制,實際上來自于我們的識別合作的機制。按照Tooby和Cosmides教授夫婦的理論,在進化過程中,我們獲得了專有的識別敵人和朋友的機制——畢竟,知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對于生存和繁衍無比重要。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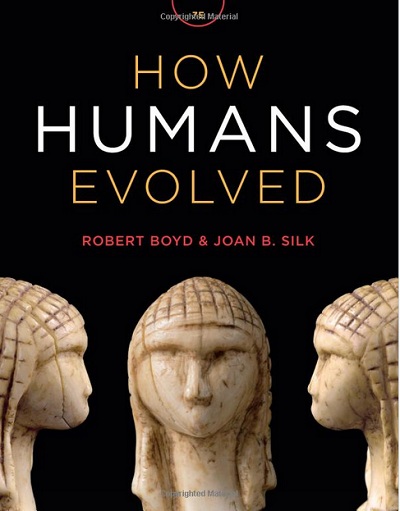
這種理論也可以解釋為何西方人逐漸把東亞人種的分類由和他們自己一致的“白人”種族逐漸獨立到了一個“黃種人”種族,也能夠解釋為何愛爾蘭人和猶太人逐步被接納入了“白人”種族——因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敵友,或者更加細微一點,種群和種群之間的政治文化關系也一同變化。一樣的理論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當今社會,種族幾乎是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因為歷史、經濟、社會等種種原因(譬如說殖民和奴役的歷史),膚色的確常常成為區分敵我的標志。
第二種解釋來自于Gil-White教授。這種解釋,可以說是“丑小鴨”假說。我們都知道丑小鴨的故事:一只小鴨因為丑,受盡了欺負。它等到長大,才發現自己其實根本不是一只鴨子,而是一只美麗的天鵝。
丑小鴨的故事可以有很多種解讀。一種和生物學相關的解讀是:我們的大腦可能有一種進化形成的專有機制。我們把動物劃分入不同的物種,并且認為物種有其不變的天性——就如丑小鴨即使是被鴨媽媽撫養長大,即使是受盡了委屈折辱,最后還是會變成一只美麗的天鵝。按照這種假說,獲得專有的機制幫助我們劃分物種,并且相信他們可能有穩定的、依托遺傳繼承的天性,很有可能獲得進化優勢。
而我們識別種族的原因,就是因為大腦“誤把”種族當成了物種。當代的社會科學認為,即使在相同的環境里,人類也會自發形成多個有明顯差異的社會規范體系——也就是區域文化。和不同區域文化的成員交流往往成本高昂:鄉下來的劉姥姥在賈府門前不知所措,喊仆人們叫“太爺”,結果還不被“太爺”們放在眼里。因此,成員往往會極其傾向于在區域文化內部結合。
內部結合的下一代又因為從小耳濡目染,往往成為了區域文化最好的繼承者。這種現象很容易產生一種誤會,即我們大腦誤以為是遺傳導致我們繼承了區域文化和長期內部通婚所給予的外貌、行為和特質。而正巧就是這種“誤會”讓我們的大腦激活了物種識別機制,把不同的種族當作不同的物種處理。
上面的機制,或多或少解釋了我們為何會迅速地識別種族。第一種的實驗支持多一些,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理論,而第二種有太多的理論步驟可供推敲,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理論猜測。
種族定見是如何被循環強化的?
說到這里,很多人要說:識別種族是一回事,日常的種族定見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日常里我們并不僅僅能夠分辨出種族,還能夠形成非常豐富的,關于種族特質的理論。不但我們能夠形成相關的理論,還常常覺得我們的理論不斷在生活中得到確證。這是為什么?
實際上,種族定見的形成既受到我們認知偏誤的影響,也受到信息傳播的社會特性的影響。從認知偏誤的影響來說,僅僅舉幾個例子,我們會無意識地更關注支持我們已有定見的信息,更忽略或者更難以想起反對我們已有定見的信息。
我們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會無意識地修改我們的記憶以支持我們的定見。從信息的社會傳播而言,我們會在傳播過程中,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把復雜的信息變得更加有結構性、更加簡化(甚至過度簡化)、更加“有意思”或者看起來“合乎常識”。這兩條途徑交互影響,不但使得我們形成關于種族的定見,并且讓我們覺得定見時常得到確證。
為了檢驗這一點,一批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實驗。他們設計了一批想象中的外星人。這些外星人可能擁有藍色、綠色和紅色的膚色。他們可能擁有方形、三角形和圓形的頭部形狀。他們可能呈現出平行移動、跳躍移動和向右上角移動的運動軌跡。上述總計27種外貌各自不同外星人分別被隨機賦予了隱秘的、好奇的、整潔的、傲慢的、嚴肅的或者易興奮的這六種性格特點中的一種。
研究者們從這27種外星人中隨機選擇出13種,并把他們的外貌和性格特點都展現給第一批受試者觀看。觀看過之后,研究者們給受試者展示全部27種外星人的外貌,并且要求受試者們回憶并且描述這些外星人相應的性格特點。之后,研究者整合了外星人的外貌和第一批受試者們提供的性格特點描述,并利用這些信息,對第二批受試者進行完全一模一樣的實驗。第二批受試者們提供的描述又被展示給了第三批受試者,如此循環,一直到第七批受試者。
結果,研究發現,伴隨著信息被傳播下去,受試者們描述的外星人性格特點越來越少。僅僅傳播到第三批受試者的時候,被用以描述外星人的性格特點的平均數量就已經幾乎腰斬。而到了第七批的時候,受試者們已經形成了非常穩定、簡化的種族定見。比如說,在一次實驗里,藍色的外星人被系統地描述為“通情達理又頗有成就”,而綠色的外星人被描述為“粗俗不堪”。
上述的成因,僅僅是故事的一面而已。伴隨著我們的定見,我們還會建立起社會機制以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強化我們的種族定見。比如說,如果我們相信某個種族善于運動,或許對于該種族的具體成員,我們從小就有意無意地鼓勵他們多多運動:“不讀書也不要緊的啦!”政府或者社會機構也可能會把資源更多地向運動傾斜。這種有意無意的合力之下,某個種族的成員或許的確在運動方面表現上佳。這又坐實了之前的種族定見,并給予我們更多理由繼續鼓勵支持和傾斜社會資源,因此不斷循環強化我們的種族定見。
雖然從生物學上說,種族并不存在,但是使用“種族”這個概念和種族定見的形成,有著豐富的認知土壤。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誤會”,我們的大腦能夠迅速地把整個人類物種劃分到不同的種族中去。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認知偏誤和社會特性,我們會不斷形成和強化各色種族定見。要糾正這些定見,我們不但要依賴理性的思考和探討,也需要利用各種心理和社會機制來糾正我們的(經常是潛意識的、不受理性控制的)認知偏誤和社會機制的偏向性。而這是一個艱巨的工程。文章末了,想以一句萬分無能為力的感慨作為總結:真的要戰勝種族主義,前途多艱啊!
延伸閱讀:
Boyd, R., & Silk, J. B. (2015). How Humans Evolved,7e.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p.392
Gil-White, F. (2001). Are ethnic groups biological “species” to the human brain?. Current anthropology, 42(4), 515-553.
Kurzban, R., Tooby, J., & Cosmides, L. (2001). Can race be erased? Coalitional computation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26), 15387-15392.
Martin, D., Hutchison, J., Slessor, G., Urquhart, J., Cunningham, S. J., & Smith, K. (2014). The spontaneous formation of stereotypes via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9), 1777-1786.
Pietraszewski, D., Cosmides, L., & Tooby, J. (2014). The content of our cooperation, not the color of our skin: an alliance detection system regulates categorization by coalition and race, but not sex. PloS one, 9(2), e88534.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