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本青年的上山下鄉:反思藝術造村潮
7月26日,三年一度的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祭正式開幕,它已成為近年來藝術青年上山下鄉熱潮的標志性事件。人們相信,通過藝術改造,不斷衰頹的農村都能像越后妻有一樣得到活化,仿佛藝術家一旦進入廢棄空間,就瞬間擁有了點石成金的能力。磨刀霍霍要進入鄉野的藝術家、商人和游客,他們真的手握良藥嗎?
一個藝術家的遷徙錄

柳幸典(Yanagi Yukinori)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新波普藝術的代表人物之一,1993年憑借威尼斯雙年展的參展作品《萬國旗和螞蟻飼養場》走紅。1995年他從耶魯回國,開始了返鄉實踐,第一站是瀨戶內海的犬島(Inuijima)。登島后他見到的是遍布四處的工業時代遺跡,曾經污染嚴重的煙囪早已廢棄,卻依舊高聳。柳幸典最初的設想是通過長期的駐村和調研,與當地人合作,改造破敗的鑄銅廠、廢棄礦場中的湖泊、山村中的舊民居。整個島嶼景觀變化只是第一步,柳幸典海希望能給村民帶來變化,盡管當時犬島常住人口不過百人。這個項目后來得到了貝樂思(Benesse)集團董事長福武總一郎(FukutakeSoichiro)的支持,建筑師三分一博志也參與進來,鑄銅廠被改造為精煉所美術館,其中陳列了大量三島由紀夫的作品。

在去年對巴黎政治學院社會學系艾德里安?法維爾教授的一次采訪中,他談到,犬島逐漸偏離了柳幸典預設的軌道,可預見的未來里,犬島成為又一個全球藝術精英的游樂場,知名策展人、畫廊、藝術家匯聚于此,人們舉著香檳在名目繁多的雙年展三年展中觥籌交錯,“沒人會在意,真實的村莊去哪兒了”。柳幸典和福武總一郎之間有何秘辛不得而知,之后柳撤離了犬島,去往下一站百島(Momoshima),并在那里建立百島藝術基地。

柳幸典的合作者是廣島市立大學藝術系的學生們,日本藝術青年上山下鄉熱潮背后是這一代青年人面臨的一個選擇題。泡沫時代,日本藝術和創意產業空前繁榮,許多年輕人進入各類藝術機構接受教育,畢業后面對的卻是一個極度收縮的就業市場,泡沫時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很難滿足于進入一家日本會社成為“社畜”并就此終老,他們認為會社文化是企業圈養的牲畜,不賣力干活就會被開除。一部分人選擇遠渡重洋在海外尋找突破口,而選擇或被迫留守國內者,很多加入了飛特族(Freeter)大軍,打零工以養活自己的藝術夢。這是艾德里安在《超級扁平:日本當代藝術簡史(1990~2011)》一書中的概念,“冗余的創意階層(Creative Surplus)”。在如柳幸典一樣的藝術家帶領下,藝術青年找到了新去處:登島返鄉。
“來犬島前請三思”,這是柳幸典的話,每天只有兩班船通向犬島,每一班車一次只能搭乘10人。日本的返鄉藝術實踐中,交通不便是常態,越后妻有也是如此,人們往往要耗費大量時間來回奔波。但柳幸典的語境中,路途不便不過是進入鄉野的諸多難題中最容易克服的一個。“進入”的考驗還包括,藝術家以怎樣的姿態進入農村?進入的只是一個空間概念還是社會概念?與當地社區發生了怎樣的聯結?進入后如何“活化”?觀者又帶著怎樣的期待進入農村?人們期待藝術家能成為新一代的開山怪,甚少者認為,入鄉者必須隨俗。
“借來的土地,借來的藝術品”
近年來動輒自稱“社群藝術”、“公共藝術”、“介入性藝術”的項目舉不勝舉,香港策展人樊婉貞給這股熱潮潑了冷水,許多藝術項目只是在“借來的土地”上展示“借來的藝術品”,許多藝術家“舉著都市文明的旗幟,踩著救世的步伐,硬生生地將自以為是的藝術插入別人的土地”。
艾德里安指出,一般意義上的藝術項目,是一幫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都市精英來到農村,踐行一套屬于都市精英的理論,擺放裝置藝術或者舉辦展覽,展覽期結束后便匆匆離去,除了發生地在農村意外,無論是藝術家還是藝術作品都與所在地沒有任何聯系。而只有通過長期的“沉潛”,才能獲得本地與外來者的共識,共同思考島嶼的未來。

柳幸典的百島基地中,長期駐村計劃為這樣的沉潛帶來可能。美國藝術家詹姆斯?杰克(James Jack)為了建造一艘木雕的船,需要從島上搜尋木頭。本地人會和他討論,或是從島上廢棄的舊民居中搜尋合適的木頭給“那個老外”。詹姆斯在其博客中寫到:“與其說藝術可以給百島帶來更多的人口,不如說它提供了一種可能:一群外來的藝術家與島民合作,共同描繪‘明日之島’的樣貌”。該項目收錄在百島藝術基地2014年的展覽“關于明日之島的100個點子:藝術怎樣帶來更好的社會”(100 Ideas on Tomorrow’s Island: What can art do for a better society?)中。

這也是近些年人們對“在地性藝術”(Site-Specific Art)的討論,在地性藝術,只能發生在某一場域,關涉當地人,甚至有當地人參加,異地重置或置于美術館的白盒子中就會削弱其意義。

越后妻有
北川弗朗2014年的回憶錄剛剛譯成中文版,在《鄉土再造之力:大地藝術節的10種創想》中,他回憶他籌辦第一屆大地藝術祭時的情形。“當時的我漫無目的地著手搞起公共藝術,也就是把藝術作品放置在路邊或公園等公共場所”,這符合地方行政力量對“公共藝術”的想象,能觸及更多的公眾,更多人有觀看藝術品的權利。但無論行政者還是北川自己都有疑惑,行政者不能理解藝術作品與農村文化有何勾連之處,北川則懷疑單純的置入能算公共藝術嗎。這本回憶錄記錄下了北川如何在每一個項目中拓展人們對公共藝術的想象。
對逝去生活的追憶和惋惜時這一波鄉野藝術最鮮明的主題。北川認為,北山善夫的《致生者,致死者》是在傳統美術館的白盒子里無法表達的作品。北山在一間廢棄的校舍中布置了他在過去數十年間搜集的簡報和學生畫像,黑板上寫著學生們留下來的文集中的詩句,黑板上貼滿了當年畢業典禮時的字跡。整個學校就在這一個個隱形幽靈的記憶中搖晃、漂浮,仿佛具有生命,一個個學生鮮活地站在人們面前。
另一個項目是克里斯蒂安?波爾坦斯基的《亞麻衣》,她從當地居民那里收集到了幾百件白色的亞麻衣,在面積0.5公頃的清津川河邊農田中整齊懸掛。許多老人家參與了面向村民的內部展示會,他們帶來了與本地和學校有關的物品,放置在教室中。對發展的反思是藝術家們又一常用隱喻,克里斯蒂安的另一件作品《無主之地》(No Man’s Land)在里山現代美術館中展出,這件作品在米蘭、巴黎、紐約等地都曾展出過,在16噸的巨大舊衣堆中,有著“神之手”之稱的吊車不斷重復著抓起、放下的動作。
另一個項目《夢之家》略顯小清新,稍不留神就會變成榜單推薦中“必去的特色民宿”。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設想是,讓旅人們用銅質浴缸中的草藥水清洗身體,穿上藝術家設計的睡袋型睡衣,枕著水晶枕躺在棺材形狀的木床上,睡醒后把做的夢記錄在備好的“夢之書”上,十年后,可以把所有的夢編成合集。這個項目最初由小蛇隊(Kohebi-tai)負責管理,不久后由村民接手,許多村民在這里記下了自己的夢。2011年的大地震中,夢之家被毀壞,當地居民參與到之后的修復中去。
盡管北川弗朗指出,他在引領每一個外來者進入越后妻有的村莊時,從不會介紹“這里都空氣環境都很好”,或是“這里的蔬菜很好吃”,而是會著力描述鄉村時如何衰敗的,但在回憶錄的后半部分,他自己也意識到,幾屆藝術祭辦下來,這樣的主題太過均質,單純的懷舊美學逐漸僵化。
北川花了很長時間才摸索出來如何獲得新瀉縣政府的支持,由珠玉在先,后來者在獲得政府支持上變得異常容易,政府堆藝術造村的理解可以簡化為支持創意產業的發展。很難簡單評判政治力量的介入是好是壞,但艾德里安認為,創意產業仍是屬于泡沫年代的思維,目標指向很明確,藝術和文化可以創造經濟價值。森大廈株式會社就運用這套概念建立了六本木之丘。意大利Matteo Pasquinelli眼中,“創意城市”的意涵是以“文化資本包裝房地產發展”,空間被迅速士紳化,創意城市的風潮是一種不需要暴力外殼的新剝削形式。
無論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祭還是瀨戶內海藝術祭,都存在諸多爭議,模糊性在于他們向政客和公眾兜售的地區復興,都與旅游業振興密不可分。“但旅游不應該是最終的解決方案,簡單來說,游客不能替代真正的人口。人口下降是不爭的事實,在一些地區發生的情況是,老齡人口正在被游客‘驅逐’出去”,艾德里安表示無奈。咖啡廳、茶肆、民宿會越來越多,盡管越后妻有擁有體量巨大的藝術作品,但終有一天,游客會被越來越多的仿制者養出愈發刁鉆的“胃口”,千篇一律的懷舊之外,總得期待點別的。


尋找“共犯”之路
回到最初的命題,剝去層層外衣,許多打著“藝術造村”幌子的活動內核只是“舊空間”和“藝術家”。如柳幸典、北川弗朗一樣的藝術家們用數年的實踐告訴你,笨蛋,重要的是關系啊!“外來者”介入的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物理空間,也不僅僅是一個充滿懷舊氛圍的情感空間,還包括一個個已經存在的社區和族群。撇開這些群體的“活化”,不過是另一個版本的士紳化。
北川在回憶錄中總結十五年的藝術祭寫到,“對我而言,藝術家與一般人之間的‘共犯性’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并將這一認識歸于早年參與日本社會運動的經歷。參與了六十年代東京學生運動的他,目睹了人們如何以“組織”、“正義”或是“大義名分”碾壓人性的恐怖,試圖磨平一切差異。他對農村運動的反思,來自于日本左翼在指導農村革命時,試圖與“地方大佬”的腐敗不公等惡勢力斗爭卻失敗的歷史。“因為他們的斗爭是以城市的、民主主義的價值觀為基礎,否定了農村的價值觀”,意識形態難以撼動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
北川及其同行者在“進入”越后妻有時,外來藝術家和“小蛇隊”和本地人的每一次相遇,都是調整藝術作品的設想和走向的契機。艾德里安認為,評判公共藝術的最重要標準在于“外來者與本地人建立了怎樣的聯系”,至于能否帶來歸屬感(a sense of belonging),這樣的討論為時尚早。如北川一樣,這些人試圖在走一條找尋“共犯”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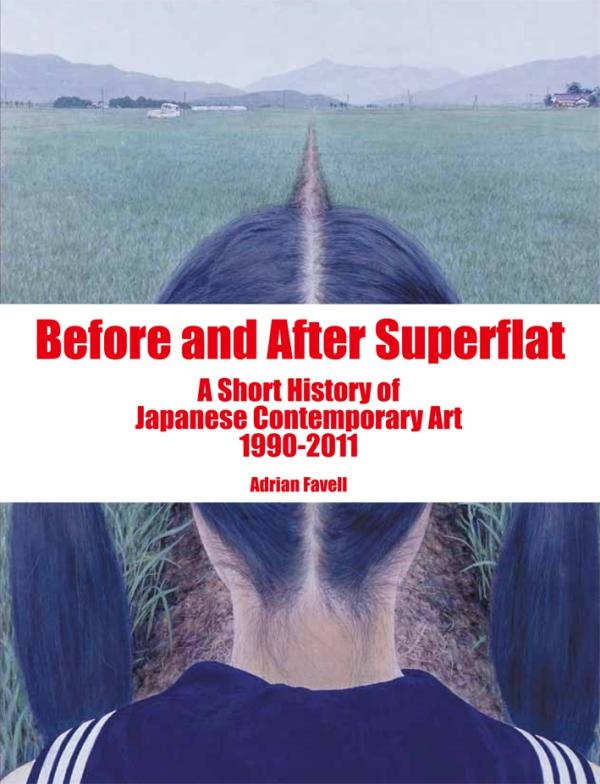
日比野克彥(Katsuhiko Hibino)的《明后日新聞社文化事業部——昨日電視公司》(Day-after-tomorrow Newspaper, Day-before-yesterday Television)索性在當地創辦了一份報紙,他選擇廢棄的莇平小學校舍作為基地,成立“后日新聞社”發行日報,報導每日村莊發生的新聞,包括作為外來人的日比野克彥,以及他年輕的學生們如何與村民互動。后來,他更加設了電視臺,制成線上新聞。他們在駐地與當地的老人交流,通過口述史搜集行將消失的記憶。明后日新聞社稱,希望“播下明日的種子”(generate seeds for the future)。
更具反叛精神的藝術家是年輕的坂口恭平,他從一群被社會遺忘者——坂口恭平拒絕稱他們是“無家可歸者”——身上看到了生存智慧,這些人用廢棄的紙板、太陽能電板搭建起自己的容身之所,經營自己的“零元”生活。坂口恭平研究了居住在自建的零元屋中人的生活,寫下了《東京零元屋的零元生活》,作為建筑師的他還設計了造價只需兩萬六千日幣的可移動小屋,讓居屋脫離了土地的束縛,這是坂口恭平的挑戰,“土地真的必須被劃分以供買賣嗎?”

在這些返鄉藝術實踐中,藝術家原本強烈的個人風格被迫磨平,側重呈現的是藝術作品與所在地方的聯系,這些“殺死作者”的藝術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帶來社群的反思,或是蘊含活化地方的能量,仍需時間的沉淀。有幸前往參觀這一屆大地藝術祭的觀者不妨搜尋一下,北川提到的若干命題有什么進展,當地人如何參與到藝術祭中,有催生出什么樣的產業發展,北川寄予厚望的紡織業復興、十日町農田發展如何。摘掉玫瑰色的眼鏡吧,一起去鄉野找尋“共犯”。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