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1949的第二年:“都市迅速遠(yuǎn)去,摩登依舊在場(chǎng)”
現(xiàn)代性的一個(gè)最大特征或許就是人之周遭世界連及內(nèi)心種種價(jià)值、認(rèn)同的多變、善變與速變。如果說(shuō)在十九世紀(jì)前,尚可以將百年作為一個(gè)變化之世代的話,那么到二十世紀(jì)后半期則可能十年,甚至五年就要“笑問(wèn)客從何處來(lái)”了。今日的上海人只能在老照片和老電影上觀看和回味還未成步行街的南京路、周邊是一望農(nóng)田的徐家匯和熱鬧熙攘的梵王渡火車站。從這種“經(jīng)變已無(wú)影,無(wú)影仍有跡”的意義上來(lái)說(shuō),上個(gè)世紀(jì)的上海已然成為一個(gè)輪廓迷離、似在霧中的都市。不過(guò)也正因?yàn)樗八圃陟F中”,反而更吸引歷史學(xué)家到神秘的“寂靜嶺”來(lái)一探究竟,張濟(jì)順教授的新作《遠(yuǎn)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以下簡(jiǎn)稱張著)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gè)如何撥開迷霧,解剖地方歷史的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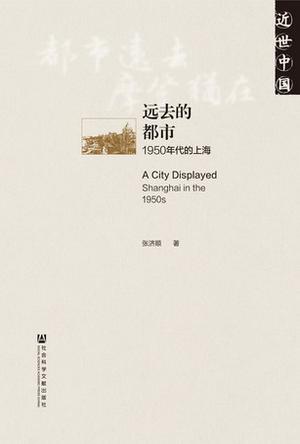
第一,魏氏師從“莫扎特式的史學(xué)家”列文森,從日后的作品看,魏氏擁有不遜色于老師的驚人史學(xué)天賦。這種天賦從表象上說(shuō)是讀其書如讀偵探小說(shuō)般過(guò)癮,若學(xué)術(shù)性地概括則表現(xiàn)為:跨地域文化的感受能力、史事之前后左右的聯(lián)系能力和對(duì)政治、社會(huì)多面復(fù)雜性的穿透能力。基于此,魏氏經(jīng)常會(huì)感到“任何現(xiàn)成的西方概念都難以容納現(xiàn)代上海歷史的豐富與多樣性”(第3頁(yè))。
第二,魏氏研究上海,一方面掌握有豐富的史料,他的“上海三部曲”引用的資料“大到系統(tǒng)的檔案卷宗,小到各式市井小報(bào),各式文獻(xiàn)和圖書資料達(dá)數(shù)千種,很多極為生僻,即使根據(jù)名目按圖索驥尚不易尋得”(韓戍:《三個(gè)時(shí)代的上海警察與社會(huì)治理》,《新京報(bào)》2011年9月22日)。但另一方面,魏氏不會(huì)被史料所束縛,他用娓娓道來(lái)的敘事描繪現(xiàn)代上海的多元文化和不同時(shí)期的各方權(quán)力爭(zhēng)斗。
第三,在上海史研究中,魏氏特別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代中國(guó)歷史演進(jìn)的相關(guān)性和連續(xù)性。以《上海警察》為例,他要建立的就是“晚清改革、國(guó)民黨的統(tǒng)一和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建立之間的聯(lián)系;搶劫者和革命者之間的聯(lián)系;警察和罪犯之間的聯(lián)系;不同背景的特務(wù)之間的聯(lián)系;從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產(chǎn)黨中國(guó)之間的聯(lián)系”。
這些基本思路在張著中都有一定的體現(xiàn),據(jù)作者總結(jié):“魏斐德教授的意見(jiàn)促使我?guī)е鞔_的‘轉(zhuǎn)型與延續(xù)’相統(tǒng)一的問(wèn)題意識(shí)跨入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為‘規(guī)律’、‘必然’與政治褒貶所構(gòu)成的‘目的論’或‘決定論’史學(xué)所左右,也不再讓豐富的歷史材料成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國(guó)家與社會(huì)等二元對(duì)立概念的填充物,而著力去發(fā)現(xiàn)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續(xù)著的歷史本身的邏輯發(fā)展。”(第3頁(yè))
張著不太彰顯,但也極其重要的另一條學(xué)術(shù)脈絡(luò)則是她多年來(lái)對(duì)大陸上海史研究成果的“繼承性反思”。讀書自無(wú)定法,但筆者以為張著較為適宜的讀法或應(yīng)從附錄的七篇文章讀起,它們無(wú)論是對(duì)于理解本書還是上海史研究的深入都有著“舊文新讀”的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
第一,當(dāng)下治國(guó)史者除少數(shù)幾位最出色學(xué)者外,不少研究都難脫從1949年談起的“橫空出世”之病。這些作史者往往因缺少晚清和民國(guó)的“前史”積累而造成其成果一往前推就露出馬腳。而附錄中的《論上海里弄》和《淪陷時(shí)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兩文正為我們理解第一章五十年代上海的“里弄換顏”提供了長(zhǎng)程的視野和“前史”的關(guān)照。
第二,作者自1990年起已經(jīng)對(duì)歷史自身的復(fù)雜發(fā)展與以簡(jiǎn)單褒貶為表現(xiàn)形式的“歷史意義”挖掘間的緊張性做出了思考,這最突出地表現(xiàn)在并未正式發(fā)表的《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一文上,作者寫道:“如果把上海租界視為一個(gè)多元價(jià)值體系,將研究思路從褒貶相加的價(jià)值判斷轉(zhuǎn)向價(jià)值關(guān)系的闡述,上海租界研究可能會(huì)向客觀和全面靠近一些。一切與上海租界有關(guān)的歷史素材都應(yīng)當(dāng)進(jìn)入研究的視野,而不是根據(jù)既定的褒貶判斷進(jìn)行篩選。”(394頁(yè))這段話寫在1993年,恰在作者赴美之前,但它又與前引作者受魏斐德影響后的研究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呼應(yīng),足見(jiàn)一個(gè)學(xué)者對(duì)于另一個(gè)學(xué)者的“影響”并非僅是單向度的關(guān)系,“影響”對(duì)于一個(gè)好的研究者而言,很多時(shí)候是等待著一把鑰匙來(lái)打開她內(nèi)心早已準(zhǔn)備好的呼應(yīng)結(jié)構(gòu)而已。
第三,作者對(duì)于如何研究“上海社會(huì)史”做過(guò)不少自覺(jué)的方法論反思。在《近代上海社會(huì)研究界說(shuō)》一文中,作者特別強(qiáng)調(diào):“基層上海人一旦成為近代上海社會(huì)研究的主角,其意義就不限于對(du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遷的決定作用,而會(huì)牽動(dòng)這一研究時(shí)限的變化”,因此“上海統(tǒng)治者的更換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的意義,而在一些更為基本的方面,特別是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范式,則可能無(wú)關(guān)宏旨”;考察基層上海人在近代化進(jìn)程中的經(jīng)歷,“階段的劃分要模糊得多,甚至可以不考慮階段的劃分問(wèn)題……上海的家庭模型、文化觀念、生活方式很難用階段來(lái)區(qū)別”(350、351頁(yè))。
這些方法論反思都證明作者二十多年來(lái)一直在考慮“轉(zhuǎn)型和延續(xù)”并存、互動(dòng)和共生的關(guān)系。“立足基層,模糊階段”雖然是精彩洞見(jiàn),但一旦落實(shí)到具體研究時(shí),會(huì)遭遇重重困難:
首先,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素以“變”而著稱,所謂“階段”的劃分正是立足于變得多、變得廣和變得深的預(yù)設(shè)之上。雖然近年來(lái)“變與不變”的交錯(cuò)互生已被不少學(xué)者所重視,但要討論以“變”為鮮明特色的一段歷史中的“不變”部分著實(shí)并不簡(jiǎn)單。
其次,為基層人物寫“民史”是自晚清梁任公就積極鼓與呼并得到一大批讀書人眾聲響應(yīng)的作史思路,但時(shí)至今日,要切實(shí)地書寫“人民群眾自己的歷史”又談何容易。
最后,具體到張著處理的“國(guó)史”中,近年來(lái)的有趣現(xiàn)象是上層政治史的重構(gòu)因檔案的開放程度等問(wèn)題而進(jìn)展稍緩,反而是基層各種類型的史料層出不窮,精彩異常,為撰寫共和國(guó)時(shí)期的“社會(huì)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與突破的可能性。但這種上下層的錯(cuò)位與不平衡,也極容易造成地方“社會(huì)史”研究的碎片泛濫和詮釋瓶頸,那么張著是如何應(yīng)對(duì)這些艱巨挑戰(zhàn)的呢?
在筆者看來(lái),作者是以包含了多種武器的“地方解剖術(shù)”來(lái)應(yīng)對(duì)的。這里先談其中最醒目的一件武器,即通過(guò)“重構(gòu)延續(xù)性”來(lái)再解釋1949年之“巨變”。作者并不否認(rèn)1949年后上海社會(huì)的巨大變化,但她不能認(rèn)同的是對(duì)于這種巨大變化的兩種看似清晰、實(shí)則過(guò)于簡(jiǎn)化的歷史詮釋:一是中共對(duì)上海舊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及其社會(huì)基礎(chǔ)進(jìn)行了徹底的清除,并在此過(guò)程中以原來(lái)的底層民眾為核心重構(gòu)了社會(huì),構(gòu)建了國(guó)家政權(quán)的社會(huì)基礎(chǔ);另一個(gè)則是1949年后黨國(guó)體制走向頂端,國(guó)家吞噬社會(huì),上海社會(huì)經(jīng)歷的天翻地覆的改造正是“極權(quán)主義”的一個(gè)佐證(24、25頁(yè))。
在作者看來(lái),這兩種詮釋看似方向截然相反,卻分享著相同的預(yù)設(shè),即“1949年是一條巨大的鴻溝,徹底截?cái)嗔藲v史!”但歷史又怎么可能被徹底截?cái)啵狂R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篇中的一段話最為深刻:“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guò)去承繼下來(lái)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張著中的話則是:“重建歷史轉(zhuǎn)捩點(diǎn)的豐富與復(fù)雜,打開重新解釋1950年代之路。”(23頁(yè))
它一方面說(shuō)明張著的“重構(gòu)延續(xù)性”承認(rèn)1949年是歷史的轉(zhuǎn)捩點(diǎn)。因此作者在各章的處理中都未淡化和忽視五十年代“改男造女態(tài)全新”的一面。如第一章指出:“在居委會(huì)的有效運(yùn)作下,非單位人群投身政治運(yùn)動(dòng)之熱烈可說(shuō)是史無(wú)前例,保甲組織無(wú)可企及的政治功能也得以充分發(fā)揮,幾乎每天的報(bào)章廣播都報(bào)道這類消息。”(48頁(yè)) 又說(shuō):“鄰里間相互監(jiān)督的強(qiáng)化一方面有助于加強(qiáng)居委會(huì)作為國(guó)家控制工具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運(yùn)動(dòng)滲透到居民的‘開門七件事’,成為里弄生活的日常方式。鄰里和家庭的政治色彩更加凸顯,共存關(guān)系持續(xù)緊張。”(71頁(yè))第五章總結(jié)說(shuō):“好萊塢的被驅(qū)逐(絕跡上海灘達(dá)30年之久)使上海電影市場(chǎng)發(fā)生了結(jié)構(gòu)性的變化,稱雄數(shù)十年的美國(guó)影片從上海文化市場(chǎng)上退凈……1950年底,上海電影市場(chǎng)已是國(guó)產(chǎn)影片和蘇聯(lián)影片的一統(tǒng)天下。”(276、277頁(yè))
另一方面這句話又告訴我們所謂“延續(xù)性”不等于“相似性”,更不等于“重復(fù)性”,而是要凸顯歷史發(fā)展的豐富性和復(fù)雜性。正如魯迅所言:“看中國(guó)進(jìn)化的情形,卻有兩種很特別的現(xiàn)象:一種是新的來(lái)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回復(fù)過(guò)來(lái),即是反復(fù);一種是新的來(lái)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然而就并不進(jìn)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較的慢,使我們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罷了。”(魯迅:《中國(guó)小說(shuō)的歷史的變遷》)作者在接受訪談時(shí)也曾說(shuō)到一些國(guó)外學(xué)者關(guān)于“延續(xù)性”的開拓性研究。她一方面肯定這些學(xué)者篳路藍(lán)縷的創(chuàng)見(jiàn),但另一方面亦尖銳指出若單純比較政策相似性,則可能慢慢“也會(huì)走到一個(gè)死胡同”中去。
因此重構(gòu)“延續(xù)性”的焦點(diǎn)應(yīng)在于考察“延續(xù)當(dāng)中怎樣發(fā)生轉(zhuǎn)型和裂變”,即“歷史的非憑空創(chuàng)造和有負(fù)擔(dān)前行”。所以一方面,作者對(duì)各章不囿于1950年代的部分極為重視,有些章節(jié)文字雖不多,但或有前期研究積累,或體現(xiàn)在背景梳理與行文點(diǎn)睛之中,另有些章節(jié)則直接將民國(guó)上海與五十年代的上海作為一個(gè)整體來(lái)處理。第四章《約園內(nèi)外:大變局中的黃氏兄弟》就把時(shí)限定為1930-1966年。同時(shí)還提出了一系列與歷史延續(xù)性相關(guān)的問(wèn)題,如“教會(huì)大學(xué)的消亡、高等教育的體制轉(zhuǎn)型及校園政治文化的變遷如何侵入學(xué)人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價(jià)值取向和精神世界,個(gè)體的能動(dòng)性是否就此消解,個(gè)人的思想、精神與情感世界是否就此變得單調(diào),個(gè)人的特殊經(jīng)驗(yàn)又如何轉(zhuǎn)化為新的政治文化意義”(193頁(yè))。這種貫通前后的提問(wèn)方式對(duì)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亦為上海城市史研究打開了“新路”。
另一方面若聚焦至五十年代,張著對(duì)當(dāng)時(shí)上海社會(huì)與新政權(quán)碰撞互動(dòng)時(shí)的復(fù)雜歷史圖景多有深刻而精彩的展現(xiàn)。第一章就梳理了當(dāng)“新政權(quán)遭遇舊里弄”時(shí)所要應(yīng)對(duì)的三大難題:一、上海基層社會(huì)的人口流動(dòng)過(guò)頻與空間分布過(guò)密;二、各階層雜居,彼此職業(yè)不同、生活條件不同,福利要求亦有所不同,因此難以用一種政治號(hào)召驅(qū)動(dòng)絕大多數(shù)居民的政治熱情,也不可能存在長(zhǎng)久的利益共同體;三、建立何種組織,既有別于舊保甲,又能有效地掌控社會(huì),依靠哪些人去取代保甲,去建立和運(yùn)行這樣的組織。
正因?yàn)橛羞@三大難題,之后的歷史過(guò)程就不可能是一個(gè)按照“國(guó)家邏輯”,運(yùn)用“階級(jí)凈化機(jī)制”徹底清除近代上海里弄中的社會(huì)基礎(chǔ)的過(guò)程,而是“上海里弄社會(huì)的積淀之深、關(guān)系之復(fù)雜,利益之多元,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新執(zhí)政者最初的估計(jì)與想象”(79頁(yè)),然后新政權(quán)“一方面推動(dòng)、允許或默認(rèn)了社會(huì)按照自身訴求,營(yíng)造一方‘新型’的自治空間;另一方面,沿用革命時(shí)期的政治動(dòng)員經(jīng)驗(yàn),掀動(dòng)底層,一波又一波專門針對(duì)里弄居民的清理整頓與普遍的政治運(yùn)動(dòng)相呼應(yīng)”(80頁(yè))。最后革命、國(guó)家、社會(huì)共同建構(gòu)了共和國(guó)早期的上海里弄。
在“重構(gòu)延續(xù)性”之后,面對(duì)讓基層民眾發(fā)出聲音和上下歷史溝通的困局,作者動(dòng)用了第二件武器——“建立機(jī)制性”。基層民眾自然不可能完全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因?yàn)槠浣^大多數(shù)沒(méi)有屬于他們本身的史料。可是通過(guò)史家在史料之海中的艱難爬梳,抓住蛛絲馬跡,建立非表面的歷史機(jī)制本身的運(yùn)作邏輯,基層民眾亦能夠在大歷史中占據(jù)一席之地,而非僅僅是大歷史的背景和注腳。張著第二章就憑借對(duì)1953年新中國(guó)第一次普選的地方開展機(jī)制的剖析,讓小人物生動(dòng)鮮活地走入了歷史。
在這個(gè)故事里既有吞金自殺的女工C,又有上了黨報(bào)的老工人李杏生,更有成為區(qū)人大代表的女工李小妹。作者講這些小人物的故事,并不是展示細(xì)節(jié)后的講完罷了,也不是要通過(guò)他們來(lái)證實(shí)或證偽普選與“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勾連關(guān)系,而是要回答在普選的三個(gè)主要階段:選民資格審查、選舉動(dòng)員和選舉人提名到最后選舉中,是什么讓女工C因?yàn)檫x舉而走向自殺,又是什么讓一個(gè)默默無(wú)聞的老工人成功登上黨報(bào),同時(shí)令一個(gè)“極為普通甚至在政治上不善表現(xiàn)的女工”(108、109頁(yè))李小妹脫穎而出成為區(qū)人大代表?
以李小妹為個(gè)案,張著就從“天時(shí)”——選舉法定程序(聯(lián)合提名制與等額選舉原則結(jié)合)對(duì)她的助力、“地利”——李所在的紡織行業(yè)和供職的仁德紗廠在選舉中的獨(dú)特政治優(yōu)勢(shì)以及“人和”——仁德紗廠的“微觀政治環(huán)境”令她成為了廠里既符合“官意”,又符合“民意”的候選人等三個(gè)方面梳理出了一條看似順理成章、實(shí)則玄機(jī)重重的底層“勞動(dòng)人民”躋身人大代表行列之路(108-113頁(yè))。
而就上下歷史溝通這一難題而言,“上層史與下層史的研究不僅不相沖突,而且是互補(bǔ)的,若能兩相結(jié)合,則所獲甚豐”(參見(jiàn)羅志田:《見(jiàn)之于行事:中國(guó)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張著可能正是一個(gè)“兩相結(jié)合、所獲甚豐”的例子。她在第二章中對(duì)新中國(guó)第一次普選中中共“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塑造”與底層民眾自我認(rèn)同之間的張力給予了充分關(guān)注(132頁(yè))。除了探究普選運(yùn)動(dòng)本身的機(jī)制外,她更努力去尋找中共在1953年初迅速啟動(dòng)普選和制憲的原因。對(duì)此作者與張鳴等學(xué)者有類似思路,即與斯大林的強(qiáng)力推動(dòng)有關(guān)(129頁(yè))。同時(shí)中共又非全盤,而是有選擇性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這主要是因?yàn)橹泄舱J(rèn)為“把共同綱領(lǐng)變成國(guó)家基本大法”、通過(guò)普選將“聯(lián)合政府”漸轉(zhuǎn)化為“一黨政府”(129-131頁(yè))符合這一階段革命的需要。然后作者將上層史研究之成果與上海的地方普選勾連起來(lái),提出了一個(gè)多面相的結(jié)論,即中共高層的認(rèn)識(shí)和理念使得普選在為底層民眾打開上升通道、激發(fā)其政治熱情的同時(shí),又和制憲一起成為中共“繼續(xù)革命”鏈條上的一個(gè)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如果說(shuō)“重構(gòu)延續(xù)性”與“建立機(jī)制性”這兩種武器具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方法論意義,那么作者還有一種武器或許就屬于“獨(dú)門秘技”,使得此書具備了鮮明的個(gè)人風(fēng)格,此即“區(qū)域體驗(yàn)”。
做“區(qū)域”或者“地方”之困難往往在于如何展示和凸顯“區(qū)域”的獨(dú)特性,使得區(qū)域不再是“全國(guó)一盤棋”中與其他棋子類似的“又一枚棋子”,同時(shí)又要回答這種獨(dú)特性是以哪些方式和各種普遍性相聯(lián)結(jié)的。而作者因自己的“區(qū)域體驗(yàn)”有著解決這一難題的優(yōu)勢(shì)。
從附錄中的《從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歷史和現(xiàn)代教育》一文可知作者的曾祖父是清末上海梅溪學(xué)堂的創(chuàng)辦人、南洋公學(xué)(交通大學(xué)之前身)首任華文總教習(xí)張煥綸。作為上海城墻內(nèi)的“老上海人”后代,她對(duì)上海的歷史變遷有一份源自于家族血脈的獨(dú)特感受。一方面作者系懷于歷史的蒼涼與無(wú)奈,看到了“消失在大上海百年歷史之中的,遠(yuǎn)不止張煥綸這個(gè)具有新思想的老學(xué)究,而是整個(gè)上海老城廂和它的居民”(413頁(yè)),但另一方面使她感到震撼的是,取代城墻內(nèi)“老上海人”的新上海人在成為現(xiàn)代都市人的歷史過(guò)程中“不斷增添和強(qiáng)化了上海文化的開放和寬容的特質(zhì)”,塑造了令人矚目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414頁(yè))。
當(dāng)然對(duì)于新上海人取代“老上海人”的歷史,或可以有更多的話可以說(shuō)一說(shuō)。現(xiàn)代上海的開放是一個(gè)“面向世界”直至“走向世界”的過(guò)程,在此過(guò)程中西潮、新潮澎湃而洶涌。如何在潮流中站定腳跟,海派文化究竟因何而成立就變?yōu)橐粋€(gè)令人頗難回答的問(wèn)題。回溯以張煥綸等為代表的“儒家經(jīng)世讀書人”的經(jīng)歷,則為問(wèn)題的回答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源。沈恩孚寫的《張先生煥綸傳》就曾說(shuō)道:“其(張煥綸)立教以明義理、識(shí)時(shí)務(wù)、體用兼?zhèn)錇橹髦肌F浣炭茷閲?guó)文、輿地、經(jīng)史、時(shí)務(wù)、格致、數(shù)學(xué)、歌詩(shī)等;甲申年始增英法文,旁及灑掃;應(yīng)對(duì)進(jìn)退與夫練身習(xí)武之術(shù)……尤尊重德育,選古人嘉言懿行為常課。”無(wú)疑張氏強(qiáng)調(diào)的不是無(wú)根的“海納百川”和無(wú)原則的“有容乃大”,而是一種“胸有定見(jiàn),心有固守”式的開放,其定見(jiàn)與固守來(lái)自于儒學(xué),又部分超越了儒學(xué)。“張傳”又說(shuō):“中法之役,俾學(xué)生受軍事訓(xùn)練,率之夜巡城廂,聞履聲者皆知其為梅溪生矣”,這體現(xiàn)了“儒家經(jīng)世讀書人”的胸襟抱負(fù)系于天下蒼生,而具體實(shí)現(xiàn)則多立足本土本鄉(xiāng)。既立足本土本鄉(xiāng),在晚清的衰世中“從事教育”為其中一正途。因此張煥綸被私謚為“宏毅先生”,沈恩孚亦能從其事跡追慕他“陶鑄時(shí)彥,警醒后學(xué)”的流風(fēng)。這種流風(fēng)曾長(zhǎng)久地澤被江南各地,在民國(guó)時(shí)期乃至今日亦能見(jiàn)其余緒,聽其回響,卻慢慢與上海的都市文化絕緣。今日返觀,當(dāng)多有長(zhǎng)思。
回到張著,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正是有了結(jié)合長(zhǎng)程歷史和私人生活對(duì)上海本鄉(xiāng)的獨(dú)特體驗(yàn),張著在不少地方展示了如何用體驗(yàn)性來(lái)突破做“區(qū)域”之難題。
首先是體驗(yàn)性對(duì)于“檔案話語(yǔ)”的修正與穿透幫助極大。張著處理史料之最大宗無(wú)疑是形形色色的檔案。這些檔案可以視作關(guān)于五十年代地方政治運(yùn)作中的各種“表達(dá)”,這種種表達(dá)是由無(wú)數(shù)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概念、詞匯和語(yǔ)言所組成,稍不留神就會(huì)跌入前文所述的“又一枚棋子”的陷阱。但作者因熟悉上海的社會(huì)與文化而在檔案處理上頗有獨(dú)到之處。如她在討論上海五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熱時(shí),就充分挖掘出政治話語(yǔ)掩蓋下上海市民特別是青年們樂(lè)看、愛(ài)看、追看香港電影的那些簡(jiǎn)單、直白、生動(dòng)的理由,進(jìn)而重現(xiàn)被檔案所遮蔽的多彩生活。如有人說(shuō)就是專為看“主角陳思思面孔漂亮”,才千方百計(jì)去覓得《美人計(jì)》的電影票;又有人說(shuō):“香港明星是‘人嗲,演的嗲’”;也有人說(shuō):“我三天三夜(排隊(duì)購(gòu)票),就是為了《新婚第一夜》,今后找對(duì)象,就要夏夢(mèng)一樣嗲的女人。”(289頁(yè))而有了觀眾群的考量,作者亦注意到電影經(jīng)營(yíng)者依舊延續(xù)著“在商言商”的特性,往往努力規(guī)避政治束縛,追求上座率,想方設(shè)法多多放映“打得結(jié)棍、苦得厲害、既輕松又緊張”的香港片(290頁(yè))。
第二,在檔案和其他歷史資料之外,作者善用個(gè)體記憶與作為上海人的集體記憶來(lái)描摹“最難以呈現(xiàn)”的感覺(jué)、體驗(yàn)層面的歷史,第五章即指出優(yōu)秀紅色經(jīng)典中的英雄人物給上海觀眾留下的印象竟往往不如片中的“反面人物”。如1958年的國(guó)產(chǎn)電影《英雄虎膽》,上海人記憶最深的是其中的女特務(wù)“阿蘭小姐”,而不是深入虎穴的英雄曾泰。“阿蘭小姐,來(lái)一個(gè)倫巴”成為了當(dāng)年許多上海人茶余飯后討論這部電影時(shí)能脫口而出的一句臺(tái)詞(293頁(yè))。這種觀察如果沒(méi)有植根其間的“區(qū)域體驗(yàn)”,大概是很難得到的。
第三,上海作為一個(gè)超大型都市,其“多元異質(zhì)”的社會(huì)特性要長(zhǎng)期生活浸淫于其中方可能抓住一點(diǎn)神髓,而張著對(duì)這種社會(huì)特性往往能通過(guò)寥寥數(shù)語(yǔ)傳神地表達(dá)出來(lái),如說(shuō)到上海里弄內(nèi)的“異質(zhì)人群”,作者就用上海鄰里間表征彼此關(guān)系的許多稱呼來(lái)證明“五方雜處之近密”,如老山東、小廣東、亭子間好婆(蘇州人對(duì)外祖母的稱呼)、閣樓大大(揚(yáng)州人對(duì)伯父的稱呼)、前樓爺叔(上海人對(duì)叔叔的稱呼)、后樓阿娘(寧波人對(duì)祖母的稱呼)等(30頁(yè))。
綜觀全書,作者著力揭示的是一個(gè)“都市迅速遠(yuǎn)去,摩登依舊在場(chǎng)”的1950年代上海。所謂“遠(yuǎn)去”指的是“1950年代的上海,確實(shí)稱得上天翻地覆,國(guó)家的動(dòng)員與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個(gè)統(tǒng)一有序的上海社會(huì)奇跡般地出現(xiàn)”(15頁(yè))。這段“遠(yuǎn)去”的歷史無(wú)論是史家還是讀者或相對(duì)還比較熟悉。但“摩登依舊在場(chǎng)”,“上海歷史與上海經(jīng)驗(yàn)并沒(méi)有在1949年這個(gè)歷史轉(zhuǎn)折點(diǎn)上戛然而止”則是張著對(duì)1950年代上海史“去熟悉化”后重新書寫的一大貢獻(xiàn)(17頁(yè))。
相較各種沉溺在追慕摩登、懷舊往昔情緒中的歷史書寫,從張著我們能夠感受到的是一個(gè)上海人——她成長(zhǎng)于1949年后,曾在艱難時(shí)世中暫時(shí)遠(yuǎn)離過(guò)這座城市,后來(lái)又因其專業(yè)而熟悉了解這座城市“由溪入海”、走向現(xiàn)代的復(fù)雜過(guò)程——其內(nèi)心更大更深的關(guān)切,即上海的世界溝通、上海的地方文化之根與各類上海人鮮活的生命故事。在這種關(guān)切里聯(lián)結(jié)了人性與歷史,老城廂與新都市,霓虹燈內(nèi)和霓虹燈外,地方、國(guó)家與世界乃至歷史的親歷者、書寫者與閱讀者,正基于此,讀這段歷史就不能不有所感慨,同時(shí)又不能不有所感悟。 ■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