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場改變美國的大火:為何中國人對工廠火災(zāi)卻如此冷漠?
【編者按】
1911年3月25日,清朝宣統(tǒng)三年二月二十五,美國紐約曼哈頓下城區(qū)的一家工廠,三角女式襯衫廠,發(fā)生了大火,奪去了146位工人的生命。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嚴(yán)重的生產(chǎn)事故之一。德萊爾認(rèn)為,這場大火改變了美國。
這場大火怎樣改變了美國?我們在一百多年后討論這場大火,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2015年6月14日,由北京大學(xué)法治研究中心主辦,由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六部書坊、雅理工作室協(xié)辦的“法意—雅理讀書會”邀請潘毅、呂途、葉明欣作為嘉賓,探討了一本關(guān)于這場大火的記者作品:《興邦之難:改變美國的那場大火》。澎湃新聞授權(quán)發(fā)表該研討會的全文實錄,共分兩篇,本篇為第一篇。
主持人閻天:首先介紹一下三位嘉賓。她們?nèi)挥幸粋€共同的特點——當(dāng)然她們都是女同胞——但更重要的是:她們都不僅學(xué)問好,而且身體力行,努力改變勞動者的處境,推動社會改革。
首先介紹潘毅教授。潘老師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學(xué)應(yīng)用社會學(xué)系。她先后畢業(yè)于香港中文大學(xué)、香港大學(xué)和倫敦大學(xué),取得了學(xué)士、碩士和博士學(xué)位。潘老師是社會學(xué)家,她的專著《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獲得過美國社會問題研究會頒發(fā)的“米爾斯獎”,是歷史上首位亞洲獲獎?wù)摺K粌H僅是個學(xué)者,有媒體概括說,潘老師每做一項研究,都是先調(diào)研,再通過媒體制造壓力,然后成立NGO,把學(xué)術(shù)轉(zhuǎn)化為持續(xù)的行動。所以我們更應(yīng)該稱她為“學(xué)術(shù)行動家”,scholar-activist。在《中國女工》這本書的開頭,潘老師也講了一個工廠火災(zāi)的故事,只不過場景移到了深圳的一間港資玩具廠。這和《興邦之難》的主題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暗合。我們期待潘老師為我們揭開這個暗合的意義所在。
下面一位是呂途老師。呂途老師現(xiàn)在的工作單位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fā)展中心,這是一家NGO。呂老師畢業(yè)于現(xiàn)在的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她在荷蘭海牙的社會研究院取得了婦女與發(fā)展問題的碩士學(xué)位,又到現(xiàn)在的荷蘭瓦赫寧根大學(xué)農(nóng)村發(fā)展社會學(xué)系取得了博士學(xué)位。瓦赫寧根是農(nóng)業(yè)研究的頂級名校,呂途老師也曾經(jīng)是農(nóng)大的一位出色的學(xué)者。但是,她不滿足于在書齋里“代表”打工者說話。她選擇成為打工者的一員,做志愿者,下工廠當(dāng)工人。這些體驗形成了兩本《中國新工人》,一本的副標(biāo)題是“迷失與崛起”,另一本是“文化與命運(yùn)”。《興邦之難》里談的也是一群“新工人”的故事,三角工廠大火的受難者大多數(shù)都剛到美國不久,是移民工人。呂老師有這么獨特的學(xué)術(shù)背景和體驗,相信對《興邦之難》的解讀也會很有特點,讓我們一起期待。
這一位是葉明欣老師。葉老師是北京義聯(lián)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這是國內(nèi)最早的一家專業(yè)勞動法律援助NGO。葉老師是我在北大的學(xué)姐,她200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并留校工作,2009年取得了北大的民法學(xué)碩士學(xué)位,又到哥倫比亞大學(xué)留學(xué),成為了中美兩大名校的法學(xué)“雙碩士”。她做了一個讓我們這些師弟師妹敬佩不已的決定。她到義聯(lián)工作,成為了一名真正的勞動法專家。她在工傷、職業(yè)病等問題上提供過很多立法建議,獲得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采納。她提供的法律援助和咨詢就更多了,我手上的這本《職業(yè)病法律制度研究》,就挖掘了義聯(lián)做過的上百個案例。包括我在耶魯?shù)呐_灣同學(xué)的弟弟,出了工傷都是請葉老師撐腰。期待葉老師結(jié)合自己的一線法律工作經(jīng)驗,談?wù)劇杜d邦之難》這本書。
作為鋪墊,請允許我先花一點時間介紹一下《興邦之難》的主要內(nèi)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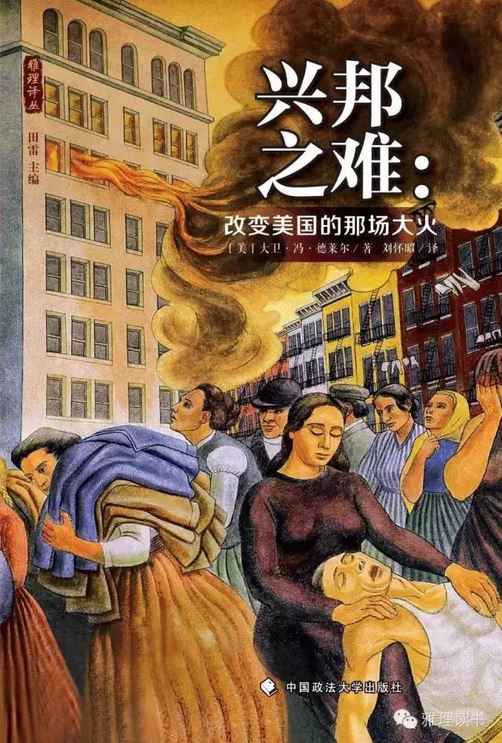
前三章談的是三角工廠大火的背景。這個背景可以分成三個方面:身份政治、政黨政治和生產(chǎn)政治。
從身份政治來說,這是一個工人運(yùn)動風(fēng)起云涌的時代。三角工廠大火的受難者的身份,主要是女性、移民、工人三重身份。(1)19、20世紀(jì)之交,大量歐洲移民、特別是猶太人和意大利裔涌入美國,為制造業(y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也成為了政客爭奪的票倉。(2)女性雖然在政治中和職場中都遭受著嚴(yán)重的不平等(美國聯(lián)邦層面1920年才修憲保障婦女選舉權(quán)),但是大量的婦女投入了工作,爭取婦女平等權(quán)利的運(yùn)動已經(jīng)興起。(3)“移民”和“女性”都是這個時期工人運(yùn)動的關(guān)鍵詞。三角工廠大火之前兩年,紐約市爆發(fā)了制衣業(yè)大罷工。移民工人、特別是猶太人是罷工的主力。罷工獲得了女權(quán)運(yùn)動支持,力量空前壯大,迫使資本家讓步。但是,罷工也因為工人內(nèi)部的分歧和資本家的鎮(zhèn)壓、分化,沒有完全成功。罷工為后來的改革做了思想和組織的動員,讓統(tǒng)治者看到了工人的力量,為后來的政策妥協(xié)奠定了基礎(chǔ)。





從政黨政治來說,這是一個保守政客與進(jìn)步主義力量激烈搏斗的時代。(1)保守力量的大本營是坦慕尼社,這是民主黨用來控制紐約市和紐約州的政治組織。坦慕尼社一面用小恩小惠拉攏勞工,換取選票,把自己中意的人選送進(jìn)政府;一面靠貪腐、甚至給妓院看場子斂財,搞得政治烏煙瘴氣。他們反對改良,鎮(zhèn)壓工運(yùn)和婦運(yùn)。(2)而進(jìn)步主義力量當(dāng)時冉冉升起,他們主張伸張女權(quán)、扶助勞工、打擊腐敗,與坦慕尼社爭奪勞工、競爭公職,嚴(yán)重動搖了保守力量的統(tǒng)治。
從生產(chǎn)政治來說,這是一個工廈制度盛行的時代。“工廈”,就是在大廈里面開工廠。早先,制衣業(yè)的生產(chǎn)組織形式主要是分散的、小作坊式的承包商。后來,制造商不再發(fā)包,改為自營。他們把許多工人集中到一起,搞集約經(jīng)營,用電力驅(qū)動機(jī)器,這樣效率提高了很多。因為需要大的場地,工廠開始向天空發(fā)展,出現(xiàn)了工廈。我這里有一本英文原版的《興邦之難》。封面上就是三角工廠所在的工廈。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棟十層大樓;從三樓開始,幾乎每層都掛著一家工廠的牌子;三角工廠占據(jù)了最高的三層。生產(chǎn)組織形式是個有趣的概念,每個地方大工業(yè)的興起往往都有對應(yīng)的組織形式:在美國是工廈,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則可能是“宿舍勞動體制”,這是潘毅老師的研究領(lǐng)域。
三角工廠大火之所以影響那么大,一個重要原因是景象太悲慘。后來統(tǒng)計,有54個人因為受不了大火,從高樓的窗戶里跳下來摔死。作者在這一部分談了很多悲劇發(fā)生的原因。比如,防火意識淡薄,為了提高生產(chǎn)效率,大量的易燃廢料隨手堆積在裁縫師傅桌子下面;防火政策執(zhí)行不力,禁煙令對業(yè)務(wù)骨干基本無效。最后就是一個煙頭或者一根火柴點燃了廢料,引發(fā)了大火。
起火之后暴露的問題就更多了。很多工人不是趕快逃跑,而是先去更衣室拿自己的衣服,這反映了安全教育的缺失。樓內(nèi)的滅火水管失靈,關(guān)鍵時刻不出水,這是安防設(shè)備的問題。大火是從八樓開始燒的,八樓和九樓之間聯(lián)系不暢。作者說,如果能早三分鐘通知九樓,就不會有那么多人死去。這一看就是從沒有搞過消防演習(xí),沒有事故預(yù)案。大樓的設(shè)計也不符合安防標(biāo)準(zhǔn),比如逃生門是向內(nèi)開的,出事的時候人們一擁而上,根本打不開門;消防通道不容易到達(dá),而且狹窄難行,甚至沒法通往地面,最后干脆被壓垮了,造成更大的傷亡。作者還推測說,工廠主為了防止工人偷走成衣,把逃生門從外面反鎖了。這個情節(jié)多么似曾相識!
可能有人會問,火災(zāi)也會給工廠主造成損失啊,他們?yōu)槭裁床患訌?qiáng)安全生產(chǎn)呢?這是因為事故保險制度變了味兒。本來,為了少交保險費(fèi),工廠主應(yīng)該減少火災(zāi)風(fēng)險。可是保險代理商不樂意,因為那樣他們的保費(fèi)提成就少了。于是,工廠主就漠視風(fēng)險,多交保費(fèi)。等到真正出了險,保險公司賠的錢比實際損失要大得多。這么一來,火災(zāi)反而成了有利可圖的事情,工廠主甚至為了清除庫存而蓄意防火。這在保險法上叫做“道德風(fēng)險”,當(dāng)時美國的保險法顯然不健全,讓這種做法有了可乘之機(jī)。








《興邦之難》這本書的最后三章構(gòu)成第三部分,談的是大火之后的改革。面對災(zāi)難,人們有兩種選擇:追究個人責(zé)任,或者/同時追究制度責(zé)任。當(dāng)時的消防部門想要給工廠主脫罪,但是地區(qū)檢察官傾向進(jìn)步主義。他在媒體的配合下,把工廠主起訴到了法院。可是,地檢官不僅服膺法律,而且有私心;媒體熱乎一陣以后,也開始疲勞;對方請了大牛律師;法官也因為個人經(jīng)歷的緣故,可能不大公正。最后,陪審團(tuán)宣告工廠主無罪。追究個人責(zé)任的努力遭遇了挫折。
而追究制度責(zé)任的努力則結(jié)出了碩果。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坦慕尼社及時轉(zhuǎn)向,支持進(jìn)步主義。這是個180度的大轉(zhuǎn)彎。紐約政壇出現(xiàn)了年輕的新面孔:羅伯特·瓦格納和阿爾·史密斯。他們主導(dǎo)建立了工廠調(diào)查委員會,啟用受過專業(yè)訓(xùn)練、注重調(diào)查研究的改革倡議者,比如弗朗西斯·珀金斯。委員會推動了規(guī)模宏大的勞動立法改革,徹底改變了紐約州勞動法的面貌。
坦慕尼社為什么會轉(zhuǎn)向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三角工廠的大火激起了工人階級的變革訴求,進(jìn)步派、激進(jìn)派都借機(jī)與坦慕尼社爭奪群眾,威脅到了坦慕尼社的統(tǒng)治基礎(chǔ)。這個轉(zhuǎn)向是被動的,但也很堅決,幫助坦慕尼社重新贏得了廣大工人的選票,也幫助阿爾·史密斯連任了四屆紐約州長。后來,阿爾·史密斯交棒給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羅斯福發(fā)動了改變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政。他重用了當(dāng)年在紐約的班底,比如瓦格納當(dāng)了參議員,和羅斯福遙相呼應(yīng),促成了《全國勞動關(guān)系法》的出臺。這部法律是保護(hù)工會的,又叫做《瓦格納法》。又如珀金斯當(dāng)上了第一任女性勞工部長。可以說,大火培育了新政一代政治家。
如果我們把鏡頭拉得更遠(yuǎn)一些,坦慕尼社的轉(zhuǎn)變也防止了更激進(jìn)的力量取得政權(quán),讓作者所說的“城市自由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它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進(jìn)步主義的。直到今天,雖然保守主義回潮,但是我們?nèi)匀豢梢哉f:城市自由主義是美國的主流政治觀點和制度。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xué)): 謝謝。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么好的主持人,把一本書的內(nèi)容全都做了介紹。(笑)我本來以為這是我應(yīng)該做的事情,結(jié)果主持人幫我做了一半。我原本打算談兩點,現(xiàn)在只要談一點就好了。
這本書的可讀性非常高,它以豐富多彩的人物和故事帶出了全書的主題。很多人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只是認(rèn)為這是一場大火以及這場火災(zāi)如何改變美國勞動立法的故事。如果我們剛才認(rèn)真聽主持人對這本書的介紹,就可以知道這本書的主題不只是勞動立法。事實上,我們應(yīng)該從政黨政治、政治身份和生產(chǎn)政治的角度來理解這本書。這本書將移民的故事帶入到美國二十世紀(jì)之交工人運(yùn)動的具體場景,也勾畫出移民社區(qū)的形成和構(gòu)成(不同的種族、語言、宗教)等豐富的生活場景。
這本書展示出非常重要的一點,這場大火不僅帶出了一場工人運(yùn)動,而且催生了一場女權(quán)運(yùn)動。我們知道,在今天的中國,不僅工人運(yùn)動很重要,女權(quán)運(yùn)動同樣重要。女權(quán)運(yùn)動如何同工人運(yùn)動交織在一起,這本書提供了很好的線索。書中提到,最初的女權(quán)主義者通常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女性,甚至有大銀行家的女兒。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這些上層婦女參與到這場社會底層的群眾運(yùn)動中,同同社會底層的人們走到了一起。她們的參與,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運(yùn)動的發(fā)展,另一方面,由于階級和性別矛盾,卻又導(dǎo)致了這場本應(yīng)更進(jìn)步的激進(jìn)工人運(yùn)動停滯于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階段。
所以,我對這場運(yùn)動結(jié)果的評價是不同的。我們可以看到,本書作者對此是支持的。在他看來,這場運(yùn)動停留在以法治緩和階級矛盾的階段,而非跨越資本主義階段,程度剛剛好。甚至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場大火的意義恰恰在于其使得工人運(yùn)動沒有走向激進(jìn)主義的道路。美國的工人運(yùn)動在二戰(zhàn)時期蓬勃發(fā)展的,到了二戰(zhàn)后,特別是在冷戰(zhàn)時期,社會主義運(yùn)動都被扼殺了,工會中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工人都遭到清除,也導(dǎo)致了今天美國的工人運(yùn)動基本上停滯不前。實際上,這同他們無法超越他們的思想認(rèn)識是相關(guān)的。
我今天想討論的倒不是美國的這場大火,而是與中國相關(guān)的問題。這本書和我的《中國女工》都以一場大火開頭。這種工廠火災(zāi)的故事,使得我走向了關(guān)注、研究工人運(yùn)動的道路。看這本書時,我就在不斷地對比,得出了許多感受。我今天就講一講中國和美國的這兩場大火發(fā)生的不同歷史背景、社會狀態(tài),以及對此不同的反思和反應(yīng)行動。
我參與中國女工的研究和服務(wù),就源于發(fā)生在東莞的1991年雨衣廠火災(zāi)和1993年的玩具廠火災(zāi)。當(dāng)時,我還是一名大學(xué)生,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xué)的一個社團(tuán)——國事學(xué)會,就是關(guān)心國家大事的意思。當(dāng)然,對于香港的學(xué)生來講,很難讓他們?nèi)リP(guān)心國家的大事。國事學(xué)會是一個比較關(guān)心內(nèi)地歷史文化的學(xué)生社團(tuán),而當(dāng)時的深圳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我們經(jīng)常去到深圳,就會看到一些問題。第一場火災(zāi)發(fā)生時,我還是一名本科生;第二場火災(zāi)的時候,我已經(jīng)是一個研究生了。當(dāng)時中國整個社會對這兩場火災(zāi)非常冷漠,很多人都不知道。媒體的報道,也只限于香港的一些小眾媒體,不是什么主流媒體。
中國南方的學(xué)者或?qū)W生,多是從那兩場大火開始參與工人運(yùn)動的,起步較早。可是,整個社會并不認(rèn)為那兩場大火多么重要,多么值得關(guān)注。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當(dāng)火災(zāi)發(fā)生的時候,我們幾個香港學(xué)生會組織的志愿者到火災(zāi)現(xiàn)場,當(dāng)時的現(xiàn)場和這本書形容的景象是一樣的,都有燒焦的、墜樓的尸體。工人之所以會被燒死,就是因為車間的門是鎖著的。實際上,全世界資本積累過程對人的傷害是一樣的,中國和美國在這一點上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分別。當(dāng)時中國的工廠不僅會把大門鎖上,還會把窗戶鎖起來,理由就是為了防止工人偷工廠的東西。在工廠方看來,把工人鎖起來是合法的,至少是合理的。
當(dāng)然,工人偷東西的現(xiàn)象是存在的,甚至是經(jīng)常的。但問題是工人為什么會偷東西。在《中國女工》里,有一個工廠是生產(chǎn)“大哥大”的,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哥大”售價在一萬五左右,而工人的工資每月只有三五百,對工人而言,任何一個零部件都是昂貴的。所以,工人如果有機(jī)會,就會偷倉庫里的東西,這其實是工人生活的一部分。臺灣、香港、日本的資本家發(fā)現(xiàn)了這種情況后,就是用把車間鎖起來的辦法來對待“野蠻”的中國工人或農(nóng)民工。我們看1991年的雨衣廠火災(zāi),有人會問雨衣廠有什么好偷的?如果我們到工人宿舍看一下,就會知道他們其實沒有什么生活資料,從工廠車間拿回一些零部件,就可以改造成一些生活工具。工廠資本家會非常警覺,動不動就搜身。搜身在《興邦之難》里也出現(xiàn)了。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工廠里,搜身普遍存在,今天,在一些惡劣的工廠依然存在。
當(dāng)然,我想討論的不是這些細(xì)節(jié),而是這兩場大火背后的歷史,以及整個社會對此的反應(yīng)。我這里主要講的是這兩場比較大的火災(zāi),其他的小火災(zāi)就不講了。當(dāng)時,我還是一名香港的學(xué)生,在同內(nèi)地學(xué)者、工會、婦聯(lián)的工作人員交流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們對此并不關(guān)心,而是將其視作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初期不可避免的“陣痛”,這種犧牲也被認(rèn)為是必然的。他們還勸我們香港學(xué)生對此不要太投入。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基本上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將村莊集體打破,制造出大量的農(nóng)村工廠;另一條腿是引進(jìn)大量的外資外企,這些企業(yè)和資本就吸納了大量的從農(nóng)村流動出來的新生代工人。






今天我們可以反思,這條路我們已經(jīng)走過三十年,九十年代初期是女工被燒死,而最近是農(nóng)民工的孩子自殺,這種犧牲迫使我們今天來思考是否可以調(diào)整發(fā)展的道路。我們的蛋糕越做越大,是否可以將一部分分給底層社會和工人階級,共同分享勞動果實。然而,從九十年代初期的兩場大火到最近四個留守兒童的自殺,我們在這方面并沒有太大的進(jìn)步。九十年代的火災(zāi)是資本家把工人燒死,還可以追究其責(zé)任,而今天富士康工人和留守兒童的自殺,則是自己傷害自己。
九十年代初期,一個工人外出打工的薪酬足以養(yǎng)活一個家庭,所以當(dāng)時是第一代農(nóng)民工,并不存在留守兒童或流動兒童。2000年之后,是第二代農(nóng)民工,出現(xiàn)了大量的留守兒童或流動兒童。原因就在于,一個人外出打工已經(jīng)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夫妻都出來打工,或者把孩子帶在自己身邊,或者把孩子留給家里有能力撫養(yǎng)他們的人。這造成了我們今天6100萬的留守兒童,幾千萬的分裂家庭,而這樣的犧牲帶來的傷痛并不比大火更輕。
九十年代初期,火災(zāi)后并沒有學(xué)者、律師或其他社會力量去推動改革,卻是幾個香港學(xué)生跑到意大利的品牌公司去追討賠償。我第一次去內(nèi)地的農(nóng)村,就是給湖北、湖南的農(nóng)民家庭送賠償款。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聽到農(nóng)民說要討回公道。那時候我才知道“討回公道”是一種普遍的話語。那么他們所說的“討回公道”是什么意思呢?在火災(zāi)發(fā)生之后,他們不可能跑到深圳的工廠去找老板,而是找當(dāng)?shù)氐恼⒋逦瘯N覀兡昧藥资f的現(xiàn)金,要送到一百多個家庭。當(dāng)時還非常擔(dān)心,會不會走到一半就會被(政府)抓了,然后送回香港,但是并沒有。那時的中國基層社會其實已經(jīng)處于半無政府狀態(tài)了,就像我們今天走進(jìn)中國農(nóng)村,根本沒人管。其中有個家庭,遇難者是一對夫婦,妻子懷孕,可以說是兩尸三命。他們的父母還很年輕,只有四十多歲,他們抓著我們幾個小孩子的手,要我們幫他們討回一個公道。我們就幫他們敲開了村委會的大門,村委會人員說自己的級別太低,管不了這個事,讓我們?nèi)フ耶?dāng)?shù)卣覀儚逆?zhèn)政府到縣政府,最后的答復(fù)是,火災(zāi)發(fā)生在廣東,湖北、湖南管不了。
所以,當(dāng)時中國的情況不是像《興邦之難》書中那樣,數(shù)萬人到現(xiàn)場吊唁,接下來是政府調(diào)查和社會改革,而是處于沒人關(guān)心、沒人管的狀態(tài)。當(dāng)?shù)卣沿?zé)任推給沿海地區(qū)政府,媒體不關(guān)心,學(xué)者也主要關(guān)心北方的國企改造。所以,東莞的兩場大火并沒推動整個社會的大變革,也沒有推動一場大規(guī)模的工人運(yùn)動的出現(xiàn)。有學(xué)者指出,1995年《勞動法》的出臺就是源于這兩場大火,而我對此是有疑問的,當(dāng)然我也不能否認(rèn)其同兩場大火沒有關(guān)聯(lián)。但是,1995年《勞動法》在出臺之后并沒得到充分執(zhí)行,因此,2008年才會出臺《勞動合同法》來推動執(zhí)行。所以說,當(dāng)時中國的情況,跟這本書里的情況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南方的NGO也是在九十年代后期慢慢發(fā)展起來的。NGO的形成顯示了工人力量的啟蒙和聚合。在美國,工人也是很清醒的,除了靠工人自己,不能靠別的勢力,因為別人是會出賣你的,比如上層社會出身的女權(quán)主義者最后讓工人運(yùn)動停滯不前。中國的農(nóng)民工、新工人更加明白:除了他們自己,還能靠誰。我們看到,因為南方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步早,也就比較早地出現(xiàn)了大量的自衛(wèi)性社會團(tuán)體。直到2000年前后,北京這邊才開始重視NGO推動勞工權(quán)益的保護(hù)。現(xiàn)在在北京會有一些社會組織幫助工人爭取權(quán)益。
所以,在這個時機(jī),出版《興邦之難》這本書非常合時宜。我們現(xiàn)在來反思,為什么中國社會對那兩場大火會如此冷漠?火災(zāi)發(fā)生之后,也沒有像美國那樣,組織一個專業(yè)的調(diào)查委員會。我們看到這本書中,他們甚至對調(diào)查委員會的人員構(gòu)成,即由立法人員還是社會人員組成,還發(fā)生了爭論,而在中國能夠成立一個調(diào)查委員會,我們就已經(jīng)很滿意了。鑒于中國存在著兩億七千萬的農(nóng)民工群體,我認(rèn)為出版界、學(xué)者、NGO 組織都應(yīng)當(dāng)以更大的力度參與到這場運(yùn)動中來,讓工人的力量從一種“自在”的狀態(tài)走向“自為”的狀態(tài)。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