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半月談刊文:超級平臺扼殺了什么
超級數字平臺在免費服務的基礎上,獲取穩定海量用戶,再通過投資、流量控制、支付、云計算、數據分析等基礎性服務控制合作經營者,借助超級平臺的地位形成數字革命時代的新型壟斷形式。依靠超級平臺,我國某些企業已占據互聯網社交市場99%以上市場份額,幾乎已不存在具有規模的競爭對手。它們利用先發優勢,直接使用屏蔽、封殺等多種手段排除、限制競爭對手,霸氣滋生戾氣。伴隨其日益強大,新創社交平臺被趕出市場的速度越來越快。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
以平臺治理的名義進行平臺競爭
具有高粘性海量用戶的超級平臺,成為整個數據市場流量壟斷的基礎。它們全方位打通社交、金融、搜索、電子商務、新聞、打車、內容分發、應用商店等賬號,是整個數據市場的流量入口。在排除社交市場的競爭后,它們依靠自身生態力量,在數據市場封禁其他平臺的企業協作及短視頻、支付、在線音樂、電商、API插件等產品的發展,引導消費者停止使用競爭對手的產品及服務。
個別超級平臺企業根據自身制定的所謂“外部鏈接內容管理規范”,對用戶行為進行“合規審查”,表面上屬于平臺自我治理,實際上是有選擇性地管理社交產品規則,優待自家產品,屏蔽其他平臺產品,對其自身投資的業務和其他企業持有雙重標準,對直接對手或未投資入股的潛在對手進行屏蔽封殺。
因此,這種封禁行為的本質是以平臺治理的名義進行平臺競爭,在平臺生態系統層面扼制其他數字平臺的業務,以穩固其在社交網絡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2
封禁損害消費者隱私權和選擇權
消費者支付數據來使用數字平臺的免費服務,但如果平臺合并產生數據集中及后續利用、分析,超出用戶原有授權范圍,改變對用戶隱私保護的承諾,則涉嫌違法。
2019年2月,德國聯邦卡特爾局處罰臉書(Facebook)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臉書向用戶提供免費社交服務,同時對廣告主提供精準營銷服務,通過收集用戶數據售賣廣告獲利。這違反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構成濫用市場力量行為。
某些企業給予用戶的僅僅是一項個人的、不可轉讓及非排他性的使用社交賬號的許可,社交賬號的所有權歸公司所有。企業認為用戶的頭像、昵稱等用戶數據都屬于公司的“商業資源”,并據此認為,除非公司同意,其他任何產品,即使獲得用戶授權,也不能使用這些用戶的相關數據,否則即構成所謂“非法使用”。
民法典第127條已明確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財產屬性。這些企業卻自設霸王條款,公然剝奪原本屬于人民群眾的財產,這不僅僅是對法律的公然蔑視,危害社會主義法治,更是剝削用戶的數據價值,完全無視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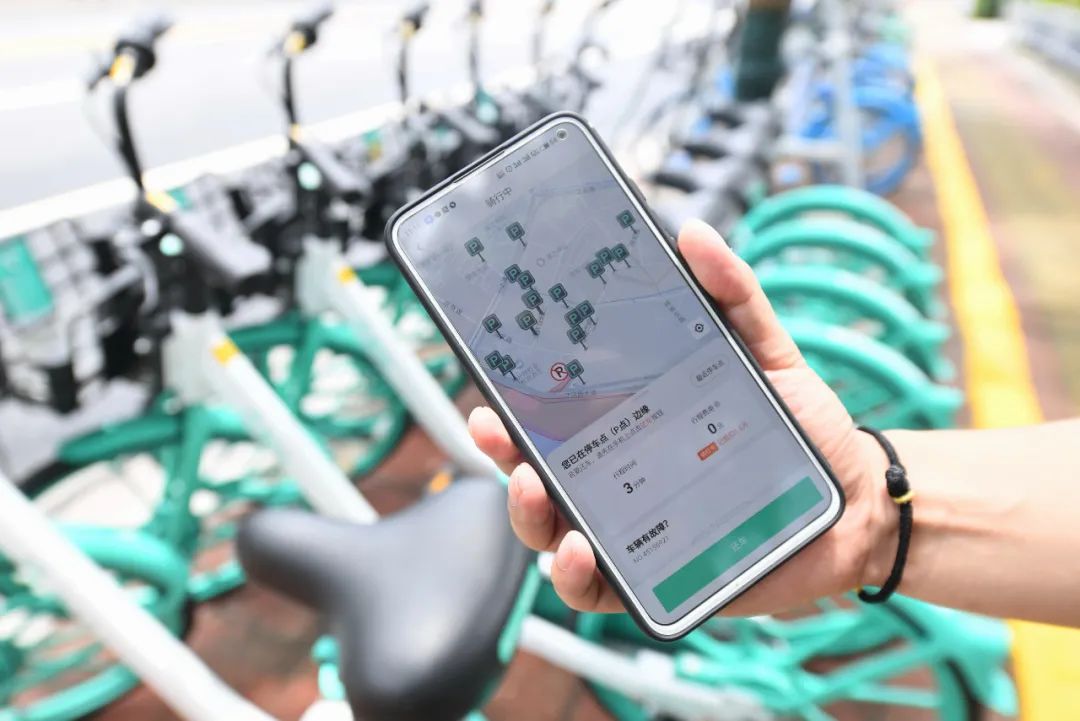
工作人員通過手機APP展示福州市臺江區一處共享單車指定停放點信息 林善傳 攝
此外,這些企業還通過抄襲其他經營者的新技術或新模式,成為互聯網社交、游戲和在線音樂行業的壟斷巨頭,通過自身強大資金和流量優勢推廣,迫使創新創業企業出局;與此同時,壟斷資源收購中小企業,將可能的競爭扼殺于萌芽之中,嚴重損害中小企業生存和技術創新。
對于中小企業而言,超級平臺是連接用戶和完成支付的重要渠道。但為了自身利益,超級平臺濫用制定和執行平臺規則的權力,無正當理由封禁中小企業,通過優待自身投資企業,打擊其他企業創新。超級平臺在數據市場的流量入口對中小企業創新具有重要作用,但它的巨額流量偏向于其投資聯盟的企業,資源的傾斜沉重打擊了公平市場的基礎,嚴重影響其他經營者的創新效率,并通過拒絕服務和形成交易封閉平臺,阻礙互聯網和技術互通產生創新。
2021年,根據某超級平臺公告,停止跳轉其他App的服務。這將推動該超級平臺成為一家獨大、自我封閉的超級數字平臺,妨礙中小經營者的技術創新,破壞國家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該超級平臺利用所掌握的規則制定權限制其他App跳轉,強制消費者只能使用自身平臺內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如此成為互聯網流量的終端。
3
封禁行為割裂數據市場統一
平臺經濟誕生了數字平臺這種新型市場主體,以微信、天貓為代表的數字平臺通過構建線上市場、撮合線上交易,開辟線下物流渠道,將傳統經濟無縫接入數字經濟市場,促進線上線下深度融合發展。但數字平臺的封禁行為會對實體經濟的生存發展構成影響,阻斷線上線下經濟的聯結,對經濟內循環發展影響重大。
超級平臺具備社交、宣傳、交易、支付等聚合功能,衍生為眾多線下經營者開展經營的“必要設施”。某些企業借助其在多個市場的寡占地位,建立了包含各行各業的龐大數字生態,但它們主導建立的生態是封閉和壟斷的。比如封禁企業協作軟件,禁止短視頻用戶進行游戲直播及上傳游戲視頻,打造超級生態壟斷和數據壟斷。這些封殺行為直接切斷了生態內外之間、生態與生態之間的聯接,阻礙了不同生態、產品之間的互聯互通,使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數據市場呈現割裂的局面,導致數據市場長久以來難以統一,嚴重阻礙形成強大的國內數據市場。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推動生產模式和產業組織方式的創新,使其能夠更好地適用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封殺行為阻礙其他經營者接入其平臺和數據,抹殺了可能由此帶來的行業創新,使更多初創企業的產品退出市場,限制數據市場百花齊放。
4
推動數據生產要素的開放與共享
不同于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的根本性變革,數據不僅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且是通過與傳統要素配合,催生了新經濟業態和經濟增長模式。隨著數據規模增加,從數據挖掘出的價值將呈現指數級增長。同時,數據非競爭性是平臺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獨占數據會損害數據的價值。在確保用戶初始權利的前提下,滿足數字平臺利用數據并受保護的需求,為數據共享、交易確立正當性權利基礎。
由于強大的網絡效應和規模經濟,在平臺經濟中增加了平臺收集數據的市場力量,利用市場力量擴大數字平臺生態,從而阻礙新進入者的創新。由數據爭奪引起的平臺糾紛早已屢見不鮮,從早期的“3Q大戰”、菜鳥順豐數據糾紛,到如今的平臺二選一、“頭騰大戰”、微信與飛書糾紛,其背后涉及的是數據的開放與拒絕使用問題。
數據的開放共享是實現價值最大化的內生要求。非競爭性意味著開放共享有利于數據要素的重復利用,在不增加成本的同時創造更大的遞增價值。零邊際成本是平臺經濟具有規模經濟的基礎,也是數字平臺向用戶提供免費商品的對價,突破了邊際成本遞增帶來的供給限制。鼓勵數據的開放共享將會極大地釋放平臺經濟的增長潛能。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其歸屬權尚待商榷的情況下,更應當推廣數據的共享,而非拒絕交易。
5
反壟斷執法須劍指超級平臺
當前,數字經濟平臺拒絕向第三方開放其所收集的數據,引發了諸多爭端,其他數據集難以同超級平臺所收集的數據集相競爭。針對此,可探索數據拒絕接入行為。這主要涉及上下游兩個市場,雙方在下游市場應存在現實或潛在競爭,并且充分考慮數據的生命周期以及相關產業和平臺的競爭方式,聚焦在數據的替代性、獲得性。同時,還應充分考慮數據與平臺相結合的新型競爭模式所帶來的外部性,以此作為衡量和判斷實行數據拒絕接入行為是否達到限制和排除競爭的效應,實現數據共享的規范化工作。

一名外賣配送員在張掖市甘州區街頭騎行 陳禮 攝
必須加強對互聯網企業數據壟斷的審查,明確反壟斷法重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包容審慎到全面監管階段,反壟斷執法也需要與時俱進。對數據流量、必要設施等涉嫌壟斷問題,應進行深入研討。反壟斷監管并非針對性抑制某些大型企業,相反是為調動、激活數據要素的市場機制,監管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經濟更好發展。
(作者楊東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臧俊恒系中國人民大學競爭法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刊于《半月談內部版》2021年第7期,原題為《霸氣滋戾氣:超級平臺扼殺了什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