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 | 香港儒家范瑞平:蔣慶是更純粹的儒家
【編者按】
自上世紀初以來,反對古代傳統文化成為中國現代思潮的發軔,其中占據古代 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更成眾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百年中,隨著傳統社會的瓦解,生活方式的變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煙往事,雖時有儒者賡續其 學、振發其旨,卻難挽其頹勢。然而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向傳統價值和傳統生活的轉向,所謂“國學熱”即其明證。一批被稱為“新儒家”的學者正努力應 對社會現實作出調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
儒家學說,特別是儒家的現代政治學說,在如今的中國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還是潛龍在淵,大有可為?為此,澎湃新聞陸續刊發對當代儒學學者的訪談與文章,以求展現這種社會思潮的大致輪廓,供讀者討論。
其中,身處東西交融的香港、接受過扎實的西方哲學訓練的新一代香港儒家學者會帶來怎樣獨特的視角?以下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方旭東,對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范瑞平,并授權澎湃新聞編輯整理首發。訪談稿已經兩位審閱。

家庭主義:是一家人“交流協商”,不應強調個人對于自己的事情擁有一種排他的、絕對的決策權
方旭東:你1979年上大學,才17歲。我認識一些學者也是78 、79級的,他們年紀較大,經歷較多。我聽有些學者講,他們甚至小學畢業就開始“放羊”了,自學較多。你好像受“文革”的影響和耽誤比較少。你基本上是靠正規的學校教育,還是也大量通過自學?
范瑞平:我覺得自學的成分比較大。我自己一直比較喜歡讀書。那時候也沒什么書好讀,主要是讀小說,尤其是革命小說,什么《野火春風斗古城》、《敵后武工隊》、《青春之歌》……即使這些在當時也被作為反動的、受批判的一類書,得在民間到處去找才能找到。
我上大學其實想讀文科。但我父母,特別是我爸爸,對政治運動深有體會,他說文科這東西沒什么用、太危險,你別學這個。我就很聽話,學理科,報考了醫科。當時我其實考得不錯,但體檢手指頭有點問題,所以到了包頭醫學院,成為那所學校當年分數最高的學生。
我的醫學學得不錯,但仍對文科有興趣,仍然關注文科方面的書。那時大概知道了文學不是文科的全部,還有社會科學。但還區分不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覺得哲學和社會科學大概都是一回事。碰巧1984年邱仁宗先生招醫學哲學研究生,我一看這個好像是文科,又是哲學,又有醫學,我覺得挺適合我。
那時我又跟父母商量,研究生我想考文科,考醫學哲學。我爸爸說:這方面現在你比我們懂得多,你要是覺得適合、有興趣,你就去學。我體會中國的家長絕大多數是通情達理的,不是要絕對說了算。我碰巧考上了,1984年就去中國社科院念了醫學哲學的研究生。
方旭東:你在選擇人生道路時,你父親對你的作用或影響大嗎?你剛才提到你的父母已經是比較開明的了,但至少在你考大學選擇文理科的時候,好像還是比較傳統的家庭氛圍?
范瑞平:確實是這樣。你知道我講生命倫理家庭主義,受到不少批評。實際上家庭主義是一種很有道理的決策機制:在人生的重要選擇上,如果一家人能夠共同商量、共同決策的話,比一個年紀很小的年輕人一意孤行要好得多。
當然這種家庭主義的意思是“商量”、是共同決策,不是說誰有一個絕對的決策權,不是說一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另一個人身上。我想對于青年人的專業選擇、婚姻選擇、醫療方式選擇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大選擇,家庭實際上能夠給予極大的幫助,不應該在這里走上極端個人主義的道路。
插一句,我昨天正好看了一檔關于張愛玲的節目。她二十來歲就顯示出很高的文學才華,但一下子被胡蘭成吸引住了。她當時就是沒有一個像樣的家庭支持,也沒有一個好的導師給她指點一下,她一意孤行嫁了這么一個人,其實把她后來的生活全毀了,令人嘆息。
方旭東:我覺得很有意思。你主張的家庭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些學者的看法是很不一樣的。你講到自己經歷中,兩次重要的專業選擇,一次是由父親主導,一次是自主決定。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同意在人還沒有完全自立的情況下,家長可以給予重大的建議或指導?你的孩子現在上中學,如果他們上大學或者選專業的時候,你會采取哪種方式?
范瑞平:我覺得有兩點很重要。第一,孩子越小,家長能起的作用越大,或者說家長的決策權越大。但第二點也很重要,那就是不能只看年齡,還應該看知識背景和人生經驗。
以前我爸爸跟我講,文科太危險,沒有什么東西好學,學出來也不知道能干什么,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因為當時他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等我大學上了五年,我說我要搞醫學哲學,我跟他講醫學哲學是怎么回事。他一聽就說,這個你知道的比我多多了,你考慮的也還周到,你覺得適合,就去做。所以我覺得,家庭決策一定要交流、商討,互相啟發,共同決策。
你問到我的孩子。我比我爸爸幸運,我的時間比他多,我和孩子的交流比較多。包括我和我太太之間,大家都是你擺你的理由,我擺我的理由,充分溝通。迄今為止孩子們還是覺得爸爸媽媽比他們知道的多多了,考慮問題也比他們全面多了。我覺得最主要是“交流協商”這件事,不應強調個人對于自己的事情擁有一種排他的、絕對的決策權。
個人思想轉向:從全盤西化到儒家認同
方旭東:你之前所學的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與一般意義上的儒學距離比較遠。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儒家發生興趣,去大量了解、閱讀的?
范瑞平:到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工作以后逐漸開始的。之前1984到1987年研究生階段主要是閱讀純西方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很激進的全盤西化的思想。
方旭東:當時時代就是那樣。
范瑞平:是,當時大家普遍都那樣。我記得甘陽好像有句話:“中國以后二百年的主要學術工作就是翻譯西方經典”,我們當時全是這種觀點。

方旭東:對,他當時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主要是翻譯西方經典。
范瑞平:當時只要有人來告訴你,西方的東西也有它的問題和缺陷,我們就反問:什么東西沒有問題和缺陷?我們要是能像西方那樣,就太偉大了——基本就是這個思路。
1987年畢業后,到了社科院,開始閱讀的東西多了,視域寬了。然后有了一些風波,我想那對中國當時的每一位學者都是極大的觸動。中國的路究竟應該怎么走?中國思想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思想?當時我們還被下放到基層去“了解國情”,我也到農村待了半年。這些經歷促使我反思,反思自己的父母是怎樣生活的,自己究竟贊成什么樣的生活方式。這個時候才去琢磨:以前讀過的那些中國哲學、中國倫理學,是不是更貼切我們的生活、更有道理?但那個時候還沒有根本的轉折。
1992年到萊斯大學,開始系統學習西方哲學。萊斯的學習壓力很大,兩年修15、16門課,必須修各種哲學課,不能只選你本身要做論文的相關課程。這帶來兩個好處。一是我發現以前在社科院學的西方哲學很不到位。盡管社科院的學者在中國都是一流的,但在出國學習以后,我覺得他們的西方哲學是有缺陷的。在萊斯那兩年我對西方哲學有了感覺,這在國內是不曾有的。第二個收獲是,真正理解了一些西方哲學以后,我發現這套學問和我安身立命的東西、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距離其實蠻大的。這就促使我進一步反思中國哲學、中國倫理學。后來回頭去讀更多中國哲學/倫理學,尤其是儒家的東西,體會就越來越深了。
概括說來,我的儒家認同之路大概開始于1987年在社科院哲學所工作的階段,發展于美國留學早期階段,基本確定于1995年左右。
方旭東:所以實際上,在你對儒家發生興趣的過程中,主要是自學的方式,并沒有受到某位當代學者或某本書的直接影響?你就是自己直接去看儒家經典?
范瑞平:是,我確實是這樣。后來在美國參加哲學學會,當代著名的中國哲學家大都接觸過、聆聽過、交流過,說不好哪個人對我有最直接的影響。
方旭東:那當時在中國社科院,李澤厚對你們的影響大不大?
范瑞平:李澤厚先生在前期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們在思想方面都受他影響。比如李澤厚先生讀了哪本書覺得不錯,我們都會趕快找來讀一讀。李澤厚先生本人的書,盡管我不是那個專業的,也會找來看一看。
方旭東:那么在美國,像杜維明、成中英,這些經常講儒家思想的華裔學者,他們的書和想法對你有沒有一些直接影響?
范瑞平:影響當然很多,但都比較零散。隨著我自己的反思,覺得中國的儒家倫理學跟現代西方強勢的倫理學、政治哲學,是有很大不同的。而以杜維明、成中英等先生為代表的這一代新儒家,基本上是在現代西方思想的套路中工作的。盡管他們的很多論證和觀點確實影響我們很多,但在總體上我越來越覺得現代西方這套東西是有問題的。
大概在2002-2003年,李澤厚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學做過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我們交流很多,我也明確告訴他我怎么看待他的一些問題。我說他受“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現代思想影響實在是太強了。當年李澤厚還受到批評,真是冤枉,因為他是真心實意相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我告訴他,我們儒家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我記得他臨走還跟我說:“瑞平啊,你太年輕了,儒家有很多不好的東西,你竟然沒有看出來”。我想大概我們已有了不同“范式”之間的區別吧。
方旭東:李澤厚的情況相對比較復雜。比如他當年與一些美學學者論戰,他其實是主張勞動創造美,是從實踐這個角度來講。但是,他同時又講“心理本體”,這就顯示出他的復雜性。我同意你關于李澤厚的看法,他受歷史唯物主義影響很深,在某種意義上,以前批他在某種意義上是冤枉了他。
范瑞平:我同意李澤厚先生具有復雜性。在我們的當代思想史發展過程中,能出他這樣一個才子、一個有思想創見的學者,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但李澤厚先生有另外一個問題。近些年來他提的那些新東西,包括“情本體”在內,有點“為新而新”的味道,既同自己的總體思想不銜接、不合拍,也與新的學術發展沒有關聯。你需要參考相關的學術發展。例如,現在的心理學、心理哲學,包括進化論的心理學、倫理學已經發達,提出了很有影響力的觀點和論證,你不必同意這些觀點和論證,但你如果根本不了解這種發展,你的觀點和論證就可能很難到位。

和蔣慶相比,李澤厚、杜維明的“儒家”都不夠純粹
方旭東:你剛才說在以儒家作為認同的過程中,受前輩學者的影響較少,即使有也是非常零散和間接的。大部分,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講法,就是“自得志”。
范瑞平:不過我受到一本書很大的影響——蔣慶的《公羊學引論》。
方旭東:那本書是哪一年的?
范瑞平:我讀的時候已經是九十年代后期了。
方旭東:也就是說你已經確立了儒家認同之后才讀的蔣慶的書。而像李澤厚、杜維明等,在你看來,好像他們都還不夠儒家?
范瑞平:他們是在現代西方思想的框架內工作的。
方旭東:就是不夠純粹。
范瑞平:對,跟蔣慶相比他們沒有那么純粹。
方旭東:你在1990年代末讀到蔣慶的書的時候,之前其實已經確立了儒家認同,所以是不是有如獲至寶、如獲知音的感覺?
范瑞平:我確實有這種感覺。但很難確定一個時間點,一下子就成為儒家了。因為儒學不像基督教,哪一天去接受洗禮,把腦袋泡到水里,就算一個基督徒了。儒學沒有這種儀式,很難說哪一天我就全部想通了。我在萊斯大學的博士論文主要是1997年寫的,那個時候盡管已有儒家認同,但我的思想還是很零亂的,只是在基本思想上已經覺得:我大概是儒家,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基督徒。
方旭東:在政治儒學方面,你好像曾經編過一本和蔣慶對話的書?
范瑞平:有兩本,一本名為《儒家社會與道統復興:與蔣慶對話》,另一本名為《儒家憲政與中國未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我為什么特別推崇蔣慶呢?因為我覺得他是真正不同于別人的。他既向西方的東西學習,又堅持儒家的天命天理天道,還能提出原創性的政治儒學。我覺得他的思想特別值得大家認真研究。
現在大概只有蔣慶、只有少數人認定儒學講的“天道”是一套真理,要從它出發來改革現代的制度,思考什么樣的政治原則和政治制度是符合天道的。這是一種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的進路。而其他更多人,可能都是自覺不自覺地采取融貫主義(coherentism)的方法,即先把儒學的基本信念打些折扣,同其他許多現代觀念融合一致,包裝一番,免得自己看起來太過保守、無知。
我覺得蔣慶的進路是更符合儒家的,儒家是基礎主義的,不是融貫主義的。

方旭東:國內現在對蔣慶的政治儒學爭議較多。你剛才主要談方法論,foundationalism你翻譯成“基礎主義”,國內還有可能不太好的翻譯翻成“基要主義”……
范瑞平:fundamentalism翻譯為基要派、基要主義,foundationalism還是翻譯為基礎主義。它們是非常不同的東西。
方旭東:你對蔣慶僅僅是方法論上的認同,還是說,對蔣慶政治儒學中許多具體的、特別是制度性的設計,也比較贊同?
范瑞平:要確立儒家立場的話,首先要真的接受儒家的一些基本信念,即有關天、地、人的天道信念。蔣慶認為儒家政治得有三重正當性,即超越的、歷史的、以及當下的(人心民意),這是政道的部分;他按照這些基本信念提出了三院制,名之為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這是治道的部分。這兩部分當然都可以討論,都有不少細節問題,爭議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認為這兩部分最好分開討論。現在最需要討論的其實是政道的部分,我們是否應該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些人把現代西方的政教分離原則信手拈來,說你還要什么“超越的”東西,這不是倒退嗎?似乎一句話就可以了結了。其實這是一種粗淺的融貫主義(coherentism),而且是食洋不化的融貫主義(coherentism)。
方旭東:我聽下來的主要印象是,你認為能夠被認為是儒家最基礎的東西,就是關于天道的這個部分。
范瑞平:儒家的天道廣義上包括地道、人道。
從儒家觀點看,應該如何進行醫療改革?
方旭東:那你真正開始用儒家的觀點做你的學術工作是不是在你到香港城市大學教書,也就是2000年之后?我記得你有一本關于儒家生命倫理學的書?
范瑞平:應該比這個早。例如我在1997年就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家庭決定還是個人決定:兩種不可通約的自主原則》,Bioethics期刊出的,基本是儒家觀點,直到現在那篇文章仍然是我所有論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應該說在1996年左右,我的轉向已經很明顯了,我大概知道博士畢業以后的學術工作會從儒學角度出發去做。
在這之后我寫了很多生命倫理學文章,主要脈絡都是比較自由主義的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的、自主的個人主義的倫理、政治進路,與儒家的更為和諧的、以家庭為基礎的、以美德為導向的人生理解、倫理價值之間的不同。
在這些論文的基礎上,我后來出了兩本書。一本是中文的,《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是英文的,Reconstructionist Confucianism,涉及范圍更廣的倫理學、政治哲學內容。
方旭東:我覺得你書中處理的主題,對我們今天大陸的儒學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補充和啟發。你可不可以大概分幾個方面來談談,你處理了哪些課題?在這些議題上,儒學和西方主流的處理方式/觀點有什么不同?
范瑞平:好的,先談《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這本書。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是有特點的。
一是儒家的家庭主義,反映在倫理方面,也反映在決策方面。我們看《五經》、《四書》、華人的倫理實踐,家庭人倫、共同決策乃是儒家倫理的基本特征,具有優異的道德價值和良好后果。但這些年來,我們在醫學倫理學研究上、在衛生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則是越來越向個人主義的路上迅跑。比如前幾年衛生部發文,醫療簽字必須個人簽,不能家屬代簽。但我們一直都是家屬代簽的,病人身體不舒服,又疼又累,家屬代簽是個很好的方式,既有利于病人,又體現家庭的完整性和道德性。如果想要避免濫用,可以要求當著病人的面簽,而不是非要逼著病人自己簽,實踐中也做不到。我們非要去趕個人主義道德的時髦,一方面表明我們對自己的道德文化失掉信心,另一方面也帶來不良后果。
二是關于市場和美德之間的關系問題。我所側重的儒學,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古典儒學,側重“制民之產”、自由市場、反對平均主義這些思想。例如我們國家整體上的醫療政策是,給醫生很低的基本工資,要求醫生不計報酬、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然后又給醫生發獎金,所謂“多勞多得”,甚至有紅包問題。這種政策從機制上歪曲了儒家所推崇的美德與利益(即所謂“義利”)之間的適當關系。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總想靠宣傳手段來解決倫理和公平問題,肯定是得不償失的。

方旭東:你說現在醫生工資很低,單純鼓勵他去講醫德,但他不得不通過多勞多得,甚至收紅包來提高收入。這是現在實際發生的情況,你覺得應該去改變。具體應該怎么去改變呢?這和美德倫理又是什么關系?
范瑞平:這涉及到經典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對于美德與利益關系的觀點。我的理解是,經典儒家絕對不會說,君子不應該去考慮利益,社會也不該給他們好的利益。孔子實際上是說,有德的人應該在社會上得到好的報酬、好的待遇,社會應該給他們與他們的德行相稱的收入,這樣才是公平的,同時也是對社會最有利的。
我們可以舉例說明。孔子那個時候,魯國有人當了奴隸,誰把他們贖回,魯國就給賞賜。子貢贖回兩個奴隸,但聲稱不要賞賜,孔子就說,以后不會有人再去贖回奴隸了。子路救了一個人,那個人要給他一頭牛,子路不要,孔子說,這樣人們以后不會積極救人了。孟子的一個學生挑戰孟子說,“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君子如此大陣仗,是否合適?孟子的回答是,關鍵在于合不合乎道,即是否公平。如果不公平,就是喝別人一碗粥都是錯的。對于報酬,孟子強調“食功”而不是“食志”的公平觀,即應該根據一個人的工作和成就來給他工資,而不是根據他的志向來給他工資,這樣才公平。醫生的志向應當是為病人服務,但你不能按這個志向來給他工資。如同孟子所言,小偷的“志向”就是偷一口飯吃,你給他嗎?你知道,那是《孟子》中很重要的一段,盡管很多人都忽視了。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徹底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思想。醫務人員經受那么多專業訓練,是精英人才,你給他兩三千塊錢,讓他好好為人民服務,這本身是不公正、不公義的做法,此其一。從效果上來看,他也不可能做到,因為他也有家庭、孩子,也要過像樣的、有尊嚴的生活。結果就是,說難聽點,產生一種很不誠信的做法,此其二。政策上允許發獎金,甚至把經濟指標分配到每一個科室去,其實就是鼓勵過度醫療,也造成了過度醫療,有百害而無一利,此其三。這個結果主要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是政策沒有理順“德”和“利”之間的關系所造成的。從儒家觀點出發,我們應當提高待遇,取消獎金。否則,醫療改革無法成功。
方旭東:你關于醫生待遇的見解,跟我想象中你的儒家式觀點很不一樣。我本來以為你會說,現在醫德太壞了,應該提倡醫生要為人民服務。沒想到你恰恰是說:不給人家醫生提高待遇,光講要提高醫德、為病人好好服務,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范瑞平:你知道,孔子這套東西一方面很平實,另一方面又非常全面、深刻。因為他是在對人的全面的把握上提出一套見解,從哲學理論上說可能不系統、不深奧,但實際上很全面、很有用。
方旭東:聽起來你在這個方面的觀點,主張市場,認為學醫的人付出了很多努力,是精英人才,社會應該給他們報酬、所得應該與之相應,這才是公平。這個和自由主義關于分配正義的觀點好像沒有太大的分歧。
范瑞平:其實當代的左翼自由主義有些傾向于平均主義。要是真的沒有太大分歧,那很好啊,說明好的東西可以被更多的學說理解和接受。
儒家如何看待基因增強和人工墮胎?
方旭東:好,這個我們可以再討論。還是繼續講《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這本書。
范瑞平:第三點是關于生物-醫學高技術的問題。這是現在生命倫理學領域人們關注比較多的問題,比如基因工程、基因增強之類。儒家應當怎么看這些問題,以及跟自由主義觀點的相通相異之處、跟基督教的觀點的相通相異之處?例如,我的關于基因增強的儒家觀點,就受到一些外國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我過于保守。
方旭東:你的大致觀點是什么?
范瑞平:我認為基因增強可以,但有兩個基本東西不能改變:第一,男女的不同,不應該抹殺掉。從儒學基本的理解上,有陰陽、有天地、有男女,這是天道的重要部分,即使技術上成為可能,也不要搞什么中性人,或要男性去生孩子,這些是不符合儒家的天道觀的。
方旭東:在這一點上,是不是可以說你和基督教的理解是比較接近的,特別是天主教?
范瑞平:可以這么說。
方旭東:你覺得在哪些問題上,儒家和天主教是有分歧的?是不是在一系列問題上,儒家和天主教的那種保守立場都是接近的?
范瑞平: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等我回答完第二個不能改變的基本價值以后再來講。
在儒家看來,后代是祖先饋贈的禮物(這一點其實同基督教的理解很不同)。儒家強調孝敬父母、尊敬祖先。假設你用基因增強的方式,要把自己孩子的個頭提高一點、智商提升一些,我看不出有什么問題;但你要把他們的皮膚從黃色變成白色、把頭發從黑色變成金色,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你做這個事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能想象的理由只能是,你認為白皮金發的人種比黃皮黑發的人種更美麗、更高級。這一理由不但是對自己的貶低,也是對祖先的不敬。這種轉變不同于你做美容、抹化妝品、用染發劑,那些都是暫時的、情境化的、相對的,是可以接受的小變化,因為不是基因上的徹底改變。人家批評我過于保守,但我的觀點只是像儒家說的:如果你信奉儒家價值,你就不應該去做那個事情。
方旭東:你現在可以把儒家和天主教的異同做個說明嗎?
范瑞平:天主教在當代基督教的大系統中并不是最保守的勢力。關于儒家和天主教的異同,我所知有限,只能簡單說說。盡管儒家的“天”有很強的人格化的意思,但也有很多面向;天主教的“天主”似乎是純人格化的,乃至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詳細的創世紀、原罪、救世主、受難、復活、再臨、天堂、地獄等等。儒家雖然相信超越的、主宰的天,但沒有這么詳細的東西,更多的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不會相信整個人類都是亞當、夏娃一對夫婦的子女相互(亂倫)結合的產物,而是傾向于未知人,焉知天,“未知生,焉知死”,乃至“盡人事,聽天命”。我的理解,儒家所信奉的天道、天理、天命的基礎性的東西就是“五經”中所顯示的那些卦象和禮儀,而不是天主教的“十誡”類的原則主義。
在人工墮胎問題上,我相信儒家和天主教有很大分歧。天主教相信每一個人的靈魂都是上帝直接賦予的,這才是你的人之為人的尊嚴所系,父母不過是個媒介。因而墮胎是絕對的邪惡,不但強奸導致的懷孕不能做,而且為了搶救孕母的生命也不能做。儒家則是持有一個更加家庭主義的倫理路線,墮胎是不好的,但有時是應該做的,提供的是一套基于儒家美德的論證。犧牲胎兒挽救母親,在儒家不會成為一個道德問題。
反思對儒學的妖魔化和殖民化,提倡重新構造儒學
方旭東:我感覺這和你之前講的醫生的待遇的問題,有某種共同的、一致的方法論的考慮在里面。現在你能否介紹一下你的英文書,譯成中文是《重構主義儒學》。什么叫重構主義的儒家?哪些地方是要重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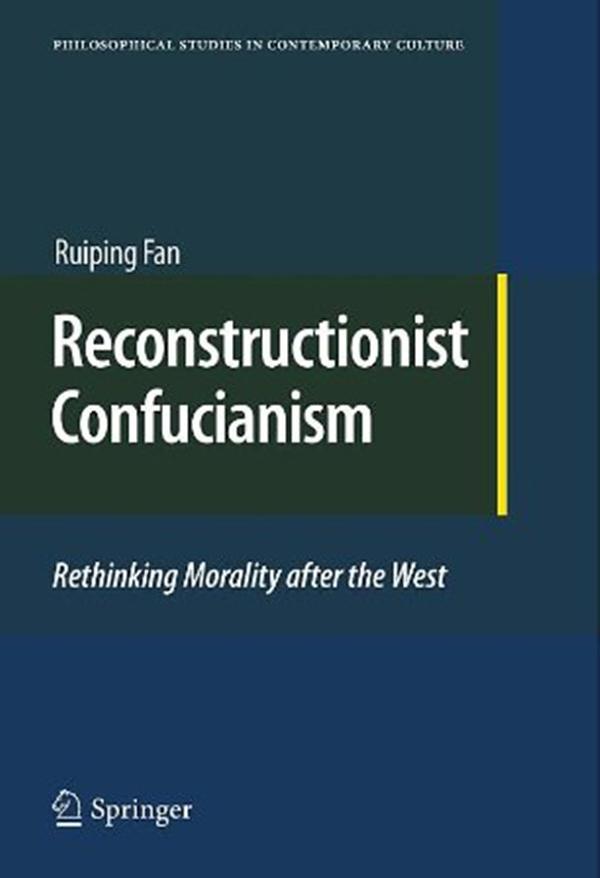
范瑞平英文著作Reconstructionist Confucianism
涉及范圍更廣的倫理學、政治哲學內容。范瑞平:重構主義儒學,為什么要“重構”呢?是因為二十世紀以來,儒學發展的兩大傾向很明顯。一個我稱作妖魔化儒學,就是以“五四”為代表的,當然不是說“五四”所有學者都持這個觀點,但基本上認為儒學是一個落后、反動的東西,要打倒“孔家店”,妖魔化儒家,說禮教是吃人的。
另一種傾向可能在海外更厲害一些,就是殖民化儒學。殖民化儒學并不排斥儒學,而是用現代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這些觀點來重新解釋儒學。以牟宗三先生為代表,他們認為儒學不但是和民主、平等沒有本質上的分歧,而且儒學有內在的理路必然發展出這些東西來。我認為這是一個殖民化的思想。因為你這樣講的儒學其實是把儒學最基本的概念、觀念和思想扔在一邊,然后拿另一套東西來改造了它,就像是我把外面的人殖入一個地方并成為那個地方的主流一樣。當然,儒學的核心觀念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西方觀念的相互關系,則是另一個問題。
《重構主義儒學》是說這兩個傾向都不合適,我們要從經典儒家出發,來重新構造儒學。這是一種基礎主義的儒學,涉及許多領域的工作。近十年來,我和香港浸會大學的羅秉祥、陳強立、張穎,組織“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學術活動,走的就是這種基礎主義的路子,雖然我們不限于儒學。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能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心理學等領域做這項工作。
儒家的行為,首先是禮儀指導的,而不是原則指導的
方旭東:最后,你是否可以介紹一下你對儒家的“禮”的理解?我記得這方面,好像同你講儒家基礎主義一樣,你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改變的。
范瑞平:非常好,旭東兄,我發現你提的問題一方面是重要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你對我的東西有所了解,讓我有點驚喜。
實際上我那本英文著作中有三四篇是講“禮”的。在這方面,李晨陽和我有過深入的爭論。在我看來,儒學是基礎主義的,但其基礎不是柏拉圖的“理念”、畢達哥拉斯的數,也不是基督教的原則——例如“十誡”,更不是當代政治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而是“五經”中所呈現的那些卦象和禮儀。就家禮而言,我們有相見禮、冠禮、婚禮、葬禮、祭禮等等,每一種禮都蘊藏著一系列構成性規則。比如過年了,我給母親鞠躬拜年,這是構成性規則指導的適當行為。所以儒家的行為,首先是禮儀指導的,而不是原則指導的。但現在的倫理學以及政治哲學,講的是原則主義:我給你一條或幾條調節性原則,你必須按這些原則去做。你傳統的禮俗也好,習慣也好,制度也好,機構也好,都要符合這些原則,否則就要改變它,即使不革命,也要改革它。我把這種思想叫做“單元指導主義”,就是說我的這套原則是唯一的、最終的指導。
按照儒學的思路,我們至少應當是雙元的指導。禮儀告訴我們做什么(過年了,要給長輩鞠躬拜年)、調節性原則告訴我們怎么做(如敬:恭敬地做)。禮是不是不可改變的?當然不是。如你所知,《論語》中既有孔子贊成的改變,也有他不贊成的改變。他贊成將麻冕禮帽改為絲綢禮帽,但不贊成免除祭祀用羊;他不贊成改變“三年之喪”,但也不提倡社會強制,而是留給個人的“心安”。是否贊成改變,我覺得孔子考慮的是整個禮儀制度的意義、價值和精神,而不是遵循外在的調節性原則來改變。
方旭東:那我們怎樣算是盡了待客之禮呢?用王陽明的話來說,我們如何評價一個人“知禮”?比如說有客人來,主人拿最好的東西招待他;還有一種,家里吃什么,也給客人吃什么;還有就是,看客人想吃什么就給他什么。那么以上三種人,我們如何判斷哪一種人是所謂的“知禮”,實踐了“禮”?這里面就會涉及到他們的原則的問題。
范瑞平:是,這里好像有三種原則:最好標準、家人標準、客人標準,應該應用哪種?這個問題我沒有完全想好,我只能給你初步的回答。
首先是“最終的標準是什么”這個問題。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講到的融貫論和基礎論的不同。融貫論說沒有最后的標準,你把所有的道德信念、重要的判斷加在一起,你看什么最融貫什么就是標準;但儒學屬于基礎論,還是有一些更具權威性的道德信念,它們可能屬于儒家禮儀系統中的核心的構成性規則,不應該改變;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去琢磨,儒家待客之道到底意味著什么、價值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哪些原則更有助于這些意義、價值和目的,等等。第二,不是所有問題在所有時候都能爭論清楚的,儒家社群也肯定需要一些程序化的東西,只要存在一個所謂儒學共同體,它里面肯定會有一些結構,比如有些人可能更有道德權威,或者有委員會或者其他組織來做決定。總之,有些問題可以實質性解決,有些問題大概只能程序上解決。如果有些問題不那么重要,留待各家各戶各人自行其是也可。你覺得如何?
方旭東:好的,明白。所有的討論都不可能一次性終結,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里,瑞平兄,以后有機會再繼續向你請教。
范瑞平:謝謝!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