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香港儒家陳祖為:我的課題不是反現(xiàn)代,是怎樣面對現(xiàn)代
【編者按】
自上世紀(jì)初以來,反對古代傳統(tǒng)文化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潮的發(fā)軔,其中占據(jù)古代 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儒家思想更成眾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百年中,隨著傳統(tǒng)社會的瓦解,生活方式的變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煙往事,雖時有儒者賡續(xù)其 學(xué)、振發(fā)其旨,卻難挽其頹勢。然而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一種向傳統(tǒng)價值和傳統(tǒng)生活的轉(zhuǎn)向,所謂“國學(xué)熱”即其明證。一批被稱為“新儒家”的學(xué)者正努力應(yīng) 對社會現(xiàn)實作出調(diào)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國現(xiàn)代化的思想資源。
儒家學(xué)說,特別是儒家的現(xiàn)代政治學(xué)說,在如今的中國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還是潛龍在淵,大有可為?為此,澎湃新聞陸續(xù)刊發(fā)對當(dāng)代儒學(xué)學(xué)者的訪談與文章,以求展現(xiàn)這種社會思潮的大致輪廓,供讀者討論。
其中,身處東西交融的香港、接受過扎實的西方哲學(xué)訓(xùn)練的新一代香港儒家學(xué)者會帶來怎樣獨特的視角?以下為華東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方旭東,對談香港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行政學(xué)系教授陳祖為,并授權(quán)澎湃新聞編輯整理首發(fā)。訪談稿已經(jīng)兩位審閱。
陳祖為,香港人,1960年生,從本科至博士研究生先后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xué)(BSocSc)、倫敦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院(LSE)(MSc)、牛津大學(xué)(DPhil)。1990年起任教于香港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要教授政治學(xué)理論,研究領(lǐng)域為儒家政治哲學(xué)、當(dāng)代自由主義與至善主義、人權(quán)、公民社會。在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等專業(yè)期刊發(fā)表論文多篇,著有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1999-2000年在哈佛燕京學(xué)社訪問。2002-2004年、2011-2013年任香港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

認(rèn)同基督教、儒家、亞里士多德等古典的觀點
方旭東:陳教授你好,首先請你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學(xué)思?xì)v程。
陳祖為:我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政治與行政系念的大學(xué),主修政治,輔修哲學(xué)。當(dāng)時我已經(jīng)對政治哲學(xué)很有興趣。后來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做政治哲學(xué),是不是真的有興趣,所以本科畢業(yè)就去倫敦政經(jīng)學(xué)院讀了一年政治哲學(xué)的碩士,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走這條路是對的。
我那時開始全面認(rèn)真地讀政治哲學(xué)的經(jīng)典,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直到羅爾斯這些人,就發(fā)現(xiàn)我對古典政治哲學(xué)的觀點很有同感。我念亞里士多德的Nichomachean Ethics(《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和 Politics(《政治學(xué) 》)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很多觀點與我的想法很相近。比如他將政治與人的美好生活連在一起,他說城邦是要去幫助人過一個美好的生活,我就覺得這個是對的。
我就想為什么我會這樣想,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我以前是一個基督徒(現(xiàn)在不是),所以我對virtue(德性)、對一個社會環(huán)境怎么樣影響一個人的道德和美好生活比較重視。另外本科時我也念過一些中國哲學(xué),我就覺得儒家跟這一套也是很相似的。所以我對基督教、儒家、亞里士多德這種比較古典的、前現(xiàn)代的一些觀點就比較認(rèn)同。
后來我申請到太古獎學(xué)金,就去牛津Nuffield College念書。到牛津我就念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xué)。本來我是想比較亞里士多德和 Thomas Hobbes(霍布斯)的,后來發(fā)現(xiàn)太難了,就單單做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xué)。但是我只去了兩年,當(dāng)時香港大學(xué)就有教師位子空出來了,我就申請,他們就請我,也不要我先完成我的thesis(論文),所以我就可以回來一邊教書一邊寫完我的博士論文。往后幾年的暑假,我都返回牛津見導(dǎo)師和寫論文。
我研究亞里士多德也不是純粹的政治哲學(xué)史,我的論文一半是重構(gòu)哲學(xué)史,另一半是用當(dāng)代的政治哲學(xué)方法來探討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xué)的基本觀點能不能成立。所以是將哲學(xué)史和政治哲學(xué)方法兩方面結(jié)合來做。
一直到那個時候我還沒開始做儒家政治哲學(xué),都是西方為主。
方旭東:你是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念的本科。我們知道,香港中文大學(xué)是由新亞、崇基、聯(lián)合(書院)組成的以中文為主的學(xué)校,新亞書院還被稱為港臺新儒家的大本營和發(fā)源地。那么,你當(dāng)時在中文大學(xué)念哲學(xué),是不是很自然地和那些新儒家有接觸?
陳祖為:我是1979到1983年讀的大學(xué),已經(jīng)很遲了,并沒有經(jīng)歷過唐(君毅)、牟(宗三)的時代。我只聽過牟先生回校來講座,但我完全聽不懂牟先生的口音。而唐君毅1978年就過世了。錢穆也已經(jīng)離開香港去臺灣了。所以我并沒有直接上過他們的課。
給我們上中國哲學(xué)史的是唐端正,而唐端正是唐君毅先生的學(xué)生,所以講課的時候他會講一點。另外我念了很多唐、牟的書,像牟宗三的《中國哲學(xué)的特質(zhì)》,還有他的宋明理學(xué)著作;唐君毅的也看過幾本書,像《人文精神的重建》、《中華人文與當(dāng)今世界》、《人生之體驗》、《中國哲學(xué)原論》這些都看一看。所以我當(dāng)時對他們做什么有一定的了解,但不能說很熟悉。我當(dāng)時的興趣還是更多在西方政治哲學(xué)。
方旭東:大概從什么時候開始,你的研究興趣有意識地從西方哲學(xué)轉(zhuǎn)向了中國方面呢?甚至用儒家思想來展開自己的研究?
陳祖為:我本來想到50歲才開始研究中國的,因為我想在西方政治哲學(xué)打下很好的基礎(chǔ)。但是1990年我就回來香港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行政學(xué)系教書了,有很多機(jī)會要參與學(xué)術(shù)會議。我記得好像在1992-1993年,新加坡、馬來西亞就開始講“亞洲價值”了,后來中國也講一點。有些這方面的國際會議在香港召開,我就被委派做評論,給西方學(xué)者的評論。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問,從中國文化的角度,Asian values(亞洲價值)講不講得通?我的著作就開始寫這些。之前都寫西方的,后來就開始寫Asian values,Human rights(人權(quán))。因為外國人會來問你們怎樣看Asian values,我不能說我不知道,于是這就提到我的研究計劃里面了。
我記得參加了一個這樣的會議,是Daniel Bell參與組織的一項頗具規(guī)模的國際性“三年計劃”,為了出一本書開了三年會,書叫The East Asia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東亞對人權(quán)的挑戰(zhàn)》),1999年劍橋大學(xué)出版的。收錄其中的,是我第一篇從儒家角度去看人權(quán)是怎樣一回事的文章,從1996年開始寫的,所以我正式開始寫儒家的東西是1996年。
這篇文章直到今天仍是我個人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有關(guān)儒家的文章,標(biāo)題叫“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除了中國搞儒家政治哲學(xué)的人,西方研究人權(quán)的人也看的,后者要處理人權(quán)跟相對主義的時候,需要看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儒家是其中一個。那一篇文章也不是所謂哲學(xué)史的角度,而主要是基于孔孟的思想來看“人權(quán)”。此文1999年出版,在那之前之后我已經(jīng)開始探討其他問題了,民主、自由、包容、社會公正,一路研究下去。
1999到2000年我有休假,就去了哈佛大學(xué)1年。那時我就決定要寫一本書,一本全面重構(gòu)儒家對一系列根本政治問題的看法。我以為我可以用一兩年寫出來,但一寫就寫了十多年。最后2014年才出版,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我的方法,用英文講是inductive(歸納的),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看的。是拿一個政治概念比如“人權(quán)”,然后就問這個概念簡單的公認(rèn)的定義是什么。然后問儒家先秦經(jīng)典在哪里可以提煉一些看法,每一次我起碼都要看《論語》、《孟子》、《荀子》三本書,由頭到尾,都要看相應(yīng)的章節(jié)。提煉之后我就問這個看法好不好,需不需要修改,它跟西方看法有什么不同,西方的觀點又是否可接受。最后提出一個我認(rèn)為在哲學(xué)上可以辯護(hù)的儒家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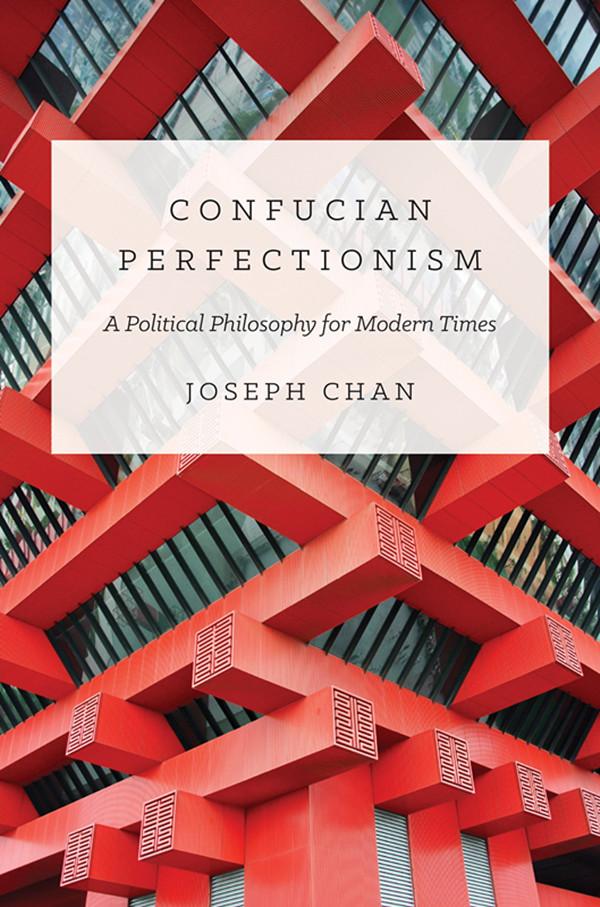
我的課題不是要反對現(xiàn)代,而是怎么樣去面對現(xiàn)代
方旭東:有一種說法是:像你剛剛提到的民主、自由、社會公正等等,都是所謂西方價值,而儒家有自己所珍視的不同價值。那么在你看來,儒家對于所謂的西方現(xiàn)代價值,整體上是可以融合、吸納的,還是根本就是兩回事?
我這樣問的背景在于:所謂港臺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唐君毅這一代,基本上有一個觀點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是應(yīng)該跟民主、自由、人權(quán)結(jié)合起來的,而且儒家傳統(tǒng)里面可以發(fā)掘出這樣的東西。而晚近幾十年,大陸出現(xiàn)了以蔣慶為代表的新儒家,認(rèn)為牟宗三的想法是承續(xù)了“五四”的思路、是跟在西方價值后面去跑,即所謂“西方民主自由的啦啦隊”。蔣慶代表的那部分大陸新儒家會說,人權(quán)、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的價值,我們?nèi)寮抑v禮、講三綱五常,這才是儒家應(yīng)該講的東西,我們不需要西方的民主自由,我們更不需要論證我們的理論可以開出這樣一些東西。你在做了非常細(xì)致扎實的概念梳理、研究和比較后,不知對此怎么看?
陳祖為:港臺新儒家有兩個不同的命題,我同意第一個,不同意第二個。
第一個是說,中國文化要和西方文化結(jié)合。這個結(jié)合觀,我在書里也是這樣講的。但是我講的結(jié)合,最重要是儒家價值跟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結(jié)合,而不一定要全面接受西方制度背后的政治價值。這個跟港臺新儒家有一些不同。
第二個命題,是他們在《中國文化宣言》里面說,在傳統(tǒng)儒家文化里已經(jīng)有所謂民主思想的種子。這個我不同意。我認(rèn)為民主、自由、人權(quán)的西方價值在儒家思想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儒家會不會排斥這些?那就要看是哪一種自由,哪一種民主的價值,哪一種權(quán)利的觀念。有一些它會排斥,有一些它不會排斥。我的任務(wù)就是選取一些好的價值表達(dá),跟儒家的價值結(jié)合。有一些西方的價值,儒家是不會接受的,哲學(xué)上也不應(yīng)該接受的,我就排除。比方說,“主權(quán)在民”。政治上平等作為一個道德的原則,不是一個制度的原則。自由看成個人的主權(quán),或者是個人的擁有權(quán)。儒家不能接受一個以權(quán)利為基礎(chǔ)的政治哲學(xué)的方法(right-base political thinking)。如果這些價值是以一些很基本的天賦人權(quán)、道德人權(quán)為基礎(chǔ),儒家可能會對這些有很大保留。
所以儒家能夠提出它自己的基礎(chǔ),去跟自由民主制度融合。比方我們不用講“主權(quán)在民”,我們可以講另外兩方面:儒家的思想就是當(dāng)政者要為人民服務(wù),人民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當(dāng)政者要獲得人民的真心的同意支持,需要人民與當(dāng)政者是一個互信(mutual commitment)的關(guān)系。這兩個是構(gòu)成儒家政治權(quán)威的基礎(chǔ)。一個我叫作service conception,一個叫ethical relationship。這兩個是儒家本身有的價值,不是西方的,它已經(jīng)可以讓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去接受民主制度。但這兩個觀點會對西方的民主制度提出一些在運作和設(shè)計方面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的書要提出一些制度設(shè)計上比較符合儒家的看法。我的理想就是這樣的。
那么實行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就是“西方民主的啦啦隊”?這個名詞不太好,但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自由民主是一個基本的制度設(shè)計,這是有它重要理由的,而不是因為西方的就是好的。主要是兩個理由,一個是外在的理由,一個是內(nèi)在的理由。
外在的理由是,我們已經(jīng)進(jìn)入一個現(xiàn)代社會/時代,這個現(xiàn)代時代已經(jīng)沒有傳統(tǒng)的社會制度,沒有掌管一切的宗教教會、教皇,在中國已經(jīng)打破了儒家的教化制度、宗族的權(quán)威、皇帝的權(quán)威,這些都沒有了。經(jīng)濟(jì)上的現(xiàn)代是指市場經(jīng)濟(jì),每一個人都自己籌劃自己的生活,沒人可以指正你。第三個方面,韋伯說現(xiàn)代是一個價值多元社會,沒有一個獨大的意識形態(tài)可以告訴你怎么樣去生活。還有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人們的流動、職業(yè)和居住的地方,以及旅游很多。所以自由就是一個根本上的事實,你無法不配合這個事實。
內(nèi)在理由是,儒家解決不了在上的人不夠有德性的問題,和貪污、濫權(quán)沒有好的管制的問題。它執(zhí)迷所謂“大一統(tǒng)”的思想,不能分權(quán),即皇帝最高,天子不能放權(quán)。所以它解決不了精英缺乏制度上的限制的問題。它也不能接受法家用很重的刑罰和獎賞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背后不能接續(xù)它對道德人格的理想。我就提出,民主制度跟自由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是儒家過去想不出來的。
方旭東:那么有一些人就會說,面對這樣一個“現(xiàn)代”的事實,我們恰恰要恢復(fù)原來的東西,如今正是被現(xiàn)代性搞得亂七八糟,所以我們現(xiàn)在不是要順著現(xiàn)代性,而是要逆著現(xiàn)代性。同樣一個事實,并不一定能推出我們就應(yīng)該迎合現(xiàn)代性,有人會說我們應(yīng)該回到原始的儒家,更加fundamental的儒家。
陳祖為:我的回應(yīng)比較簡單。我從來不覺得往回走是一個現(xiàn)實上需要嚴(yán)正考慮的alternative(選項),因為我覺得不可能,不能走回頭路。
你看中國的發(fā)展,政治上是要保守,但經(jīng)濟(jì)上仍跳不出市場經(jīng)濟(jì),人們做什么職業(yè)、在哪里住,基本全都自由了。這個自由人有時候不會那么容易被取消的。所有制度都在推動這個社會里人的流動、個人的發(fā)揮,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已經(jīng)是不能改變的了。如果我們能夠回去的話是不是最好,這是另一個問題。但事實上我是覺得不能回頭了,totally unrealistic(完全不現(xiàn)實)。
當(dāng)然,我也不是說現(xiàn)代的都是好的,或者西方的現(xiàn)代性就是唯一的現(xiàn)代性。外國的學(xué)者比方說是S.N. Eisenstadt(艾森斯塔特),他們提出multiple modernities (多元現(xiàn)代性),后來杜維明也用這概念。我基本是同意的,現(xiàn)代性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文化系統(tǒng)里發(fā)生的變化有所不同,面貌也有所不同。我的課題不是要反對現(xiàn)代,而是怎么樣去面對現(xiàn)代。我的工作就是將古代的一些精神價值,跟現(xiàn)代的制度和價值連結(jié),找一個比較平衡的modernity(現(xiàn)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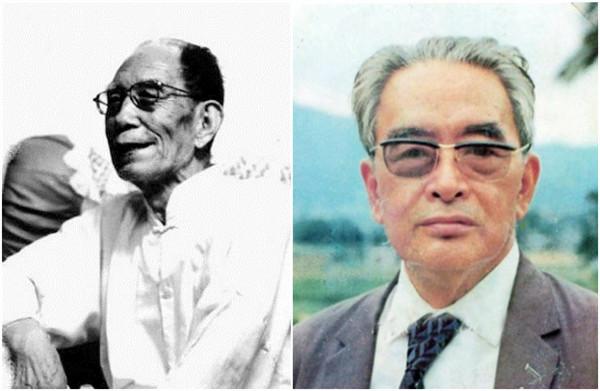
儒家注重用人的道德動機(jī),不能接受法家式太嚴(yán)厲的懲罰、太多的獎賞
方旭東:我注意到你對中國儒家的一個整體上的重新思考和重構(gòu),是從政治權(quán)威開始的,我覺得這是非常關(guān)鍵的政治哲學(xué)問題。而且也正是在這里,儒家可能有它自己的某種堅持。
前段時間李光耀去世,中國國內(nèi)學(xué)界也在熱烈討論。討論李光耀,其實就是在討論新加坡的模式,就會講到威權(quán)政府。有提法認(rèn)為新加坡是威權(quán)政體,而同時新加坡的人民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很富裕,現(xiàn)代化程度也很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說政治上能夠沒有西方式的民主(因為顯然新加坡和地道的英美議會民主不一樣)?西方民主制度對儒家來說是不是必需的?
陳祖為:不是必要的。我剛才說儒家政治權(quán)威有兩個基礎(chǔ),service + relationship。我可以想象有其他的制度如果運作好的話,可以同時滿足這兩個。所以我告訴你的是,民主不是唯一滿足這兩個要求的。再退一步,一個皇帝,一個很好的、賢能的皇帝,他也可以解決人民幸福的問題,又可以獲得人民的信任,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來說我覺得在制度上這需要滿足很多條件。我覺得給皇帝一個制度,能夠在制度上多一點的表達(dá)信任。因為從service來說,民主制度下如果service不好的話,人民可以不投票給執(zhí)政者;從relationship來說,投票就是去表達(dá)信任的最明確的一個方法。當(dāng)然有其他方法去表達(dá),比如李光耀過世,很多人出來哭,也表達(dá)了很多的信任。
新加坡的service做得很不錯,但relationship是不是真的很好呢?我覺得儒家也會對它有所批評的。有兩個批評的方面,第一就是對所謂異見分子,處理的手法太兇,讓他坐牢、干涉他們的反對,政治言論自由不夠。真正儒家的圣王或賢能,不怕反對,也不會意見不同就讓人坐牢。所以relationship部分在新加坡包含壓制的元素,跟儒家的理想有一段距離。第二點是,新加坡過去二十年,他的領(lǐng)導(dǎo)產(chǎn)生雖比較注重賢能,但是他們的工資世界最高。按照儒家賢能的理想,用錢才能留住人是不好的。
方旭東:你的意思是,儒家認(rèn)為不需要付給賢能的人最好的報酬?
陳祖為:需要好報酬,但不需要最好。你看,新加坡政府官員會認(rèn)為,比如我是商業(yè)部長,我管這么多的機(jī)構(gòu),那些CEO都是年薪一兩千萬,我怎么可以兩三百萬呢?我起碼要跟他們差不多,才能有地位跟他們談判。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是儒家的觀點,而是法家的觀點。所以新加坡的統(tǒng)治方法,其實有很多法家的內(nèi)容在里面。
方旭東:新加坡一貫以來講高薪養(yǎng)廉,這和香港也有相似的地方。現(xiàn)在政府官員貪污,在中國也是一個非常現(xiàn)實的問題。是不是說新加坡的高薪養(yǎng)廉,你認(rèn)為是不可取的?
陳祖為:那倒不是。我是說新加坡不是高薪養(yǎng)廉。開始的時候是的,但現(xiàn)在不是了。香港政府的工資也不低,但新加坡是香港工資的三倍,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養(yǎng)廉的問題了,他們要的是recognition。商界的巨頭拿這么多工資,我們官員怎么能少他們這么多,我們是政府的CEO,權(quán)比較大。所以他要equal recognition,recognition of power, recognition of ability。這是merit(應(yīng)得),完全不是養(yǎng)廉。
方旭東:我之前正好和范瑞平教授有一些交流。我們談到一個不完全相同但相關(guān)的問題,他就講到醫(yī)院的醫(yī)生收紅包。范教授的一個基本看法是,醫(yī)生怎么說也是社會的精英,受那么多教育,工作量也很大,他們應(yīng)該得到一個非常值得的報酬。當(dāng)然他并沒有直接說新加坡這種高薪給政府官員的做法就是對的,但是他提出來一個講法:儒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支持給有德者相應(yīng)的地位或者說報酬的。
陳祖為:我不反對。但他這個“相應(yīng)”的程度不能太離譜。我們知道儒家很注重用人的所謂動機(jī),moral motivation(道德動機(jī))。你要信任那些人是為人民服務(wù)的吧?如果你用這么高的薪水,那么你信任的人可能就不是出于真心為人民服務(wù),而是為了錢去做這個事情的。這個在賢能方面是有差別的。我不是說我們要給很低的工資,但是新加坡的例子是太離譜了。所以過去這四五年,新加坡人民開始不同意了:為什么要給官員這么多錢?后來政府就下調(diào)了一點。大陸則是另一個極端,完全不理物質(zhì)的要求。
而我整本書的理論方向就是所謂dual perspective(兩重的觀點)——即現(xiàn)實與理想的連結(jié)。我們需要提出一些可能的辦法去解決現(xiàn)實的問題。所以一定的懲罰、一定的獎賞都是需要的。因為現(xiàn)實的人不全是圣人。但如果只談賞罰,成了唯一最重要的moral motivation,那就有問題了,那就是法家了。儒家就不能接受法家,儒家不能接受太過嚴(yán)厲的懲罰、太多的獎賞,因為那會改變?nèi)藗兊赖碌呐囵B(yǎng),否定儒家的道德理想。所以dual perspective就是如何能將現(xiàn)實的辦法,放到儒家的理想里面去重新結(jié)合起來。

民主制和賢能君主制,孰優(yōu)孰劣?
方旭東:剛才我有一點沒有太明白的地方。你講民主不是唯一滿足好領(lǐng)導(dǎo)者要求的制度,也承認(rèn)如果賢能君主能滿足service和relationship兩個要求也是OK的制度。所以從理論上來講,你是不是也同意國內(nèi)有些儒家學(xué)者說的,回到所謂君主立憲的思路上去?國內(nèi)學(xué)者最近兩年有在講所謂“康黨”,甚至還有往前推得更厲害的,推到霍布斯那兒去了。所以在你看來,民主制度是比賢能君主制度要好一些,還是說這兩個沒有高下之分?
陳祖為:在理想情況下,如何比較是一個很奧妙的事。很多人將賢能政治最好的狀態(tài)和現(xiàn)實民主不太好的狀態(tài)去比較,這并不公平。所以公平的比較是,都在非常理想化的情況下進(jìn)行比較。
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樣,就是你能選出最好的賢能的人,他也是通過選舉的產(chǎn)生。所以哪一個好一點?我覺得民主好一點。
但這都是在最理想的層面。而在現(xiàn)實層面,所謂的民主制度還是所謂的賢能君主的制度,都不能保證選出真正賢能的人。
方旭東:所以如此說來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陳祖為:你說得對。我認(rèn)為儒家一直以來都沒有唯信任何一個制度。歷史上一開始可能是禪讓,認(rèn)為禪讓制度很好。然后發(fā)現(xiàn)君主世襲,繼承是比較穩(wěn)定的,能解決所謂承繼的問題。諸如此類。這不是因為儒家有什么很大的道理或理想,儒家就是哪一個制度在現(xiàn)實上能夠發(fā)揮效用,它就接受,它就用儒家的理想來改良。
比方說君主制度是不是一定會產(chǎn)生賢能呢?當(dāng)然不是。很多君主都一出生自然就是太子,并不能保證擁有賢能。那么怎么辦?就是要培養(yǎng)他,然后還有首相制度、官僚制度,輔佐他,教他提升。民主也是這樣。儒家是不是盡信融入到民主?我覺得也不是。但是它在現(xiàn)實上覺得這個比賢能政治制度可能好一點。
所以回到我要講的東西,怎么樣比較理想、一般現(xiàn)實和最壞情況三方面?最好的情況就是,賢能政治和民主制度中執(zhí)政的都是有賢能的人,那么相較而言民主是不是好一點?我覺得是,因為它有制度上的表達(dá),人可以投票,同意你是賢能就選你出來,制度上的表達(dá)比較清楚肯定。一般現(xiàn)實就很難說了,新加坡可能比印度好,但是可能芬蘭跟丹麥又比新加坡好。最壞的話,兩者相較,民主應(yīng)該也是好一點。
我覺得我們?nèi)寮业挠^點就是要在民主制度上吸收賢能的元素,兩者結(jié)合在一起就是最好。
方旭東:所以你的觀點是否可以概括為:以民主為基礎(chǔ),然后輔以儒家的理想。
陳祖為:對,這是在制度上。在價值基礎(chǔ)上還是儒家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制度的設(shè)計和運作,要用這些價值去補(bǔ)充、修改。
如果一個國家只發(fā)展經(jīng)濟(jì)不發(fā)展民主,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難
方旭東:你談到了一些核心和關(guān)鍵的點。你認(rèn)為關(guān)于比較的模型,要從三個方面來比,賢能制和民主制在最好的、一般的和最壞的情況。最后你得出的結(jié)論還是民主制度要比賢能政治要好一些。所以你最后是說,儒家要在民主制度的基礎(chǔ)上對它做一些修正或者補(bǔ)充?
陳祖為:但我不是說任何國家都要搞民主。這個要看條件。
方旭東:那么符合搞民主的條件是什么?
陳祖為:有一系列的條件。第一就是經(jīng)濟(jì)條件,國家不能太窮,不能太落后。太窮的話人們最關(guān)心的是生活和溫飽,那么政治的票對他們來說是很遙遠(yuǎn)的。第二就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會帶動教育和公民素質(zhì)的發(fā)展。第三就是,官僚制度的能力、國家管理的能力也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有關(guān)。你有民主制度,但官僚制度非常薄弱的話,很難解決問題。另外,一般西方學(xué)界認(rèn)為如果社會存在宗教的矛盾、種族的矛盾、階級的矛盾、語言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矛盾越大,民主就越難發(fā)揮它的功效。最后就是政治文化,擁有一定的包容,能尊重不同的意見,才能發(fā)揮民主的效用。
方旭東:這里面我感覺似乎遇到了一個悖論。我同意民主是需要一些條件的,但對那些暫時沒有達(dá)到民主條件的國家,它要實現(xiàn)這個條件似乎又不能不通過民主的方式,那么它怎么才能夠達(dá)成那些條件?比如以教育為例,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很難保證教育公平。而統(tǒng)治者可能非常樂于讓老百姓保持愚民的狀態(tài),因為那是最好統(tǒng)治的。所以這不是一個悖論嗎?
陳祖為:我覺得這在以前是可能的。但現(xiàn)在,假如公民的教育程度低,國家在經(jīng)濟(jì)上根本不能跟人競爭。從經(jīng)濟(jì)發(fā)展來說,你也要給人民高學(xué)歷、高能力去拼。
方旭東:但有種說法恰恰認(rèn)為,中國現(xiàn)在之所以會有競爭力,就在于中國人力低成本的優(yōu)勢。
陳祖為:當(dāng)它意識到低成本優(yōu)勢不能繼續(xù)發(fā)揮作用的時候,它就需要高層次的教育是不是?還有你看東亞過去幾十年的發(fā)展,就是權(quán)威政體推動經(jīng)濟(jì)發(fā)展,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這四小龍都是因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教育提高,中產(chǎn)階級出現(xiàn),它們就有壓力有需求去發(fā)展民主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如果一個國家只發(fā)展經(jīng)濟(jì)不發(fā)展民主,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難。李光耀去世之后,可能新加坡也會走向多一點民主的道路。所以這個悖論是正常的發(fā)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論述,經(jīng)濟(jì)改變上層建筑。
方旭東:你似乎比較樂觀,覺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必然會帶來民主條件的實現(xiàn)。
陳祖為: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會給民主發(fā)展帶來很大的推動力,但是這個壓力也不一定就會變成民主。因為歷史是有它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新加坡就有一個強(qiáng)人這么厲害,可以說服民眾。
方旭東:但你是從理論上來肯定這一過程是必然的。
陳祖為:我不說必然,社會科學(xué)不說必然。我是說會有一個很大的tendency(傾向)。

儒家的道德教育能為化解西方民主中的沖突提供方向
方旭東:你剛才說儒家能采用民主這樣一種制度,但可以用儒家的一些價值來改善它修正它。這方面具體是怎么樣的呢?要修正哪些價值?
陳祖為:我覺得理念、文化是一方面,制度設(shè)計是另一方面。理念和文化方面,因為儒家不承認(rèn)人天生就有政治權(quán)利。擁有政治權(quán)利的人,不應(yīng)該將這個首先看成是我的一個 privilege(權(quán)益),而應(yīng)該看成是一個責(zé)任。民主給每個人一票是為了能夠達(dá)到民主的好的功能,表達(dá)relationship的功能,以及為了serve the people better的功能。
方旭東:你覺得應(yīng)該從權(quán)利轉(zhuǎn)換成為責(zé)任?
陳祖為:對,政治責(zé)任。公民是一種責(zé)任。當(dāng)然有權(quán)利,但其精神是要發(fā)揮公民用自己的思考去關(guān)注公眾利益。這個責(zé)任不是說我要做順民,不是上面講什么我就要服從什么,而是當(dāng)一個好的公民。好的公民就是要知道社會需要什么,不應(yīng)該將自己個人的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
另外就是文化政治的道德教育。我們會發(fā)現(xiàn)西方民主中有很多沖突和斗爭,很多時候會變質(zhì),民主的過程會產(chǎn)生很多不好的東西。這就需要,用西方概念來說就是civility(禮貌,文明),公民文明的教育。我覺得儒家的基本道德教育,能為此提供很多很好的方向。西方的公民教育比較著重批判,著重知識的掌握,critical thinking。我覺得在此之外也需要強(qiáng)調(diào)civility,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尊重你的意見。另外可能還需要compromise。儒家講很多比如和而不同,要禮讓啊、要尊重啊,我覺得儒家的道德教育是比較好的。
方旭東:我同意你的講法。
陳祖為:細(xì)部的設(shè)計方面,我就提我書里的內(nèi)容。比如下議院是民主選舉產(chǎn)生的。上議院就是用賢能選拔,通過推薦和挑選。
上議院的設(shè)計主要是有兩個前提。第一個,在現(xiàn)實社會里面,并非人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勢必有部分人比較有賢有能。怎樣知道他們在哪里?有些人從事公務(wù)二三十年,他們會表現(xiàn)出來。所以我主要是吸收這些資深的、有政績的人。那么一般老百姓可能認(rèn)識他們,但不知道他們好不好,所以你首先要選一些能夠認(rèn)識他們的人。是什么人呢?三方面,第一是他們的同事、自己人,可能分屬很多不同崗位,法官、外交官、立法委員,和政府委員會那些人。當(dāng)然這是香港的情況。其次,去為這些人服務(wù)的行政官僚和秘書,他們是獨立的,每一天跟那些資深官員工作,最清楚哪一個比較賢能。第三個是跑政治、跑公務(wù)線的記者。比方說有一些提名出來,有這樣三批人去打分,“賢”一個分,“能”另外一個分,然后就加起來。過了某一個程度的分就當(dāng)選。
方旭東:聽起來似乎比較合理。也避免了讓不了解的人去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有一種尊重專家的意味。
陳祖為:這個是通才的專家,不是科學(xué)的專家、工程的專家。
方旭東:其實他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政治方面的專家。
陳祖為:這些都是比較符合儒家講的。關(guān)于具體什么是“賢能”,我們也不能完全根據(jù)儒家的說法,要修改一下,但是主旨上也符合儒家的。“賢”就是你是公正的,你個人比較有開明的態(tài)度接受不同的意見,有原則,也有責(zé)任感。“能”就是對一般的公共事務(wù)的掌握能力,具備思考的能力,清楚、準(zhǔn)確和到位的表達(dá)能力等。都是generic qualities。
方旭東:從你前面的表述來看,你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的確非常深入,而且已經(jīng)形成一套有說服力的想法,這對大陸的讀者思考儒家政治哲學(xué)會有很好的參考意義。謝謝你,這次訪談就到這里。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