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厄奎奧拉談美國大學的公平和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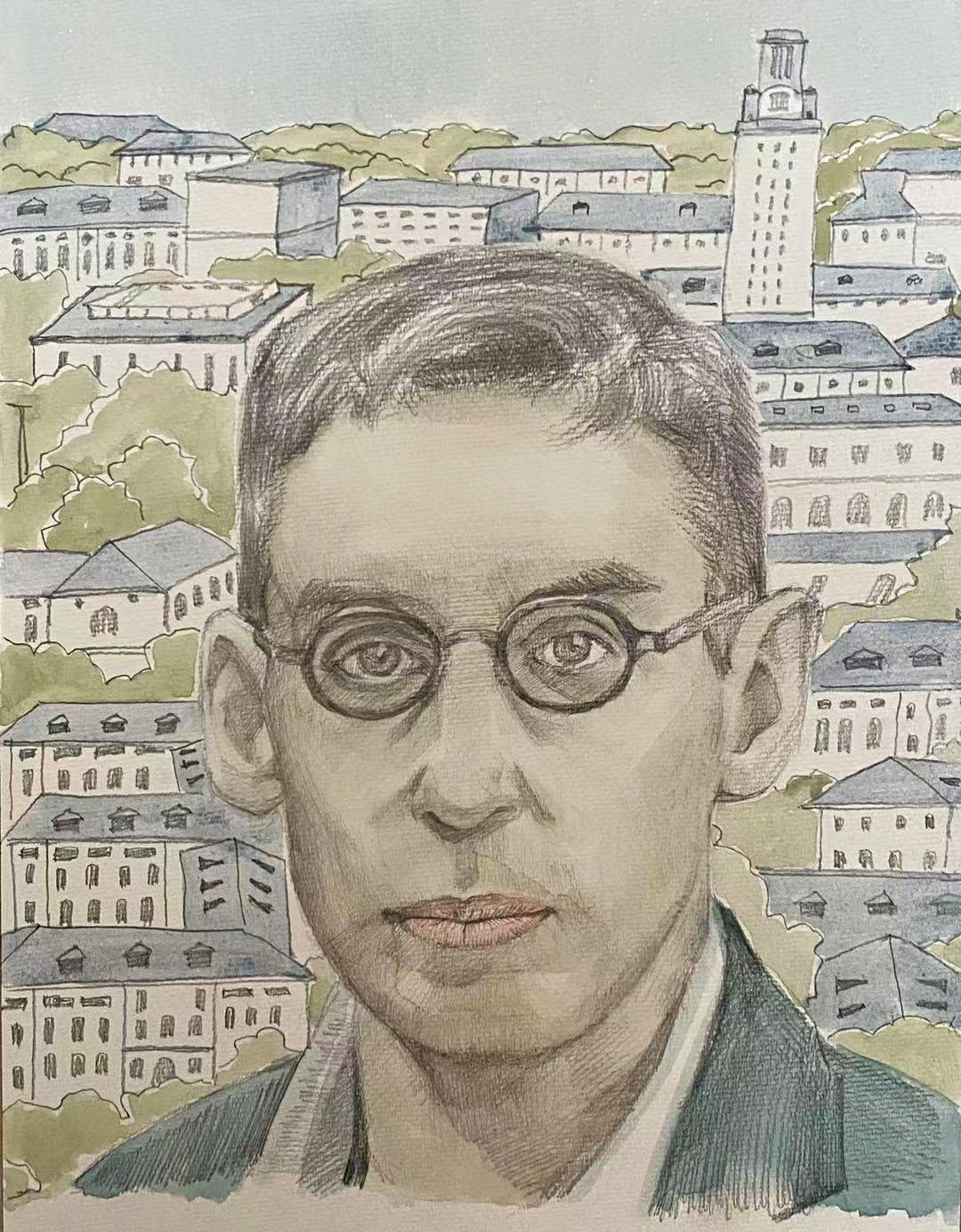
厄奎奧拉(邵仄炯 繪)
在QS、《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上,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美國頂尖名校經常占據榜首位置。關于這些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歷程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普遍的看法是,美國的一眾名校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甚至是二戰之后才逐漸脫穎而出,成為科研領域的執牛耳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主任米蓋爾·厄奎奧拉(Miguel Urquiola)的近著Markets, Minds and Money: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市場、頭腦和金錢:為何美國能引領世界大學科研》,2020)卻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并將美國大學的“發跡史”往前推至1860年代,即美國內戰(1861-1865)前后。他運用自由市場原則,解釋了為何美國的一流大學在南北戰爭前忽視科研工作,而戰后又能積極把握社會趨勢,有效地將資源匹配起來,用一整套機制發現、吸引和激勵最優秀的人才,從而在二十世紀初實現了對歐洲大學的反超。《上海書評》特約記者倪韜日前采訪了厄奎奧拉,請他圍繞這本書的內容以及當前美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談了談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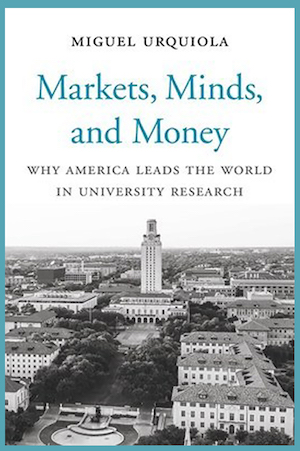
Markets, Minds and Money: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經濟學里的“八二法則”被廣泛用來形容各行各業的“頭部”現象,根據您的研究,在美國,百分之一的頂級名校創造了全美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最具價值的研究成果。為何“八二法則”在教育領域被發揮到了極致?
厄奎奧拉:這種情況很有意思,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世界其它地區,“八二法則”的適用性取決于供探討的教育“產品”的類型。舉例而言,美國的常春藤聯盟包含八所院校,這八所大學的平均校齡比多數美國大學都要悠久。如果將這八所“藤校”的畢業生視為其所打造的“產品”的話,那么它們的產出的確只占到全美高校畢業生人數的很小一部分,而且這一群體的培養成本相對更加高昂。因此,如果我們討論的教育“產品”是畢業生的話,“藤校”的出品率并不高。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將“產品”界定為科研成果,那么諸如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這幾所“藤校”的表現無疑出類拔萃。
至于說為什么科研領域會有這樣的現象,我的理解是,頂尖科研成果的價值十分突出,而研究型學府想要獲得卓越的成績,首先需要有發現優秀人才的慧眼,能將他們招至麾下;其次還要為他們配備足夠的資源,比方說可供自由調配的時間。我在書里提出的一個觀點是,美國在這方面的制度設計十分奏效:最頂尖的美國大學擅長發現最聰明的頭腦,并輔之以經費支持。要做到這點絕非易事,但是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發展出的一套科研體系在整合人才和資金優勢方面證明行之有效。此外,這一制度并非中央規劃的產物,而是去中心化市場力量推動的結果。
您的書里提及的許多美國名牌大學能迎來重大發展,和一些老校長/教務長的遠見卓識有關。我不算是卡萊爾英雄史觀的擁護者,但就您來看,拋開自由市場原則,個人決策和領導力等因素起到了多大作用?舉例而言,如果不是因為一些校長,比如哈佛的Charles Eliot、普林斯頓的James McCosh、霍普金斯的Daniel Coit Gilman以及他們英明的繼任者,或許這些名校就不會有如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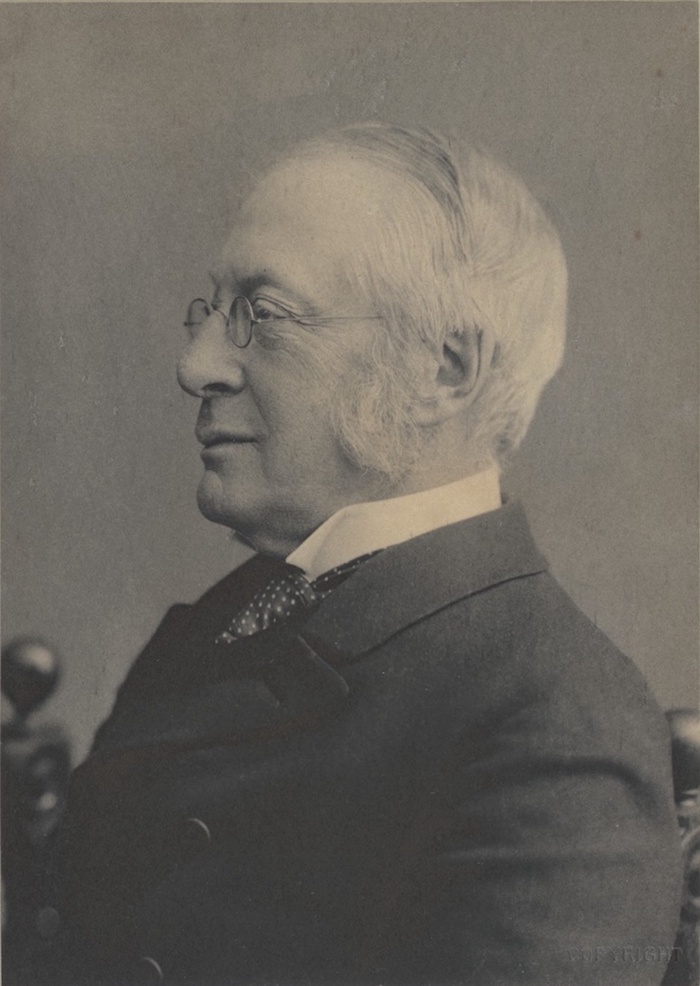
哈佛大學校長Charles Eliot
厄奎奧拉:你說的沒錯,本書確有相當一部分篇幅在評述個別大學領導人的事跡。這里我僅指出兩點:一、我之所以花費大量筆墨寫這些大學校長的故事,是因為他們極大地影響了其所供職機構的發展路線。這既反映出部分大學需要改革,也說明有些大學是新建的,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往往充滿了曲折。因此,了解個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有助于了解為何特定的學校能夠完成轉型,繼而脫穎而出。
二、我認為你的提問其實也暗示了一點,即個體在左右制度層面的結果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沒那么舉足輕重。所謂制度層面的結果,是指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最終在全世界大學科研能力一項上獨領風騷。關于這一點,我在書中也有強調,指出其核心要素在于美國的自由市場導向。它賦予大學極大的自由度,可以自主辦校,進入教育市場,同時鼓勵大膽創新,銳意進取。在這樣一種寬松的氛圍下,只要有充分的機遇,那么就會像十九世紀末那樣,涌現出一批有能力抓住這些機遇的學校。因此,即便由于某位校長的關系,X大學未能做到一枝獨秀,Y大學可能會在另一位校領導的帶領下鑄造自己的領先地位。因此,我的看法是,那些能夠帶頭推動關鍵改革的大學領導人一定會出現,只是早一點晚一點罷了。因此,就這一點而言,個體的作用或許并不是決定性的。
反過來講,那些早期顯赫、后來沒落的大學,是否和領導層的決策失誤有關?據您觀察,成功大學的領導人都有哪些共性?
厄奎奧拉:這個問題提的好,不好回答。依我看,大學校長需要具備三大素養:一是創新能力,也就是要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機會;二是要有能力推動變革。世界各國的大學內部其實都錯綜復雜,都存在團體抵抗變革。即便一些人能夠看到未來的方向,知道有些事是必須做的,但是真要推下去,還是頗具難度。所以說,作為校長,一定要能勾畫清晰的愿景,帶領眾人朝一個方向努力。除了上述兩點外,大學校長和任何行業的領軍人一樣,也需要明白他們所在的組織機構具備哪些比較優勢。舉例而言,如果某位校長想要成功地領導一所研究型大學,那么理想情況是他/她自己就有從事科研工作的經歷,這有助于他/她了解自己手下教職員工的日常工作,以及激勵他們的動因是什么。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延續上一個問題,同樣是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為什么某些美國大學發展特別突出?這是否說明自由市場原則也是因人而異?不同的人和要素,對于自由市場的領悟能力、接受度和匹配度不同,所以導致了各所大學最后在研究績效和排名地位上存在差異?
厄奎奧拉:是的,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下有贏家,就會有輸家。如果有人在1860年向美國高等教育的觀察者發問,請后者猜測哪些學校會取得成功,那么基本上會有一堆錯誤的答案。為什么會這樣?我覺得原因有三點:首先,許多后來崛起、獲得巨大成功的大學(比如斯坦福和霍普金斯)在當時尚未成立;其次,如果按照1860年的標準來看,一些大學,比如哥倫比亞,當時處在一個很弱勢的地位,沒人會認為哥大等學校有能力引領美國大學的崛起趨勢;再次,當初也很難預測諸如克拉克大學和聯合學院等學府會攀升至金字塔頂端,之后盛極而衰,被遠遠地甩在后面。
誠如你所提到的那樣,所有這一切大概率都取決于不同的學校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去擁抱自由市場原則,以及它們的領導層是否管理有方。另外,和許多其他領域一樣,運氣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哥倫比亞大學
您的書里提到了移民對美國大學科研的影響,但是并沒有展開。我想問的是,拜登政府有否撤銷了部分特朗普時期出臺的限制移民政策? 另外,除了政策,我們還應該看到社會氛圍的變化,在美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歧視和仇恨亞裔事件的影響下,美國大學對留學生和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會受到何種影響?
厄奎奧拉:先回答第一個問題。簡單地說,是的,拜登政府的確開始修正特朗普政府時期實施的一系列針對移民的限制性措施,其中一部分是因為抗疫的需要,但隨著疫情的緩解,大概率會逐步得到放松。總的來講,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那樣,反對移民的情緒和由此催生的政策可能會有損美國大學對全球人才的吸引力。
你提到美國目前存在反對移民的社會思潮,而且其矛頭有時候對準的是亞洲人或者亞裔。這種情況屬實,但需要指出的是,反亞或者說排亞思潮其實一直都存在。在美國,每隔一段時間,這個話題就會重新冒頭,成為熱點。但受到這種排外心理影響的族群還不光是亞洲人和亞裔。歷史上的不同時期,美國都出現過類似的排外現象,其針對的人群包括來自意大利、愛爾蘭、墨西哥、德國和東歐等地的移民。這反映出一點,大規模的移民涌入,的確需要新來者和老移民雙方同時做出巨大的調適。從這個意義上講,大規模移民對于美國等國家而言,的確構成挑戰。它們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需要不斷去應對這種挑戰。我的感覺是,總的說來,美國在接納移民一事上做的還是相當不錯的,前后共吸收了幾百萬移民。這種選擇增強了美國在多方面的實力,學術界自然是受益方之一。至于美國是否能夠繼續應對上述挑戰,則有待觀察,但是鑒于以往的經驗,我對此還是比較樂觀的。
放眼全球,許多大學的排名都在迅速提高,比如中國的清華大學和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后者好幾次蟬聯亞洲第一),這是否意味著,政府主導的模式一樣能培育出很好的研究型大學?作為自由市場論者,您怎么看待這些變化?另外,諸如中國和新加坡大學的成功,是否意味著自由市場主義更適合美國,但在國際上未必適用?
厄奎奧拉:我這么說可能會讓你感到很驚訝,因為我絕大多數的研究工作探討的其實是自由市場為何在教育領域往往不能發揮最大效用。盡管如此,在《市場, 頭腦和金錢:為何美國在大學研究上引領全球》這部書里,我提出的論點是,自由市場原則在推動科研進步方面,還是能有相當不錯的功效,這一點有美國的經驗為證。正如之前回答的那樣,市場環境下孕育的教育體制擅長發現和識別研究型人才,并為其提供配套資源。
除了美國外,其它國家走的路線或許是政府主導的公立大學體系。它們一樣能為優秀人才提供資源支持。這方面的例子你也提到了,我要補充的是,除了中國和新加坡,不少歐洲國立大學和公辦教育體制一樣能產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畢竟,曾幾何時,德國大學(基本都是國立大學)的研究實力是要強于美國大學的。
美國的路徑別國很難效仿,而且美國也有自身的劣勢。比如說,我在書中提到,大學提供的教育產品的性質一旦發生變化,或許會削弱其在科研方面出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美國的模式或許會繼續展現其價值。舉例而言,公辦教育體制下,負責分管教育的官員往往必須是“明白人”,需要知道在哪方面可以有所作為,但是他們是有可能會犯錯的。而在類似美國這樣一個去中心化的體制內,有賴于校領導自己摸索未來的出路。從長遠來看,這種制度或許在適應性上更勝一籌。
美國國內關于大學學費上漲導致學生背負巨額債務的討論由來已久。您在書里提出,實際上學費上漲只是相對的,而且這部分上漲的成本實際上仍然是劃算的投資。可是當許多學生一畢業就要面臨償還高額債務的重擔時,難道不會影響本科生的入學率和學習體驗么?
厄奎奧拉:我的書主要涉及的還是美國的研究型大學。放在整個美國教育市場的大背景下,這些學校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并不具有代表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的畢業生其實遠沒有達到畢業即遭遇“債務危機”的情況,這么說是言過其實了。事實情況是,這些畢業生在走出校門時,多數都不會背負債務,要么是他們的家庭為他們支付了全額學費,要么就是學校本身吸收了培養他們的這部分成本。舉例而言,據我了解,普林斯頓會為其本科生打造一攬子的助學金計劃,這樣學生就不會有任何后顧之憂。誠然,普林斯頓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我想要表達的是,這些美國名校的運作方式還是有別于普通大學的。當然,你提的也沒錯,在美國,學生因為學費高而面臨債務壓力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只是在拙作所聚焦的那部分學校當中,這算不上是一個多大的問題。
您書里提到了legacy students(“傳承”學生,即父母是名校校友,可以增加子女被同一所學校錄取的概率),那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會不會使得哈佛老校長James Conant的預言成真——美國成為一個“世襲貴族體制”(hereditary aristocracy)?
厄奎奧拉: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談三點:一、一流美國大學的確會在錄取階段考察申請人的“家世背景”,看看他/她的父母是否是同一所學校的畢業生。不過依我看,這種風氣自從Conant的時代以來,已經變得不那么普遍了。這是因為許多名校會提供覆蓋面十分廣的助學金。此外,他們還會特地去物色那些父母非該校校友的申請者,甚至有的父母連大學都沒有讀過。
二、需要記住的是,頂尖美國研究型大學其實只占到美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的很小一部分。這一方面,Raj Chetty等學者的研究顯示,除了名牌私立大學外,其它類型的教育機構,例如某些招生比例很高的公立學校,其實在教育機會平等化上所做的貢獻大得多。這部分是因為它們錄取人數比諸如“藤校”要多得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大學系統整體上遠未夠得上“世襲貴族體制”的標準。
三、我想表達的是,不能將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一批學校身上,它們并不是萬能的。不同的學校組合,發揮的是不同的功能,其中一些相對更專注于研究人員的培養,而剩下的那部分則側重于擴大教育服務的可得性。這樣一種分工在我看來十分正常。以紐約市為例,哥倫比亞大學或許主攻學術研究,而紐約市立大學則著眼于提升入學率。這樣的分工有其內在價值。換言之,在我看來,要求哈佛大學去承擔教育系統的每一項任務,可能算不上是太有效益的做法。
眾所周知,美國大學的校友捐贈,構成endowment(捐贈基金)的一大來源。我最近在看高瓴資本創始人張磊的《價值》,他是耶魯畢業生,曾在耶魯投資辦公室工作過。耶魯校友主持的各個名牌大學捐贈基金每年回報率在百分之十二到十五,這種浮盈,超過了很多行業的投資回報率。舉例而言,哈佛捐贈基金高達四百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奉行長期價值投資的捐贈基金,可以為大學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與此同時,這也加劇了資源分配的不公平。您在書里提到,美國政界就是否針對大學捐贈基金征稅展開過討論。問題是,面對幾百億美元的本金,和每年幾十億的高額回報,稅收這種調節手段能起到多大作用?
厄奎奧拉:這點我同意你,迄今為止,征稅對于大學的捐贈基金基本沒產生太大的影響。我對于以確保學校之間平等為目的的公共政策持懷疑態度。在我看來,制定公共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激勵公共物品的生產。諸如耶魯或者哈佛等大學的捐贈基金所產生的一大部分浮盈,都被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以最新的mRNA新冠疫苗為例,這類疫苗的誕生將對結束全球疫情大傳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賓夕法尼亞大學科研團隊的工作在該疫苗開發過程中居功至偉,當然其它機構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說,大學捐贈基金使得上述研究成為可能。所以,若制定政策的目的是對捐贈基金課稅,我不清楚這么做的意義在哪里。
美國在二戰期間,和蘇聯一起瓜分了不少德國的頂尖科學家。這種爭奪人才的行動,給美國后來的科研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沒有馮·布勞恩,或許阿波羅計劃的歷史就會改寫。您的書里沒怎么談到二戰,二戰是否是美國大學科研進化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嶺?畢竟,戰前德國大學和科研院所科學家獲得諾獎的人數,是美國的三倍。所以,自由市場原則是否只是美國在擁有了人才的“原始資本積累”之后,進一步強化自身地位、防止被趕超的手段?而并非造就美國科研領先地位的根本性原因?

馮·布勞恩
厄奎奧拉:不少美國高等教育的觀察者——其中也包括美國觀察者自己——都非常強調二戰在美國研究型大學崛起過程中的作用。二戰固然影響了美國大學的發展路線,其中一大因素就是許多富有才干的德國學者移居至美國,這一過程始于1930年代納粹當權之后。不過,撇開這層背景,我在書里主張的一點是,美國研究型大學實際上在很早以前就開啟了“趕超模式”,時間要追溯至1860年代。到了1920年代,美國已經趕超或者即將趕超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因此,從分析方法來看,我們有必要將目光投向二戰之前。
研究型大學體制要想運轉順暢,務必要建立一套物色人才的機制,去判定哪些人擅長搞研究。一項重要的判定工具就是在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中的發表情況。那么,這類期刊是何時在美國出現的?粗略來講,最早出現于1880年代。舉個例子,美國經濟學會成立于1885年,到了1888年開始出版一份期刊,再到1911年時,這本刊物更名為如今大名鼎鼎的《美國經濟評論》。從1885年到1911年這段時間內,芝加哥和哈佛等大學紛紛推出自己的同類期刊,與《美國經濟評論》構成競爭。到了1910年前后,美國已經擁有一套完備的學術刊物矩陣,用以傳播最新的經濟學思想和評估研究成果。大抵在同一時期,其它學科領域也見證了類似的情況(建立學會和創辦刊物),譬如數學、生物學、歷史學,等等。學術發表和評估體系的發展,促使美國開始締造一套衡量學術質量和辨別人才的基礎設施,而在過去,美國在這方面是落后于歐洲的。這樣一套基礎設施對于提升研究績效至關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基礎設施并不是因為軍事行動,在1945年時神奇地冒出來的。美國大學的重大改革早在很久之前就已開啟。無獨有偶,諸如康奈爾和斯坦福等名校的發展歷程其實也遠早于二戰。這就是拙作要強調的觀點:頂尖研究型大學體系不是憑空產生的,這是一個過程,而且在美國是特別漫長的過程,原因是美國的體制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沒有人從一開始就統籌一切。然而,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才催生了一種卓越而富有活力的教育體制。
我讀完您的書之后的一個印象是,美國大學體制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做了取舍,選擇了自由市場法則,利用更多的金錢和資源,去匹配更聰明的頭腦,從而把資源牢牢攥在手里,鞏固自己的“頭部”地位。簡言之,更偏重效率。這本身無可厚非,但現在各種跡象表明,資源不平均發展到一定程度,會危及美國大學的整體發展。美國一些普通大學的校長以及社會批評家,會否對“藤校”擠占資源的現象加以抨擊?
厄奎奧拉:人們對于大學之間不公平的擔憂,至少根據我的觀察,主要來源并不是非精英大學的校長或者教育評論家。我認為,這些觀察者主張的還是廣泛擴大對于教育的財政支持力度,為更多學校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但是很少會有人要求減少對頂尖大學的財政撥款和支持。我覺得你的問題反映了兩種認知。第一種是名牌大學的捐贈基金的確起到了作用,比如為大學生提供豐厚的經濟補助,第二種是根據頂層設計,一流院校的經費本來就不足以解決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存在的所有痼疾。那些以研究為導向的學校中的佼佼者依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入學的機會公平方面,除了affirmative action(平權法案)、獎學金等措施之外,美國名牌大學還有推出哪些措施,防止因為利益固化而阻斷貧困和少數族裔學生的上升之路?
厄奎奧拉:正如你所言,這方面的措施包括提供助學金等等補助,或者是招攬家庭條件和背景不佳的申請人。除此之外,美國的頂尖大學還越來越重視出臺新的機制,幫助這些弱勢群體的學生獲得成功。另外,它們還在持續增加投入,旨在打通“人才輸送管道”,在學生學習生涯更早的階段介入,以獲得更多優質生源。
您的書里兩次提到了“近親繁殖”(inbreeding),比如說,James Conant治下的哈佛,在社會科學領域曾落后于芝大和哥大,很大一個原因就是“近親繁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則反對“近親繁殖”,堅持不聘用自己的學生。目前美國大學在這一塊是怎么做的?比如您所任職的哥大,自己培養的博士生留校任教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其它名校呢?
厄奎奧拉:這方面我沒有詳細的數據,但我可以說的是,美國名校的不少院系都奉行一種準則,或者說一種模式,盡可能避免錄用自己的畢業生。其實并沒有明文規定應該這么做,只是業界已經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準則。我覺得這種準則還是有裨益的。具體而言,某一時間點上,這種準則或許會造成錯失人才,比如某所學校可能培養出了一位能力超群的畢業生,好像沒道理不聘用“自己人”。但是問題在于,常會有人替人求情,希望留下“自己人”,而這種情況發生得太過頻繁了。因此可以說,避免“近親繁殖”是有充分理由的。
另一種可行的做法是,讓出色的畢業生先在其它地方開始職業生涯,日后再將他們返聘回來。這在一個名牌大學林立的國度里并不難實現。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