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王希:美國總統為什么會越來越強勢

澎湃新聞:林肯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那么他在美國歷史上為什么會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王希:這看上去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仔細回答起來卻很難。關于林肯,已經有無數人寫了很多書,很多著作。我就簡單講幾個方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他拯救了美國。內戰的發生表明美國的第一憲政秩序走向了失敗,國家分裂了。通過內戰的一系列決定,林肯扭轉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林肯對歷史賦予他的使命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1862年他對國會講述內戰的重要性時,說我們要拯救的不光是美利堅聯邦,而且也是在拯救“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the last best hope of the earth)。這句話有很深的含義在里面。他認為,聯邦之所以出現分裂,是因為南部在1860年總統選舉失敗后采取了退出聯邦的舉動,這證明美國的制度是有嚴重問題的。他說,我們必須要打贏這場戰爭,表示聯邦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民主制度并維護國家的統一。林肯要挽救的不光是作為聯邦的美國,而且當時的美國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存活的民主共和國,這意味就非常深遠。
第二,林肯做出了永久性地解放奴隸的決定。其實在他之前,奴隸已經開始了自我解放的行動,國會也通過了一些法令,部分地廢除了奴隸制,比如在哥倫比亞特區以及還沒有建州的聯邦西部領土上,但效果有限。林肯的《解放宣言》提出:從此開始永久性地解放奴隸,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膽的舉動,等于把奴隸主手中的擁有奴隸的財產權全部否定了。
在他看來,只有解放奴隸,美國人才會有真正的自由,“當我們將自由賦予奴隸的時候,自由人的自由才得到了保障”,林肯的這個觀念非常重要,他將“自由”升華了。也就是說,過去的美國是不道德的、不正義的,一部分人享有的自由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之上的。作為一個領導者,林肯要說服北部的人民接受解放奴隸這個選擇。他需要有一種理論來說服大家,這需要深思熟慮,高瞻遠矚,需要個人的才華。我們知道,林肯的政治演講詞都是他自己寫的,所以,作為一個領袖,他是一個思想的原創者,是我們當代熟知的關于“自由勞動”和“人類解放”等思想的第一作者。
第三,如果說安德魯·杰克遜的當選是現代政黨政治的結果,那么林肯應該是第一位真正的現代美國總統——他在內戰中將執法權發揮到了極致,打破了許多陳規陋習,也開創了許多的新“權力”領域。
當時的美國聯邦政府是一個很羸弱的政權,規模很小,但面臨一場大規模戰爭,遭遇各種困難,包括軍事、內政、外交、社會動員,等等。這些都需要一位具有堅強的意志力、富有行政才華、清楚的思維邏輯的總統來領導國家。因為國會在國家遇到大難時,它因為利益分散,不可能很快形成一個集中的意志,而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林肯出現了。他的許多決定和認知都是對當時政治情勢的反應。他的思想很多都是他的首創。我覺得林肯不僅在理論上有建樹,也是一個偉大的實踐者,而這些建樹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處理危機的時候建立的執政方式為后來的總統所效仿。

林肯最后的遇刺,當然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但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悲劇意義上的完美結局,他的遇刺和死亡幫助他成為美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神一樣的人物。他是在第二次順利當選、并發表了就職演說之后遇刺的。他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種宗教意味極濃的語言(他平時并不是一個宗教感很明顯的人),并提到了上帝通過給予這場“可怕的戰爭”而對美國施行奴隸制所做出的懲罰。不久他就遭遇刺殺,為他力圖捍衛的憲法和國家貢獻了生命,這讓人感到特別心痛。他自己也成為內戰的代價之一,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烈士。他的死在某種意義上為這個國家留下了一個永久性的注腳——對自由的爭取,對民主的爭取,對正義的爭取,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總統本人的生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
林肯的不朽名聲還來自于后世的塑造。不過他的經歷、他的寫作,幾乎讓過去所有的總統都黯然失色,華盛頓除外。林肯是一個原創性的思想者(original thinker),因為他面臨的是新形勢,要求他有新的思想,可他只接受過一年半的正規教育——完全是白手起家,他沒有華盛頓的戰功,沒有杰斐遜的博學——他有的只是個人的經歷:出身貧苦,具有獨立精神,非常善于學習,極有雄心,又富有智慧,成為律師,進入政界,最后成為總統。所以,林肯的經歷成為早期美國夢的一種化身。
我最喜歡讀的關于林肯的書,是一本寫給兒童的書,叫《林肯笑話集》(The Abraham Lincoln Joke Book),里面列舉了一些林肯喜歡講的笑話故事(jokes)。林肯特別喜歡講故事,這是他的一種獨特的交流方式。我把這本書放在床頭,喜歡在睡覺前讀一下,從中領悟林肯的幽默感。里面沒有什么嚇唬人的“大道理”,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真智慧”。這本書是我從舊書攤上買的,像《伊索寓言》的風格,小學生都可以看懂,這也反映出林肯被神化的程度。
林肯之所以受到尊重,還有家庭的原因。他的一個幼子是在他入主白宮時因病去世的。林肯的妻子瑪麗出生于肯塔基州一個奴隸主家庭,喜歡政治,喜歡花錢,喪子之后,患了強烈的抑郁癥,而林肯雖然是政治老手,但在生活上卻是一位廉潔、樸實、不喜奢華的人,他在夫人抑郁癥發作的時候,必須要陪伴和安慰她。他同時要面對處于內戰的國家危難和無法修復的家庭苦痛。林肯留下的照片中,幾乎沒有一張是有笑容的,他的內心深處埋藏著一種很深的悲傷(grief),然而他的內心是堅強的。
最后一點,我要補充的是,林肯的文字非常簡潔,通俗易懂,幾乎沒有你看不懂的詞,普通人就可以讀懂,但同時也很優美和優雅。正因為這樣,他的寫作具有極大的感召力,不信你看看他的《葛底斯堡演講》和第一次、第二次就職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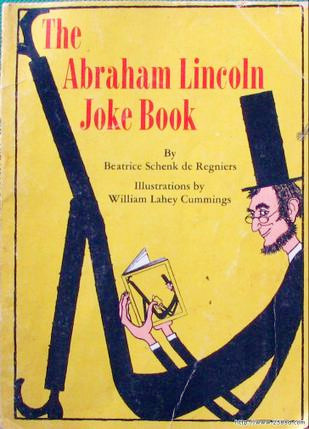
王希:其實整個19世紀的美國,可以說都處于“弱總統強國會”狀態,這和美國革命時期立憲的傳統有關系。當時非常強調立法權,而國會是立法機構,所以無論是在州制憲還是聯邦制憲的時候,國會都是三權之中的重中之重。我在《原則與妥協》增訂版中專門增加了對憲法各條用字的字數。立法機構國會用字2200多字,占了憲法全文的一半。總統掌握執法權,但在內戰之前,擴展權威的機會不多,內戰給了林肯一個機會,讓他展示出總統所能發揮的巨大權威的潛力。
林肯的遇刺是總統權威增長的一個轉折點。林肯的繼任人是安德魯·約翰遜,也就是老約翰遜。老約翰遜在南方重建的問題上與國會中的共和黨人產生了矛盾,溫和派和激進派共和黨議員聯合起來,否定了他的很多重建政策。這個問題就變得非常復雜,表面上看是總統和國會(或國會中的共和黨人)的重建方針不同,但從政治上來講,實際上是國會與總統,立法部門與執法部門爭奪重建的領導權的問題。有的人會把這次沖突解釋為聯邦政府內部的部門權力之爭,但重建時期的情況比較特殊,其實包含更多的是如何處理內戰遺產的問題,涉及如何處理戰前與戰后的意識形態界定與經濟利益的分配的問題。
老約翰遜是南部來的總統,在南部退出聯邦時,他所在的田納西州沒有退出,他作為參議員也沒有離開國會,因而被認為效忠于聯邦的南部議員。1864年總統大選時,林肯選他為自己的競選伙伴,展示聯邦的統一。但約翰遜在政治上并不認同北部共和黨人的很多理念,而此刻國會主要為北部共和黨人所占據。所以表面上看是立法部門和執法部門的權力之爭,但在深層次意義上,是北方的“自由勞動”和民族國家建設的思想與南部傳統的州權之上的保守思想發生了沖突。1868年國會共和黨人對約翰遜的彈劾和審判極大地打擊了總統職位的權威。
老約翰遜之后的總統是共和黨人格蘭特。格蘭特雖然是內戰的英雄將領,但做總統非常一般,能力有限,當政時內閣丑聞不斷。接下來是海斯,他的當選是1876年南北就選舉爭執而達成的妥協的結果,沒有用權的底氣。再接下來是加菲爾德,屬于溫和派共和黨人,當選不久后就遇刺。接替他的是阿瑟,他是共和黨的地方大佬,做副總統本身就是黨內利益平衡的結果,本身沒有什么才能,也沒有大的成就。后來的克利夫蘭、哈里森等也是受制于分裂的國會。這些都對“弱總統強國會”局面的形成有影響。
此外,內戰和重建之后,美國進入了全面工業化的時期。這個時期并沒有像內戰一樣,需要總統部門發揮很大的作用。總統想在內政上做到強勢,也沒有太多的機會,直到后來1930年代小羅斯福(FDR)的時候才出現。在這個時期,國會也不知道如何應對工業化,因為當時管理經濟的權力主要在各州手中。所以政黨在這一時期也開始走向職業化、職能化,傳統的意識形態的爭執在降低,競選功能性的作用在加強。
早期的總統可以發揮意識形態領袖的作用,但林肯之后的幾位總統沒有什么人能夠對民族和社會發表有深刻思想的洞見,他們幾乎是在機械式地擔任這個職務,這也是造成“弱總統”的原因之一。所謂“弱總統”,就是他的權威始終是處在國會的鉗制之下,沒能發揮出相應的作用。
雖然內戰是美國走向現代集權聯邦制的起點,但當時的美國還沒有走向世界,在國內事務的管理方面,凡是與經濟發展和公民權利有關的事務,管理權限仍然在州,聯邦的行政部門從體制上也處于弱勢。直到20世紀初,強大的聯邦“行政國家”才開始出現。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等代表了新一代的“強勢總統”。所以當“行政國家”處于弱勢的時候,總統權威的發揮是非常受限制的。

王希:老羅斯福對推動美國走向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老羅斯福的前任麥金利開辟了擴張主義路線,把美國利益從北美大陸推進到拉美和太平洋領域,但這種擴張是在老羅斯福任內完成的。尤其是對巴拿馬運河權的搶奪,對拉美、中美這一帶的控制等,老羅斯福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老羅斯福在內政方面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對美國海軍的建設,對市場秩序的干預,介入勞資談判,打擊破壞性托拉斯等。他在內政方面開始扮演一個強總統的角色,提出了“公平施政”的方針,強調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對壟斷大資本的節制,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等,這些都是能動主義政府的舉措,讓人們想起內戰時期的林肯。
另外,老羅斯福本人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喜歡郊外生活,喜歡打獵,強身健體,給人一種充滿活力的印象。他還特別喜歡和善于與普通人在一起,在某種意義上他比杰克遜更像是一位“人民的總統”。
他的經歷非常豐富,上過哈佛,當過州長,與牛仔生活在一起,組織遠征軍到古巴去參戰,建立了自然資源保護的國家制度,等等,所以他給美國政治和歷史留下了很多影響力巨大的遺產。

澎湃新聞:從美國建國初期的第一憲政,到內戰時期開始的第二憲政,到羅斯福新政以后的第三憲政,這三個階段就總體趨勢而言,為什么美國總統的權力會越來越大?甚至出現尼克松這樣的“帝王總統”?
王希:很高興你提到美國歷史上的三個憲政秩序。這是我在《原則與妥協》增訂版前言中提出的一個分期概念,與其他的美國憲法史學者的提法不同。
就總統的權力來說,在內戰之前的第一憲政秩序時期,它是有限的。總統雖然可以購買領土,可以發動和指揮戰爭,譬如說1812年戰爭和1846-48的美墨戰爭等,但這些權力都是有限的,基本上是外交領域的權力。
1861年內戰發生之后,大致到1930年年代初,屬于第二憲政秩序時期。在這個時期,總統的權力擴大了。首先通過內戰展現出來的,總統有統帥軍隊的權力、處理外交的權力,還有管理內政的權力,甚至擁有一部分立法權,執法范圍很大,不過這些權力基本上都是運用在比較大的國家事務上。
小羅斯福新政開始,進入第三憲政秩序時期,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此后總統的權力由于美國勢力范圍的擴大,與世界事務的聯系日趨緊密。經過一戰、二戰和冷戰,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重要,作為執法官的總統的權力也隨之越來越大。
舉個簡單的例子,二戰中美國發明并擁有了核武器,而核武器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總統有權下令使用;然而,這種執法權大大增加了總統在三權中的分量。因為大戰隨時可能爆發,總統需要做出決斷,有的時候他需要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做出很多決定,而這些都容不得國會翻來覆去地去辯論。從1946年的“國家安全”到今天的“國土安全”,往往成為總統部門要權、用權、創造權力的通行證。
為什么會出現“帝王總統”?“帝王總統”當然主要是指尼克松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總統競選過程中候選人與政黨的關系。尼克松上臺后,很會利用機會,通過打開與中國和前蘇聯的對話與交流,以及對1960年代后期的法治秩序的重建,他贏得了選民的民心。第二次競選總統時,他幾乎不需要共和黨的幫助,僅僅依靠民意就能贏得競選,所以他認為自己可以超越黨派,擺脫國會對他的控制,有一種“帝王總統”的心態。我覺得,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總統的職位變得非常重要,總統可施展的執法權的空間越來越大,所以才給予了他較大分量的權威,而這種權威不是虛的,而是實實在在的。

澎湃新聞:面對總統權力越來越大的態勢,作為三權分立的另兩個代表,國會和最高法院如何制衡總統的權力?
王希:這種情況,有的時候是可以制衡的,有的時候是無法制衡的。
比如發動戰爭的權力,可以說自杜魯門介入朝鮮戰爭開始,直到奧巴馬時期,幾乎每一任美國總統都使用過。尼克松之后,國會采取的一個鉗制措施就是,總統在發動戰爭的時候需要向國會報告;如果出于保密的需要,不能向全體議員報告,至少也要向參眾兩院國會領袖報告,知曉國會。布什打伊拉克戰爭之前,他就向國會領袖做了通報,這是在尼克松“帝王總統”之后確立的規則。
最高法院沒有辦法鉗制總統的戰爭權,但它可以將總統在戰爭期間做出的涉及公民權利的決定宣布為違憲,比如在反恐戰爭中對戰俘的處理等。總統不能無限制地使用軍事法庭來審查參與反恐戰爭的美國公民的罪行。即便如此,最高法院的作用是有限的。
國會對總統權力的鉗制,要看具體的情況。比如說9?11之后,國會是一邊倒地支持布什的很多政策,包括發動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我們很難想象,沒有國會多數的同意,沒有大多數民意的支持,總統能悍然發動大規模戰爭或繼續進行戰爭。越南戰爭就是一個例子。越南戰爭是使用了錯誤的情報才得以發動的,但是到了后來就打不下去了,因為傷亡太大,媒體都在報道,對總統形成了很大的壓力。可是在1964年針對是否打越戰投票時,國會兩院的贊成票是壓倒性的。
不過,我們最近也看到美國國會和總統之間的僵持。奧巴馬現在遇到了體制上的極大障礙,他想推動的任何政策改革,共和黨人占多數的國會都會給他設置種種障礙。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動用總統行政權,但這不是長久之計,而且會加劇國會和總統部門之間的敵對情緒,后患無窮。

澎湃新聞:在拜讀您這部大書的過程中,最強烈的一個感受是民主是個長途跋涉的艱難歷程。您在書中提醒讀者,“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制憲會議的辯論中,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力主建立中央權威的制憲領導人極少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詞,在談及政體時,他們經常使用的是‘共和政體’(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或‘共和傳統’(republican tradition)。”“對絕大多數代表來說,制憲會議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流芳百世的民主政府體制,事實上,制憲會議的大多數代表并不真心欣賞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那么,從“共和”到“民主”,美國憲政為什么會發生這么大的轉折?
王希: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因為“共和”是當時追求的目標,而“民主”常常會跟“群氓政治”(mobocracy)牽連在一起,制憲者對此很擔心。在建國者中,杰斐遜是最敢提倡民主的,即便是他,也有一個前提:只有“自食其力者”,也就是要擁有一定的財產,方才能參與政治。他們認為,只有經濟獨立了,政治上才可能獨立。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又擁有政治參與的權利,那么你可能會被政客收買。
18世紀的制憲者是一群like-minded people,他們志趣相近、利益相近,因此能夠分享對政治的參與,“共和”他們來說更為現實。但正如伍德所說,他們不想要民主,但他們設計的制度含有很多“民主”的成分,他們自身的政治行為也造就了“民主”的政治生態。中下層民眾對政治的參與也施加了壓力,從“共和”走向“民主”是歷史潮流,不可避免。后來的政治人物不可能去重走他們的老路子,再去做“紳士政治”,而只能做“大眾政治”,因為形勢變了,政治不再只由精英掌控。
“民主”本身也經歷了語義的轉換,深層次的轉換,平常不易察覺。“民主”通常指每個公民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來參與政治,參與政治的目的是要求政府保護我既有的權利,這是傳統的意義;現代“民主”還包含了這樣的意思:我參與政治,是為了要求政府去創造我不曾擁有過的權利。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語義和內容轉換。“權利”與“權力”一樣,都是要“生長”的,所以人們必須要參與政治。不參與,不但保護不了既有權利,也無法獲得新的權利;參與政治,是改變“權力”的組合,最終是為了改變“權利”的構成與分配。
所以,從“共和政治”的角度出發,參與政治的目的是要求政府保護財產權;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出發,參與政治的目的不光是為了保護已有的權利,而且還是為了創造新的權利,包括新的財產權。這個轉換過程的發生,從杰克遜時代的民主擴展開始,經過內戰和重建,然后是進步運動,到后來的民權運動,直到今日的多元文化主義運動,實質上都是一種擴大民主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政黨政治、基層抗議、以及包括選舉機制在內的“頂層設計”都起了作用。
19世紀上半葉“杰克遜式民主”的宗旨,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你只要能夠交稅,就應該有權參與政治。杰克遜相信,人民是有政治判斷力的,不需要接受很高的教育,也不需要擁有很多的財產,只要政治與你的利益相關,只要你知道你的利益所在,你就不會不懂得如何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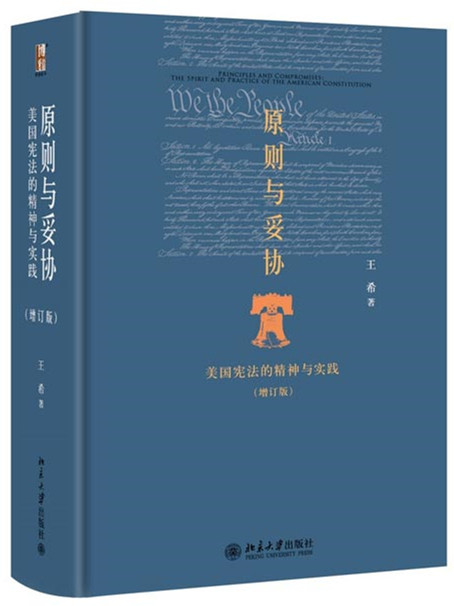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