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磅︱金沖及:胡喬木、胡繩怎樣編撰中共黨史?

金沖及很少在媒體上露面,這次說是要談中共黨史研究的前輩學(xué)者胡喬木、胡繩,才答應(yīng)接受采訪。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區(qū)前毛家灣1號,金沖及那間辦公室過去是葉群的臥室,旁邊就是林彪、林立果的居處。訪談就在這樣一個(gè)曾經(jīng)的“歷史現(xiàn)場”進(jìn)行。
今年已經(jīng)84歲的金老先生精神很好,三小時(shí)的聊天中絲毫沒有顯露疲態(tài),說話有條不紊、始終笑容滿面,講到激動(dòng)之處還手舞足蹈。有人問他養(yǎng)生的秘訣,兒子金以林在一旁打趣說:“抽煙、喝酒、吃肥肉”,他像個(gè)被錯(cuò)怪的小孩,馬上反駁說:“我不愛吃肥肉。”——邊說邊伏案給一疊新書簽名,一筆一劃地簽。
金沖及說他從高中時(shí)開始讀胡繩的作品,并如數(shù)家珍地報(bào)了一串書名,“那個(gè)時(shí)候沒有能夠?qū)嶋H跟著他學(xué)習(xí),但事實(shí)上受到他們的影響很大。”后來他進(jìn)入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長期跟隨胡喬木、胡繩工作,包括參與1990-1991年間《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下文簡稱《七十年》)的編寫。而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最權(quán)威的官方黨史之一,也是定義黨史上諸多重要問題的依據(jù)。
先后主持《七十年》編寫工作的胡喬木、胡繩曾就此做過多次重要的內(nèi)部談話,金沖及出于職業(yè)習(xí)慣對這些講話都做了記錄。他練過速記,又熟悉“二胡”的江蘇口音,錄下的內(nèi)容極其詳盡。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金以林的協(xié)助下將這些記錄整理出版,定名為《一本書的歷史》。

談《一本書的歷史》:不是“著”也不是“編”
澎湃新聞:您整理出版這些講話記錄的緣起是什么?
金沖及:我已經(jīng)84歲了,說實(shí)在話,到這個(gè)年齡,時(shí)間花在哪里是要反復(fù)掂量的。我自己當(dāng)然也還可以寫點(diǎn)東西,但我感覺,自己寫書,不如講講胡喬木、胡繩這兩位同志,他們怎么思考問題,他們講了些什么,我想對后人可能更有用。這就成為我優(yōu)先考慮的事情。
嚴(yán)格說來,這本書是胡喬木、胡繩講的話,我只是記錄、整理,沒有發(fā)表什么自己的議論,更不會(huì)以我的看法改動(dòng)他們的觀點(diǎn)。所以署名只有個(gè)名字,沒有寫“著”,因?yàn)閮?nèi)容不是我寫的,是他們的話;也沒有寫“編”,他們沒有授權(quán)我編。寫我的名字表示我負(fù)責(zé)任就是了,這里的內(nèi)容都是嚴(yán)格按我自己的記錄整理的。
澎湃新聞:您在前言中再三提醒讀者,這些話是23年甚至24年前說的,有當(dāng)時(shí)的歷史背景,有些問題可能還在思考中,未必都是考慮成熟的意見。那么現(xiàn)在看來是否有些內(nèi)容需要重新商榷討論?
金沖及:這我沒有很多地去想,能把它整理出來我就已經(jīng)松了一口氣。但我想我應(yīng)該做這么一個(gè)說明。這是二十幾年前的講話,而且當(dāng)時(shí)并非準(zhǔn)備發(fā)表的。我相信如果是他們自己寫的話,會(huì)更字斟句酌,寫出來的也許就跟這些記錄稿有所區(qū)別。
要說變化,我想任何一個(gè)人,包括我自己,想寫的東西,隔了十年二十年,可能都會(huì)有變化。這里的很多話,不一定是最后定論,很多是在思考的過程里講的。講話的時(shí)候我都在場,我看他們常常是一面想、一面講,有時(shí)要停一停再講。而他們對文字的推敲非常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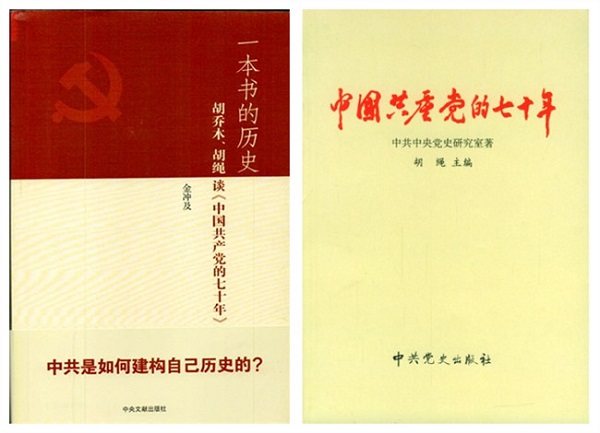
談胡喬木、胡繩:政治和學(xué)術(shù)雙重身份,確立黨史敘述的關(guān)鍵人物
澎湃新聞:胡喬木、胡繩兩位先生在我們的黨史研究工作中是一個(gè)什么樣的地位?
金沖及:胡喬木和胡繩當(dāng)然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大師。對他們的研究,對具體問題,別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夠得上他們那個(gè)水平的人,到現(xiàn)在為止我感覺沒有多少。
胡喬木在延安整風(fēng)的時(shí)候就被調(diào)到毛澤東身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編《六大以來——黨內(nèi)秘密文件》(注:為了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進(jìn)行總結(jié)清算,研究分析六大以來黨內(nèi)的各種原始文件,1941年上半年黨中央決定編輯此書,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正式成書之前,該書曾先以散頁形式選印一部發(fā)給高級干部閱讀,1941年12月正式出版)。這是一個(gè)文件匯編,包括20年代大革命失敗后到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會(huì)議記錄,詳細(xì)極了。會(huì)上誰講話、誰插話、說了什么,都有。這些材料當(dāng)時(shí)裝了十幾個(gè)皮箱,周恩來給瞿秋白寫了個(gè)條子,交給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陳為人保管,叫他脫離一切工作,就管這十幾箱材料。后來抗戰(zhàn)期間陳為人因病去世,就交給另一個(gè)人。準(zhǔn)備進(jìn)行延安整風(fēng)的時(shí)候,要梳理此前黨的歷史,就到上海,從那些箱子里選出一部分送去。胡喬木就編這部資料。

在那之后,因?yàn)閱棠靖诿飨磉叄芏嘀匾缯摱际撬麑懙摹=夥藕螅?951年“七一”,原本要署名中央——或者是少奇同志,我記不清了——出版《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結(jié)果寫出來以后,毛澤東給它署名胡喬木,用他的名字發(fā)表。
這一時(shí)期的黨史,除了何干之的《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講義》、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這兩本是學(xué)校里的教材,并不是中央正式認(rèn)可的——真正意義上的黨史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1990年寫《七十年》的時(shí)候,喬木也講到,當(dāng)時(shí)一般的黨史就只寫到1949年,有的寫到1956年,極少數(shù)提到改革開放。所以《七十年》要搞出一份比較完整、簡要的黨史。
另外,胡喬木、胡繩都是黨史的親身經(jīng)歷者。解放前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一直在他身邊;胡繩長期在《新華日報(bào)》,這是周總理直接抓的報(bào)紙。后來發(fā)生皖南事變,把胡繩派到香港,回來以后還是在《新華日報(bào)》。解放后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幾個(gè)“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們講的歷史,不光是根據(jù)文件來研究,還是親身經(jīng)歷,而且在主要領(lǐng)導(dǎo)人身邊。胡繩跟領(lǐng)導(dǎo)人沒有胡喬木那么密切,但他也經(jīng)常講到少奇同志的一些事、1938年博古怎么講,等等。這是我們很難做到的。

澎湃新聞:那是否可以說,建國后黨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結(jié)論,基本是“二胡”定的基調(diào)?
金沖及:當(dāng)時(shí)管這些事的,主要是他們兩個(gè)。黨史領(lǐng)導(dǎo)小組是楊尚昆當(dāng)主任,副主任呢,胡喬木放在薄一波前面。照理說薄一波資格更老,但這事實(shí)際上是胡喬木在做。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這兩個(gè)機(jī)構(gòu)都是胡喬木當(dāng)主任。后來他不當(dāng)了,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是李琦當(dāng)主任,黨史研究室就是胡繩。胡繩原本在文獻(xiàn)研究室當(dāng)副主任,后來到黨史研究室去當(dāng)主任了。
“文革”前曾經(jīng)要編黨史,當(dāng)時(shí)想成立一個(gè)黨史委員會(huì),由董必武負(fù)責(zé),后來這件事沒有做。除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以及前面提到何干之、胡華那兩本書,幾乎就沒有其他黨史著作。(胡喬木、胡繩主持黨史編寫的工作,)他們管得具體著呢,不是跟你講講思路就算了,寫完他要一遍一遍改,連標(biāo)點(diǎn)都給你改。這樣的大家,管到這樣的程度,(很不容易)。
澎湃新聞:您長期跟著兩位先生工作,也參與了《七十年》的編寫,您覺得他們的講話記錄中,哪些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金沖及:比起具體的論點(diǎn)、問題,更要看他們思考問題的方法,我覺得這對大家有益處。從某種程度上講,如果你看我后來出版的書、發(fā)表的文章,就會(huì)知道,多少是從他們那里學(xué)的,或者按照他們的希望去做的。
跟著他們工作,聽他們那么多講話,我印象很深的有幾點(diǎn):
第一,他們總是強(qiáng)調(diào),寫書要有一個(gè)籠罩全篇的思想、一個(gè)貫穿全書的線索。中國人過去寫文章講究“文氣”,黨史也要這么寫,比如《七十年》要有貫穿黨的70年歷史的那么一口氣,就是告訴別人中國共產(chǎn)黨是怎樣一步步走來的。
第二,講脈絡(luò)線索不能是干巴巴的幾條。寫《七十年》的時(shí)候胡繩同志講過多次,40萬字要寫70年的復(fù)雜歷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說明什么問題,詳略得當(dāng)。他不只一次提到《木蘭辭》:“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寫得很細(xì);但是“萬里赴戎機(jī),關(guān)山度若飛”,上前線的故事那么長,幾個(gè)字就了了。這一點(diǎn)從方法上來講對我也一直有影響。喬木同志則是強(qiáng)調(diào),能讓人身臨其境的材料,就得展開說。比如他講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壯的歷史,那你就應(yīng)該用悲壯的文字寫出來。有一些關(guān)鍵性的事情,得有特寫鏡頭。
第三,強(qiáng)調(diào)“夾敘夾議”,喬木同志講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帶議論的。事實(shí)上他后來也說,有時(shí)議論就在敘事中間。我們這里(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寫很多領(lǐng)導(dǎo)人的傳記,我以后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們這個(gè)思想的影響。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淚。但巴金寫到那里的時(shí)候如果突然跳出來說,你們看,這個(gè)封建大家庭多么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嗎。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事實(shí),把你要議論的內(nèi)容展示出來,這樣議論就是畫龍點(diǎn)睛。
我感到他們有一個(gè)很重要的思想,寫歷史不能像法官寫判決詞一樣,好像讀者不需要思考,這個(gè)事情就是怎么樣的。他講要夾敘夾議,并不是要你離開事實(shí)去發(fā)很多議論,而是把事實(shí)擺出來,從事情本身的經(jīng)過中引導(dǎo)出結(jié)論。它是一個(gè)平等的、商討的過程,不是強(qiáng)加于人。但要是一點(diǎn)議論都沒有,也沒什么意思。所以最后《七十年》的通過討論會(huì)上喬木同志也講,希望同類著作都能夠用這樣一種寫法。
第四,力求準(zhǔn)確。他們很講究文字干凈。我來文獻(xiàn)研究室的第一個(gè)工作就是編《周恩來傳》,給胡繩看過、改過。后來回憶的時(shí)候,胡繩說我都忘了,只記得給你勾(刪)掉了幾十個(gè)“了”字。他說我們講歷史都是過去時(shí),一般不需要“了”。還有,寫“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huì)”,他說“秘密”這兩個(gè)字應(yīng)刪,因?yàn)樵趪顸h統(tǒng)治區(qū)沒有哪一次中央全會(huì)不是秘密召開的。所以他對文字、包括提法的準(zhǔn)確度要求很高。

澎湃新聞:那您覺得他們是不是不可復(fù)制的?既是當(dāng)事人,又是理論家,這樣的黨史工作者是不是很難再出現(xiàn)了?
金沖及:是,我就感覺現(xiàn)在很難能夠找到代替他們(的人),一方面他們親歷了許多關(guān)鍵時(shí)刻,常常在領(lǐng)導(dǎo)人身邊,這個(gè)本身就(不容易);另外他們的知識面(廣)、理論水平(高)。胡繩說胡喬木是百科全書式的學(xué)者,其實(shí)我看胡繩也是百科全書式的。他們兩個(gè),無論是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歷史學(xué)、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哪個(gè)方面的問題去找他,他都能講出一番你沒有想到的道理。講得夸張一點(diǎn):我看現(xiàn)在我們的理論工作者中,像他們這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一個(gè)也沒有。
澎湃新聞:不少學(xué)者研究胡繩晚年的思想變化。比如他說“如果不經(jīng)歷一些過渡階段,不能保證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高度發(fā)展,不能享受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徑直走向社會(huì)主義的勝利和成熟的。”有人批評他“走資本主義的回頭路”。您怎么看?
金沖及:以我跟他的接觸,在我聽來,他就是認(rèn)為,對資本主義好的東西,我們必須學(xué)過來,以前不強(qiáng)調(diào)這一點(diǎn),是個(gè)失誤,我知道他是這樣一個(gè)思想。但要說反對社會(huì)主義、主張搞資本主義,他不會(huì)有那樣的想法。他寫了一篇《中國為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寫好了卻沒有發(fā)表,為什么呢,因?yàn)樗f還有一半沒有講。他指的就是,我們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但資本主義好的東西,它跟現(xiàn)代化大生產(chǎn)相結(jié)合的那些東西,我們都要好好學(xué)。我認(rèn)為,他的想法只是到這里。
談《七十年》:背后的問題關(guān)懷是“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不垮”
澎湃新聞:《七十年》寫作和出版的時(shí)代背景很關(guān)鍵,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1989年國內(nèi)國外的一系列風(fēng)波。時(shí)代背景對于這本書的寫作有什么影響?
金沖及:1990年提出要出版這本書。大家知道那時(shí)候東歐基本上都變了,前蘇聯(lián)還沒解體,另外1989年的風(fēng)波剛剛過去,這時(shí)提出的一個(gè)問題就是:那么多共產(chǎn)黨都垮了,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不垮?黨史就是要告訴人家,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一個(gè)怎么樣的黨,如何一步步走來,這個(gè)過程不容易。我覺得,那個(gè)特定的條件下,迫切感到需要把這些問題講講清楚,是很自然的。
但真到1991年寫的時(shí)候,我們也沒有很多地涉及東歐,就是把中國共產(chǎn)黨本身是什么說清楚。這個(gè)黨在中國的土地上自己摸索,會(huì)碰釘子,他也不可能一開始都想得對。碰釘子以后總結(jié),總結(jié)了改正再前進(jìn)。喬木講要“實(shí)踐-認(rèn)識-再實(shí)踐-再認(rèn)識”,我們心里想寫的就是這個(gè)。
澎湃新聞:《七十年》對黨史上的問題提出不少新看法,胡喬木也說這本書的特點(diǎn)是“不滿足于重復(fù)已有的結(jié)論與研究成果”、“獨(dú)立做出判斷”。可不可以說,對于抗戰(zhàn)的正面戰(zhàn)場、土地改革、延安整風(fēng)這些問題的說明,是在1991年《七十年》、包括后來的《黨史二卷》出版以后,才得以打破“禁區(qū)”?
金沖及:也不能說是因?yàn)檫@兩本書出來才打破,我覺得在那之前已經(jīng)陸續(xù)放開了。其實(shí)你讀《毛選》的話,它對正面戰(zhàn)場也有肯定。我跟臺(tái)灣學(xué)者講,我是接受國民黨教育長大的,不是共產(chǎn)黨教育長大的。我1947年進(jìn)復(fù)旦大學(xué),解放前還做了兩年大學(xué)生。所以我當(dāng)然知道國民黨的正面戰(zhàn)場。這一類問題,我一直就覺得沒什么不能講的。當(dāng)然有的同志可能擔(dān)心一點(diǎn):怎么共產(chǎn)黨的(抗戰(zhàn))你不講,光講國民黨的?或者說共產(chǎn)黨講得少了、國民黨講得多?有時(shí)候因?yàn)橐郧斑@方面講得少嘛,一段時(shí)間多講一點(diǎn)我覺得也沒什么了不得。
關(guān)于蔣介石的抗日,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在《七十年》中有一句話,說當(dāng)時(shí)國民黨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對抗戰(zhàn)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xiàn)。這最開始是我寫的,我寫“蔣介石對抗戰(zhàn)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xiàn)”。后來胡繩可能考慮到用黨史研究室(的名義編的),就改了一下,改成“中國國民黨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主要領(lǐng)導(dǎo)人嘛,當(dāng)然就是蔣介石了。
澎湃新聞:為什么在1991年就敢講這樣的話?
金沖及:我覺得事實(shí)是這樣,就這么寫了。抗日戰(zhàn)爭我是經(jīng)歷過來,1935年進(jìn)小學(xué),之后抗戰(zhàn)爆發(fā),1945年我高中一年級念完準(zhǔn)備升高二。蔣介石做了什么,我自己也看到的,這是事實(shí)。而且讀《毛選》也可以找出根據(jù)來。另外胡繩改得也是很巧妙。
澎湃新聞:《七十年》這本書的議論性很強(qiáng),寫作過程中的作為研究人員的“自由裁量權(quán)”有沒有受到影響?
金沖及:如果說史料清清楚楚、完全有把握,那么不管以前什么結(jié)論,事實(shí)是什么樣,就改過來寫,沒有問題。但是有兩種情況特殊。一種是和中央有過決定的重要問題結(jié)論不一樣。比如第一個(g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析錯(cuò)誤的階級根源,說是因?yàn)樾≠Y產(chǎn)階級犯錯(cuò)。胡繩別的問題沒有報(bào)告,這個(gè)問題專門報(bào)告了一下,說我們這本書里沒有這樣寫,為什么,因?yàn)檫@樣講就意味著你要求無產(chǎn)階級不會(huì)犯錯(cuò)誤,但事實(shí)上無產(chǎn)階級如果對形勢判斷錯(cuò)誤,也會(huì)犯錯(cuò)。為什么要專門報(bào)告呢?因?yàn)檫@個(gè)論述跟中央發(fā)表過的重要文件不一致。報(bào)告了以后他們也都同意,那就這樣寫。還有一種,是重大問題而你又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我舉個(gè)例子,誰最早提出游擊戰(zhàn)十六字訣(“敵進(jìn)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兩位當(dāng)事人、都是負(fù)責(zé)同志,一個(gè)說是毛主席提的,一個(gè)說是朱總司令。我個(gè)人也可以有判斷,但又不能說百分之百有把握,這個(gè)事情又重大。所以,我原來寫了幾千字初稿,又把它全勾(刪)掉了。因?yàn)檫@本書是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出版的,不是個(gè)人名義,兩個(gè)當(dāng)事人說法又不一樣,我不能根據(jù)自己的判斷就寫。除此以外,問題都不大。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說,胡繩在寫《七十年》期間看了好幾本外國學(xué)者寫的關(guān)于中共黨史的書籍,包括特里爾的《毛澤東傳》、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他認(rèn)為麥克法夸爾的書“臆測居多”。那么我們的黨史寫作,是否還是主要受前蘇聯(lián)黨史寫作(《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影響?
金沖及:當(dāng)然有很大影響,現(xiàn)在無法一一展開。但我是非常認(rèn)真地學(xué)過聯(lián)共黨史,尤其是1952、1953年的時(shí)候(注: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四次會(huì)議上發(fā)出號召“應(yīng)該在全國掀起一個(gè)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高潮來建設(shè)我們的國家。”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黨員干部學(xué)習(xí)《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尤其是九到十二章(即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民恢復(fù)國民經(jīng)濟(jì)、實(shí)行國家工業(yè)化和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內(nèi)容)。光筆記就寫了滿滿一本。

談黨史研究:西安事變有些檔案當(dāng)時(shí)為什么不能公開
澎湃新聞:您覺得黨史是一個(gè)政治理論還是一門科學(xué)?黨史研究和一般歷史研究最大的差別在哪里?
金沖及:當(dāng)然是科學(xué)。講歷史首先要有事實(shí)根據(jù),你要有一個(gè)論點(diǎn),得拿證據(jù)來。我和中宣部的領(lǐng)導(dǎo)同志也說過,宣傳跟研究,是有聯(lián)系、有差別的。宣傳是把已經(jīng)知道的結(jié)論——對或不對可以推敲——讓更多人知道。這是已經(jīng)解決的、有定論的問題。當(dāng)然,宣傳工作極重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好,要擺事實(shí)、講道理使人信服。而研究工作,是要解決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黨史研究和一般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樣的。當(dāng)然,我也很坦率地說,黨史涉及的問題有時(shí)候敏感性很強(qiáng)。
舉個(gè)例子,西安事變。周總理在世的時(shí)候,他說西安事變的事情你們不能隨便寫,因?yàn)閺垖W(xué)良現(xiàn)在還在臺(tái)灣,要考慮他的安全問題。這是很現(xiàn)實(shí)的問題。1980年代初,我是文獻(xiàn)研究室副主任,我們的刊物《文獻(xiàn)和研究》首次公開了關(guān)于西安事變的幾十個(gè)電報(bào),那是當(dāng)時(shí)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個(gè)電報(bào)。它講的是對蔣介石的處理:“必要時(shí),誅之為上。”我看過大量相關(guān)的(未公開)檔案,我也知道,第一,所謂“必要時(shí)”是指兩種情況,在另外的檔案里講得很具體——一是國民黨的中央軍進(jìn)潼關(guān),要打到西安了;第二種情況是內(nèi)部不穩(wěn)。在這些前提下“誅之為上”。這話本身沒有錯(cuò),周恩來也公開講:只要你們中央軍不進(jìn)潼關(guān),委員長的安全是有保證的。這個(gè)話反過來意思就是,那要是進(jìn)了潼關(guān),對不起,他的安全就沒有保證了。但那個(gè)時(shí)候我把這封電報(bào)扣下了,沒有公開。為什么呢?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必要時(shí)”指什么,看到這個(gè)就會(huì)簡單說共產(chǎn)黨是主張殺蔣介石的,這不符合實(shí)際。有些人就會(huì)渲染,說哦,原來還有一個(gè)“誅之為上”的說法。而且你越解釋,人家越認(rèn)為你要逃避問題。另一方面,張學(xué)良還在臺(tái)灣,這不能不考慮。所以就沒公開。后來有人編西安事變的書,把這個(gè)電報(bào)發(fā)了,萬毅,當(dāng)時(shí)的七大候補(bǔ)委員、東北軍的將領(lǐng),就寫信給胡耀邦,說這個(gè)電報(bào)不該發(fā)。耀邦同志就通知這本書停售。那么我想,當(dāng)時(shí)的決定沒有錯(cuò)。所以,黨史研究牽涉一些現(xiàn)實(shí)、敏感的問題,跟其他如古代史研究就不一樣。
我有一次看英國人寫的太平洋戰(zhàn)爭,是根據(jù)美國1980年代初公布的檔案寫的。書里有好幾個(gè)地方寫到,公布的材料是復(fù)印的,有些地方被遮蓋了。可見美國的檔案,涉及到他認(rèn)為有現(xiàn)實(shí)影響的、政治敏感的檔案,也不會(huì)公布。
但是,從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公布出去的檔案,大概比什么單位都多。這個(gè)話,我想大概并不夸張。
談“非官方”黨史:有些材料他們看不到,只能靠猜
澎湃新聞:您編著的可以說都是“官修”黨史,那么您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在社會(huì)上也非常活躍的黨史學(xué)者?
金沖及:我有一次在山西跟高華聊了半天。要說年齡,我差不多比他長一輩。他父親是廈門大學(xué)地下黨,我是復(fù)旦大學(xué)地下黨,所以講經(jīng)歷很多事情都能夠說到一起。他父親被打成右派,我想這對人看待問題確實(shí)會(huì)有影響。
高華的書出版后就寄給我了,當(dāng)時(shí)因?yàn)槠渌驔]有全部看,但我聽別人說了大概印象。關(guān)于延安整風(fēng),他用的是公開發(fā)表的材料。延安整風(fēng)核心的材料是會(huì)議記錄,特別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會(huì)議記錄等等,很關(guān)鍵,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統(tǒng)地看過就會(huì)知道,有些東西他還是比較隔膜,很多是靠猜。
2008年前后我到法國去,當(dāng)時(shí)有一個(gè)德國教授講毛澤東,我就說你有幾件事講得不對,我的根據(jù)有會(huì)議記錄、有當(dāng)時(shí)的電報(bào),一條條講。休息的時(shí)候他就過來,他說是啊,你講的這些檔案會(huì)議記錄我們都看不到,只能去猜了。這倒也是老實(shí)話。延安整風(fēng)里面當(dāng)然有很多問題,特別是搶救運(yùn)動(dòng)。但是從會(huì)議記錄來看,最中心的問題是反對主觀主義,實(shí)事求是也是這時(shí)提出來的。陳云也講過一句話,說我延安整風(fēng)時(shí)候把毛主席起草的這些電報(bào)文件系統(tǒng)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就是“實(shí)事求是”。

澎湃新聞:楊奎松先生的研究很棒,在讀者中也很有影響,您怎么看?
金沖及:楊奎松的東西我當(dāng)然看,他書都送我的。他的第一本書還是我給寫的序言,《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有許多長處,搞材料是非常用功的。說起來他們搞材料沒有我們這樣方便,有很多是一個(gè)省一個(gè)省的檔案館去跑,另外他一直在那里想問題。所以楊奎松到北大去當(dāng)教授,我給他寫的推薦信。推薦信當(dāng)然都要全面地講,我先講了他的很多優(yōu)點(diǎn),也講了一句,有時(shí)候有片面性。
我覺得創(chuàng)新有兩種。一種是原來的結(jié)論沒有錯(cuò)、但很籠統(tǒng),你用大量的事實(shí)把它弄清楚。另一種是過去說錯(cuò)了,你糾正。現(xiàn)在都認(rèn)為后面那種才是創(chuàng)新。關(guān)于“翻案”,有一次胡繩跟我講,說他們要?jiǎng)?chuàng)新,把我推倒;結(jié)果推倒我的意見,在我看來就是當(dāng)年我們推倒的蔣廷黻他們的意見。人有時(shí)候總是喜歡一個(gè)新鮮的說法,以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婦女穿旗袍,一段時(shí)間風(fēng)行長旗袍,過了一陣又流行短旗袍。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可以這樣講,有的事情,有時(shí)候不方便講我頂多不說,絕不會(huì)明知不是這樣,卻瞎寫。假如是你的推測,用“看來、據(jù)我分析”,那也好。寫過周恩來的高先生,他出國前我們就坐在這個(gè)沙發(fā)上聊了一下午。我們都很熟。他的那部書,兩頭引的材料都是真的——他的引文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沒有發(fā)現(xiàn)有編造的——但是,兩段引文中間的敘說,有很多是他的推想。人家一看,全信了,全接受了。對這些情況,我的想法就是,我認(rèn)為怎么樣的,就怎么說。不方便的,我最多是不說,我絕不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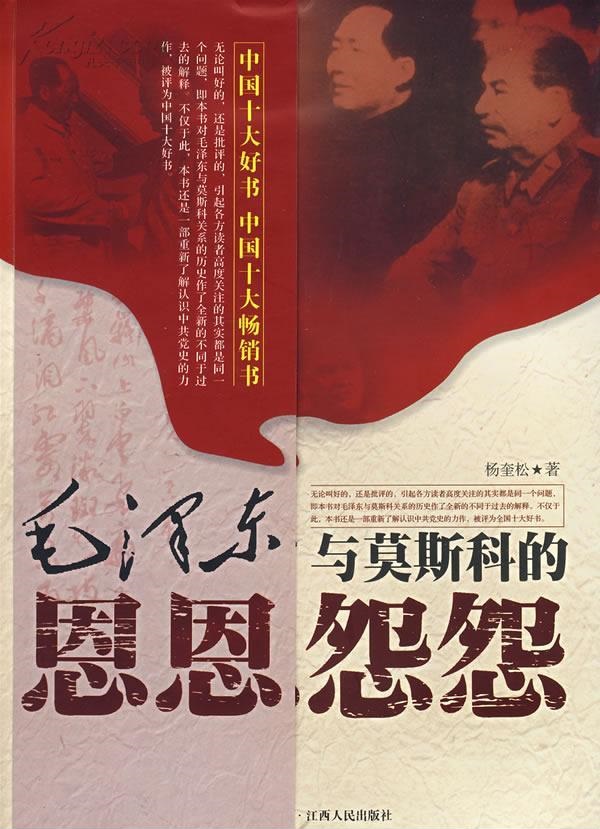
澎湃新聞:現(xiàn)在民間對中共黨史、國民黨史的研究都很有興趣,他們可能更愿意聽和官方敘述不一樣的歷史。您怎么看?
金沖及:可能有很多原因。現(xiàn)在的人有一種心理狀態(tài),如果我說共產(chǎn)黨對,他們就說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學(xué)家),你替政府辯護(hù)。另一個(gè)人說共產(chǎn)黨不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挑它的過錯(cuò)講,人們覺得這是過去沒聽說過的,(就趨之若鶩)。這種心理狀態(tài)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但看問題是不是一定非得這樣看?
剛才說我和高華的父親是同一輩人。我也在“文革”中吃過好幾次苦啊,但現(xiàn)在我想的還是希望把我們的國家搞好。
其實(shí)我這個(gè)人,跟我熟悉的都知道,我大概屬于比較溫和的,不是很極端的人。我當(dāng)年上學(xué)也是去讀書的,不是一開始就想著去革命。那時(shí)是想著,這國家搞到這樣怎么辦啊,大學(xué)生要改變它。那么共產(chǎn)黨的主張我接受,我就參加。
我現(xiàn)在不是說,國民黨的好話一句也不能講。這我太了解,我是接受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我上學(xué)時(shí)就讀過《緬甸蕩寇志》(關(guān)于中國遠(yuǎn)征軍在緬甸作戰(zhàn)的作品,1946年出版),感到很佩服的。我們也都看,不是不知道(國民黨抗戰(zhàn))。但現(xiàn)在人好像有一種逆反心理,講國民黨凈說好的,講共產(chǎn)黨凈說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實(shí)啊。有些人說這些過去我都不知道,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啊。我只能說,有的是事實(shí),有的是事實(shí)的一部分。現(xiàn)在人的心理狀態(tài)就覺得,誒,這是老一套,那個(gè)新鮮,就相信那個(gè)。但是我看(有些研究),總是感覺,哎,他太年輕,他沒有經(jīng)歷過。
我今天也不是官方的代表了,沒有義務(wù)去為什么辯護(hù)。我現(xiàn)在沒有官職,只是說我自己的看法。
當(dāng)然聽不同的聲音常常是有益的。有一次我參加中國大陸、臺(tái)灣、日本三方共同參與的研討會(huì),談中日戰(zhàn)爭里的軍事問題。日本、臺(tái)灣學(xué)者的發(fā)言也給我很多啟發(fā),對于不同的敘述,如果有道理,那我就要放棄原來的看法。比如跟臺(tái)灣學(xué)者蔣永敬討論的時(shí)候,他說“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不是孫中山提出的,國民黨一大也沒有提。我仔細(xì)查材料,確實(shí)找不到,這話他站得住。那我就跟他講,我接受這個(gè)意見,三大政策是后來才提出的。但是,在實(shí)際工作中孫中山是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蔣永敬說這他也能接受。這就是一個(gè)例子,我們跟臺(tái)灣學(xué)者可以達(dá)成共識:孫中山和國民黨一大沒有提三大政策,但事實(shí)上是照那樣做的。
(澎湃新聞實(shí)習(xí)生石偉杰協(xié)助訪談錄音整理,謹(jǐn)此致謝。)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