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張弛: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是如何降臨的?
【編者按】
張弛,1982年生,浙江湖州人,2012年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現任教于浙江大學,主攻17-18世紀法國史,譯有威廉·多伊爾所著《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牛津法國革命史》(北京師范大學即出),熱拉爾·瓦爾特《羅伯斯庇爾傳》(商務印書館)。
不久前,他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專著《法國革命恐怖統治的降臨(1792年6月—9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書中,他將研究觸角深入連外國學者都少有涉及的法國革命中的“第一次恐怖統治”,乃至有網友將其譽為“年度最佳的法國史著作”。
張弛曾于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在哈佛訪學,師從法國革命史專家伊格內教授和著名新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教授。在此期間,他有幸旁聽了達恩頓在哈佛首次開設的書籍史課程。課堂上,達恩頓真實再現了過去書籍“誕生”的一系列環節,這深深影響了他,從此閱讀史料之于他就是一種觸摸歷史、感知過去的體驗。
作為優秀的世界史青年學者,張弛對國內世界史的研究前景充滿信心,他認為任何國家對別國史的研究都有一個漸進緩慢的發展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他認為對于世界歷史的研究不要緊盯著與國際對話,而是要發現歷史研究中的樂趣。
本訪談后還附有張弛推薦的2014年“年度史書”。

澎湃新聞:您最新出版的《法國革命恐怖統治的降臨(1792年6月—9月)》和法國史學大家勒費弗爾的名著《1789年》(Quatre-Vingt-Neuf: l’année de la Révolution,漢譯本為《法國大革命的降臨》)的書名有相似之處。請問如此命名是否意味著您在向這位前輩史學家致敬?
張弛:敬意由來已久,但是致敬,卻配不上。
勒費弗爾是史學大師,法國革命這塊研究領域,從來不乏大師級的人物。如勒之前的奧拉爾(Alphonse Aulard),同時代的馬迪厄(Albert Mathiez),饒勒斯(Jean Jaurès),還有后來的孚雷(Fran?ois Furet)。無論是在研究的開創性上,還是轉折方面,這些人都起到過十分關鍵的作用。但與這些人相比,勒的特點很明顯。他的研究要比奧拉爾更具厚度,又不像馬迪厄和孚雷那樣鋒芒畢露,比起饒勒斯來,他對思想和觀念的分析更見功力。我讀他的書是一種享受,他能把敘述和分析,歷史的斷裂與延續、個人與時代,思想與現實,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在我看來,語境主義或歷史主義這些現在比較時髦的方法論,說到底就是恰到好處。
勒費弗爾靠自學成才。他的國家博士論文《法國革命期間諾爾省的農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有一千多頁,數百頁的統計表格。這是他利用高中教書的業余時間,跑遍了弗蘭德斯數百個村莊,花了二十年完成的。勒費弗爾說,這是他第一個蜜月。他平生還有兩個蜜月:三十年代下鄉做調查,是第二個蜜月,這成就了他那部 《1789年大恐慌》(La Grande Peur de 1789),能把謠言在一個個村莊間傳播這件事寫得那么有趣。到現在我都能記得自己當年讀這本書時,甚至能體會到作者在翻檢檔案,有所發現時的那種興奮愉悅。第三個蜜月是他80歲時,坐農民的板車,調查奧爾良地區的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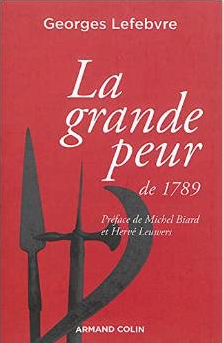
勒費弗爾到老都喜歡坐公交,坐板車,從不坐頭等艙。他始終覺得,學者應當是清貧的。所以他對牛津大學的奢華很不能理解,這么好的條件怎么能做研究?勒費弗爾自己的生活也帶有點苦行僧的味道,守時、簡單、樸素。一張破藤椅,白天讀《人道報》,晚上讀《世界報》。書桌上放著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饒勒斯的照片,還有一尊羅伯斯庇爾的破胸像。他的生活就有點羅伯斯庇爾的味道,他覺得歷史學家是不應該結婚的,結果那位既崇拜他,也怕他的索布爾(Albert Soboul),在結婚兩個月后,才敢告訴他的老師。
勒費弗爾的幾部代表作,都有中譯本。這里尤其要推薦顧良先生主譯的《法國革命史》。這本書是我的入門讀物,當時法語不好,對照著法文本、英譯本,還有這本中譯本看。這本譯本不僅僅翻譯得準確,我覺得甚至把勒費弗爾特有的那種精煉簡潔都表現出來了。《泰晤士文學副刊》曾這樣評論勒的著作:敘述毫無瑕疵,但不太生動。中譯本體現得特別好。當然,首先要能讀得進去。
澎湃新聞:您的這本著作著眼于1792年6月到9月的法國大革命,而這段時間通常也被稱為“第一次恐怖”,是雅各賓派恐怖統治的前奏和序曲。您能否簡單介紹下您選擇研究“第一次恐怖”的緣由?
張弛:其實很偶然。勒費弗爾有套《索邦講稿》(les Cours de Sorbonne)。從1789年革命一直講到督政府,有六卷,大概是當年在索邦大學的講課筆記,國內學界好像不太關注,或許是因為印數很少的緣故。我有一套,是油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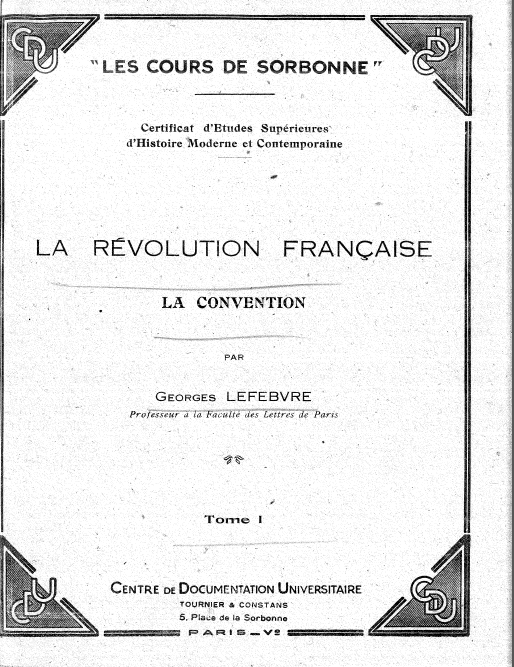
《索邦講稿》中有一冊就是“第一次恐怖統治”,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詞。據我所知,這也是國際學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研究。當時我在哈佛,哈佛沒有這套書,靠館際互借,從伯克利借來。讀了之后,覺得這一階段的恐怖統治與1793年大為不同。于是就開始留意了。勒費弗爾的講稿有一個特點,這是份不成型的研究,有些問題上是猜測,有些判斷則比較大膽,所以能讓你看到很多研究的空間。
其實一旦留意,就有了問題,情況就不一樣了,自然會對相關材料開始留心。而且,后來我又注意到了卡龍(Pierre Caron)編訂的幾冊通信集,是第一次恐怖統治時期,由立法議會派到外省,執行緊急任務的特派員的信件。卡龍原來是法國國家檔案館的管理人員,寫過《九月屠殺》(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1792年9月初三天的事情,花了七百頁,典型的法國人研究。大約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卡龍決定研究立法議會的特派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沒有完成這個計劃。在學界,關注這個題目的人很少,大約只有一個人做過專門研究。根據這些情況,我大約覺得第一次恐怖統治可做番研究。
前幾天,法國魯昂大學的比亞爾教授(Michel Biard)來浙江大學訪學。他是革命史權威伏維爾(Michel Vovelle)的學生,擔任過《法國革命年鑒》主編。我送了兩本給比亞爾。他說要給《法國革命年鑒》寫個書評,另外還告訴我美國史家的塔克特(Timothy Tackett)明年要出一本與我同題的書,也是講恐怖的誕生。這是個令人既興奮,又有點忐忑的消息。我讀過塔克特的所有論文和專著。在革命史學界,他的研究有“十年磨一劍”的美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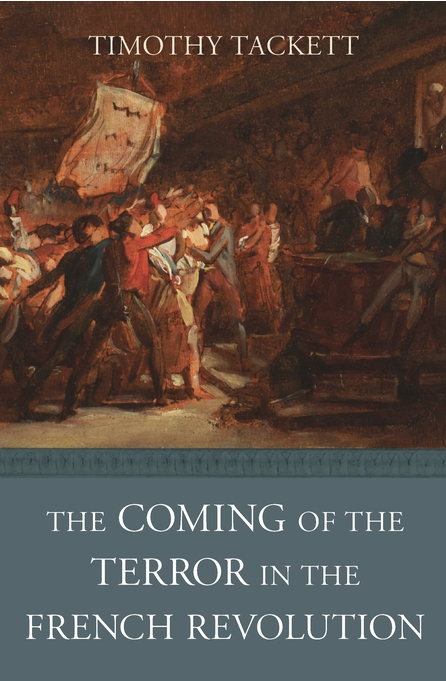
澎湃新聞:1792年6月到9月,這段時間醞釀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同時法國持續近千年的君主制被廢黜。我注意到書中提及這樣一個現象:8月10日革命后,民眾有著廣泛的廢黜君主制的呼聲,卻較少提及建立共和國。法國人為什么不用“共和國”這個詞來描繪他們的新制度。
張弛:這的確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奧拉爾、勒費弗爾等法國史家都說過這個問題。奧拉爾遍查了所有材料,發現僅有羅貝爾(Robert)支持建立共和國。但是羅貝爾這個人的材料不太可信,我覺得他更像是借共和之名,為自己拉選票。
我想,當時的法國人對他們過去的看法很明確,要廢黜君主制,而他們對未來的看法也很明確,即要建立一種真正能體現人民主權的體制,用國民公會代表巴巴魯(Barbaroux)的話說,這種主權不能因為被代表就沉默了。他們要的是一種永遠活躍著的人民主權,能不斷地對現有的體制實行監督,能發表輿論,能審核所有法案,對憲法實行公投,能撤回不合格的代表。這也就是索布爾說的無套褲漢的民主觀念。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這樣的觀念正在成型。他們要建的新體制,是能體現這種民眾觀念的體制。而這樣的一種體制,無法用共和制來概括。因為歷史上所有的共和國都不符合他們的想法。換句話說,“共和”這個詞屬于過去,而他們是在創造一種全新的體制,無先例可循。所以,他們不提共和國,這表明,他們是在創造歷史,而不是重復歷史。就這個問題,我請教過比亞爾。比亞爾在浙大講座,就是有關革命前后的共和思想。他很贊同我的看法。

澎湃新聞:研究法國大革命,有一位人物從來不可能被忽略,他就是被稱為“不可腐蝕者”(l’Incorruptible)的羅伯斯庇爾。您能否談談您眼中的羅伯斯庇爾?
張弛:羅伯斯庇爾是個復雜的人物,從19世紀以來就如此。我去年翻譯了本書,以前有節譯本,《羅伯斯庇爾傳》,要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是法國人熱拉爾(Gérard Walter),就19世紀人對羅的評價,寫得很詳細。
關于這個人,我想談一點。很多人都覺得,羅伯斯庇爾是抽象的理論家,好幻想,好原則,不切實際。我想,如果太把羅伯斯庇爾本人說的話當作歷史本身,當作事實,那就會出現這樣的看法。他的確有很多煽情的話,對社會的不平等,對財富的不平等,但是要放在具體的環境里看。
我覺得羅伯斯庇爾恰恰是合格的政治家,審時度勢,他很清楚,沒有無套褲漢支持,救國委員會難以立足,更談不上號令全國。他要做的就是拉攏無套褲漢。他的言論,以及當時救國委員會頒布的不少帶有“社會民主”色彩的法令都是為了這個目的。但是,羅伯斯庇爾很清醒,依靠無套褲漢,絕不等于被他們牽著走。所以,當更激進的平民領袖挑戰救國委員會的時候,他毫不手軟,把包括丹東在內的一干人等送上斷頭臺。這是所謂的風月芽月危機。
學界通常認為,熱月政變的本質是資產階級重新鞏固自己統治,是對共和二年的背棄。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從風月芽月就開始了。而且啟動這個過程的正是羅伯斯庇爾。不過,打壓了平民,救國委員會看似權力更穩,實則不然,它很快在熱月政變中落敗。對此,羅伯斯庇爾也是早有預見。

澎湃新聞:您研究的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恐怖”,而公眾熟知則是1793年開始的雅各賓派恐怖。在您看來,“第一次恐怖”對雅各賓派恐怖有著什么樣的影響?
張弛:首先要澄清一點。第一次恐怖統治沒有結束,只是緩和了。這兩次恐怖統治嚴格來說只是革命恐怖統治的兩個階段。所以,我想更合適的問題,或許應該是第一次恐怖統治對此后的革命政治有何影響。
我想可以說以下幾點。首先,1793年恐怖的很多措施在這時期都已成型了,包括革命法庭、特派員、基本的恐怖法令,還有那種強調共和美德的激進的政治文化。只不過,第一次恐怖統治在廣度和強度上比較有限。
另外,誕生于第一次恐怖統治的共和國是分裂的,體現在方方面面,吉倫特派與山岳派的分裂,巴黎與外省的分裂等等。我們知道,大概從1789年來,外省基本上唯巴黎馬首是瞻,但在1792年之后情況不同了。這些分裂對共和二年的政治有直接的影響。要注意的是,分裂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源自啟蒙的那種樂觀主義、浪漫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情緒,受到了現實政治的強烈沖突。后期的很多政治分歧都與此有關。
可以說,1792年是革命心態的轉折點。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平民登上了政治舞臺,并且發揮了絕對性的作用。當然,革命一開始就有民眾介入,比如攻占巴士底獄,但是在1792年之前,平民的力量從未對政府議會構成威脅。第一次恐怖統治卻不同,民眾不僅再度影響了革命的進程,而且他們構成一股革命的權力,與議會的正統權力并駕齊驅。這個情況不斷激化,到了1793年5月底,革命的權力甚至威脅到了議會代表的人身安全,吉倫特派因此倒臺。
與平民的出現有關,第一次恐怖統治孕育了民主共和主義、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這三種政治文化不僅體現在政治上,而且也體現在社會經濟層面,它們之間的交織互動,是理解共和二年恐怖主義的很重要的線索。
澎湃新聞:對于恐怖統治的研究,歷來似乎有兩派學者爭論不休。一派認為恐怖統治是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的結果,另一派則認為恐怖統治是政治理念的產物。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環境論”與“觀念論”之爭?
張弛:環境論與觀念論的論戰由來已久,熱月政變以后大概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本書的導言里,我有過簡單介紹。大體上,形勢論強調客觀作用,認為恐怖統治是應對危機的非常手段,觀念論則認為不管有沒有外因作用,恐怖終歸要產生的,這是革命根本觀念所致。
我看,這兩種觀點都有問題。第一,盡管針鋒相對,但是都把革命者看作是被動的,幾乎完全忽視了人的主動性能動性。比如,觀念論實際上就是一種宿命論,不管革命怎么發展,遇到什么情況,恐怖一定會來的,所以和誰當政,誰在其中,毫無關系。實際上,很多恐怖法令在危機到來之前就已經頒布了。這說明,恐怖不能簡單看作是對外界危機做出的反應。現在不少新的研究,都在強調革命者的所作所為對恐怖誕生的影響。比如法國學者葛尼菲(Patrice Gueniffey)有本《恐怖的手腕》(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他的觀點是恐怖在1791年4月就出現了,當時的一些政治家想要通過頒布更激進的法令,來為自己博得聲望,是利用恐怖,以達成政治目的的做法。所以,他把恐怖看成是一種政治工具,是一種手腕。
但葛尼菲的書有明顯的缺陷,太狹隘。他說的恐怖統治,就是一種專斷的權力。但實際上恐怖統治是有多層面的,多階段的,每個層次的恐怖完全不同,不可能只歸結到一個原因上。這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我覺得,至少有三個層面。首先,是因為出于對貴族陰謀的擔心和恐懼,簡單地說,是總擔心貴族或其他反革命勢力搞破壞,因此要先發制人,這種恐怖是預防性的。第二,法國革命時期的戰爭是全民戰爭,軍隊極其龐大,為滿足軍隊的供給,救國委員會采取了經濟統制,要把一切人力物力統一起來,為戰爭服務,所以就有了限價令、全面征兵等各種措施。在這個層面上,恐怖統治即是這種國家主義的一個有力保障,即靠著恐怖這種強制手段,強迫社會服從國家號令,比如私藏錢財,有武器而不愿上報,這些行為都成了恐怖懲罰的對象。第三個層面的恐怖統治是為了維護救國委員會統治,這體現共和二年芽月風月,把丹東、埃貝爾一干人等送上了斷頭臺,隨后頒布牧月法令,救國委員會凌駕于國民公會之上。恐怖統治進一步強化,但已不是為了應付危難。
這三個層次,既是恐怖統治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是三種不同性質的恐怖統治。第一種與心態有關,第二種與恢復國家權威有關,第三種則與專政統治有關。觀念論的代表孚雷曾說,1793年3月是革命最困難的時候,但處死的人遠沒有1794年年初多,他由此得出結論,說恐怖和環境是沒有關系的。他的問題就在于沒有注意到恐怖統治的多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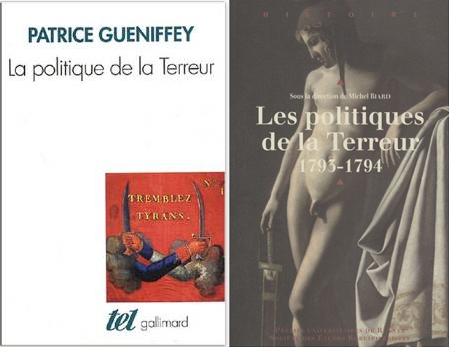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您在研究恐怖統治和革命政府時,有不少與法國學者商榷、對話的內容。那么您的研究同以往學界對法國革命的認識有何不同?
張弛:要說有對話,那還夠不上格。只能說在某些小問題上,略有些心得體會罷了。
我們以前常認為危機之下,往往會出現一個集權的革命政府,比如1793年的山岳派專政。1792年夏天的情況也很糟糕,內有貴族作亂,外有普軍逼近,8月10日革命前國王還連連否決議會法案。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并沒有出現任何集權的跡象。相反,立法議會采取的措施是,越是危機,下放的權力越大,市鎮享有的自由也越多。第一次恐怖時期,沒有類似后來救國委員會這樣的集權政府,這是一個最明顯的區分。
另外,我們都知道,托克維爾曾說,中央集權不是大革命的發明,而是舊制度的成就,換言之,中央集權的發展跨越了革命的斷裂,從路易十四一直延續到拿破侖帝國。但是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我注意到,1789-1792年實際上是國家力量被削弱了,政府也沒有那么大的權威,中央對地方的監管也不太有力。在本書中,我對這個現象做過分析。實際上,如果我們細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及他的遺作《革命與帝國》(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會發現他的看法也不是那么簡單的。
澎湃新聞:聽法國史研究者評價,您是國內世界史學者中少數史料、理論功底俱佳的一位。而似乎您碩士期間還醉心于理論,對史料還不夠重視。據說您窮盡史料,最初是因為知名新文化史家達恩頓教授的一節課。能否細說下具體的情形?
張弛:這個問題覺得有些突然,我想需要澄清一下。首先,功底俱佳是過譽了,決不敢當,我只不過對兩者都有濃厚的興趣 。
讀史料的感覺令人難忘。史料好像是有魔力的,你打開它,馬上就能聽到兩百多年前的人說的話,他們就像電影里人一樣,突然活了,你似乎就到了國民公會的會場。一旦把史料合上,就恢復平靜了,好像都沒發生過。這種使死人復活帶來的沖動,應當是極其強烈的。所以我很能理解法國史家羅什(Daniel Roche)為什么會認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發現了梅尼特拉的日記。

羅什主編《梅尼特拉日記》,羅伯特·達恩頓作序,1998年。
當然,理論的魅力也是難以抗拒。我說的“理論”應當做寬泛的理解,不只是某類成型了的解釋框架,而是一切能道出我從未能意識到的東西。在一次訪談中,史家金茲伯格說,“我們在說的語言,并不是由我們這一代人發明的。那是一種有著若干層次的語言,嵌著一些非常古老的詞匯。”這也是理論,它讓我突然覺得,這些習以為常的東西,突然陌生了,原來天天用的東西竟然有這樣的厚度。
說到達恩頓教授的課,那是他在哈佛大學第一次開書籍史,我有幸旁聽。你知道,他的書籍史有個特點,即是研究與書相關的那些人的歷史,比如賣書的,買書的,運書的,讀書的,癡迷于書的。他在第一堂課上,就親身扮演了一個游走鄉間的,收購破書的人,當然,是沒有道具的,他也還穿著他那身筆挺的西裝,接著他又表演了包括打漿、晾曬等環節在內的書的“誕生”過程。歷史幾乎就活了。歷史不再只是那種被“環境論”,或者“觀念論”說來說去的歷史了,歷史就成了它自己了。

其實,另一位哈佛的老師,對我影響也很深,他叫伊格內(Patrice Higonnet),他的課是關于18世紀法國史,包括大革命這段。一樣的生動,不管是他對巴黎街頭生活的描述,還是對羅伯斯庇爾的再現。他把羅伯斯庇爾每天的穿衣打扮,講得清清楚楚。
這些經歷,讓我覺得,觀點只是觀點,歷史還是歷史,了解再多的研究趨勢、研究轉向、研究動態,也不代表對歷史本身有了解。最后我想說一句,我們從事的是知識領域的工作,不要簡單地用學科的框架或是研究時段來框定自己的閱讀與思考,興趣是最好的導師。和那些史學大家有過接觸,無論是達恩頓,還是比亞爾,或是英國的多伊爾,給我印象最深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學識,更是他們的那種好奇心,那種童心未泯的性格。要知道,八十歲的勒費弗爾依舊像個六歲的小孩一樣,對歷史和過去充滿了好奇。
附:張弛2014年讀過的最佳歷史書
1,Arlette Jouanna, Le pouvoir absolu :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e?, 2013 ; Le Prince Absolu: apogée et déclin de l’imaginaire monarchique, 2014.
【簡評】Juanna兩部新作,回答了她導師Roland Mousnier的問題:為何17世紀的法國人想要一部憲法?她的答案比以往大多數人的回答更令人信服。
2,Henri Fréville, L’intendance de Bretagne, 1689-1790 :essai sur l’histoire d'une intendance en Pays d'Etats au XVIII siècle, 1953, 3卷:Armand Rebillon, Les Etats de Bretagne de 1661 à 1789, leur organisation, l’évolution de leurs pouvoirs, leur administration financière, 1932.
【簡評】18世紀的外省三級會議是否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已無實權?這兩部提供了有益的反思。
3,Matthieu Lecoutre : Ivresse et ivrognerie dans la France moderne, 2011.
【簡評】這或許是近期有關舊制度研究中視角最獨特的。
4,M. S. Dupont-Bouchat, Willem Frijhoff, Robert Muchembled, Prophètes et sorciers dans les Pays-Bas XVIe-XVIIIe siècle, 1978.
【簡評】除了《共和六書》外,博丹曾寫過《巫術的魔憑狂》。獵巫與絕對王權的確立之間確有聯系。
5,Pierre Mesnard. 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e?cle, 1969.
【簡評】斯金納推崇的經典之作,百科全書式的匯總。
6,Jeremy Adelman,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2013.
【簡評】2014年度美國經濟史協會斯彭格勒獎得主。
7,[美]埃德蒙?威爾遜:《到芬蘭車站: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劉森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簡評】本年度讀過的最好的中譯本,愛不釋手。
8,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聯經,2013年。
【簡評】在史學研究泛娛樂化、泛文化史化的大潮下,這類嚴肅之作少之又少。
9,劉節:《劉節日記》,大象出版社,2009年。
【簡評】不管什么時候,先生都在讀書。
10,趙翼:《陔馀叢考》,中華書局,2006年。
【簡評】“百年史學推甌北”
11,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東大,2011年第二版。
【簡評】陳寅恪先生曾復此書:作者知我。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