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戰俘營里的日本守衛:無論多么殘暴,都不是惡棍那么簡單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說這是場考驗。他十分著迷于一種念頭,就是他那一代的男子生得太晚,沒能參加大戰,也就沒能經歷強加于他們父輩的那種男性成人禮。1915年衣修伍德十歲,他的父親、職業軍人弗蘭克·衣修伍德死在法國戰場上。這對他產生了極深的影響。男性氣概的考驗,對他而言要比真槍實彈的拼殺更重要(因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性至關重要。他常說要冒險才能證明自己。他的同性戀取向披掛著反叛的外衣。倒不是說和柏林街頭的猛男亂搞可與面對索姆河的德軍機槍相提并論,但至少在衣修伍德心目中,這里面有種細微的關聯。
澳大利亞小說家理查德·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的書《通往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剛得了今年的布克獎。他出生于二戰結束后十六年,也許時間隔得太久,對所謂考驗已經不在意。但他的父親是戰俘,曾被迫修筑泰緬鐵路。很難找到比這更能考驗人的事了。
這條鐵路曾被稱為“死亡鐵路”,修建的目的是通過泰國把馬來半島的增援和物資送給占據緬甸的日本部隊。日本工程師根據崎嶇的山區地形推算,鐵路至少要五年才能完成。之前的英國人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但是有了六萬名盟軍戰俘可供差遣,還有許多亞洲勞工,日本軍方首腦決定,這項工作應在十八個月內完工。

因日本和韓國守衛的野蠻態度,加上熱帶疾病、饑餓、過度繁重的勞動(尤其是1943年瘋狂的“高速”勞動),逾一萬兩千名西方戰俘死亡,亞洲人死亡數可能在十萬以上。今天東京的靖國神社依然自豪地展示著“死亡鐵路”上開過的第一輛火車的機車頭,但實際上當時修筑的鐵軌極為粗制濫造,戰后泰國人不得不重修大部分軌道。
在“死亡鐵路”工作的經歷,恐怕很難想象。不過這正是弗蘭納根試圖做的:去想象。除此之外,他還試圖想象那些監督修路的日本軍官的心理。
結果就是,這本小說描述的恐怖,有時讓人無法承受。例如:一個名叫達基·加迪納的澳大利亞戰俘,被冤枉消極怠工,先被日軍守衛打得半死,然后被淹死在公共茅坑的屎溺中。弗蘭納根的小說也提及了男子氣概的考驗。從某種方面說,這是對澳大利亞人陽剛之氣的探討,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此書對男性氣概的觀點陰冷黯淡,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觀點,那也是反陽剛的。
很明顯,弗蘭納根欽佩那些在泰國雨林的爛泥地里受苦挨餓、被奴役,甚至死亡的人。但他的小說并不是人類戰勝逆境的老套故事。故事中彌漫的是一種失敗之感——尤其是在極端環境中無法找到意義,也無法得到寧靜生活的回報。我們在生命中尋找意義的唯一希望,似乎要依賴于文學和藝術。弗蘭納根的祖輩是強硬的愛爾蘭政治犯,他生于以前流放犯人的塔斯馬尼亞島,這里的人們可沒閑工夫去欣賞藝術。不過弗蘭納根本人文學修養很高,還是一位精妙的散文詩人。
小說的主人公名叫多瑞戈·埃文斯,是個醫生,他總是竭盡全力幫助那些忍受非人條件折磨的病人。據說這個人物有真實的來源,經歷和“疲倦的”愛德華·鄧洛普(Sir Edward “Weary” Dunlop,“疲倦的”是他的綽號,因與鄧洛普牌輪胎的“tyre”的諧音“tired”同義——譯注)爵士頗有些相似。鄧洛普是運動健將,生來就有領導氣質,他是緬甸鐵路上的傳奇英雄,以公共人物的身份為戰俘做了許多好事。要說有任何人通過了陽剛考驗,那就是“疲倦的”鄧洛普。
但偉大的英雄有時也是很煩惱的。弗蘭納根塑造的多瑞戈·埃文斯是個復雜而痛苦的人物。他在戰爭中的行為相當英勇,也因英雄氣概而為人稱頌。但俗世的浮名對他來說意義不大,社會授予他的種種榮譽只會加重他內心的空虛。他和一位美麗心善的女子艾拉成婚,但只是盡義務而已。他有許多情人(大部分是同事的老婆),但沒有女人能取代一段戰前的回憶,他和叔叔基斯的妻子艾米有過一段不倫之戀,這也是他唯一經歷過的真正激情。
他主要的愛好是讀書。“睡覺時沒有女人沒關系,沒有書可不行。”戰爭結束很久以后,他在一次毫無新意的車禍中受了重傷,躺在醫院病床上還輕輕吟著丁尼生的詩《尤利西斯》:“【我決心駛向】太陽沉沒的彼方,超越 / 西方星斗的浴場,至死方止。”護士以為他在囈語,事實上,這首詩很應景。多瑞戈的奧德賽之旅,充滿了無數塞壬的誘惑,終于到了盡頭。他的旅途的意義,不是衣錦還鄉,或柴米油鹽的家庭生活,而是旅途中的考驗。這些只能在詞語、文學的語言、詩歌中找到意義或解答。
對那些參加過戰斗的人來說,之后的人生時常令人感覺寡淡無味。有什么能比在暴力死亡面前與戰友共同奮戰抗敵更為劇烈的感受呢?對一個經歷過戰斗的人來說,在郊區超市里和人擠來擠去買菜太讓人失望了。那些死亡營里的幸存者雖沒有理由去懷念可怖的日子,但有時他們也會覺得很難從接下來的人生里找到什么意義。剛剛經歷過戰爭的國家,上上下下會有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著迷狀態,編織出大量神話,因為之前從未有如此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以后也很難再有。
弗蘭納根的小說里,有個戰俘名叫吉米·比奇洛,他的戰后生活要比大部分人成功。對他來說,戰爭“只不過是真正世界和真正人生的一次間斷”。但即便是他,最終也無法徹底逃離回憶。他結了婚,生了孩子,有了孫子,但逐漸地,他想起戰爭的時候越來越多,而生命中其余九十年的光陰慢慢分崩離析。最后他很少會想到或說起別的事情,因為他越來越覺得,其他的都像沒有發生過。
埃文斯(以及我們可以假設弗蘭納根本人)對戰爭沒有任何浪漫幻想。他不相信受苦是為了讓受苦的人學到美德。事實上,埃文斯“痛恨美德,痛恨美德受人敬仰,痛恨人們假裝表揚他的美德或是假裝自己有德”。他相信,美德只是“虛榮心盛裝打扮,等待別人鼓掌”。
這里有一種招牌的男性姿態:一個男人就是要做他應該做的,諸如此類。但埃文斯并不認為他的戰時行動是美德。在弗蘭納根的小說里,日本人并不都是魔鬼,包括埃文斯在內的澳大利亞人也遠非圣人。他們會欺騙朋友,偷走別人的最后一份口糧;有可憐人累得栽倒在地,臉浸在血染的泥土里,他們就當沒看見。但埃文斯依然關心他的病人,哪怕他無力挽救大部分。他們都病懨懨的,長期挨餓,被迫在叢林中日夜工作修筑鐵路,日本軍官要趕上瘋子制定的工期,根本無所謂多少戰俘死在鐵路上。埃文斯知道苦力們必須互相支撐,因為“一旦活人任由別人死去,他們自己的生命也停止了意義。如果他們想活下去,就必須結為一體共患難,現在如此,永遠如此”。
也許,正是這種團結之感,這種生命隨時會被(疾病、饑餓或是日本人無情的鞭打)奪走的強烈感覺,在回到“正常的”生活后很難再現。弗蘭納根再次為主人公在戰后世界的疏離增加了一種文學元素。埃文斯感到了某種東西在枯萎,原本危險重重的生活被乏味的新世界取代了,在這個和平世界的眼中,準備飯菜要比讀詩更叫人感動。
詩歌和冒險之間的共生關系并不常見。但在弗蘭納根這本用文學方式處理陽剛考驗的小說中,它是如此自然。
令這部小說尤為有趣的是,無論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徑多么殘暴,他們并沒有被簡單地描繪成徹頭徹尾的惡棍來襯托澳大利亞人的文明體面。日本人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宗教信仰、愛國主義、武士道精神與別人不同,這是肯定的。要說弗蘭納根對日本軍人的描寫有什么毛病,就是有些太整齊,陷入了無條件崇拜天皇和變態的武士倫理的程式。無疑日本軍人被灌輸了投降便是極大恥辱的觀念,所以對待投降的戰俘可以任意蔑視糟踐。西方人尤其是個子高的人,有時會被故意當眾羞辱,讓他們知道在亞洲誰是老大。然而更常見的事實是,馬來人、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的境遇更差。
但可怕的日本憲兵隊的特長是折磨犯人至死,這可不是武士道傳統。事實上,在之前的戰爭比如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軍人對俘虜還相當尊重。但1940年代的日本皇軍要比1905年殘暴許多,也更不講紀律。弗蘭納根的神來之筆是寫出了日本人的思維過程,比如殘忍的勞動營指揮中村少校,盡管他被灌輸了各種可怕的觀念,但仍然能夠與埃文斯那樣的人形成怪異的平行。
中村接到上級命令迫使他完成不可能之任務,以至于他指揮的戰俘營成了一個活人屠宰場,他在絕望時刻,也會在詩歌中尋找意義。他的上級古田上校是用武士刀砍掉犯人首級的高手。中村需要藥物興奮劑的幫助才能繼續執行任務,而古田實際上很享受屠殺他人。一天他們兩人談到戰俘營、鐵路和戰爭,中村說:“這不光關乎戰爭,也關乎讓歐洲人知道他們不是高等人種。”古田加了句:“也讓我們知道我們才是。”在片刻沉默思索之后,古田吟了一首詩:
即便身在京都,
聽到布谷鳥鳴,
依然會向往京都。
芭蕉的俳句,中村說道。
松尾芭蕉最有名的一首俳句寫于十七世紀末,講的是旅行,就叫《通往北方的小路》。中村認為,緬甸鐵路的目的是讓日本軍隊一直達到印度,這樣可以把印度從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在中村眼里,“日本精神的當下體現就是這條鐵路,鐵路也就是日本精神,我們這條通向北方的小路,幫助芭蕉把他的美和智慧帶到更廣闊的世界。”
我不太確定這能有多大說服力。俘虜營指揮官的詩歌隱喻也許更多地透露出弗蘭納根的審美趣味,而非日本軍官的想法。但這是挺好的比喻。日本是優越的,它發動的戰爭是高貴的,是戰爭就要有可怕的犧牲,包括把外國戰俘推向死亡,所有這些都在一首十七世紀俳句的凝練語言中表達了出來。
重申一下,中村并不是邪惡之徒。戰爭結束后,他很和氣,甚至謙卑。而正因為他不是暴徒,他得為那些殘暴的命令找些看似高尚的虛假借口。他試圖把自己想成一個高潔之人,因為他為更高的事業克服了對折磨勞工的反感。但接著他發現戰爭結束后他和他的受害者一樣難以繼續生活。戰后的日本已經沒有天皇崇拜和尚武精神的空間,正是這些把中村這個單純的工程師變成了殺人犯。
戰后,古田為中村在日本血庫找了份工作。古田所屬的這個機構,現實中就是在東北進行可怕細菌實驗的一個前戰犯創立的。這樣的巧合當然有可能,但也許有點太造作了。還有就是古田在死后被做成一種干尸保存起來,這樣他的女兒能兌現他的福利支票。他的床邊也有一本芭蕉的《通向北方的小路》。一葉干草書簽標記著這一句:“日月是行者的永恒,流年亦然。”
同樣,這并非無法想象的場景。但弗蘭納根的敘述有點用力過度的傾向,總要表達一種哲學觀點,而且時常用詩性的語言來表述。
弗蘭納根的文學技巧反映了他對詩歌的關懷。他的小說中詩意形象不斷再現,好像主導動機。其一是塵埃在光線中飛舞,正如生命一般偶然無常。埃文斯的無愛婚姻讓他感覺“如同一百萬個飛舞的無意義的微塵般叫人喪氣”。他妻子寫的一封家書抵達戰俘營,通常這是愛意的珍貴信號,叫人珍惜生命。但她的文字“像塵埃般四散升起,于是越來越多的塵埃互相碰撞……”
戰后許多年,他突然看見戰前的戀人艾米在悉尼海港大橋上走過。他任由她擦肩而過。他身邊來來往往的人們像“光線里狂飛的粒子,失落已久,正如他知道如今一切都失去了……”
詩意的隱喻在日本守衛身上也適用。中村去北海道拜訪一個戰友,看到機場的大路邊矗著許多冰雕,有哥斯拉、鐵甲人和其他怪獸。他聽朋友說話時,回憶起了那些戰爭暴行;它們好像冰雕怪獸,及時凍結了,但隨時會突然撲向他。
弗蘭納根向讀者展示的寒冬視角,也很接近傳統的日本情感,一種源于佛教的生命虛幻無常之感。相信一切都只是幻覺并非沒有安慰,至少它能幫助我們度過無法承受之難關。弗蘭納根對泰國的戰俘營的描述完美地體現了這一點。
埃文斯在戰俘營里有一個小手術室,他竭盡所能弄些最基本的工具,有偷來的瓶子、管子、刀具,去修補那些八成要死的人的殘破軀體。他知道這是“神奇想象力的勝利”,他對一位護工解釋,“我們只有在幻覺中保持信念,生命才有可能……”
有時,所見所感太痛苦以至于難以忍受時,幻覺能夠提供出口。當日本人逼迫戰俘們看著達基·加迪納被竹枝打得皮開肉綻時,叢林中飄來的水果香味讓他們中的一些人想起了雪梨酒和圣誕午餐:
雖然他們會帶著達基被打的回憶赴死,不管是六天后還是七年后,但當時他們似乎束手無策,在他們的意識里,這與石頭砸下或是暴風雨來臨沒有區別。最簡單的辦法,是找點兒其他事情去想想。
到最后,一切都會過去,甚至回憶。曾經有無數人慘死的緬甸鐵路,如今成了旅游景點,泰國的導游會推薦游客去看看。戰俘被鞭打至死的地方,現在是紀念品小攤。中村的內心被沖突折磨著,他到底是承擔了帝國責任的高尚之人,還是那些揮之不去的冰雕怪獸呢?于是“帶著當年在暹羅叢林里的鋼鐵意志……他決定必須從此以后把自己想成一個好人”。
這也是一種遺忘術,一種有意的幻覺,可能許多施暴者都會選擇這種方式,而且不光是在日本。不過有些日本人選擇了不去遺忘的畏途。一個叫佐藤的人告訴中村一個可怕的故事,基于真實發生的事件,說日本醫生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進行活體解剖。中村不想聽到這類故事,于是總躲著佐藤。
多瑞戈·埃文斯沒有忘記過去。但他又對當下的空虛感到痛苦:“他無法承認,其實是死亡給了他的生命意義。”只有詩歌能提供某種解脫。一個日本婦女代表團到塔斯馬尼亞去拜訪他,為日本人在戰爭中的暴行向他道歉。她們帶了一本關于死亡的日本詩歌集送給埃文斯,作為痛悔的信物,埃文斯欣然接受,因為他相信“書有種光環在保護他……”。
其中一首俳句尤其打動了他,這是十八世紀禪僧Shisui在臨終前寫下的。整首詩只有一個圓,“一個封閉的空洞,一種無盡的神秘,無限的呼吸,巨大的輪,永恒回歸:圓——乃直線的反題”。
直到自己臨終,埃文斯才明白了這首無字俳句的另一層涵義——跟隨幻覺、不顧一切向前行的動力,這樣才能繼續生命的循環。他的臨終遺言是:“先生們,前進,向窗臺沖鋒!”(小說人物因臥病在床,體力所及之處只達到窗臺而已——譯注)
然而小說并沒有以這些臨終遺言結尾。尾聲是以閃回的形式完成的。加迪納被溺死在糞坑后,埃文斯收到了一封妻子的家書,告訴他一個錯誤的噩耗——艾米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塵埃飛舞的意象又一次出現了。埃文斯無助地盯著煤油燈的火光:
他望著光,望著煤灰。好像有兩個世界似的。這個世界是隱蔽的,但是真實的,塵埃飛舞旋轉,發著微光,任意碰撞,于是新的世界誕生了。
他拿起一本書,講的是真愛故事。但最后幾頁沒了,大概是被哪個犯人撕下來當了手紙。他放下書,走到暗處的竹林小解。回營房的路上,他發現黑色的淤泥里半掩著一朵絳紅色的花。他用油燈照著“這小小的奇跡”,在傾盆大雨中彎下腰細細觀賞,然后直起身,“繼續走他的路”。
淤泥中的紅花這一形象,很醒目,但也有些乏味扭捏。但它與這部非凡的小說的整體語調是協調一致的,那就是對戰爭絕無多愁善感(只對詩歌除外),更別說什么陽剛考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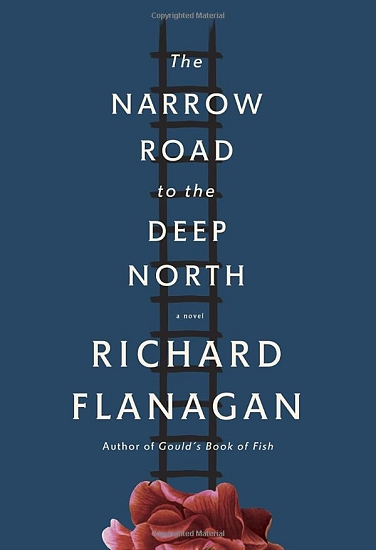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