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梁文道專欄:危險的思想
很多年前,某大學曾想召開一場張愛玲文學國際研討會。可是很不巧,那年正逢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所以計劃只得告吹。為什么紀念抗戰的同時就不能研究張愛玲呢?那當然是為了她“失足”的歷史,什么人不好愛,竟然愛上了漢奸胡蘭成。此中邏輯,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是要被大多數人嘲笑的,仿佛“漢奸”是種神奇的傳染病,不只會在男女黏膩間交流,而且還能潛入文字,把后來讀者一一熏染成了小漢奸。于是胡蘭成的文章固然不可讀,就連愛過他的張愛玲也一樣不準研討。
我想,現在大部分自認是講點道理的人,都會覺得文章和政治必須分開來看。別說張愛玲沒寫過一篇附逆文字,就算她有,也不能影響讀者對她的癡迷。這種道理,大概已成常識;不同領域我們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作品與人品,本來就不能輕易混淆;不以人廢言,豈非古有明訓?
問題是會不會真有這種情況:一個人既是我們政治上的公敵,同時又是個大文豪、大哲人,并且言行如一,政治上的邪惡完全表現在他的文字和思想里頭,乃至就連讀他的東西都可能是錯的呢?兩個月前,海德格爾遺稿的最后一部,未出版先轟動的《黑色筆記本》,終于成書上市,掀起風暴。那風暴的核心大抵就在于思想的危險。

1945年,戰后不久,彼時聲望甚隆的卡爾·雅斯貝斯受邀考察他這位昔日老友,看看這個墮落了的大哲學家到底適不適合再當老師。結果,他向盟軍占領當局的負責機構報告:“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青年人的教育問題事關重大,責任非淺。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完全的教學自由,現在還不能馬上實施。在我看來,海德格爾的思維形態是拘謹、專制、封閉,如讓這種思想在青年教育中發生影響,后果不堪設想。在我看來,思想的形態比政治判斷的內容重要。政治上的判斷的進攻性很容易轉變方向。只要這個人沒有在現實行動中證明他已完全悔過自新的話,就不可以向幾乎毫無抵抗能力的學生推薦此人為老師。首先要讓青年人學會獨立思考。”盡管四年之后,雅斯貝斯就又寫了一封信給弗萊堡大學的校長,要求把海德格爾這位“在德國沒有人能超越他”的哲學家帶回學校;但他這段相當有名的證詞,已然種下后來的根莖,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字叢林戰。

然后我們就能理解《黑色筆記本》的分量了;一部一千多頁的哲學家遺稿,居然上了歐陸好幾份大報的社論(忍不住要學陶杰的口吻;對比內地、香港的報刊為了街頭便溺交火,人家和我們似乎真有文明的差距)。你看,這里頭竟然有這種話:“世界猶太主義在各處的影響深不可測,當我們在犧牲我們種族中最優秀者的血液時,他們卻根本用不著介入軍事行動。”猶太人之反對納粹的種族理論,“那是因為他們自己憑著計算的天分,就可以按照種族原則活得長長久久”。這兩句話還不算什么,對于稍稍讀過海德格爾的人而言,最震撼的莫過于他還把他那著名的“無世界性”概念與猶太人聯系了起來,指出現代世界的拔根與空洞,多少得算在四海為家,心無所屬的猶太人頭上。于是,時常批評猶太人“離地”、“不夠本土”的納粹意識形態,便與海德格爾哲學對現代人之病的診斷,發生了奇詭的關系。難怪海德格爾家族囑托的遺稿主管,是書主編彼德·圖朗尼(Peter Trawny)都說:“海德格爾不只摭拾了這些反閃觀念,而且還哲學地推演它們。他無法使他的思想免疫于如此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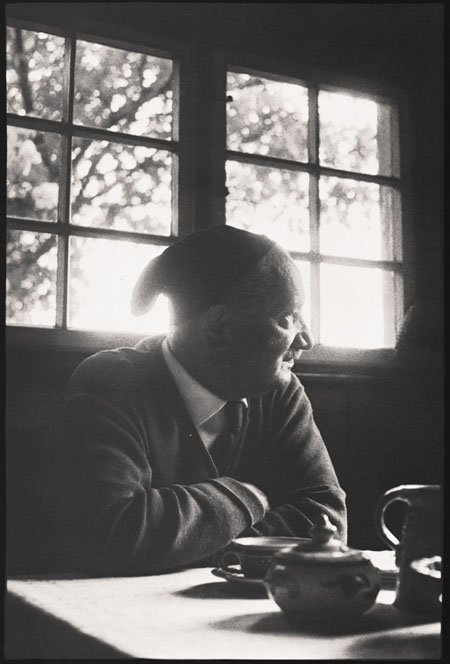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