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寫字樓里的嘻哈歌手
原創 尹磊 首席人物觀 收錄于話題#《Z時代商業故事》1個

作者:尹磊
編輯:江岳
2017年以后,所有Rapper都知道,如果上了那個節目,命運就有可能改變。
但說唱的普及,正在把選秀一夜成名的概率不斷拉低。對年輕的Rapper來說,選擇一份固定的工作,是一個相對聰明的選擇。在兩條人生軌道并進的未來規劃里,職場中的嘻哈歌手,同樣向往大廠、期待高薪,并和996的壓力嘗試和解。
在求職簡歷里,他們會加上這樣一行描述:“我是一個說唱歌手”。
通常,這是一個加分項。他們在公司里正襟危坐、察言觀色,然后在周末的舞臺上放飛自我。
在都市的晝夜之間,寫字樓里的說唱歌手,分飾著兩種角色。
01
導演,你到底喜歡什么樣的Rapper
在一場《中國新說唱》的海選之后,所有來參賽的Rapper在場外等待活動結束,幾個導師相繼走出來,坐上愛奇藝為他們準備的“保姆車”。最后出來的是吳亦凡,他徑直走向自己的法拉利,一腳油門,馬達轟鳴聲呼嘯遠去。
有人脫口而出:“一個真正的Rapstar”,現場鴉雀無聲,無人反駁。凱桑站在人群里,欲望在一秒鐘內迅速變得具體。
嘻哈文化的根源中,有一種迷人的物質化光澤,它具有誘惑力。“不想紅”對多數年輕的Rapper來說,是一個謊言;但在說唱事業上All in,則更加荒唐。更多的Rapper,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尋找機會。
凱桑已經是第三次參加《中國新說唱》的選拔,他來自PhoenixGang鳳凰社,有穩定的演出渠道,95年的說唱歌手、銀川的YoungOG。圈子里流傳著一條不成文的規則,2017年《中國有嘻哈》播出那年,是說唱玩家之間的一道分野。早于2017年的Rapper,根紅苗正,更配得上YoungOG的稱號。

凱桑的制作人詠者,在2019年的節目上被網暴上了熱搜,他與福克斯的合作分歧,在愛奇藝的剪輯中被賦予了玄妙的戲劇張力。
凱桑為兄弟解釋說:“他被節目組消費了,他本人不是那個樣子。”
選秀節目是一把雙刃劍,有時候,你可能會成為博眼球的犧牲品,對于視頻平臺來說,“賦予選手人設”是產品包裝的一種選擇。
平臺與歌手維持著一個話語權失衡的關系。
凱桑依然每年報名《中國新說唱》。2020年的導演見面會在西安,他當時還在銀川的橋梁設計院工作,為了參加導演見面會,他提前請了一周的假,自費買了往返的機票。
行程臨近,設計院突然接到外出勘測的工作,雷打不動的七天到崗,凱桑要迅速做出選擇。
和領導對話的開場白冰冷嚴肅,“你這一去,別人就得把你那份活兒干了,你要知道公司給你錢,你就得給別人干活。”

去西安這件事,對凱桑來說很重要,但對公司,沒有任何意義。“就是他的話讓你沒有辦法反駁,你懂嗎?”他低下頭,點開App,準備取消西安的行程。
領導的態度突然有了松動。新的建議是,找別人協調一下,倒個班。
很多時候,說唱歌手在臺上有多能Diss,在公司的領導面前,就有多Peace,一個打工人的桀驁不馴,是有代價的。
如約飛到西安,和前兩年報名一樣的流程——導演見面會,鉆到一個錄音棚里、唱自己的作品、講自己的故事。
導演在現場并不會給出一個明確的反饋。工程師Rapper是凱桑身上的一個亮點,有反差效果,是節目組喜歡的一類。
但漫長的等待后,當節目的預告片都已經釋出,凱桑知道他的第三次海選,又以失敗告終。
“我自己是被選擇的,Get不到他們的選擇標準,我不覺得選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強。”在他所在的銀川說唱圈里,去參加節目的有十個人左右,一半去了體育場,兩個拿到了鏈子。沒有節目效果的人,在拿鏈子的60秒,也會被剪輯壓縮到慘不忍睹。
創作能力的提升,有時候是在筆頭上磨出來的,凱桑需要解決加班的問題。2020年,他離開橋梁設計院,投奔了一家互聯網公司,成為了一名數據分析師。
并沒有出現傳聞中的互聯網風氣,能支配的時間反倒變充裕了。
2020年凱桑進入了一個創作爆發期,最高產的時候,5天寫出4個Demo。新的專輯也開始醞釀,還要配兩支MV,這是他目前為止最隆重的一次作品集發布。
其中一支MV已經完成拍攝,取景在銀川的巖畫公園,沒有布景,服裝都是自己的。
凱桑在京東上花80塊錢買了兩個探路蜂,保安巡邏用的那種超強亮度手電筒;還買了一卷透光的塑料彩紙,擋在手電上,能拍出不同顏色的效果。這些是唯一的物料成本。
拍攝當天零下二十多度,是銀川最冷的時候。一件短袖外面套一件毛衣,連拍兩個晚上,從傍晚拍到凌晨,凱桑他們手舞足蹈,手電筒的強光穿過塑料彩紙,打在他們凍僵的臉上。幫忙拍攝、剪輯的也是同事,給了2000塊的辛苦費。
“做音樂這事,完全是用愛發電,不管是拍MV還是錄歌、混音、修音,都要花錢,都是工作賺來的。”
在國外的平臺上購買一個伴奏的版權,需要500塊,而且限制在一萬次轉發、十萬次音頻收聽以內,超過的另付;錄音的棚時費300,混音500,這還是詠者給他的友情價;做單曲封面還要至少300。
一首歌,最起碼的成本是1600元。最后把作品發到播放平臺上,換來的可能只是十幾個評論。
不久前,凱桑剛剛和詠者合作了一首歌,新歌會在詠者的網易云上發布。兩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2019年詠者遭到網暴,凱桑叫上所有朋友,有女朋友的叫上女朋友,讓他們給詠者的微博控評,但勢單力薄,后來回憶,凱桑說,“詠者和福克斯我都很Respect,但愛奇藝的魔鬼剪輯把詠者給消費了。”
在詠者的評論區里,有個人義憤填膺地評論道:“你們都在說Real,但一個真正Real的人出來的時候,你們卻在批評他不Real。”詠者點贊了這條評論。
02
我就服那些80后
“我后來去詠者那錄音的時候,我問他還記不記得他轉發我的那條評論,他說他忘了。”豆特本來以為兩人有惺惺相惜之處,但詠者的回答,讓人失落。
詠者被網暴的時候,豆特還是另一個社交圈里的人,后來他第一次見詠者,是凱桑拉著他去錄音。那時候豆特的父母逼他考事業編,在銀川,進入體制是更舒服的活法,但他沒有這個意愿,借口去圖書館學習,背著一書包的“事業單位招聘復習教材”,和凱桑跑到了詠者那。

三室兩廳的房子,Muaboss和B·P·E都在里面睡覺,兩個人都是有Hitsong(金曲)作品的人,有讓人羨慕的粉絲量。傳說中的前輩,不枉此行。
意料之中的臟亂,煙灰缸里塞滿了煙頭。他本以為這些人都是一副兇神惡煞,比如渾身紋身,滿嘴臟話,但等前輩們睡醒,聽到他們聊的都是關于“房子在哪買”“怎么找工作”,他覺得這不像一群Rapper會聊的事。
Muaboss跑過來跟凱桑開玩笑,說房間里還睡著派克特(2018新說唱止步六強),豆特腦子還在放空,沒反應過來;凱桑信以為真,已經準備去認識一下新朋友。豆特后來說:“真是把我們唬得一愣一愣的。”那天豆特縮在角落里,他本來計劃給大家留下一個Hip-hop的印象,但眼前的三個陌生男人,讓他最終選擇了沉默。
他沒有選擇銀川的事業編,去了北京,遠離家人的安排。先找份工作,在一個共青團合作單位做剪輯,要求不高,保證能活下來。
“我本來以為你努力就能適應工作,但在這家公司,我領教了什么叫爾虞我詐。”
一場活動,高強度的加班,豆特三天只睡了五個小時。最后一天結束,和公司里一個前輩吃飯,喝了點酒,價值觀迅速拔高,討論的議題變成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
深刻的話題,釀成了出乎意料的后果。
“我就記得他說的一句話,他跟我說好人要有大格局,壞人會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出賣別人……”前輩的話讓豆特肅然起敬,臨睡前不忘回味一番。
結果第二天,老前輩和豆特的頂頭上司吵了起來,豆特坐在兩人旁邊,突然老前輩扭過頭,盯著他:“豆特在會場上不干活,買了一堆飲料,就為了追公司里的女孩。”
“我人都傻了。”豆特聽完腦子嗡的一響,他迅速在腦子里過了一遍在公司里的所有記憶。一無所獲。
“昨天我們一起聊得那么投緣,他今天就拿我當槍使。我就佩服這些80后,你說他跟我一樣都睡了那幾個小時,我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他還有精力玩心機。”
晚上,一個雪上加霜的消息——好兄弟和自己喜歡的女孩在一起了,而且是早就在一起了。
“我的世界全黑了,你懂我意思嗎?”采訪中,豆特用手比劃著,試圖表達那種黑暗的面積。
請了假,他買了次日回銀川的機票。回去路上,前面出事故,堵車誤了航班,改簽到凌晨兩點,豆特被霉運包圍。
一下飛機,豆特抱住母親,腦子昏昏沉沉,心里委屈。他第一次在家里抽煙,母親說:“心情好了就不要抽了。”
在家躺了三天,像治愈一場大病。

晚上9點下班,在北京的7號地鐵線上,豆特開始了新歌創作,在家里就醞釀的一個作品。地鐵前半程,他安靜、專注,維持公共交通上的基本禮儀;后半程,整個車廂的人都走空了,他開始手舞足蹈,車廂里傳出“動次打次”的節奏,“7號線坐到后面就沒人了,我可以蹦著寫。”
寫了三天,他把歌發在了網易云上。整個歌曲的制作過程,被做成Vlog,放在了B站。
然而,創作者的傷感是洶涌的,但網民的回應是“骨感”的。
周末下午,在他的合租房里,一個固定的錄歌時段。
他輕車熟路地把筆記本電腦、聲卡、電容麥挪到兩平米的陽臺里。電腦放在地上,聲卡擱在架子上,然后用麥克風夾緊墻壁的水管,兩根連接線卡在陽臺和臥室之間的門縫處,中間露出一道細縫。他養的兩只貓有時候會去扒那條縫,看里面的人充滿好奇。
他一會蹲下來戳電腦,一會站起來湊到麥克風旁邊唱幾句,他滿頭大汗,有時候氣喘吁吁,在里面已經待了五、六個小時沒出來。
貓咪一叫,他就得重錄一遍。
03
每天都給領導泡咖啡
和豆特相比,兔子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盡管在采訪的最后,兩瓶啤酒下肚,豆特和兔子就情投意合地做了決定——合作成立一個新組合,未來的演出計劃越說越有眉目,最后聊到了凌晨十二點,各自錯過了末班車,才不舍地道別。
這就是兔子所擅長的,他幾乎可以和各色人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在采訪中,只要你不打斷他,他可以一個人說個不停。
從大學畢業,到進入德企,兔子從一個組織各大高校說唱演出的“風云人物”,變成了每天早上給全組人泡咖啡的職場新人。
在北科大,他牽頭創辦了說唱高校聯盟,成員幾乎囊括了五道口的所有大學,舉辦的三次專場,每一張海報的聯系人處,留的都是他的微信。
在兔子組織高校聯盟的那一年,五道口的高校但凡玩說唱的,多多少少都會知道他這么一號人。
39塊錢的門票,辦完活動之后,有些學校的團體會找過來抱怨,一次活動下來,自己的學校200塊都分不到。
兔子說在活動結束后,他自己幾乎就沒有收入,“我也不需要有盈利,北京小孩哪有缺錢的,我從上大學到現在,沒有體會過缺錢的感受。”他又琢磨了一會,說:“也不是我凡爾賽。我跟他們去談這些活動的時候,我也沒有談過因為我辛苦,所以要分到多少錢,從來沒談過。”
2020年12月27日,最后一次專場演出的時候,因為一個流程上的疏漏,導致沒有把演出順序安排好,歌手直接在兔子面前摔了麥克風,然后瀟灑地走了。
“面對兩三個人的時候,你還能應付一下,面對三四十個人同時問你問題,你怎么辦?”活動前的規劃沒有精確到分鐘,就會出亂子。
通過高校聯盟,兔子認識了更多人,他在這個圈子里打響了名字,一些酒吧老板也知道了他能做什么。他也學會了怎么在一個活動上獨挑大梁。
這些就是他“吃力不討好”換來的回報。
今年三月,《中國新說唱》在北京的高校海選,全中國的Rapper很多都在,活動結束后,兔子又發揮了自己的特長,他主動攢局,把在場的所有Rapper都拉到了五道口的Young Club。
和Rapper以及酒吧老板兩頭通過氣兒,資源互換,全場免單。
那天晚上,他和到場的每一個說唱歌手喝酒,一杯一杯地敬過去,最后斷了片。據前臺后來描述,喝得迷迷糊糊的,還在到處找垃圾桶,最后問前臺要了個垃圾袋,又把垃圾袋套到垃圾桶里,最后才放心吐在了里面。
大家一致認為兔子有很強的環保意識。

在德企工作的兩個月里,兔子還沒有結束試用期,他的資源目前還沒有發揮的空間,辦公室里七個組員,無論從資歷還是年齡上,都是他的前輩,也都是他的領導,他放低姿態,希望工作能有個Peace的環境。
對他自己身份最好的解釋,是在三亞學潛水時,教練跟他說過的一句話:“很多人都想成為一個厲害的人,但是,我覺得一個人最重要的是成為有趣的人。”
面試這家德國機械類公司時,HR對他簡歷中最感興趣的是他的說唱歌手身份,“我在大學就開始玩說唱,這個愛好能讓我在人群中凸顯出來,說唱這個標簽能增加一點個人魅力。”
上班第一天,領導就教了他一個新本事,公司有一套做咖啡的器具,領導讓他看自己做一遍。后來,這個活兒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兔子的。花上二十分鐘,磨豆子、煮咖啡,每個領導的口味不一樣,有多加水的,有加奶的,有加糖的,研發部的七個人,習慣不一,兔子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強調了好幾次,說自己不是一個多聰明的人,但在做咖啡這件事上,他的反應力和記憶力發揮超群。
“我也不是特意湊上去做,就是我來了,就順便做了。其實他們人都很好,買了東西都會一起吃。”兔子也從來不在公司里戴耳機,他覺得領導看到,觀感上不好。
和兔子聊得越久,就越覺得他與其他的說唱歌手不同,他有更強的社會適應性,尤其在職場上。
去德國,混進當地的說唱圈,這是兔子理想的未來生活。出國早有計劃,只是疫情拖延了時間,“我是向往德國的,甚至包括那邊一直被詬病的美食,我也很喜歡,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練德語,就是想要去德國,去德國就是為了進企業。”
兔子開始苦練Freestyle。
健身為了練肺活量,學兩年美聲給聲音打基礎,平時走在街上有意識地聽伴奏,學小語種練習咬字……兔子為說唱做了大量的準備,后來他的風格明確為快嘴,技術流。
每一個八拍里,他的歌詞密度都要比別的歌手多得多。在他的網易云音樂上,播放量TOP1的是和北科大社團的說唱接力《北科2021 CYPHER》,排在第二的是《為中華之崛起》,白銀單曲里還有一首《朱紅畫卷》,后面兩首主旋律的歌,擱在說唱圈子里,得到的第一反應會對作者的動機產生懷疑,而最惡毒的揣測,莫過于,它有“迎合”的嫌疑。
3月的時候,兔子履行了先前飯桌上與豆特的承諾,他在中關村給他們即將成立的組合安排了一個辦公室,免費的,他們想了兩個很酷的新組合名稱,現在陷入了二選一的困擾。兩個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在2021年,開始計劃新的時間表,這可能是他們最后的機會,兔子隨時會去德國,豆特正急于沉淀,他讀完了《人間失格》,內心苦澀。
04
兄弟,牛
去了天津之后,唐克的說唱之路就被“冷凍”了,他找不到一起玩說唱的朋友,也找不到多少說唱演出,在當地占統治地位的相聲表演,他也從來沒去看過。
整個城市給他一種慵懶的氛圍,出生在新疆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唐克,從中國的最西邊,一個人跑到北京讀書,然后就業,從一家明星培訓機構離職后,去年把簡歷投到了天津,依然是教育行業。
在北京的時候,唐克的口頭禪是:“騷呀,兄弟”,和剛認識的人說這句話,他會解釋一番,他老家那邊這話是個褒義詞,代表“牛”。
現在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家長群里,他的這句口頭禪都是禁語。
每堂課,他負責給主講老師開場,開場白通常是:“我是你們的唐克老師,今天咱們新一周的課程就要開始了,大家有沒有準備好,咱們要進入我們的上課狀態,唐克老師今天要表揚一下我們作業做得特別好的小朋友,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的表揚榜。”
對于了解唐克說唱歌手身份的人來說,他在課堂上的語調像是一種陌生的人格。他教授的學生主要是9~10歲的孩子,其話術中不斷出現的“我們”,是一種親和的姿態,他在用語言傳遞一種“像蹲在你身邊的一個慈祥的老師”的體驗,在民營教育機構,教育不光是一種義務,更多是一種服務。

課堂上每一個家長都有唐克的微信,助教老師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給主講老師分擔課堂以外的工作量和壓力。剛上崗的時候,領導讓唐克看到家長咨詢要第一時間回復,反響速度會計入考核,現在時間久了,回復的監督稍有松動。但唐克的時間還是會被無窮無盡的咨詢撕碎。
“我的精力很難從工作上抽離出來,再加上我自己又懶,在這里不到一年,總是感覺提不起勁兒,像是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城市,我僅僅是在這里打工。”
大半年的時間里,沒有一次商演,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公司。
“在公司的演出真的演得很傻,他那個設備很垃圾,唱完一首就不想再多唱一句。”演出后,同事們會熱情地包圍過來,對著唐克說:“哇,你真牛。”
后來公司只要有才藝表演,大家就會想起唐克。

一個數學專業的老師跑過來找唐克,說他們那也有一個Rapper,公司突發奇想,說讓兩人搞個配合,給公司寫首歌,最好能拍個MV。
“畢竟人家都找到我了,我也不好拒絕。我一邊受公司壓榨,我還得寫歌贊美它。”唐克花了半小時就“交了卷”,他總共寫了八、九句歌詞,“當時我就想,我們是英語學科的,那我就突出一下我們學科的特點吧。”
他套了小青龍一首歌的伴奏,OldSchool的風格,更親民一些。
“后來那個MV就在我們公司大門口的樓梯間,上頭有一個大屏幕,在那上面無限循環,播了一天。但是我沒去看,各種教委和組長開會的時候都看到了,然后他們就在群里喊,夸我厲害。”他覺得同事和領導稱贊他是應該的,“我花自己的時間給公司寫歌 ,他們要是不稱贊我,我心里也過不去啊。”
唐克說自己是一個性格反叛的人,有話是不會憋著的,從小學開始,因為一個“良好”的環境,他自小就形成了這個性格,“小學的時候,我媽是學校的數學老師,我哥在學校也能罩著我,我在小學沒人敢惹我”。
“但初中就不行了,我初中在石河子上的,我在那邊沒靠山。”
直到高中畢業,唐克在新疆的石河子待了六年,他最早聽到的嘻哈音樂是從吉爾吉斯斯坦傳過來的外國說唱,但那里的語言和他的民族語言是相通的。
“那時候我聽了那個國家的好多嘻哈音樂,后來聽國內的說唱,第一個聽的是喀什的,那里距離我住的地方大概兩小時的路程,艾熱就是那的人。當時我就聽艾熱他們的歌,就發現喀什說唱太牛X了,然后我就瘋狂地循環聽。”
高二的時候,唐克和他的同學們決定自己也試試說唱,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一個聲卡,一個電容麥。
“我們學校是半封閉管理,只有周末才能出校門,那時候我們連網購都不會,就在校門口找了一個電腦店,讓他幫我們下單,幫我們收貨。”幾經輾轉,唐克他們在一個大冬天的夜里把設備帶進了宿舍。
這群高中的孩子創作的第一首歌叫For My Life,歌曲發布在了一個翻唱平臺,最后在克州意外地火了,他們不是當地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唐克他們的歌是第一個在那里火起來的,克州的一些孩子,有時候會哼他們的這首說唱。
“我們出完這首歌以后賊開心,感覺就是牛X壞了。”
唐克的說唱生涯就此展開,在大學聯合組建了自己的說唱社團,后來又在北京的DDC和School酒吧演出。直到2020年的五四青年節那天,他以一個助教老師的身份,加入一家在線教育機構。在求職簡歷上,唐克習慣在里頭加上一句話,“我是一個說唱歌手”。
通常,這是一個加分項。他在課堂上給小寶貝們耐心地授課,察言觀色,不冷落任何一個孩子,在任何一個晚上,他的微信都能跳出一個學生家長的咨詢,他知道他最好能第一時間反饋對方。
在北京的時候,晝夜交替,他是寫字樓里的說唱歌手,而現在,說唱歌手的身份,只有當他在公司的文藝匯演上,才能被大家想起來。
2016年唐克第一次見到黃旭,那時候還沒有《中國有嘻哈》,黃旭在圈子里已經非常有名,唐克特別激動,按他的話,就是瘋狂地上去套近乎。
他當時自我介紹說,“我真喜歡你,我也是新疆來的,我也是一個Rapper。”
黃旭說:“兄弟,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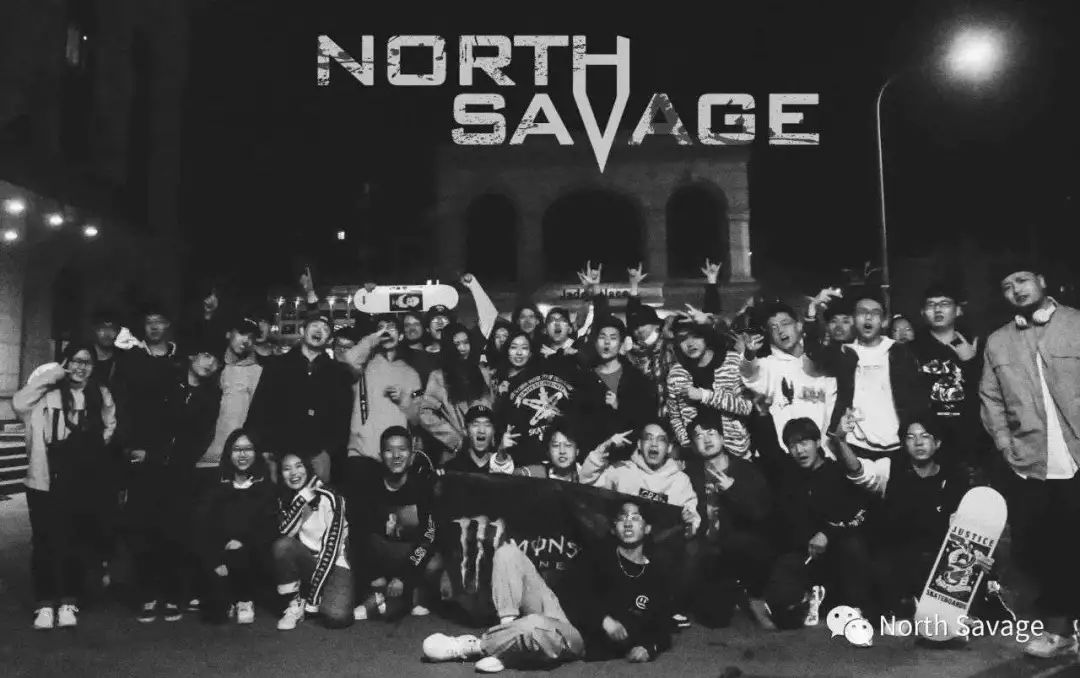
2017年的《中國有嘻哈》上,8強賽,唐克拿著黃旭給他的入場券,還有一條印著黃旭名字和頭像的大圍巾。
那場比賽上,唐克舉著這塊圍巾,抬著脖子,眼前是吳亦凡、狗哥、岳哥、潘瑋柏,以及日后走向中國嘻哈頂流的GAI。
圖片來源于網絡,侵刪
原標題:《寫字樓里的嘻哈歌手》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