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夏鼐傳稿》:折射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歷程的三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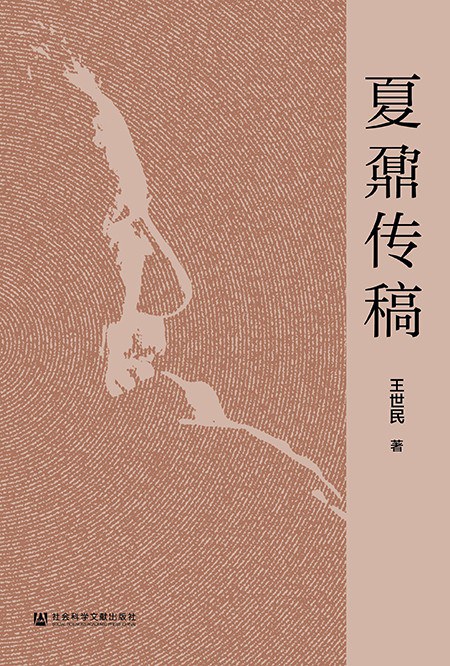
《夏鼐傳稿》,王世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6月版
2020年是新中國考古學的主要指導者、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者之一夏鼐先生(1910-1985)誕辰110周年、逝世35周年,首部以書的形式呈現的傳記《夏鼐傳稿》于歲末出版,這真是件令人欣慰之事。當我讀到《夏鼐傳稿》的作者王世民先生用了近20年的時間準備書稿的寫作,而他本人今年亦是85高齡的時候,敬佩之情油然而升。
兩度普利策獎獲得者、美國歷史學家和歷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對傳記寫作頗有見地。在《作為歷史三棱鏡的人物傳記》一文中,塔奇曼指出,人物傳記寫作的意義在于“燭照歷史”。一部傳記相當于一個“歷史三棱鏡”,能夠折射出傳主生活的時代。(見塔奇曼:《歷史的技藝》,張孝鐸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第68-78頁)作為一部學者傳記,《夏鼐傳稿》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夏鼐傳稿》的主要篇幅在于講述夏鼐對新中國考古事業的奠基和推動之功,而第三章“立志為中國田野考古獻身”和第四章“負笈英倫五年”講述的青年夏鼐從傾慕書齋生涯的學子轉變為以田野考古實踐為本的考古學家的故事,這幾乎是早期中國考古學歷史的縮影。夏鼐1934年從清華歷史系畢業,先于8月初投考清華研究院中國近代經濟史門,后于8月下旬投考清華公費留美考古門,兩次均獲優異成績。(《夏鼐傳稿》,36頁,下文引本書只注頁碼)在選擇留美后,夏鼐一方面對“爬到古塔頂上去弄古董”的未來感到迷茫,覺得自己離社會越來越遠;另一方面也按清華要求,積極做出國前的準備,包括到安陽殷墟實習。其間,他就“去哪里,跟誰學,學什么”這些問題,多次與梁思永、李濟和傅斯年進行面談或書信溝通,對這些討論《夏鼐傳稿》做了詳細記錄。總括起來,梁思永建議夏鼐先到倫敦大學讀人類學,打好基礎;然后去愛丁堡或劍橋大學,攻歐洲考古和中國考古。他總結說赴歐洲留學的三個目標是:博物館及田野工作的技術;歐洲考古學知識和人類學背景;考察歐洲保存的中國古物。(47-48頁)傅斯年對留學期間的叮囑是:學習的范圍“須稍狹”;選定合適的導師;“最好不研究中國問題”。(49頁)李濟面談時則直接叮囑夏鼐加強技術與訓練,“注意有史考古學”。(49頁)受命運捉弄,夏鼐陰差陽錯地入了倫敦大學學院藝術研究所,師從葉茲教授攻讀中國藝術史碩士學位,但他很快發現這位教授的中國學問和考古知識都不足以指導他,深感懊悔。于是他痛下決心,舍棄葉茲教授及很容易到手的學位,從零開始改學埃及學。在改換門庭的過程中又出現了兩個選項:或者赴愛丁堡跟隨柴爾德學習史前考古,或者在倫敦大學學習古典考古或埃及考古。但當時考慮到國內史前考古方向已有梁思永和李濟兩位前輩,還有正在英國讀書的吳金鼎也是史前方向,所缺正是歷史時期考古的人才,故夏鼐最終選擇了埃及考古學,希望以之作為未來中國考古學的“借鏡”。(59-60頁)中國考古事業開創之初舉步維艱,連人才都需要定向培養;對歷史時期考古的倚重也反映出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即承載著證史之目的。
另一個折射歷史的例子是第八章“特殊時期的經歷與貢獻”中對夏鼐在“文革”時期主要工作的記述。1968年發掘滿城漢墓后,在整理出土文物的時候,夏鼐因受運動沖擊“靠邊站”,只能進行“幕后指導”。《夏鼐傳稿》中這樣記述:負責修復文物的同志“巧遇”掃院子的夏鼐,故意放慢腳步,低聲詢問鐵劍去銹法和鑲嵌玉版復原法,夏鼐當即給出了前沿的專業指導。(193頁)這段文字描寫之生動,竟營造出了一種做地下工作的緊張感。1972年《考古》復刊后,夏鼐當年即以多個筆名發表了8篇文章,多與古代科技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古代文化相關。在講述這些文章的成文過程時,王先生以白描的手法寫道:“那時,常常是夏鼐一面趕寫,筆者和王仲殊一面協助潤色,貼標簽,加語錄,后來他在1977年編輯《考古學和科技史》論文集時,將那些語錄統統刪去。”(200頁)若無王先生這樣的親歷者的記錄,后人如何能夠知曉這些文物和文章背后的故事呢?這些故事將與夏鼐的行跡和作品一起載入歷史。
塔奇曼認為,傳記的來源是傳主的自傳、日記、書信,哪怕這些材料會有偏頗,它們都是傳主人生的自然流露。(《歷史的技藝》,76頁)《夏鼐傳稿》完全符合這個要求。《夏鼐傳稿》所依均為一手資料,包括十卷本《夏鼐日記》;2010年為紀念夏鼐誕辰一百周年編纂的《夏鼐先生紀念文集》,該書收錄了夏鼐逝世以來海內外報刊上發表的主要悼念、回憶和學術評論文章,還有專門為紀念文集撰寫的稿件,如夏鼐家人回憶等。在闡述夏鼐重要學術觀點和見解時,《夏鼐傳稿》還參考了三卷本《夏鼐文集》。幸運的是,王世民先生正是《夏鼐文集》的編輯者,《夏鼐日記》整理項目的主持者,以及《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等多處夏鼐小傳的作者,因此在援引上述一手資料的時候駕輕就熟。不惟如此。王先生1953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時,即聆聽過夏鼐親授的“考古學通論”和“田野考古方法”課程;1956年入考古所工作后長期擔任夏鼐的學術秘書,還曾與之比鄰而居,與夏鼐有多年的直接交往。這些經歷使得王先生記錄了不少未曾出現在上述材料中的夏鼐行跡與故事,其中不少記錄都可與《夏鼐日記》中的記載相佐證或補充。
比如,王先生統計了聽過夏鼐20世紀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課程的共有80余人,記下了那些后來在考古界卓有成就的同仁的名字。更珍貴的是,王先生記錄了他1953年1月12日下午與同學們一起在北大文史樓一層108號階梯教室聽夏鼐首講“考古學通論”和“田野考古方法”的實況。他回憶,由于院系調整,當時是1950級至1952級的學生一起聽課,夏鼐當時穿的是“灰布短大衣,頭戴皺巴的布質解放帽,講話聲音很低、溫州口音很重,板書筆畫輕淡又常隨手擦掉,因而多數同學聽不明白”。(137頁)因此學校后來安排了青年教師進行記錄,記錄稿經夏鼐本人審閱后,做成油印講義發給同學。查同日《夏鼐日記》,僅有一句話:“上午赴所。下午赴北大講課,與蘇秉琦君一起返城。”(《夏鼐日記》,卷五,第3頁)傳記作者的記錄增補了傳主自己的記錄,有效還原了北大授課的情景。
凡讀過《夏鼐日記》的人,不會不對夏鼐的閱讀量和閱讀速度留有深刻印象。自求學時代起,夏鼐會在日記中記錄每日閱讀的書目和頁數。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即便在改革開放之前,夏鼐對外文學術書籍和期刊的閱讀亦未中止。1949年,美國化學家利比(W. F. Libby)發明了C-14斷代法,夏先生1954年7月因閱讀其著作而知悉,次年即呼吁組建實驗室,幾經周折,于1959年將錯劃為“右派”的復旦物理系高材生仇士華、蔡蓮珍夫婦調到考古所,不僅挽救了他們困頓的人生,更成就了其事業的輝煌。(161頁)曾經聽聞考古所外文圖書和期刊藏量驚人,但卻不知原由。讀《夏鼐傳稿》第六章“重視圖書資料的基本建設”一節,終于找到了答案。考古所成立伊始,即接收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全部藏書,以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部分圖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科學院享受了國家的傾斜政策,夏鼐親自抓外文書采購,查閱外國新舊書店書目,留意相關期刊出版資訊。此外他還利用出國訪問和接待來訪外國考古學家的機會,把贈送他本人的書刊轉交考古所,并且督促與外國學術機構進行書刊交換。他本人更是幾乎每天到圖書閱覽室瀏覽新到的外文書刊,以追蹤世界考古的前沿。(148-149頁)此外,《夏鼐傳稿》還對考古所年終田野匯報會做過生動有趣的記錄。在一定意義上,這些材料都是對考古所所史的有益增補。
《夏鼐傳稿》還寫到了社科院其他學術大家。1970年5月21日夏鼐隨考古所同仁赴河南息縣五七干校;10月22日因夫人生病請假回京,之后因需要“為阿爾巴尼亞修復古書”做準備,便留京工作,沒有再返回干校。在1971年6月22日的日記中,夏鼐輕描淡寫地記錄了修復工作:“阿爾巴尼亞的兩位外賓在我所參加修古書工作,自從3月21日起今已3個月。現已將古書的性質搞清楚,是有名的Berat Codex [培拉特圣經],乃是《新約·福音書》的7世紀及11世紀兩種希臘文寫本。前者是大字本銀書,后者是小字本金書。修復工作,后者已完成,并開始復制。前者決定不久將動手。……”(《夏鼐日記》第7卷,277頁。日記中Codex誤為Codax)《夏鼐傳稿》則對羊皮紙《福音書》手抄本的識別過程做了詳細描述。首先是夏鼐識別出了希臘文,于是請來同住干面胡同學部大院的希臘戲劇文學大家羅念生。羅念生說西文古書“既不斷句又不斷字”,字母連成一片,但他讀出了扉頁頭像旁的“Lou-kas”,于是夏先生脫口而出:“那就是《路加福音》”。之后王先生同夏鼐一起找到宗教所留守處負責人黃心川,從不同文字的《圣經》中找出來加以比對,最終鎖定就是《路加福音》。(197頁)作為一個社科院人,這個故事讀來倍感親切。
塔奇曼認為,曾與傳主同時共在的傳記作者所享有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是一把雙刃劍,因為作者容易迷失在無窮盡的細節當中,還因塔奇曼認為“愛和敬不該是歷史學家應有的情緒”,因此她傾向于把這樣的著作稱為“回憶錄”而非“傳記”,(《歷史的技藝》,76頁)這一點或可當作一說。根據前述,由于王先生在《夏鼐傳稿》中增補了很多彌足珍貴的歷史細節和材料,因此他曾與夏鼐共事的經歷無疑就是一種寫作優勢。當然,出于對夏鼐的“愛和敬”,在個別問題的認識方面或有不自洽之處。例如,在評述夏鼐步入考古門的變化一節,王先生認為這一變化“來得突然,考察起來卻又并不偶然,因為他的考古情結由來已久。”(37頁)王先生把夏鼐童年時代收集古錢,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讀過《人類學》等書,并不止一次去燕園、圓明園和故宮等地參觀考察,隨清華畢業班去太原和大同進行為期一周的參觀考察活動,都算作正式學習考古學的預演,雖然王先生也承認,即使在考取留美生后,夏鼐仍對終身從事考古工作有所猶豫,這種情緒甚至一直延續到1935年在安陽實習的時候。當他獲知當年留美有經濟史一門,暗自懊悔,理由是自己是讀書人,對田野考古實踐所需的組織和辦事能力缺乏自信。他甚至還通過已在清華任教的好友吳晗,希望得到通融,但梅貽琦校長的答復是,必須先放棄已獲得的留學機會,重新投考。夏鼐權衡后放棄冒險,決定在考古門內“咬牙硬干”。(49頁)根據《夏鼐日記》記載,他真正對考古學發生濃厚興趣,當是在1936年5月15日隨惠勒博士(Sir Mortimer Wheeler)帶領的參觀團活動之后。當時他們參觀了英國索爾茲伯里“巨石陣”“巨木陣”以及皮特-里弗斯將軍發掘遺址和博物館,并在重要參觀地點聆聽了惠勒博士演講。夏鼐不僅對考古學的興趣日益濃厚,更是萌生了將科學發掘技術和研究方法引入中國的責任意識。在1936年7月5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考古學在學術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學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國現下的上古史界情形,舊的傳說漸被推翻,而新的傳說又逐漸出現,與舊的傳說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書齋中書生的想像,假使中國政治社會稍為安定,考古學的工作實大有可為也。書此以自勉。”(《夏鼐日記》,卷二,53頁)。從誤入考古門的遲疑,到迅速成長為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之一和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主要領導者,其間自然有夏鼐個人天資、努力和機緣等多重因素在內,但入門之初的偶然因素似不便排除。倘若我們再結合夏鼐對科學的考古學與“‘玩物喪志’地玩弄古董”的古物愛好之間的區別,(135頁)那么,夏鼐早年對古錢的興趣更不能算作是后來從事考古學研究的動因。
王先生秉持老一輩學人的謙遜美德,認為自己不從事田野考古實踐,因而“并非夏鼐先生的合格弟子,對他的學術思想未能深刻領悟”,所以只將書名定為《夏鼐傳稿》,寄希望后來賢者能夠寫出更好的夏鼐傳記。(351頁)或許未來會有新的夏鼐傳記問世,但我相信絕非出于王先生自陳的理由。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夏鼐為中國考古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將會得到新的考察和評價,新傳記或可從學科發展史角度出發進行再認識。目前這部《夏鼐傳稿》因記錄了與夏鼐同時共在、同甘共苦的歲月,因其用愛和敬書寫,將成為永遠的唯一。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