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時尚都市的背后:美國血汗工廠一直都存在
在洛杉磯時尚區中心一棟破舊的11層哥特復興式辦公大樓——本迪克斯大廈的頂層,通過略微半開的金屬門,我窺見了在光線昏暗的房間里,工人們彎腰在機器上縫制衣服的場景。成堆的布料堆在油氈地板上。到處都是線、碎屑和灰團。
突然,門一扇接一扇地被猛然關上。 嗙!嗙!嗙!
“哇,動作挺快的嘛,”瑪麗拉·馬丁內茲(Mariela“ Mar” Martinez,昵稱“瑪”)說道。她負責管理在洛杉磯的非營利性成衣工人工會中心。有人認出她了,并相互通風報信。
我們往下走到八樓。那層樓的車間門已經關閉并已鎖上。有不速之客造訪的消息已傳遍整棟樓。我們從走廊的盡頭向街對面望去,看到了聯合工藝大樓——另一棟20世紀初修建的市中心塔樓,里面也有很多違背倫理的血汗工廠。它的藝術派裝飾外觀逐漸破損坍塌。有幾扇窗戶用石灰水重新粉刷過,看不到里面。透過幾扇破爛的窗扇上的裂縫,我們可以聽到里面有縫紉機在咔嗒咔嗒作響。
我們乘本迪克斯大樓的電梯回到了平層,然后向街對面走過去。大廳里有一個收銀臺和一個正在使用公用電話的拉丁裔男子。馬丁內茲跟我解釋說,大多數洛杉磯血汗工廠里的工人來自拉丁美洲,而大多數血汗工廠的老板是韓國人。我們從樓梯爬到三樓。窗玻璃都壞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也許是這里的經理,坐在生銹的防火通道的臺階上吸煙。“你敢從這里走下去嗎?”馬丁內茲問我。防火通道的鋼纜很細,固定墻壁的器件也已有百年歷史,感覺如果有超過三個人在上面就會承受不起,直接垮下來。防火通道只修到了二樓,所以如果你走到二樓了,要想下去還不得不往下跳,下面就是一個垃圾箱。
“我把這叫作洛杉磯的白噪聲,”我們一邊設法回到街上,馬丁內茲一邊告訴我,“沒有人看到或即使看到了也不愿意承認,但它的的確確就在這里。”

美國洛杉磯
如今,洛杉磯已成為美國最大的服裝制造中心。該行業始于20世紀初,那時當地的針織廠開始專門生產泳裝,當時的品牌包括Cole of California和Catalina。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泳裝制造業繼續發展,成為一股“加利福尼亞式風尚”(一種面料輕薄的休閑時尚剪裁)在全國范圍內流行開來。最終,在1990年代初,洛杉磯取代紐約成為美國的時裝生產之都——中心城區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時尚區來說是致命一擊。2017年,加利福尼亞時裝協會主席伊爾莎 · 梅契克(Ilse Metchek)告訴我說,當地服裝業的年收入約為420億美元。馬丁內茲估計,洛杉磯有45000名從事服裝生產的工人。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工人是合理合法的,是按照加利福尼亞的最低工資水平——當時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10.50美元——支付工資的。
另一半屬于非法勞工,在一些非法工廠為美國當地品牌縫制服裝,偷偷摸摸地干著時薪僅為4美元的工作。沒有加班費。沒有醫療保障。工作環境差得嚇人。然而,靠這些血汗工廠供貨的大型中端品牌卻宣稱,其服裝是“美國制造”的。就好像這樣的聲明自然而然地會讓人覺得,這些在美國生產的服裝就要比離岸外包出去的服裝更可靠和有保障,且質量高級些。仿佛它們更真實、更正直和具有更高的品質。這種企業行銷策略一邊公然地違反美國勞動法,一邊討巧地迎合消費者的愛國主義情懷。
美國的血汗工廠一直都存在。理查 · 阿克萊特時代,幾乎每個工廠都是血汗工廠。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紐約的下東區也是如此。當工會和勞工法將其取締后,他們轉入地下繼續干。由犯罪組織經營的美國血汗工廠已成為隱蔽的人口販運和洗錢中心。有時,搜查出一個血汗工廠就可能成為新聞,且報道出來的查獲現場通常都很恐怖。1995年,聯邦特工突襲了位于洛杉磯郊區艾爾蒙地地區的一家秘密服裝廠,這家工廠四周被鐵絲網和帶有尖刺的柵欄包圍著,還有哨兵站崗。在工廠里,他們發現了72名被奴役的泰國工人,價值75萬美元的鈔票和金條,還有一本記賬本,上面記載了數十萬美元現金的轉賬記錄。
由于目前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持反對全球化觀點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呼吁購買“美國制造”,美國國內血汗工廠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洛杉磯,因為這里有大量非法移民。2016年,由馬丁內茲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勞工中心(UCLA Labor Center)合作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被調查的洛杉磯服裝工人中,有72%的人反映工廠很臟;60%的人反映工作的地方通風不良,導致了呼吸系統疾病;47%的人反映洗手間臟得令人惡心;42%的人說他們工作的地方有老鼠。調查發現,存在上述情況的品牌包括Forever 21,Wet Seal,Papaya以及Charlotte Russe。
2016年,美國勞工部指控上述品牌及其他南加州服裝制造商違反了基本的聯邦保護法,要求它們支付工人最低工資和加班費(按85%的工作時間計算),并責令制造商們支付130萬美元拖欠的工資和賠償金。(Forever 21和另外一家服裝零售商Charlotte Russe之后表示,他們對待勞工問題很認真。Forever 21還補充道:“這些被指控的廠商是完全獨立于Forever 21的,他們所做的業務決策與我們沒有關系。”)這份報告的另一位執筆人詹娜 · 沙杜克-埃爾南德斯(Janna Shadduck-Hernández)后來說,這些生產商大多數都“剛好位于時尚區的中心,距離市政廳有20個街區。”
這就是吸引馬丁內茲參與這場斗爭的原因。她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孩,從小生活在距離美國中南部一處服裝工人中心只有幾英里的地方。她的父母都是市里合法的制衣工人,她的父親負責用繡花機繡花,母親則為時裝品牌裁剪樣品。她高中的時候就活躍于各種人權活動中,在布朗大學讀本科時加入了“美國學生反對血汗工廠組織”(USAS)。這個青年組織致力于通過組織倡議和抵制運動來改變現狀。布朗大學畢業后,她回到了洛杉磯,加入了服裝工人中心,協助組織運動。每周她會花兩個下午,在位于洛杉磯街道的一棟破舊的低層樓房的中心辦公室里與工人會面,在密不透風的無窗房間里讓工人們暢所欲言,傾聽他們的抱怨與不滿。
最常見的是“無薪加班,或工資盜竊”(wage theft):老板支付工人的工資大大低于州或聯邦的最低工資標準。通常,她會直接與雇主聯系并嘗試協商解決。如果案件特別嚴重,她會聯系州和聯邦機構,例如美國勞工部的工資和工時司,然后這些機構就有可能會通過突襲檢查的方式展開調查。馬丁內茲會跟調查官一起參與掃蕩調查。她說,有時她竟然會發現標明“非血汗工廠制造”的品牌標簽。當被抓現行后,這些品牌商還狡辯,聲稱他們并不知道自己“認可”的承包商將衣服分包給了血汗工廠。分包在服裝行業中很普遍,導致供應鏈分化斷裂,工人很容易就陷入危險之中。
馬丁內茲或者政府官員會就工人們損失的收入(即最低工資與實際支付的工資之間的差額)提出索賠。供應鏈中的每一方(分包商、承包商、品牌商、零售商)都拒不承擔責任。她說,工廠“將關閉商店,或以其他名字重新注冊營業。雇主的身份證是假的,或者注冊人信息一欄其實另有其人。這些都會破壞案情”。
當馬丁內茲設法要到賠償時,用她的話說就是要到的金額通常“甚至不及實際欠款金額的一半”。“我們要求的工資賠償不包括罰款的話是五萬美元,而我們實際追回的只有五千美元,最多一萬美元。這還是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情況。如果沒有工人代表參與進來,承包商只會給一兩百美元,而很多人還是會接受,因為總比一分錢都沒有的好。”
在這樣的賠償協商會議之后,馬丁內茲繼續說道:“品牌商會告訴承包商,‘要么你來賠錢,要么以后就別想從我們這里接到活。’他們就這樣把自己的責任撇得干干凈凈。如果品牌商真的不給活干,承包商將無錢支付欠薪。我不是說很同情承包商,但是他們也只是這個體系中的棋子而已。如果洛杉磯的每個制衣工人都提出工資賠償要求的話,那將是數以百萬計的金額,可是這數百萬美元已經落到首席執行官的腰包里了。”
她悶悶不樂地看著我說:“跟你說吧,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穿的這身狗屎是在血汗工廠制作出來的,但所有人都置若罔聞。沒有人在意!”
……
當服裝業在19世紀向美國轉移時,隨之而來的還有勞工虐待。那里的許多慈善事業也都是假惺惺的表面功夫,毫無實質作用。但是也有例外。1890年,兩個年輕而富有的進步主義者——一位是在內戰期間失去丈夫的寡婦約瑟芬·肖·洛厄爾(Josephine Shaw Lowell),她的丈夫是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爾(Francis Cabot Lowell)的侄子,另一位是嫁給了股票經紀人的塞法迪猶太人莫德·內森(Maud Nathan)。她們兩位共同創建了紐約市消費者同盟——一個由中產階級婦女組成的非營利性倡導團體,致力于改善當地服裝業的就業條件。她們這樣做既出于公德心,也有私心成分:她們看到剝削女工和童工的報道后很難受,同時也擔心傳染病會污染她們的衣服。
隨后,美國眾議院對美國服裝業展開了調查,并獲取了大量改革的支撐證據,但是后面什么措施都沒有。因此,激進主義者弗洛倫斯·凱利(Florence Kelley)將廢除美國的血汗工廠作為自己長期奮斗的目標。作為美國消費者聯盟[1]的第一任秘書長,她認為,現代的機械化和精簡的配送方式是降低生產成本的最有效方法,而不是降低工資。的確,她認為血汗工廠的存在增加了成本,因為它使得工廠主們不愿意將機器更新換代。她呼吁抵制血汗工廠,說道:“如果人們讓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芝加哥百貨商店零售商)和其他跟它一樣的服裝零售商們知道,他們是不會從后者那里購買血汗工廠生產的衣服的,那么就不會再有血汗工廠了。”
1899年,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推出了“白標”策略。服裝上貼有“白標”就說明這款服裝的制造商是遵守州制定的就業和安全法規以及該聯盟標準的。“白標”賦予了消費者權力,促使他們在購物的同時還懷有社會公德心。“我們可以去買正當途徑生產的、干凈便宜的內衣;我們也可以去買通過可恥的方式生產的、不衛生的廉價內衣,”凱利說,“以后,我們的選擇,我們自己負責。”
一些零售商看到這個政策就退縮了,但費城百貨公司巨頭約翰`沃納梅克(John Wanamaker)卻沒有。他加入了聯盟改善工廠條件的運動,在商店里推廣有“白標”認證的服裝,并讓櫥窗設計師在布羅德街的玻璃櫥柜中擺滿了展示架,向眾人展示血汗工廠和獲得“白標”認證的工廠之間的差異。這些櫥窗展示的照片后來還參加了國際貿易巡展。五年內,就有60家美國制造商獲得了在自己生產的服裝上使用“白標”的資格。
盡管如此,許多工廠還是修得很簡陋,并且經常違反健康和安全法規。一個常見的違規行為是為了防止員工盜竊,竟然將緊急出口鎖住。這種做法會招致災難,就像1911年紐約的三角內衣廠(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火災一樣。逃命的工人們沖上搖搖欲墜的火災逃生通道,然后通道垮塌了。幾十個工人從窗戶和屋頂上跳下來,其中許多人頭發和衣服都燒著了。這次火災共導致146名員工死亡,其中女性123名、男性23名。在2001年9月11日前,這是紐約市最嚴重的工作場所災難。
為了對這種情況進行反擊,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出現了。她積極倡導工人權利,并在1910年成為紐約市消費者聯盟的執行秘書,與弗洛倫斯·凱利并肩作戰。在三角內衣廠火災事件之后,珀金斯加入了紐約州負責監管工廠的工業委員會。20世紀30年代,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任命她為勞工部長,這使她成為美國首位女性內閣成員。她是迄今為止任職最長的勞工部長,在她任職的12年里,通過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創建了包括公共工程管理局在內的機構。其中,通過的《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規定了失業保障金、社會保障金和退休金;以及《公平勞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FLSA),該法規第一次提出了美國的最低工資保障線,確保工人享有加班費,禁止雇用童工,并提出了每周40小時工作制。《公平勞工標準法》的頒布和實施使美國制造業得到整頓,并步入了黃金時代。
但時裝區是個例外。比爾·布拉斯(Bill Blass)回憶說,這個地方仍然“到處都是煤灰和毛絮,就像批判現實生活主義作家德萊賽(Theodore Dreiser)筆下所描述的那樣”,“制造商們想盡辦法維護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權利,即使我們中的一些人剛從戰場回來,身上還穿著軍裝,都不準與雇主乘坐同一部電梯。我們只是這筆骯臟生意背后的打工仔,我們要終結第7大街上的所有骯臟生意。”
直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之后,服裝制造業轉移到海外,而這些工場中的大多數都倒閉了,上述現象才有所改觀。在海外,老式的血汗工廠體系死灰復燃。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勞動法的限制遠沒有那么嚴格,而且幾乎沒有法律監督。因此,在國會1993年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后的六個月內,眾議院勞工管理小組委員會就舉行了幾次關于洪都拉斯一家工廠(美國女裝品牌Leslie Fay的外包工廠)虐待工人的聽證會就不足為奇了。
Leslie Fay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時尚界的標兵。Leslie Fay創立于1947年,其創始人弗雷德·波梅蘭茨(Fred Pomerantz)是一位喜歡抽雪茄的服裝公司高管,他從11歲起就在曼哈頓的時裝區工作。Leslie Fay是以他唯一女兒的名字命名的。這個品牌以靚麗的連衣裙而聞名,這些裙子由位于威爾克斯-巴里的工廠里的工會工人縫制而成。弗雷德1982年退休時,該品牌已遍布全國一萬三千多家百貨公司和專賣店,年營業額達5億美元。
弗雷德的兒子約翰畢業于沃頓商學院,在公司工作了幾十年。在他中年時通過杠桿收購將公司私有化(在經濟繁榮的20世紀80年代,這種做法很常見)。兩年后,前公司經理們和獨立投資者們進行了第二次杠桿收購,使約翰·波梅蘭茨獲得了高達4100萬美元的收益。憑借著如此巨大的財富,他和他的妻子勞拉(Laura)成為“新社會階層”(這是對那個年代的超級富豪的稱呼)的亮點。
1986年,Leslie Fay再次在證券交易所上市,1990年銷售額達到了驚人的8.59億美元。那時,約翰任公司董事長;他的妻子勞拉那時擔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她的家族經營零售業,她曾是投資銀行家。1993年1月,正在多倫多進行商務旅行的約翰·波梅蘭茨接到了首席財務官保羅·F.波利森(Paul F.Polishan)的電話,電話那頭的波利森不安地說道:“我們遇到了麻煩……或許還不是個小麻煩。”
眾所周知,小型私人服裝公司每個季度都會對財務數據——在計算實際銷售完成并獲得利潤之前的銷售訂單額和利潤做下手腳,以使全年的財務數字看起來很理想。但是Leslie Fay是一家上市公司,數據就沒那么容易操控了:該品牌聲稱獲利2400萬美元,而實際上卻虧損了1370萬美元。
消息傳出后,公司股票暴跌,股東提起了集體訴訟,兩個月后,Leslie Fay就成了《美國破產法》第11章破產保護條例的保護對象。波梅蘭茨發誓說他從來不知道有財務欺詐現象。他說,這是某些無恥的員工的個人行為。(波利森后來被起訴,并最終入獄。)
威爾克斯-巴里總部的高管們發起了一項削減成本計劃運動。在那之前,波梅蘭茨一直拒絕外包業務,因為他認為在國內制造(從工廠到零售商店的周轉更快)是明智的業務開展方式。他還說,他覺得選擇在國內進行生產是他的道德義務。
破產后,所有的良好理智和道德風度都蕩然無存。Leslie Fay將生產轉移到洪都拉斯,距離管理層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州東北部很遠。很快,明顯看得出來,就像其他許多在美國以外進行生產的美國服裝公司一樣,Leslie Fay的高管們并不清楚自己的品牌服裝的實際生產情況。
令人尷尬的是,直到1994年他們才從威爾克斯-巴里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的一位證人那里得悉了工廠的情況。國家勞工委員會(位于匹茲堡的舉報商業非法行為、致力于制止侵犯人權和侵犯勞工權利行為的非營利組織)將二十歲的洪都拉斯女孩多爾卡·內奧米·迪亞茲·洛佩
茲(Dorka Nohemi Diaz Lopez,她一直在Leslie Fay的工廠里做衣服)帶到了公司管理層面前。洛佩茲告訴委員會的成員說,工廠里有的女孩才13歲,時薪才40至50美分,而Leslie Fay美國工廠里的工人每小時工資為7.80美元。洪都拉斯工廠的條件就像以前的曼徹斯特一樣。這些女孩輪班十二小時或更久。室溫通常超過100華氏度,也沒有干凈的飲用水。她作證說:“門是鎖著的,沒有他們的允許,你不能出去。”
威爾克斯-巴里的反對聲音也很強烈:下崗工人的孩子們寫信給波梅蘭茨,問他為什么要辭掉他們的父母;牧師在主日講道中公開譴責公司;被辭掉的工人們舉行抗議活動;該地區的報紙刊登了社論專欄,強烈譴責了波梅蘭茨轉向海外生產的行為。“我們一直覺得工廠就像我們大家的家一樣,”在Leslie Fay工廠當了38年機器操作員、現年56歲的珍妮·科瓦萊夫斯基(Jeannie Kowalewski)對小組委員會說。
波梅蘭茨有些不知所措。他在給國會小組委員會的信中寫道:“這是一個虛假的問題。將技能要求低的工作(離岸外包)……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中心問題,而且談判都已經結束了啊。”
許多美國服裝公司,包括一些家喻戶曉的名字,例如Kathie Lee Gifford,J.Crew,Eddie Bauer和Levi Strauss,都面臨類似的指控。作為回應,一些公司開始起草“行為準則”:公司期望其供應商遵守的一系列標準。或者應該叫期望的標準,因為沒有一條是強制性的,一切都是基于自愿。對行為準則制定的需求揭示出時尚界最大的、看似無法解決的矛盾:如何以最低的價格生產商品,同時確保安全、人性化的工作條件和體面的工資。
Levi Strauss的執行管理委員會于1992年3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前)通過了時裝界的首個行為準則。該準則是由Levi’s被稱為“采購準則工作組”(SGWG)的內部工作組制定的。該公司稱其準則是為了“確保在合同工廠為我們生產產品的工作人員受到合理對待和尊重,并在安全健康的工作條件下工作”。“采購準則工作組”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則為指導原則:無童工或強迫勞動,沒有性別、種族或民族歧視,遵守法定工作時間,合理的工資,享有福利保障,享有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以及其他為公司生產服裝的制造商們應遵守的健康、安全和環境方面的標準。
該品牌的動機令人懷疑。李維·斯特勞斯取消了與美國塞班島一家工廠的合同(據報道該工廠侵犯了工人的權利)后不久就引入了該行為守則。該工廠里的景象跟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廠一樣糟糕:破舊的宿舍、無休止的加班時間、骯臟的廁所、緊鎖的消防通道,整個工廠四周都用帶有尖刺的鐵絲網圍起來,并且有武裝警衛巡邏。由于該工廠廠址所在地塞班島也是美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在那里外包生產的公司(包括Levi’s,Gap,Ralph Lauren和Liz Claiborne)都可以在商品上貼上“美國制造”的標簽。在Levi’s推行其行為守則后的幾天,美國勞工部在同一家族經營的十多家塞班島工廠中發現了有違聯邦健康與安全法規的行為,并提起了訴訟。最終,工廠老板向工人支付了900萬美元的拖欠工資。
為了執行這些法規,品牌商們雇用了獨立的監督員來進行監管。監管人員巡視工廠前會提前通知,因此在這之前工廠會被打掃得干干凈凈,并且有人指導工人如何回答監管人員的提問。即使到了現在也是這樣。據報道,在某些國家多達一半的工廠篡改了員工記錄,以通過檢查。監管員不監管,賄賂現象猖獗,丑聞層出不窮。
2003年,美國說唱明星肖恩·庫姆斯(Sean“ P-Diddy” Combs)和杰斯(Jay-Z)就被卷入了一樁丑聞:他們各自創立的嘻哈時尚品牌Sean John和Rocawear的衣服都被發現是在洪都拉斯的血汗工廠制造的。在當年11月舉行的參議院民主政策委員會聽證會上,現年19歲的制衣工人——洪都拉斯女孩萊達·伊萊·岡薩雷斯(Lydda Eli Gonzalez)通過翻譯講述了她在東南紡織廠(Southeast Textiles,SETISA)所遭遇的恐怖經歷。SETISA的訂單約80%來自Sean John;其余的20%來自Rocawear。
SETISA所在的工業區被一圈高墻所包圍,入口處鐵門緊閉,有武裝哨兵站崗。官方公布的營業時間為上午7點至下午4點45分,時薪為75至98美分,但有強制性免費加班。Sean John襯衫在布魯明戴爾(Bloomingdale’s)等美國百貨商店的零售價為40美元。該工廠每天生產一千多件。岡薩雷斯作證說:“一件襯衫的價格要比我一周的工資還多。”
她繼續說:“監工們會站在旁邊,對我們大喊大叫,喊我們動作快點或者咒罵我們,罵我們是(該死的)蠢驢、婊子,甚至更難聽的話。”室溫很高,工人們“整天都汗流浹背”。織物纖維和灰塵使他們的頭發“變成了白色、紅色或是其他我們正在制作的襯衫的顏色”。據報道,飲用水被排泄物污染了。工人被禁止講話。他們只能在早上和下午各上一次衛生間,并且在進去之前還要搜身;通常,衛生間里是沒有衛生紙或肥皂的。女工要接受妊娠測試,如果有人測出來是陽性,就會被解雇。他們每天一到工廠就要被搜身,隨身帶的任何東西,包括糖果或口紅,都要被沒收。晚上下班出廠時還要被再搜一次身。
庫姆斯知道這個丑聞將給他的品牌帶來致命打擊,于是迅速作出反應。十周之內,美國國家勞工委員會[2]宣布SETISA工廠的生產主管和副主管都被解雇。現在,加班是自愿的并且是有償的;浴室的鎖已經打開,武裝警衛被廢除了;安裝了空調和凈水系統。所有的工人都被納入國家醫療保障體系,且允許建立工會。據說妊娠測試也會被廢除。
然而,工資仍然低得不能再低。
“工作只是為了有口飯吃,真的。想要存點錢根本不可能。什么都買不起。 這只是為了生存。”岡薩雷斯告訴參議院小組委員會的成員說,“與兩三年前相比,我的生活并沒有什么改善。我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說到困境,沒有哪個地方會像孟加拉國那樣,讓人覺得困境纏身、難以擺脫、痛苦萬分。
孟加拉人民共和國位于孟加拉地區,是夾在印度和緬甸之間的一小塊區域。據2019年統計,該國有1.68億公民,其中約有四分之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它是世界上第九大人口大國,在人口密集型國家中居第十位。
世貿組織的數據顯示,在2018財政年度,四千萬工人生產了價值超過三百億美元的出口成衣或RMG,這使得孟加拉國成為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服裝生產國。孟加拉國服裝制造商和出口商協會會長斯迪庫爾·拉曼(Siddiqur Rahman)告訴我:“我們的外匯中有83%來自服裝生產行業。五千萬人要靠服裝制造業生活。 我們的經濟也要靠服裝制造業。”政府計劃在五年內將產出翻一番。
孟加拉國的服裝制造業始于20世紀70年代脫離巴基斯坦的獨立戰爭之后,起步相對較晚。當時韓國已將出口美國的服裝和紡織品配額用到了極限,因此,制造企業家們便轉向孟加拉國的鄉村建造和裝備工廠。與以前的情況一樣,新的制衣工廠一建立,貧窮的年輕婦女就蜂擁而至,或是被家里人派到這些地方工作。那里的工資低得驚人,工作時間長得令人難以置信,這使得孟加拉國成了另一個曼徹斯特——最廉價的服裝生產地。
成千上萬的工廠修建了起來,然而這些簡陋的工廠通常都沒有得到許可證,甚至連一些基本的安全預防措施都沒有,比如接地線或設置消防通道之類。盡管如此,這些工廠的安全保衛設施卻是一流的,就是為了把工人關在里面和防止偷盜。孟加拉國的工廠距離品牌商的總部十萬八千里,發生在這些工廠里的事情就不為人所知了。
非政府組織的倡導者們也在努力推動變革,如國際勞工權利基金(ILRF)的負責人朱迪·吉爾哈特(Judy Gearhart)。國際勞工權利基金成立于1986年,設在華盛頓市區,是一家非營利性人權組織,旨在維護“全球經濟中工人的尊嚴與正義”。吉爾哈特從1992年開始,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期間就在為墨西哥的工人爭取權利。2011年加入了國際勞工權利基金,擔任執行董事。她做事干練、從不拖泥帶水,為人和藹可親,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懷著毋庸置疑的熱忱。
國際勞工權利基金長期駐扎在孟加拉國,以打擊那里的童工現象。但是悲劇仍然發生了。2005年4月11日,光譜針織實業有限公司(Spectrum Sweater Industries Ltd.)——一家位于孟加拉國首都達卡(Daraka)郊區薩瓦爾(Savar)的九層樓簡陋工廠,在午夜后不久坍塌了,事故造成64人死亡,80人受傷。之后,吉爾哈特告訴我:“我們深入推進了對服裝行業的調查工作。我們開始調查工廠的火災和倒塌緣由,并與‘潔凈服裝運動’( Clean Clothes Campaign)和‘工人權利聯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密切合作,與那些跟‘不干凈的工廠’有合作關系的公司作斗爭。”
國際勞工權利基金的策略有三方面:推進法律和政策改革;對企業更多地問責;支持并加強工人和當地工人組織的影響力。但是阻力依然存在。制衣業為孟加拉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收入,且不僅僅是在稅收方面。國際勞工權利基金的組織和傳播總監利亞納·福克斯沃格(Liana Foxvog)告訴我,2018年,孟加拉國議會議員中有10%的人是制衣廠老板,有30%的人其家庭成員中有人是制衣廠老板。“所以,你可以想象這是怎樣的一種利益勾結”。同樣,腐敗、貪污也不難想象了。如同一百多年前的紐約一樣,這終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2010年12月,位于達卡郊區的一棟10層樓高的That's It運動服制衣廠發生了火災,盡管Gap剛剛才派人視察過工廠。災難現場如出一轍:出口被鎖,工人們慌亂中躍窗逃命。事故造成一百多人受傷,29人喪生。不幸的不止他們。在2006年至2012年,有五百多名孟加拉國服裝廠工人在工廠大火中喪生。因為That’s It運動服廠是Gap,Tommy Hilfiger和Kohl’s這些大品牌的供應商,因此此次事故成了國際新聞,并有人呼吁要進行改革。
工會和非政府組織與品牌商們坐下來討論工廠安全問題,并敲定了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名為《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Bangladesh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Agreement)。但品牌商們遲遲未在協議上簽字。直到2012年冬天,That’s It運動服制衣廠致命火災發生一年多后,紐約ABC新聞再次報道了此次事件,并借此質詢了設計師Tommy Hilfiger及其首席執行官為什么要在這種沒有任何消防措施的工廠里生產衣服。直到那時,PVH公司(旗下品牌有Tommy Hilfiger,Calvin Klein,Van Heusen,IZOD,Arrow,Michael Kors,Sean John和Speedo)才同意在《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上簽字。六個月后,德國零售連鎖店Tchibo也在上面簽字了。但是之后就沒有品牌簽字了,而該協議需要有四家公司簽字后才能生效。
在安全協議被擱置八周后的十一月的一天晚上,位于達卡郊區阿蘇里亞的一棟九層高的塔茲林時裝廠(Tazreen Fashion factory)的四樓里,23歲的蘇米·阿貝丁(Sumi Abedin)正在縫紉機上工作,她回憶道:“突然有個人跑過來,大喊道‘著火啦’。”
而她的經理和主管信誓旦旦地跟所有人說沒發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們告訴工人們:“哪里有火災,快回去繼續工作。”然后鎖上了門。
隨后火警警報響起。主管和保安人員仍然堅持認為這只是一次火災演習,并要求他們繼續工作。
“五到七分鐘后,我聞到了煙味,”阿貝丁回憶道。“我跑到門口,門是鎖著的,又跑到樓道口,門還是鎖著的……煙霧是從樓下傳上來的。”她設法爬到了二樓,但走不通了。樓道“被大火吞沒了”。
有1100多名工人被困在里面。開著的門道和樓梯間很狹窄,逃生通道不但少而且搖搖欲墜。工人們試圖拆除窗戶上的安全欄,終于有人把安全欄拆下來了。那個人趕緊跳了下去。然后又有人跟著跳下去。
“我也跟著跳了。”阿貝丁說。
她摔斷了胳膊和腳。與她一起跳下的同事卻撞到地上摔死了。
在這次事故中總共有200多人受傷,至少117人死亡,其中近一半的尸體被燒得面目全非。這是自一個世紀前的三角內衣廠大火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服裝制造業事故。調查人員后來在發現的標簽、衣服和文件資料里找到了西爾斯(Sears)、沃爾瑪和迪斯尼在那里代工生產的證據。然而這三家都聲稱他們沒有授權塔茲林廠生產商品。
利亞納·福克斯沃格(Liana Foxvog)告訴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塔茲林事件在全球媒體中鬧得沸沸揚揚,但是“仍然沒能迫使品牌商們”簽署《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這使得像索赫爾·拉納(Sohel Rana)這樣無恥的服裝廠老板覺得自己不可一世。
索赫爾 · 拉納曾是個流氓惡棍。在他三十多歲時,他以蠻橫霸道的做生意方式與招搖過市的生活方式而出名。他經常帶著一幫人,騎著摩托車繞著薩瓦招搖轉悠。他還善于與白道打交道,他擺平了政府官員和警察,這使他可以明目張膽地販毒和毆打異己,而不受法律制裁。他父親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賣掉了家里鄉下的土地,并在薩瓦買了一小塊土地,他就跟著他父親一起做生意。有了警察撐腰,拉納從曾經的商業伙伴那里搶了一塊地,又通過偽造契約的方式把臨近的另一塊地也霸占了。執法部門在這件事情上始終保持沉默。正如拉納迫害過的其中一名受害者所說:“警察都很怕他。”
2006年,拉納蓋了一棟六層樓的建筑,用來做制衣廠房、商店和銀行。這棟建筑修得很快,也很粗糙,完全沒有且無須考慮城市分區規劃法律或安全法規。2011年,拉納設法獲得了許可,又建了兩層樓。當地人懷疑這是私下行賄的結果,這在薩瓦司空見慣。一位當地的前政客承認,這個建筑群“迅速擴張、毫無規劃可言”。出現了“很多像拉納廣場(Rana Plaza)風格的建筑物”。
2013年4月23日的上午,拉納廣場里的五家制衣廠的工人們正忙著縫制衣服,突然一聲爆炸震動大樓,緊接著大樓從二樓開始像地震斷層線那樣被劈開。“裂縫是如此之大,我都可以把手伸進去。”矮矮胖胖的年輕女孩希拉·貝古姆(Shila Begum)回憶道。五年前的那個時候她正在五樓的Ether Tex服裝廠(Ether Tex Ltd.)的縫紉機上工作。
驚慌失措的工人們涌入大街。管理層喊了一位工程師來檢查損壞情況。這位工程師覺得應該立刻封閉這棟危險建筑。這個提議被當時正在拉納廣場會見記者的索赫爾·拉納否決了。據報道者稱,拉納說:“這只是墻上的灰泥掉了,僅此而已。沒什么大不了的。”工人們當天都被送回了家,但第二天早上被命令回去上班。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的上午8點左右,馬哈茂德·哈桑·赫里多伊(Mahmudul Hassan Hridoy)聽到有人在敲門。原來是他的老板兼鄰居上門提醒他今天得回廠上班。赫里多伊,27歲,身體狀況良好,性格溫和,他剛在那個周末迎娶了戀愛三年且懷著他的寶寶的女朋友。兩周前,他辭掉了薪水不高的幼兒園老師的工作,然后到位于拉納廣場的時裝品牌供應商New Wave Style公司當質量檢查員,薪水比以前高得多。由于他有數學才能,因此管理層向他保證,他在那里會晉升得很快。“這就是我到拉納廣場工作的原因,”2018年我倆在薩瓦的肯德基午餐會面時他告訴我。
他聽了老板的話,然后乖乖去上班,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希拉·貝古姆也是其中一員。在正午烈日下,我和她走在薩瓦的街道上,她回憶道:“我當時真的很恐慌。”工人們全都回去上班了,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回去的話,月底就拿不到工資。孟加拉國當時的最低工資為每月38美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按經濟學家計算得出的結論,38美元相當于生活開支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包括了住房、食物和衣服等基本需求所需的開支。(在2019年1月,孟加拉國的最低工資線提高到了每月95美元,但仍然僅相當于生活開支的一半。)
希拉·貝古姆告訴我說:“停電的時候,我正在忙著手頭的活,為一個法國品牌制作藍色牛仔褲,就像你身上穿的這種。幾分鐘后,發電機開始運轉。”隨著發動機的隆隆聲,大樓開始震動。“接著樓就塌了。”說完她看著我。她的黑眼睛暗淡茫然,好像有人把她內在的希望之光熄滅了。
她繼續說道:“水泥天花板砸在我手上,我的頭發被縫紉機纏住了。掙扎了很久,我才把頭發從縫紉機里順出來,但我無法將手從水泥堆里扒出來。”16個小時后,她的鄰居也作為數百名緊急響應人員之一,加入現場救援隊伍,并把她救了出來。她說:“他們在現場用鐵棍和鐵管把我撬了出來。他們說我的腸子散得到處都是。我昏迷了27天才醒來。”
當周圍變得漆黑一片、寂靜無聲時,赫里多伊正在七樓驗收牛仔褲。他回憶說,發電機開始運轉了,“感覺我腳下的地板像在移動。然后,什么感覺都消失了。”當他在瓦礫中睜開眼睛時,他意識到自己被困在了水泥柱下。當他慢慢看清周圍的事物時,他發現與他面對面躺著的是他的在二樓擔任縫紉機操作員的好朋友費薩爾(Faisal)。“我不確定發生了什么。”赫里多伊低聲說。“我想應該是我這一層樓的地板一直往下掉,掉到了他在的那一層樓。”費薩爾的頭骨被砸碎了。“他的腦漿都灑出來了。”
赫里多伊哭了起來。“我不能忘記他的頭在我面前裂開的情景,”他抽泣著說,“那些記憶仍然困擾著我。”
拉納廣場坍塌事件造成1134人死亡、2500人受傷,是現代歷史上最致命的服裝工廠事故。
“在那場事故中,我失去了所有朋友,”貝古姆說,“許多人的尸體至今未找到。”

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國首都達卡郊區的一座建筑物發生坍塌
斯德哥爾摩時間凌晨5點,H&M可持續發展負責人海倫娜·赫爾默森(Helena Helmersson)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電話那頭是她在薩瓦的主要負責人,正在跟她重述拉納廣場坍塌的恐怖瞬間,并向她保證,H&M沒有以正式的名義在那里生產任何服裝。也就是說,她被事先預警,H&M的承包商有可能把業務分包給了拉納廣場的某家生產車間;而且在事故調查完成之前,誰也沒法確定。鑒于H&M是孟加拉國最大的服裝出口商,即使這次H&M的外包工廠沒有卷入其中,但仍可能受到勞工權利組織和消費者的抨擊,以此抗議離岸外包的種種劣跡:缺乏監督和安全執法,侵犯人權,復雜而難以追蹤的供應鏈。兩個小時后,早上七點,赫爾默森與H&M首席執行官卡爾-約翰·佩爾森(Karl-Johan Persson)會面,謹慎周密地制訂公司的應對措施。
H&M的回應聲明里寫道:“H&M沒有在事故大樓中的任何一家紡織工廠代工生產。需要記住的是,這場災難是孟加拉國的基礎設施問題,而不涉及紡織行業特有的問題。雖然我們的供應商工廠沒有涉及此次事故,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會旁眼冷觀。我們會積極投入,為建設性地解決這一問題盡一份力。”
然后,大多數品牌仍然保持緘默。
“拉納廣場事件后,沒有哪家品牌會敢于出面承認它們在那里有工廠”,福克斯沃格告訴我。
為了弄清楚在那里生產的有哪些品牌,好幾隊研究人員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瓦礫堆中尋找蛛絲馬跡,搜尋標簽、瀏覽進口數據庫和工廠網站以搜尋采購信息。她說:“這是真正的三角互證(triangulation)。”
當證據擺在眼前時,沃爾瑪仍然聲稱公司并未授權將業務轉包給拉納廣場的工廠,法國的家樂福(Carrefour)也否認在那里生產,而杰西潘尼(J.C.Penney)和李庫珀(Lee Cooper)、艾康尼斯(Iconix)則毫不回應。即使確認了有十幾個美國和歐洲品牌在那里進行生產,但大多數品牌還是躲避責任,拒絕向受害者家屬和幸存者賠償,并且由于還沒有相應的保障工人權利的協議,因此這些品牌也沒有支付賠償的義務。
這一次,在毫不留情的媒體報道的猛烈攻擊之下,品牌商們開始緊張了。塔茲林火災和拉納廣場坍塌事件的相繼發生,說明事態確實很嚴重了。他們必須得做點什么。然后,品牌商們想到了被他們完全忽略了兩年的倡議——《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
在六周內,包括Primark,Inditex,Abercrombie&Fitch,Benetton和 H&M在內的43家公司簽署了該協議,并將其更名為《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the 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截至10月,該協議已有200名成員,其中包括迅銷公司(Fast Retailing,優衣庫的母公司)和美鷹傲飛公司(American Eagle)。
大量其他品牌(主要是美國品牌)以責任認定問題為由拒絕加入。7月,沃爾瑪宣布實施《孟加拉國勞工安全聯盟》(the Alliance for Bangladesh Worker Safety),該安全條款與《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類似。簽署的品牌包括:Gap,Target,Hudson’s Bay Company(旗下品牌有Saks Fifth Avenue和Lord&Taylor)和VF Corporation(旗下品牌有Lee Jeans,Wrangler,The North Face和Timberland)。但是該聯盟條款沒有法律效力,非政府組織認為它不及《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那么有效率、有誠意。福克斯沃格解釋說,《孟加拉國勞工安全聯盟》的“影響較小,適用于較小的工廠”。并且《孟加拉國勞工安全聯盟》是自愿加入的,而經數十年來的火災和倒塌事件證明,凡是自愿加入的組織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對拉納廣場事件的新聞報道直言不諱,也不可避免。隨后的意識宣傳運動也搞得有聲有色。但是美國人并沒有改變他們的服裝購物習慣。2013年,他們在時裝方面的支出為3400億美元,是購買新車投入的兩倍多。其中大部分時裝是在孟加拉國生產的,其中一些就是在拉納廣場坍塌事件之前由那些工人生產出來的。
……
塔茲林的老板德爾瓦爾·侯賽因(Delwar Hossain)最終被捕,并被指控犯有過失殺人罪,這意味著他知道自己對工廠安全的無視可能會導致人員死亡。這個案子2015年就開始審理了,但由于原告找不到證人出庭,就一直拖到2018年11月(也是塔茲林事故六周年紀念日)都還沒有結束。
2016年,索赫勒·拉納和其他17個人,包括其父母、拉納廣場的工程師、薩瓦市長、三名政府監管員及城市規劃師,均被指控犯有包括殺人罪在內的多種罪行。一年后,拉納因未向反腐敗委員會透露自己的真實財產而被判處三年徒刑。由于罪犯向上級法院上訴,因此針對謀殺罪名和其他指控的審判仍舊懸而未決。盡管效率不高,但這兩起案件的審判在孟加拉國服裝業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吉爾哈特(Gearhart)告訴我,在1998年的時候,只有大約15%的公司在公司行為守則中包含了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條款,而現在這兩項都是常規條款了。各大品牌都在將生產廠商公布出來(這在5年前想都別想),甚至當有工人死亡時,他們還會支付賠償金。
與孟加拉國服裝制造業其他方面的進步一樣,其推動力都是拉納廣場事件。事故過后,品牌商們突然覺得壓力重重(有可能是真心出于內疚,但更可能的是害怕聲譽因此受損),不得不為死去和致殘的工人支付點錢。“但他們不管這叫‘賠償金’,”福克斯沃格補充說,“這叫拉納廣場撫恤金。”由潔凈服裝運動組織反復商討確定下來的這筆3000萬美元的捐贈,由品牌商承保,以減輕死者家屬和遭受毀滅性創傷的工人的負擔。但是想要獲得這些錢沒有這么簡單。
希拉·貝古姆的傷勢很重:她必須穿醫用緊身衣,右前臂上纏上矯正帶。 她告訴我:“我的腎臟被壓到,嚴重受損。我幾乎不能用右手。”她還說她沒有得到政府補償,也沒有得到任何品牌的賠償。現在她殘疾了,沒辦法工作,她丈夫又去世了,她沒有其他經濟來源。這迫使她不得不讓她14歲的女兒輟學。雖然教育是免費的,但她再也負擔不起書籍和午餐等雜費。對于日常開支,她承認:“我得乞求家里人給點錢。”她開始哭泣。她看著我們面前空空蕩蕩的拉納廣場,說:“我不想活了。”
新婚的赫里多伊拄著拐杖走路,還飽受頭痛的困擾。有時他睡著的時候會使勁扯自己的頭發。在他漫長的康復期間,他的妻子離開了他并墮了胎。“那場事故毀了我的生活,”他邊說邊擦了擦眼角的淚。
事已至此,赫里多伊還是努力地重新生活。赫里多伊是我在薩瓦遇到的幾十名幸存者中唯一一個成功從拉納廣場善后信托基金中爭取到自己的賠償金的人。他用那些錢開了一家小藥房。他還成立了薩瓦拉納廣場幸存者協會,該協會由300名成員組成,每個月在他的藥店里小聚一次,以互相幫助,走出困境。有時,這樣的友情幫助還不夠:分別在2015年和2016年,兩名協會成員在自家客廳里上吊自殺了。
政府仍然反對結社和工會自由。工廠中的性虐待和身體虐待仍然猖獗。等到工廠都垮了,工人們還沒拿到賠償金。
即使是與品牌商簽了合同的,但在他們面前,工人和工廠主還是顯得軟弱無助。201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一群激進分子持槍襲擊了達卡一家海外僑民和外國人經常光顧的精品咖啡店,劫持了40名人質,并殺死了20人。從那以后,孟加拉國就常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在繼而展開的營救中,五名武裝分子、兩名警察和兩名咖啡店員工被殺。時裝銷售代表立即取消了預定的行程,并撤出了在該國的工作人員,這使那里的工人和工廠主都慌了神。“如果他們不來孟加拉國生產衣服了,我們該怎么辦啊?”一位縫紉女工大哭起來,她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西方人光顧的連鎖酒店用水泥筑起了屏障,搭設了金屬探測器、X射線機,安排了警衛用炸彈探測棒對進出人員搜身檢查。服裝制造業又回到了以前的老樣子。
隨后就是工人爭取工資權益的長期抗爭,要求工廠主支付的工資起碼能養家糊口。2016年,工人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立即加薪。工廠主和政府對此進行了報復:有55家工廠關閉了一周;1500名工人被解雇;35名工人被抓進監獄,24人還不能被保釋。“那真是太黑暗了,”吉爾哈特回憶道,“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過,這么多的工人被逮捕或拘留了那么長時間,或被拒絕保釋。”
賓夕法尼亞州全球工人權利中心主任馬克·安納(Mark Anner)告訴我,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服裝行業十分在意季度收益”。“如果每三個月股東就跟你提一次要求更多利潤或威脅要退股,你怎么去制訂長期計劃呢?這種涓滴式的運行機制對工人有何影響?”或對整個孟加拉國有何影響?吉爾哈特說:“如果工人賺得體面的工資,經濟就會增長,因為這樣他們才有能力買午餐和理發。如今我們對工人的投資體現在哪里?他們真的只是整個行業運行體系里的小小齒輪嗎?”
注釋
1.美國消費者聯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該聯盟成立于1899年,是一家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職責是團結當地的消費者組織。
2.美國國家勞工委員會:NLC,后來稱為全球勞工和人權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Labour and Human Rights。
本文摘自黛娜·托馬斯的新作《時尚都市:快時尚的代價與服裝業的未來》,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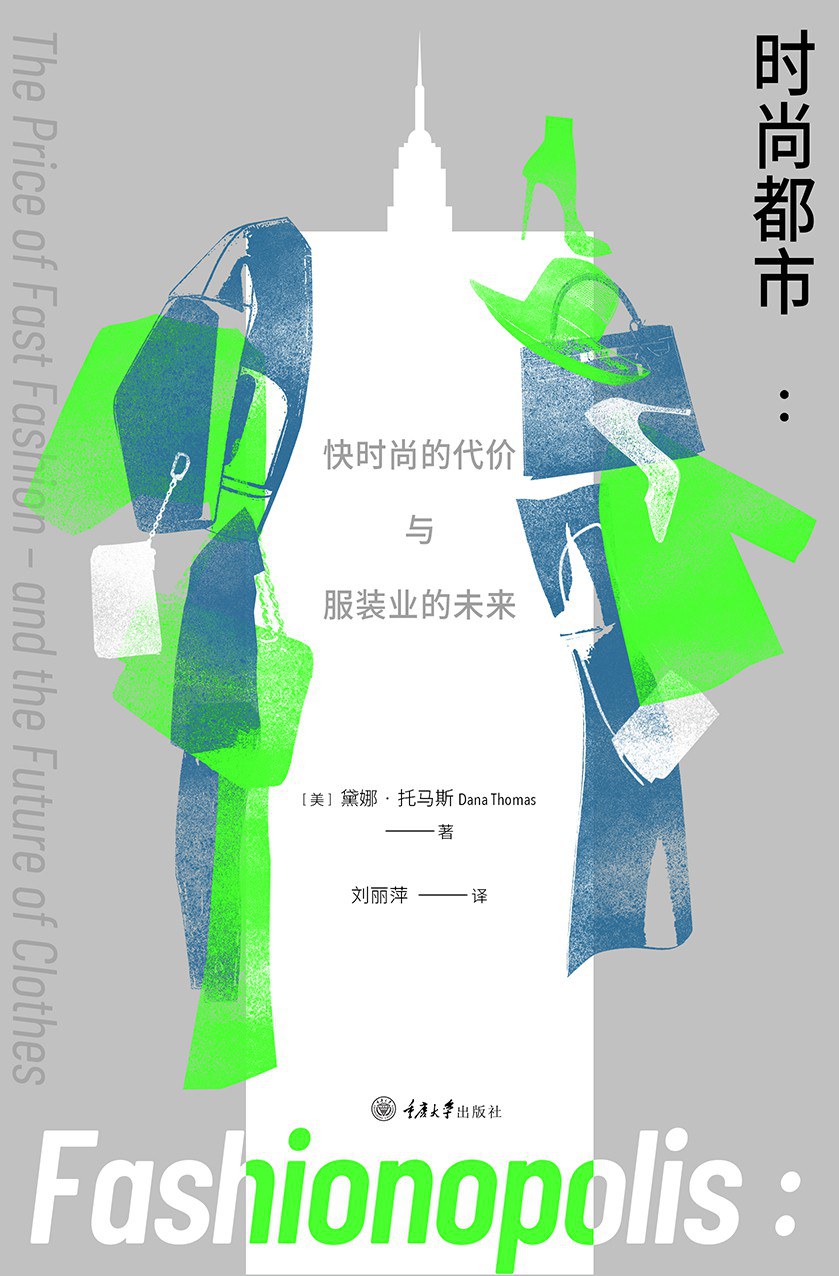
《時尚都市:快時尚的代價與服裝業的未來》,【美】黛娜·托馬斯/著 劉麗萍/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