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數字媒介時代:我們不是邁向更高級的未來,而是更高級的過去
在寫作已經出現了幾千年之后,閱讀依舊是人們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主題。人們對閱讀的敘述是相互矛盾的,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些敘述體現為人們對于讀寫能力的祛魅或者對于其未來的擔憂,而今,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則進一步發展為更加嚴重的兩極對立。
如今,對于啟蒙運動時代的讀寫能力概念的祛魅常常是通過一種對于數字技術的不加批判的贊美而表達出來的。后麥克盧漢時代的技術主義者對互聯網大加贊美,認為它可以顛覆書本所曾經享有的那種令人不快的權威性。一位名叫克雷·舍基(Clay Shirky)的數字媒體專家宣稱,人們沒有必要為了深度閱讀(deep reading)的消亡感到哀傷,因為它原本就是一個騙局。在談到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名著《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時,他似乎因為“沒有一個人”再會閱讀這部小說而感到非常高興:它“過于冗長并且如此乏味”,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托爾斯泰的經典著作實際上根本不值得他們花費時間去閱讀”。舍基所表達的這種民粹主義情緒迎合了當今的時代精神,以至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在2010年將他提名為“最頂尖的一百位全球思想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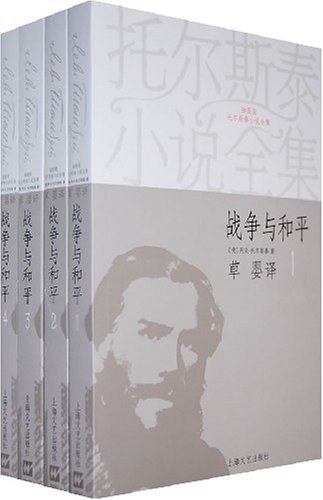
《戰爭與和平》
當某些人為所謂的古滕堡式印刷文化之死而進行歡呼的時候,那些因為社會正面臨讀寫能力的危機和文學經典的必然衰落而憂心的批評家們則發出了悲嘆。有人聲稱學校沒有辦法讓相當一部分學生學會如何閱讀,而這一傳言常常會引起人們圍繞著誰應為此負責的問題而展開憤怒的相互指責。患有技術恐懼癥的人士指責說,互聯網的干擾使得人們無法再進行嚴肅的閱讀,而受其影響,關于讀寫能力正在下降的警告也發展為一種聲稱嚴肅閱讀正面臨空前困難的觀點。昔日那些懺悔文學作品的作者們曾經聲稱自己難以抑制閱讀的激情,可是在今天這個容易分心的時代,評論家們常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表明,人們在試圖閱讀嚴肅的文學作品時將面臨非同尋常的困難。
爭論的一方把技術看得如同救世主一般,而爭論的另一方則把技術看成罪魁禍首。雖然爭論雙方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但是他們都把閱讀意義和閱讀地位的變遷歸因于數字媒介的出現。然而歷史表明,大多數被他們歸因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之影響的事物都曾經是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人們關注過的主題。關于信息過量、媒介干擾和注意力缺乏等方面的傳聞絕不是什么新生事物。那些討論讀者所面臨的當代挑戰的文章不過是某些流傳已久的關于選擇過多、信息過量和變化過大的老論調的翻版。一位當代批評家在談到那種以數字形態進行的泛讀時指出:“可供瀏覽的文本太多了,以至讀者們心生敬畏和恐懼,且無力對它們加以辨別,所以讀者們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匆忙地從一個網站跳到下一個網站,而無法讓文字引起他們內心的共鳴。”
我們由此得出結論:我們所面臨的當代困境并非起因于那些強大的和令人興奮的新式交流技術,而是由于我們難以決定應該交流什么內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閱讀不可避免地獲得了一種新的意義。
脫離內容
當人們的閱讀內容對他們來說變得真正重要的時候,讀寫能力才能體現出其自身的價值。寫作和閱讀并不僅僅是交流的技術,而且閱讀也不純粹是一項可以被個人用來解讀文本的技巧。讀者可以從他們對閱讀內容的沉浸式體驗中汲取意義,而他們的閱讀方式又會受到所處身時代中更為廣泛的文化態度的影響——要知道,每個時代流行的學術氛圍,以及思想和文本所擁有的對于共同體的意義,都會塑造出某種看待讀寫能力的文化態度。由于猶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對文本閱讀加以神圣化,所以曾有很多人相信,閱讀可以讓他們接近真理并更好地理解上帝賜予人類的旨意。宗教改革促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掃盲運動,因為在當時有成千上萬的文盲信徒試圖閱讀那些已經被翻譯成母語的《圣經》。識字率的上升同宗教改革的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
18世紀的啟蒙運動十分重視思想和教育,從而有助于創造一種高度重視閱讀的環境。在18世紀的時候,“閱讀興趣”成為一句習語并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并不是每一個學習如何閱讀的人都會對精致的哲學觀點感興趣,但是在閱讀被人們當作一項重大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贊美的環境下,它成了一種用于增長知識、促進理性和提升審美趣味以及實現自我完善的媒介。學會如何閱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正如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e)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知性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的工人階級當中,有很多人都學會了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來進行閱讀,因為他們相信自我教育的重要性。這些自學成才者為了學習閱讀而投入的精力和熱情表明,當閱讀顯得很重要時,人們很容易以讀書為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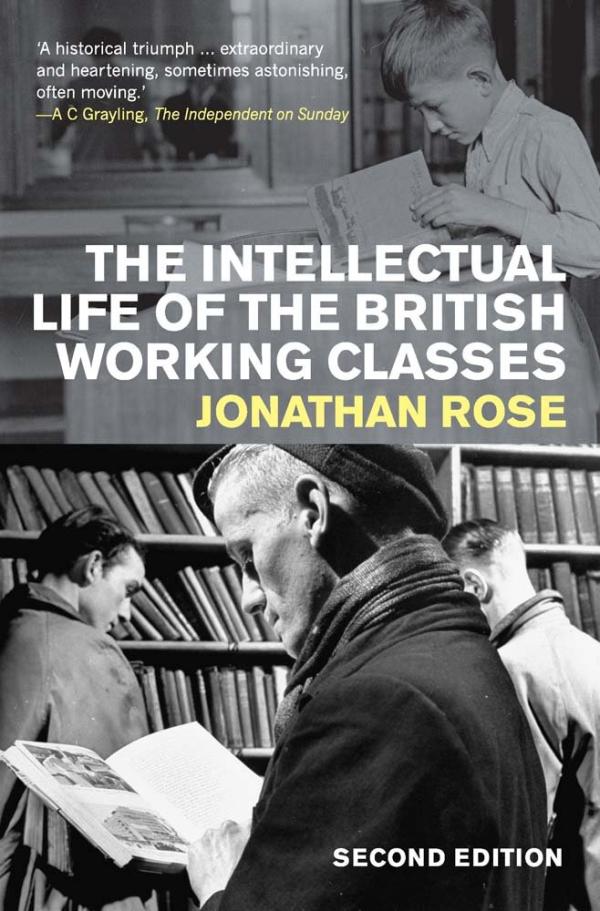
《英國工人階級的知性生活》
正如我曾在一項關于知性生活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現時代的人們發現自己很難認真地看待思想以及知識的權威性。我們所在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而不是一個思想的時代。在思想的地位和知識性論斷的客觀意義得不到重視的背景下,讀寫能力本身也會被看得無足輕重。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探討過的那種對于讀寫能力的袪魅正是這種文化困境的表現之一。它的另一個甚至更令人不安的表現是,人們顯然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語言來表達閱讀的價值。讀寫能力的倡導者常常采用公共衛生運動的倡導者所采用的那種方式來吸引潛在讀者的注意力,例如他們常常宣稱:閱讀可以充當一種有效的壓力緩解療法。
英國教育部于2012年發布了一份用心良苦的報告《關于快樂閱讀的研究證據》(Research Evidence on Reading for Pleasure)。這份關于“快樂閱讀”的研究報告實際上并未能把閱讀的快樂說成是一件具有內在價值的好事。相反,它得出了這樣一個不痛不癢的結論:“證據表明,快樂閱讀是一種能影響情感和社會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還意味著“可以為讀者贏得更高的評價”。它在陳述快樂閱讀的情形時所采用的這種扭扭捏捏的表達方式本身便意味著,在讀寫教育上出現了某些嚴重失誤。這份報告的作者找不到一套規范性的語言來闡釋快樂閱讀的意義,可以說,他很難勝任賦予讀寫能力以意義的艱難使命。
這些倡導閱讀的善意人士發現,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語言來論證自己的理由并讓人們注意到閱讀對閱讀者的變革性影響。他們撰寫的倡導閱讀的宣傳材料中,很少像人文主義者那樣強調閱讀具有內在的價值;相反,他們把讀寫能力當作一種可以為讀者帶來重大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有用技能。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聲稱:英國的失業問題同讀寫能力的低下有關,而且“只要這個國家能采取行動來確保每個孩子都在11歲之前掌握良好的閱讀技能”,那么它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320億英鎊以上”。
閱讀的意義是在閱讀主體同文本內容的互動中產生的,這種互動有助于啟發讀者的靈感或激發讀者的情感。在整個歷史上,讀者的所有感受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于他們同閱讀內容之間的互動。然而,當社會發現賦予內容以意義很困難的時候,又會發生什么呢?
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的《古滕堡哀歌》(The Gutenberg Elegies)一書生動地闡釋了閱讀這種活動的意義:由于閱讀具有形而上的性質,例如它能塑造自我,所以需要按照閱讀自身的價值來評價它。他還描寫了“印刷文本的穩固地位”如何“被新發明的電路中脈沖的急流取代了”。伯克茨擔心,書本喪失權威性將會對“由信仰、價值觀和文化愿景所構成的完整體系”造成嚴重影響,因為“我們整個人類的歷史——我們社會的靈魂——都記錄在印刷文本之中”。
伯克茨指責電子媒介的興起及其帶來的變革讓社會變成了“一個未知的領域”,并且指責數字技術及數字媒介的興起讓“我們的大部分遺產都變成了對我們完全陌生的東西”。絕非只有他一個人認為,社會對于印刷文化的疏離起因于數字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在他之外,還有眾多的文化評論家和媒體評論家也先入為主地相信,互聯網導致了古滕堡時代具有線性思維方式的讀者的消亡。他們還聲稱,那種同啟蒙時代的思想有關的理性認知形式已經讓位于一種全新的認知形式。那些對后古滕堡時代的到來表示歡迎的人們實際上正在為這種與印刷文化有關的理性形式和知識形式的衰亡而喝彩。
無論互聯網導致了何種長期的變革,它都沒有直接導致社會對于自身文化遺產的疏離,也沒有直接導致那些同讀寫能力危機有關的問題。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關于閱讀危機的討論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已存在,而關于社會同其文化遺產之間的緊張關系的思考自現代以來便是導致人們陷入長期爭論的根源。各種形式的權威都在遭到挑戰,以至到了20世紀下半葉的時候,權威一詞越來越多地被打上了負面含義的烙印。
在關于21世紀社會發展道路的爭論中,這種把文化權威的衰落同新媒體的興起和影響混為一談的觀點變成了一種流行思潮。一種執著于新技術和新媒體之影響的思想傾向在文化景觀中產生了重大影響。麥克盧漢最為系統地闡釋了這種技術決定論的觀點,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東西是媒介而不是內容,并且把內容描述為“竊賊手中的一塊美味多汁的肉,其用途是干擾和分散‘心靈的看門狗’的注意力”。
然而,假如內容果真只是一種干擾,而媒介才是“信息”,那么閱讀內容的相對重要性便成了主觀的東西。按照這種觀點,在印刷文化中形成并體現出來的內容——知識、智慧和文化遺產——將失去其對于新媒體的權威性。這種觀點得到了后古滕堡時代生活方式的支持者們的公開贊同。《衛報》(The Guardian)的主編凱瑟琳·維納(Katherine Viner)以樂觀主義的語氣談到了“長達五百年的由印刷主導信息的時代”的終結:
實際上,數字技術是一次巨大的觀念轉變、一場社會變革和一顆集束炸彈,它徹底改變了我們的身份、我們的社會秩序、我們的自我認識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們正置身于這一變革之中,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因為離它太近而難以察覺到它。然而,這一影響深遠的變革正以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對于技術變革的過分強調不僅會導致對于內容的文化意義的低估,它還表現了一種對于內容的脫離。因此,盡管伯克茨等人對于隱含在內容的主導性地位之中的文化連續性的喪失表示哀嘆,但是維納卻興高采烈。
按照維納的觀點,印刷文本中總是存在某種固定的格式。在古代的蘇格拉底看來,閱讀文化是不自然的,因此還缺少此前的口傳文化所具有的那種純粹性,而繼承了這一偏見的當代批評家們不僅厭惡文本的固定性,而且興奮地認為,數字技術有可能幫助人們打破固定的文本對于讀者的僵化限制。似乎如此一來,印刷文本的人為性特征便可能被一種更具自然性和自發性的閱讀態度所超越。
如同其他那些贊同“古滕堡間歇期”(Gutenberg Parenthesis)的人士一樣,維納也預測人類將會回歸到印刷技術出現之前的那個更加自然和更具參與性的口傳時代。她宣稱:“在長達五百年的時間里,知識以固定的形式被保存在印刷文本之中,而且這種形式的知識被人們視為可靠的真理;如今,在邁向后印刷時代的過程中,我們將重新回到此前的時代,即從我們遇到的人們那里聽取正確或錯誤信息的時代。”
假如我們真的像維納所說的這樣,不可能再通過對印刷文本的閱讀來接近“可靠的真理”,那么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將比一場單純的“讀寫能力危機”更加嚴重。閱讀的歷史總是同尋求意義的活動相關聯。而且意義——無論是宗教意義、哲學意義還是科學意義——總是通過提供對真理的洞見來獲得自我實現的。閱讀一旦喪失了其尋求真理的潛能,便會淪為一種平庸的活動。閱讀一旦淪為了工具性的技能,它的作用便會局限于對文本的解讀和對信息的獲取。在“二戰”之后的時代,由技術專家們主導的培養功能性讀寫能力的學校正是以此種方式來理解閱讀的目的,而麥克盧漢所鼓吹的那種脫離內容的閱讀觀也以一種迂回的方式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由技術專家們主導的培養讀寫技能的學校同那些反對人文主義閱讀觀的復古思想結合在一起,再次出現在今天的教育領域中。在學校里,閱讀之戰的爭論雙方都未能認真地看待閱讀的內容及其文化意義。爭論的一方所關心的是如何保證學習的自然性及其同兒童習性之間的關聯,而另一方的目的則是指導學生掌握讀寫的技巧。一旦剝奪了閱讀所具有的審美的和知性的內容,閱讀教育便可能淪為一種技能培訓活動。
回到前古滕堡時代的幻想
那些對印刷文化感到失望的人們相信,數字媒介交流將有助于把讀者從靜止不變的印刷文本的不自然限制之下解放出來,而且他們把數字技術的發展視為一種同寫作的發明一樣意義深遠的變革。一些評論家對于這一信念做出了最為系統化的表達,他們宣稱,古滕堡在1500年左右取得的這項發明開創了一個長達五百年之久的印刷文化時代,而這個時代現在已讓位于另一個采用更為自然的交流形式的新時代。
拉爾斯·奧利·索爾伯格(Lars Ole Sauerberg)發明了“古滕堡間歇期”這個術語,來表示一個從文藝復興晚期直到21世紀初期的歷史時期。在這個間歇期——從1500年直到2000年——書籍的印刷出版和批量生產成為西方文化的同義詞。索爾伯格認為,隨著印刷書籍被一個屬于數字媒介的時代吞沒,借助文本形式進行傳播的知識也發生了改變,進而為那些更能同前現代的口傳文化的價值觀相協調的交流形式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瓦爾特·翁把這一轉變稱為第二種口傳性,意思是書本時代是一個介于此前的口傳傳統和今天出現的第二種口傳形式之間的過渡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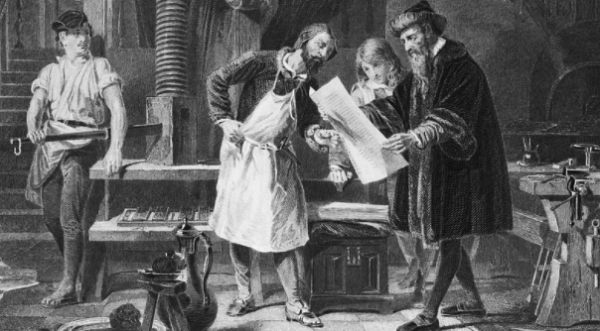
繪畫:古滕堡拿到第一次印刷出的《圣經》場景
這種觀點將麥克盧漢對新技術力量的崇拜同某些人對中世紀傳統的尊崇結合了起來,并由此把古滕堡時代及其代表的現代主義知識傳統視為一個已被超越的階段。“古滕堡間歇期”的主要提出者之一、丹麥媒體理論家托馬斯·佩提特(Thomas Pettitt)不僅認為“我們不是在邁向更高級的未來,而是在邁向更高級的過去”,而且還進一步指出:盡管社會擁有了更為先進的技術,但是“我們正在回歸很久之前的狀況”。按照他的說法,運用新技術的媒體網絡使我們有可能復興一個具有更多的關聯性、群體性和參與性,并具有更少的個人主義的社會。這套理論非常符合19世紀的保守主義者埃德蒙·伯克和費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等人的社會理論。然而,不同于古滕堡間歇期的倡導者,這些19世紀的社會理論家們對于恢復此種社會的可能性持有悲觀主義的態度。
佩提特以一種非常愉快而又神秘的語氣評論道:
按照正確的拼寫方法,“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一詞包含在“中世紀研究”(mediaeval studies)一詞之中。對于那些正統的神秘主義者來說,一件事情的意義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可以激發你的思考:一個中世紀研究者可以成為一名未來主義者,因為古滕堡間歇期的理論告訴我們,未來是屬于中世紀的。
佩提特使用了“恢復”(restoration)一詞來表示這種試圖回歸一個具有更少的理性和更多的自然性的交流形式的主張。另一位熱衷數字媒介的人士特倫特·巴特森(Trent Batson)則提出,古滕堡間歇期已經走向了終結,“人類正開始通過互聯網而再次認識到知識具有共有(communal)的屬性”。在巴特森看來,古滕堡時代是一個畸形的時代——它偏離了此前的那個更為自然的和注重口頭參與性的文化——而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屬于第二種口傳性的時代,該時代將“使我們回歸到人類始終保持的交流規范和交流過程”。
這種企圖回歸中世紀傳統的幻想導致了對讀寫能力及書本的文化權威的貶低,因為它認為,在中世紀的時候,知識的形成和傳播是更有參與性和交流性的,而在屬于古滕堡間歇期的歲月里,知識的形成和傳播則是非自然的。匯集在書本中的客觀知識的權威性——實際上也包括一切形式的知識和文化的權威性——都被斥為某種試圖建立僵化的和非參與性的等級制的企圖,而對于書本的權威性的否定則被說成是一種以解放讀者為目標的反等級制的民主化進程的動力。這種對于書本的內容及其權威性的貶低是通過一種為讀者爭取其應有權力的民粹主義語言表達出來的。
為了避免讓人感到自己擁有任何形式上的文化權威,維納以一種謙虛的口氣指出,“我們再也不能像洞察一切和知道一切的記者那樣,居高臨下地對被動的讀者發話”,相反:
數字技術幾乎在一夜之間便摧毀了等級制,并創造出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在這個更加平等的世界上,讀者可以做出即時的回應,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某些讀者對于某個特定主題的了解要勝過新聞記者,并且也更有能力去揭穿謊言。
然而,維納對讀者的奉承并不意味著讀者受到了真正的重視。她之所以花言巧語地抹殺讀者同作者、記者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為了制造一種文化平等的幻象。當她說讀者不再是“單純的讀者”,而是能夠參與到職業記者和作者的工作之中的新聞制造者與合作者時,她只是在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來貶低閱讀的文化價值,并重申過去那套“被動的閱讀不具有任何內在文化價值”的陳詞濫調。僅僅就讀者可以同網絡記者分享某些奇聞逸事而言,被動的和非參與性的讀者才被她轉變成了主動的和具有文化參與性的公民作者(citizen author)。
按照維納的想象,在長達五百年的印刷文化時代,讀者是一個由沒有思想的個人組成的被動群體,并且只能消極地接受“無所不知的記者”(all-knowing journalists)所提供的權威知識。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幻想。成千上萬的書籍的被焚、國家的新聞審查制度、官僚機構對于閱讀可能產生的政治力量和情感加以限制的企圖等等,都表明了閱讀曾經是并且依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活動。當維納要求讀者變成合作者的時候,她未能認識到閱讀——尤其是嚴肅的閱讀——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文化價值的活動。
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于1967年宣布“作者之死”以來,所謂的作者之死便開始被用來宣揚讀者地位的上升。然而,為何作者之死——無論是存在意義上的死還是數碼意義上的死——具有某種積極的或解放的文化屬性呢?無論人們如何看待作者的權威,作者都要為自己的作品負責——常見的那些匿名的且不斷變換網頁內容的作者除外。讀者能夠對固定在文本中的觀點做出回應并展開爭論。同作者旺盛的創造意志打交道并不總是那么容易和令人愉快,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這種體驗,閱讀才具有了引人入勝的魅力。
那些對作者之死感到高興的人士聲稱,被解構的文本之中并沒有什么不變的意義,因而歡迎各種開放的解釋:“確定文本中的意義屬于讀者的責任和特權。”按照解構主義的觀點,“通過處理手頭的文本(不僅僅是書本),讀者成了意義的權威決定者和真正的作者”。當然在某種意義上,讀者總是作者話語的解釋者,而且閱讀總會涉及對意義的尋求。然而,在閱讀一本書的過程中獲得的意義并不同于一個具有內在穩定性的文本中的意義。在閱讀一本書的過程中,意義是同尋求真理的活動相結合的;在一個具有內在穩定性的文本中,意義則具有片斷性和獨斷性的特征。
試圖解構文本并剝奪書本的權威性,導致了對閱讀的前提和文化內涵的質疑。正如伯克茨所評論的那樣,這種將讀者的想象力從“作者施加的全程引導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的嘗試意味著“必然性將被隨意性取代”。然而,閱讀活動最令人興奮的和最具轉化力的一個方面就是:在讀者進行解釋并獲得意義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學會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并最終做出自己的判斷。正如詩人彌爾頓曾指出的那樣,讀者的力量和真正權威都是通過他們自身的判斷力而獲得的。意義一旦被當成隨意性的東西,便會降低讀者通過閱讀來發展其判斷能力和闡釋能力的可能性,從而在事實上剝奪了讀者的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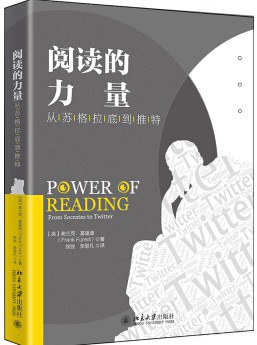
本文摘選自《閱讀的力量》([英]弗蘭克·富里迪/著,徐弢 李思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