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回歸多元時代
原創 維舟 維舟

許多年前,在被北愛爾蘭局勢長期攪擾得不得安寧之后,有人曾說,在英國人的心底里,都巴不得如果能來一次劇烈地球板塊運動,好讓那個討厭的小島一直漂流到大西洋中央,然后永遠地停在那里。
這種心態現在似乎又重現了。這些年來許多人的不滿,從恐怖襲擊到英國脫歐,到美國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潛在的聲音都是:“讓我們自己過好日子吧!遠離那些討厭的鄰居。”
如果說近五百年來的歷史都是將世界日漸編織成一張越來越密切的“人類之網”,其內在的精神是交流與聯結,那么現在許多的不滿則指向這種聯系本身,就像《魔鬼辭典》里所說,電話發明的結果是“你想要把一些討厭鬼拒之千里之外變得再也不可能了”。
因此,那種“別管他們”(停止干涉或拋下同伴的呼吁)和“別管我們”(奪回控制權的愿望)的聲音合流了。現在很多反全球化的聲浪,多是受一種保守主義傾向的沖動驅使,認為應當捍衛那些自己已有的東西——而要守住已有的,那就意味著要筑墻。

借用葉芝當年的詩句,如今的世界看來又走向了“事物分離,中心不存”(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的境地。這是一個離心運動的時代,紛紛攘攘,眼花繚亂,不同的國家和團體都紛紛掙脫原有的軌道,而原本起作用的那個中心也漸露疲態。
雖然多年來的國際政治學說一直在談“多極時代”、“一超多強”,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近兩百年來一直是個單極時代——這一極就是西方。當年的美蘇爭霸,也不過只是這種西方文化的兩個變體之間的競爭。所有其它文明中也許唯一一個得以自我更新的例外,是在近代喊著“脫亞入歐”的日本,也就是說,它是以大幅度改造自我的方式才得以被西方接納為小伙伴。
就此而言,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西方體系的內戰,其中唯一扮演了積極角色的非西方大國,是二戰的戰勝國中國。戰后的反殖民運動,可說是原本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所表達的第一波不滿——但它們即便得到了獨立,卻大多并未得到經濟繁榮和文化復興。
到頭來,這僅僅是一種政治關系上的象征性改變。1950年代英國殖民大臣在和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親王會談時曾說:“貴方不是一個殖民地。”親王答道:“這并不妨礙貴方把我們當作殖民地對待。”
如果以前許多人擔心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不肯放下自己帝國中心的架子,即便在看似共享繁榮的全球化時代,也仍無處不在地操控著這個星球,那么現在的好消息是:他們似乎自己也干膩了。
當然,尤其是美國——和以往的各個帝國不同的是,美國在歷史上每每干得不愉快的時候,就總想著撂挑子不干了。它是有前科的。以前世人擔心美國太積極了(尤其是不必要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那么到了特朗普時代,世人開始擔心的則是美國會太消極了。
正如左翼哲學家齊澤克十多年前就在《伊拉克:借來的壺》中說的,“今天的美國,其問題并不在于它是一個新的全球帝國,而在于它不是:換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國,一面繼續扮演民族-國家的角色,無情地追逐自身利益。”它把那句生態主義箴言“放眼全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顛倒了過來:在全球行動,但只出于美國自身利益的考慮。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大國都是利己主義的,美國也不是沒放棄過領導權(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但那時會有不少國家搶著上,現在則既無人愿意出頭,也沒有什么一統天下的意識形態。事實上,現在各家提出的論述從本質上說都是在地的、防御性的,頗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架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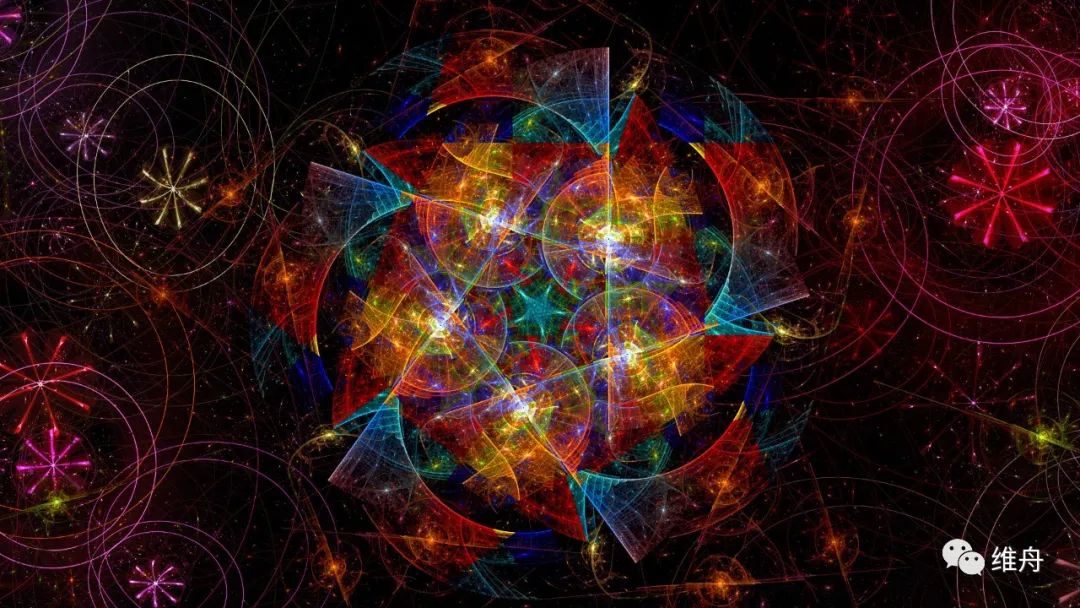
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以來西方對世界局勢的支配,原本就是一種歷史的異常。如今,人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現代化”是一個復數詞,它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和亞形態。
如果說許多期待復興的傳統文明真實的吶喊是“要現代化,不要西化”,那現在看起來也不完全是一個矛盾修辭,它也許在現實中也是可行的。也只有當它們各自都找到了運用現代技術來為自身的復興服務,世界的多元化才能真正成為可能。
在《易經》中有一句看似費解的話:“群龍無首,吉。”這當然不是說一盤散沙是好事,而是說,在諸多事物蓬勃發展、最終方向未明之際,群賢俱興,各盡其能,或許也未必需要“首”的出現。
這些年來,也有國際政治學者提出“G0”時代正在到來,即一個沒有哪個大國領頭的時代,之前的國際秩序或許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現在更可能出現的則是一個群龍無首的網狀結構。在這個新的構造中,要緊的,是成為新的節點。
對原有秩序的不滿,常常會帶來破壞或革新,但像現在僅僅守住已有的東西,那是不足以開辟新時代的。很多人也許都難以適應這樣一個全新的局面,以至于一種悲觀、彷徨、不安的情緒似乎彌漫于每天的新聞中,人們看不懂這個世界是怎么了。實際上,“守住自己已有的東西”是一種喪失安全感之后的防御性反應,但它并不會帶來新東西。
很多國家善于利用既定國際秩序下的規則,例如冷戰時期的日本,但諷刺的是,正是因為它非常適應并滿意于這樣的秩序,結果在冷戰結束之后,日本遲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今后,也許很難再會有什么“穩定的國際政治結構”了,一切就像技術和產品更新一樣,會變成一種多元動態競爭的概念,差距領先者很難再保持幾代人甚至一代人那么長時間的優勢。也許這才將是真正的多元:在一個政治也已碎片化的世界上,在結構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而不必仰賴他者的鼻息。
原標題:《回歸多元時代》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