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仇晟X蘇七七:在回憶與未來的盡頭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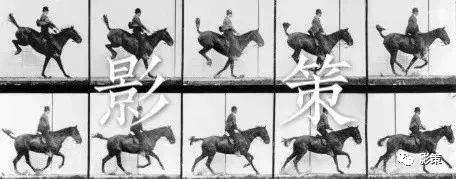
因為計劃寫一本叫《湖中之云》的浙江導演訪談錄,我約了好幾次仇晟導演,他或者在北京,或者在廈門,幾個月之后,我們才終于在杭州城西的一個小咖啡館見了面。這是快過年的時候,他告訴我《郊區之鳥》要在元宵節上院線了,距離2018年這個電影在FIRST獲得最佳影片獎,已經過去了兩年多。能在電影院看這個電影,是件值得珍惜的事。
我們認識還在此之前,因為同在杭州,他在拍《郊區的鳥》時,我還幫他找過小演員(很遺憾沒有選上)。但在一個導演與影評人之間,隔著作品的交流似乎是更真誠的,在寫影評之前,我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拉過片子做過筆記,但不曾問過導演創作意圖之類的問題——在文本兩側,評論者與作者可以有一種互相隔絕的獨立平等。
正如導演所說,這個電影只是需要“帶有一點敏感與天真之心”的觀眾,每個人都可以從在影像與經驗的共振里,找到那種“不曾經歷的熟悉感”,在你觀看電影時,電影也觀看著你的心靈。
因此在這篇訪談里,我們不止于談《郊區的鳥》,還談了一些周邊的事情——一個人是怎樣接近電影并后來與電影“相依為命”的,談了藝術電影在當下的困境與可能的方向。個人的選擇像是偶然,而終在堅持里成為必然,時代的順境逆境,在給出機遇時又給出考驗。這些都在電影之外,又與電影融合在一起。

1
觀影之初與迷影之癮
七七:我們就先從電影啟蒙聊起吧?你的電影啟蒙是在什么時候?
仇晟:最早應該是在初三的時候,那時候網絡上BT剛開始興起。當時看的片子很雜,而且大多數比較俗。我會看一些網絡上打包好的資源,比如“十大禁片”、“最恐怖的電影”之類的。現在想來還有些印象的片子有《低俗小說》,感覺它和其他片子有些不一樣。
我的觀影順序和同時代的人比可能剛好是倒過來的,初中時先通過網絡下載資源的方式看了不少電影。到高中的時候,因為學校不讓用電腦,而且我家離學校比較遠,所以周末的時候經常呆在學校。高中這段時間,我反而回到了用DVD觀影的方式。
七七:學校里可以看電影嗎?
仇晟:我在杭州外國語學校上的高中,對面是浙江工業大學,它邊上有一條小街,被學生們叫做“墮落街”。街上有一個小市場,市場里面有賣盜版DVD的。周末除了呆在學校復習,我還會去買一些盜版DVD回學校。這樣我們兩三個,最多四五個周末留校的同學,就用教室的投影儀看碟。
當時碟商那兒基本什么片子都賣。高中時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導演和片子有希區柯克的《迷魂記》,大衛·林奇的《我心狂野》、《藍絲絨》,還有佐杜洛夫斯基的《鼴鼠》、《圣山》之類的片子。
七七:你讀高中是什么時候呢?
仇晟:06年到08年。
七七:那時候差不多是盜版碟的尾聲了,之后大家相繼轉為線上觀影。
仇晟:對,但那時候碟商的片子種類還是挺全的。然后他會給你推薦一些當下的熱門影片,基本都是商業大片。我當時也沒有系統學習過電影史,基本就靠看碟片封面的感覺來選片。
七七:這挺有意思的,在選片與看片的過程中,你也不需要通過電影雜志或者電影史的推薦,還是能自然而然地選到自己想看的,或者是好的影片。
仇晟:對,這是挺奇妙的,不過當時我們杭外語文組的老師,會在課上給我們放一些片子。比如郭初陽老師給我們放過胡杰的紀錄片《尋找林昭》,課上還放過《美麗人生》、《黑暗中的舞者》。《黑暗中的舞者》這部片子放完后還在同學間引起了不小的爭議,有同學覺得這部片子拍得很怪異,但我看完后覺得很感動。那時候大家看片的狀態也比較輕松自然,基本都坐在桌子上看。大多數同學看完這部片后都離開教室了,只剩我一個人靜靜地躺在桌子上哭。這可能來自于某種表演欲,又來自片子本身。
七七:所以你那時就想去學電影了嗎?
仇晟:初中、高中的這些觀影經歷就像涓涓細流一樣,無形中將我往電影這條路上引。但我清楚記得有一個時刻,我特別想學電影。那是在高考前三個月,我看到格斯·范·桑特執導的《我自己的愛達荷》。看那個片子倒不是被它的故事情節感動,而是看到片子里一個鏡頭:夕陽下,許多魚躍出水面,水波粼粼,倒映著陽光。這個畫面來自男主角的回憶或者幻想。之所以對這個畫面特別有感覺,是因為在我的印象中,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畫面,但當我在電影中第一次看到它時,又莫名覺得熟悉。這讓我感覺很神奇。好的電影畫面可以喚醒或調動你的記憶,讓你覺得在現實生活中是經歷過這一幕的。
這一點給我產生了很大的震撼,讓我萌生了學電影的想法。有這個想法后我也詢問了老師,如果想學拍電影我應該報考什么學校和專業。老師很認真地向我介紹了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這些專業院校需要藝考這件事。因為當時離高考只剩三個月了,時間過于緊張,所以最后還是走了普通高考這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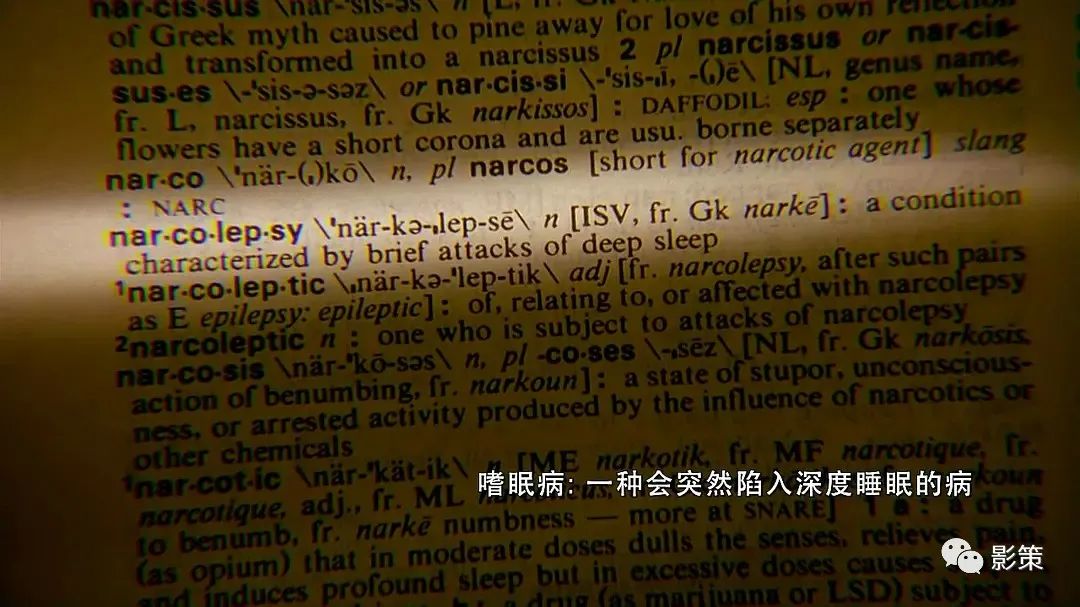
電影《我自己的愛達荷》
七七:你是進入清華大學后就加入了電影社,并且成為了社長嗎?
仇晟:對,一般社長都是大三的同學,但因為我加入電影社后表現得很積極,加上前任社長要準備考研,分散不出太多精力來打理社團的事,所以我在大一下就接替了社長工作。我總共當了一年半社長,后來就讓朋友繼續做了。
七七:之前看你在其他訪談中提到不看電影會焦慮,這個狀態我覺得很有意思,想問下這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呢?
仇晟:可以說是對看電影有點上癮吧,這個狀態也是最近兩三年才有的,讀書時其實還好。
七七:是因為要工作比較忙,看片時間減少才產生這樣的焦慮嗎?
仇晟:可能因為在日常工作時,我的注意力和精力比較容易被分散,但看電影時我的注意力會相對集中,尤其在看好片子時。這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時光,所以每隔一兩天,我都要靜下來看一部片子。
七七:就是說在看電影時那種集中、投入,甚至沉浸的狀態,是很愉悅的。那你對這件事在心理上是有所警惕的,還是任其發展的呢?一個創作者,是不是更應當在創作中獲得高峰體驗?而看電影是以“進入”的方式獲取某種體驗,您對這兩種狀態是如何理解的呢?
仇晟: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有意思,你說的“進入”的狀態,其實和我18年拍完《郊區的鳥》有關。那時候我的主要工作是帶這部片參加電影節,新的片子只有一個概念還沒正式啟動,所以那段時間其實挺空閑的。電影節與電影節之間也就間隔了十幾、二十天,這個時間體量也不太適合有其他安排。所以參加電影節的時候,我會像上班一樣把我的觀影行程排滿。基本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對看電影這件事開始慢慢上癮的。后來這癮就越來越大,2020年疫情期間,我看片挺猛的,基本一天看三到四部。
觀影這個行為對我來說也挺復雜的,一個它能通過讓我變得專注,來帶給我一種愉悅的體驗。另一個也是出于學習的目的。之前我會尊重每一部電影,點開一部就把它看完,但最近我的觀影習慣稍有變化。如果這部電影我覺得不是很感興趣,那就關掉不看了。
對電影創作來說,從手頭出發切實可做的事是寫劇本,但看電影的體驗,其實比寫劇本離真實拍攝層面的創作更近。因為電影的本質是拍攝與觀看,最直接的創作發生在拍攝現場,具體可以落實到你看監視器的狀態。看電影的狀態其實和看監視器的狀態類似,比如你看著看著會覺得這場戲中演員表演、或者攝影感覺不對,那等下喊“卡”后就要對這部分進行調整。雖然我在家看電影的時候沒有喊“卡”這個動作,但這兩者的狀態還有過程其實是有相似性的。反而我會覺得寫劇本這項工作與真實拍攝比顯得比較虛。電影拍攝在前期準備階段,離真正的拍攝還存在一定距離。對我來說,只有舉起攝影機的那刻才算真正進入了創作。
七七:那你在看電影時會有一個傾向性嗎?比如最關注哪個部分?
仇晟:看電影時傾向哪個部分這件事其實挺奇妙的,往往在看越好,或者我越喜歡的電影時,我會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來看,不太能對此做分析性批判,我甚至寫不出什么評論性的文字。但如果一部電影的各要素結合得不是很緊密時,我就會相對客觀地從比如表演、攝影、燈光等各個部分來看。所以我也一直特別期待能看到讓我忘掉分析的片子。
2
在拍電影的人生里
七七:你想拍的電影和喜歡的電影是同類的嗎?
仇晟:隨著閱片量的增加,會有一些比較喜歡的導演,比如大衛·林奇、戈達爾、格斯·范·桑特、洪尚秀、阿彼察邦。你會發現有一些和自己心性比較相像的導演,而你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和這些導演更接近。《郊區的鳥》在創作時,覺得自己有受到洪尚秀的影響,但最后發現在創作的心性上會更接近格斯·范·桑特,而又有某一部分像大衛·林奇。原本受到的來自洪尚秀的影響,可能化為營造表層視聽的手段。因為洪尚秀本質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在他的電影中特別有諷刺性的東西,但我個人其實并沒有那么虛無主義。
七七:因為我們是在電影誕生一百年后拍電影與聊電影,所以在我們面前,其實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宗派。在觀影與創作的過程中,不太可能走在一條前人完全沒有走過的道路上。在創作的路上,總會有意無意地接近與自己心性更為相像的導演。之前我在其他訪談中看到你說想尋找創作上的“宗師”,是有這樣的想法嗎?
仇晟:是的,而且在尋找“宗師”或者標桿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焦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準確的答案。在《郊區的鳥》之后,我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二部長片。最近對我有啟發的一些片子它們還是有一定傾向性的,比如拉皮德導演的《同義詞》、《教師》,還有法國導演卡拉克斯的一些片子。因為我最近在探索人的身體性,試圖通過挖掘人身體中的最基本的潛能,然后拍攝在身體表現上相對激烈的片子,在某種程度上把人拍成某種野獸或機器。
七七:聽上去和《郊區的鳥》的風格大不相同呢。
仇晟:相對來說《郊區的鳥》是比較平和的,因為它的基本動作是游蕩和守望。而《犬父》基本動作可能是拳擊和奔跑,它的速率和姿態可能和《郊區的鳥》不太一樣,所以也想找一些新的靈感與資源來補充自己。
七七:但你不會傾向于建立題材或風格上的相對穩定性嗎?年輕導演比如說畢贛、顧曉剛、忻鈺坤,他們的前兩部作品在主題和風格上都有較為鮮明的延續性。試圖做得更深入。你則沒有這個想法?
仇晟:第一個片子中我想表達的點,有些完成了,有些沒有,但在之后我通過看片或與其他人交流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那我就也不想再拍一個片子去完成之前未完成的部分。因為我的興趣點已經發生了轉移,沒必要在片子中做一個完美的呈現。
七七:理解。我們這個時代做電影的人,總是在看了很多電影后才做電影的,但也有一些人在觀影量并不高的情況下拍攝電影。之前在平遙見到《媽媽和七天的時間》的導演李冬梅,她有一個特別想表達的東西,所以當她看到某部電影時,好像瞬間被喚醒了,覺得電影是她可以用來表達的最好方式,于是就奮不顧身地開始了拍攝。但大多數完成電影教育的人,創作電影好像更多是因為熱愛電影本身,與電影之間有一種相依為命的感覺。所以想請問,你是怎樣的情況?
仇晟:至少現階段我還是很喜歡和電影相依為命的感覺的。假如把電影拍攝的整個過程進行拆解,我會發現自己還是挺喜歡其中大部分階段的。比如前期調研的階段,讓我有更多理由與時間去看電影。而勘景階段,可以讓我和朋友去一些沒去過的地方。現場拍攝也是我十分享受的階段,剪輯則是我認為特別有趣的階段。所以如果把拍攝階段拆解開看,一年四季的工作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挺愉快的。我反倒不是很享受寫劇本的階段,除了最后完稿的時候會有成就感。因為寫作過程中,我時常覺得腦子里想的比手寫的浮現得更快,但劇本又是必備的,因為它是一個讓各類人員與資本得以組織的文本。但拍攝的其他過程我基本都還挺喜歡的,它也可以說成為了我的生活方式。
七七:嗯,電影這個用以表達的工具,以及創作過程中的諸多流程,和你的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仇晟:希望它們可以融合在一起吧,但還是有一些不融合的地方。比如在等待演員、資金方面,還是存在一些焦慮。
七七:就是說在進入香港浸會大學之前,你在電影學習方面主要是靠自我教育。而在進入浸會大學后,開始專業地學習拍電影,而且在香港學習期間還拍了好幾部短片。請問在拍攝短片的過程中,具體學習和掌握了什么呢?
仇晟:總的來說從高中到大學,學習電影主要是靠自我教育。其實我在本科階段也拍過幾個類型傾向比較明顯的短片,比如恐怖片、黑色幽默喜劇。到了香港浸會大學后,我在那里接受的電影教育與訓練,也不能稱之為學院教育,那兒的學習氛圍更像一個社團。研究生階段一個班30多人,每人每學期要拍兩到三部短片,相當于你幾乎都處在和別人不斷合作與磨合的過程中。自己要寫劇本,還要不斷在別人的短片中擔任演員、燈光、場記等工作,這是一個很瘋狂的創作與合作過程。同學間相互合作與磨合的好處在于,大家來自不同的地域與專業,各自對電影有著不同的見解,互相教育與碰撞是一個特別有趣的過程。
所以在自己拍短片時,我可能會在意自己拍的這部片是不是有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有幾個同學的創作,對我來說影響還是比較大的。當你身邊有一群人都在創作時,你就會想找到自己的風格,而創作短片是一個很好的尋找與打磨自己風格的方式。
七七:我看過你的短片《高芙鎮》,當時看完覺得有點像諾蘭的《記憶碎片》。而當我看完《郊區的鳥》后,感受到它和《高芙鎮》之間有一點聯系,就是去用影像回溯記憶。你好像總是能在影像中找到重返過去與進入未知的方式。
仇晟:經你這么一說,我還真是第一次意識到這兩部片子間好像確實存在這樣的關聯。《高芙鎮》和《郊區的鳥》中的兩個小男孩,他們之間還真存在著一些對應性。
七七:在你的作品中,重要的不僅是記憶的具體內容,記憶這件事本身也特別重要,通過影像,從具體的記憶中抽象出記憶本體。從這點出發我有一個問題,電影中的記憶常常會走向觀念和世界觀的闡釋,有一種從具象到抽象的傾向,一種思辨性。你你怎么看待這種傾向?
仇晟:在創作《郊區的鳥》時,一直很想做的事就是在有機體與無機體,或者說在有機體與城市之間找尋一種聯系或者比喻,但這也是劇本創作與拍攝到后半段才形成的想法。最開始想的就是這群小孩記憶中有一個創傷性事件,他們一起去找同學小胖子,但找著找著就迷路了。還有一個是對杭州城來說的創傷性事件,就是地鐵造著造著發生了地面沉降,然后一群工程隊的人去找原因。最開始寫劇本的時候,就想這兩群人會在什么地方相遇?寫著寫著就把他們寫到一起去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群孩子去找小胖子的路其實是被城市建設所切斷了。孩子們尋找小胖子的路被阻斷后,城市的現代化建設仍在進行中,直到地面沉降開始滲水后,某種程度上又有回到了建設前那種城市原始狀態的可能。因為水是流動的,它是一種可以儲存記憶的記憶質。而大樓、隧道這些固態的建筑與之相比可能沒有那么好的儲存性能。因為造地鐵使地面出現沉降,地下水的滲漏在某種程度上好像觸及并帶動了記憶的流動。這是我在創作《郊區的鳥》后期時對故事的理解。
七七:作為一個觀眾,我在電影中看到,一邊是童年的終結,一邊是現實的陷落,童年與成年在電影中呈現的狀態好像是相向而立的。您說由于地面陷落,地下水滲出帶動了記憶的流動,現實時空借水這一記憶介質得到了轉換,當時好像沒有很好地理解這一點。
仇晟:所以我在想電影中隧道的部分,還有水滲漏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拍得更具象一點,比如頭頂有水在嘩嘩地往下流,這樣觀眾是不是能更好理解一些。
七七:可能也不是,地面陷落,滲出的地下水作為記憶介質貫通童年與成年兩個時空的邏輯,觀眾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是感受不到的。可能要等到整個城市陷落,我們才能感受到那種有機體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或者隱喻。這是一個需要很大時空尺度才能完成的體驗,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體驗的。所以從這個層面出發,我覺得《郊區的鳥》很有科幻感。但我還是非常喜歡結尾部分,就算沒有完全理解電影的邏輯,還是能感受到電影著落之處的過去與未來的重疊,它著落在一個電影能給大家帶來的,特別美與放松的地方。
七七:那是如何聯系到李淳與黃璐來出演《郊區的鳥》呢?
仇晟:一開始我也不認識李淳,他是這部片的監制黃茂昌推薦給我的。然后我就把劇本發給了他,約他見面聊,第一次見面我們倆就一見如故,感覺特別合拍。他從小在美國長大,開始學中文也沒兩年,所以我也想利用他對中國不太熟悉的感覺,對一切雖然陌生但充滿好奇的感覺。黃璐是因為之前看過她不少戲,然后就請黃茂昌老師幫忙聯系約了見面。見面聊了之后,也覺得比較合適。確定想找她出演是因為看了她在《云的模樣》中的表演,她在這部片中的表演比較“虛”,不像《盲山》里那么“實”。
七七:《郊區的鳥》的拍攝過程順利嗎?
仇晟:還是比較順利的。有一次差點停,但好在還是繼續拍了。那一次是因為我們在雙浦鎮,轉塘那邊,住的酒店差點被拆遷。
七七:你們是在轉塘那里拍攝的嗎?
仇晟:住宿在那里,拍攝不在。酒店選在雙浦一帶是因為那里是郊區,房價比較便宜。二是因為那里離高速口近,我們上下高速方便。拍攝地點比較分散,但相對來說集中在繞城周圍,幾乎沒有在很市中心的地方取景。除了在環城北路的隧道取了一個李淳坐在車里的景,其他基本都是在城區外圍拍攝的。
七七:拍電影的過程中,有感到特別愉快或困難的地方嗎?
仇晟:十月份拍小孩的戲份時感覺特別愉快,那時候天氣好,而且拍攝特別有序,每天都早睡早起。早上五點起來開始拍攝,一直拍到太陽落山。因為孩子的戲多是日戲,太陽落山也就拍不了了,然后就收工回住地。我們拍攝地周圍有野柚子,口渴的時候就請場務兄弟去打幾個野柚子下來,劇組成員一起分著吃。就像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樣。
壓力一個來源于和成年演員的溝通,因為大多數參演的演員已經出演過好多作品了,每個人拍戲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樣。當我想要一些即興的東西,或是讓他們拋掉一些表演習慣的話,就可能會遇到一些阻礙。最后就是努力去找一個雙方都舒服的點,但這個找尋過程還是比較掙扎的,因為同一畫面里有四五個人,每個人表演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樣,要將他們在表演上統一起來還是比較困難的。其實到最后,也還有沒太弄明白的地方。
七七:這個故事中的成年人事的關系是同事,本身就并不親密,剛開始看的時候,感覺人物之間的隔離感比較強,但一旦接受了這個設定,就覺得這樣帶有隔離與疏離感的人物關系和狀態還挺好的,因為人與人之間就好像處于一個溝通不是很順利,交往也不是很自然、和諧的狀態中。
仇晟:本來想在人物狀態中表現出“隔”與“不隔”,但最后在呈現上好像太“隔”了。原先的設想是人物間有一個表面的親密,但在深層還是有一些隔閡,現在表面的親密可能呈現得不太夠。
七七:對你來說,電影是足夠好的表達媒介嗎?
仇晟:在《郊區的鳥》開拍前,我寫過短篇小說。在網絡上發表,我想多集幾篇出版一個集子。最近也不怎么寫短篇小說了,開始對更接近美術館的裝置藝術感興趣,但還沒怎么實踐。想法不少。有時候覺得還是先把電影拍得再明白一些后,再去嘗試轉型。目前,電影對我來說還不是一個完全的表達媒介,它更多承載的還是我青少年時期對于電影的熱愛,沒法完全表達我的一些想法。


3
藝術電影的受眾與生態
七七:在我看來,《郊區的鳥》不是一部很容易欣賞的電影。不同觀影者可以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但有一定藝術電影的素養,甚至是美學觀念的素養,才能更好進行理解與欣賞。這類具有較高藝術修養的觀眾,往往近乎美術館的觀眾,而不是電影院的觀眾。我想請問你是如何看待當代藝術電影與院線觀影機制之間的關系的?
仇晟:這兩者的關系,我是這樣理解的,雖然這種理解可能來自我的一廂情愿。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觀看《郊區的鳥》這部影片,并不需要觀眾具有某種知識儲備。當時的希望是一個一無所知,但帶有一點敏感與天真之心的觀眾,他能感受到我這部電影想表達的一些東西。其實在一些映后交流的現場,倒是有挺多老年觀眾喜歡這部影片。
在洛迦諾放映時,有一位老太太在放映結束后過來和我說這部片讓她想到了自己小時候,她還說這這部電影應該去洛迦諾當地的大廣場上放映,那是一個能容納近八千人的大廣場,我很感謝她。2019年,這部電影在電影資料館百子灣店參加環保影展。觀眾是招募來的,有很多五十多、七十多的老太太,她們也很喜歡這部電影。雖然可能略過了一些看著沒感覺的段落,但她們看完會說:以前的小孩還能在河里喝水,現在因為河流污染,也沒有人在河里喝水了。還會說這部影片還是挺有價值的,之類的話。
所以我想是不是有的時候,觀眾在觀影前或是觀影時預設的東西太多了,想抓緊電影的每一刻,由此導致觀影的體驗感下降了。看《郊區的鳥》時,也許可以更放松一點。但反過來說,大多數觀眾可能還是更習慣于接受類型片或者通俗電影的敘事。如果缺少了觀感上的刺激,可能一下子不太好進入與接受這樣的影片。
七七:“敏感與天真之心的觀眾”,這既是一個很低的要求,又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啊,它其實是在要求觀眾與電影有某種核心的同質,源于同質的共振。這是最美好的關于電影的相遇了。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不是普遍的。在電影院買票觀影的觀眾,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通觀眾,而他所理解的觀影行為和他最終在銀幕上看到的電影形態間可能存在著差異。
仇晟:這個問題是挺頭疼的,我也想過這個問題,是說就沒有出路了嗎?是沒有這么多觀眾了嗎?還是只有這么多觀眾會去看這部電影?如果還有其他觀眾,那他們又“藏”在哪兒呢?是不是還有辦法能把他們重新請回影院觀影。之前老提及文藝電影的票房天花板,但我覺得這個事奇怪在觀眾的人數不是可以經過培養慢慢提升的嗎?
七七:杭州算是有一批比較成熟的文藝片觀眾的城市,同時還有藝聯、大象點映等組織在做藝術電影的推廣工作。但我覺得如果藝術電影的觀影機制難以形成經濟閉環,那藝術電影就比較難進入再生產。美術館的觀眾雖然很少,但美術館里陳列的作品是按藝術品來定價的。但院線電影是大眾文化商品,它需要靠很多的購買者,以類似集資的方式去幫助它實現經濟閉環。那你會不會覺得藝術電影在面對當下市場時,處于一個比較彷徨的狀態。在第六代導演拍電影時,海外版權還可以覆蓋國內的制作成本,但這個時代都已經過去了。我們所身處的當下,在拍藝術電影這件事上所遇到的困境好像并不比之前小。
仇晟:賈樟柯導演拍片的時代,因為有價格的優勢,他們在國內幾乎不用花太多錢拍,拍完又可以把它的版權拿到國外賣。但現在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國外基金已經停止贊助中國了,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它已經不再被認為是第三世界國家,而且從海外獲得的資助與國內的物價相比,也是杯水車薪。
我覺得國內政府應該增加對電影的投資,世界范圍內很多國家都已經在這么做了。比如歐美設立專門的政府基金來支持電影行業發展。政府基金對藝術電影的支持,基本超過百分之五十。制片公司看這部影片的資金基本到位了,就會投入制作。所以如果沒有政府資金的支持,藝術片其實很難生存,更不用說要形成商業循環了。
七七:現在國內很多藝術電影在走各種創投的渠道,但以一個需要五百萬資金的片子為例,創投很難滿足它的成本需求。
仇晟:在創投上獲一個獎可能也就十萬。
七七:那這些創投活動對國內藝術電影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仇晟:理論上還是幫助大家找到合適的資方吧。
七七:相當于是一個展示的平臺。
仇晟:即使片子在創投上獲獎,但它在商業性上還是比較缺乏的話,可能拖了兩三年也沒能真正啟動拍攝,這樣的情況也挺多的。如果純粹靠商業循環,可能只有少數幾個片子能實現,比如刁亦男或者畢贛的電影,其他電影基本是做不到循環的。
七七:刁亦男的電影有大卡司,而且不斷在其中融入類型元素。你在未來的創作方向上是會像刁亦男那樣,從卡司或者類型上多做嘗試,使片子在外在特征上更接近商業片嗎?
仇晟:這個問題我也在想,把某一類型揉入我的創作中,邀請一些比較有影響力,又愿意出演我的電影的卡司,可能會成為我未來創作中的一個著力點,以此來帶動投資和市場。
七七:那您的第二部長片《犬父》,目前的創作正處于什么階段呢?
仇晟:它帶有一點科幻成分,在制作上它所需要的資金支持要比《郊區的鳥》多,所以之前在融資上一直處于碰壁的狀態。最近在和一些流媒體平臺談。
七七:這個聽起來還挺有意思的。我平時也組織一些放映活動,感覺現階段院線的體制,比如排片,很難和藝術電影相匹配,不僅是能不能發動觀眾的問題。電影放映是一個線下的實體活動,雖然某部影片值得一看,但如果在很遠地方的一個小影院放映,匯集觀眾就很難。但如果這部影片是在線上發行,線下放映作為輔助,這種模式可能對更有希望使藝術電影形成經濟閉環。
仇晟:線上的引流更好一些,它會開辟不同的版塊專門放置某類型的影片。現在的電影院我覺得它們基本已經放棄了實體的引流,前臺其實形同虛設了。之前在美國參加影展時,發行是這樣操作的:他們先挑選邀請一些媒體或報刊的影評人來觀影,《紐約時報》有一個影評人看了我的片子之后特別喜歡,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登載在《紐約時報》的第四版。然后發行商就把這篇評論文章打印出來,放在影院門口供觀眾取閱。這家影院是美國的一家新影院,一共只有兩個放映廳,樓下是酒吧,樓上是餐廳。影院只放藝術電影,但上座率經常能達到50%以上。
七七:藝術電影的觀眾來觀影往往不是為了消遣,而是抱著某種學習的意圖,希望有所收獲或思考。所以我覺得在影院門口放評論性文章的做法非常好,有點類似于當代藝術展的導覽。
仇晟:當下我們確實有很多獲取信息的辦法,但這些信息在流通過程中,其實也在空間與資源上造成了一定的浪費。在中國幾乎沒有人看報紙了,公號推送的文章大家也基本就看頭條,后面幾條很少有人關注,所以電影宣發會演變為一定要去搶公號頭條。但頭條又沒有開設相應的分類,比如此刻我想了解一下電影院最近在上映哪些小眾但有意思的電影,根本不知道該去哪兒看。但在紐約的話,只要拿一份《紐約時報》然后翻到第四版就可以了解到,因為那一版總是做電影導覽與推薦的。所以我不建議將所有的選擇權都交到觀眾手里,我們幫他們做一些有益的選擇不好嗎?但問題是現在沒有人去幫他們做這件事。
現在的營銷已經變成了片方和觀眾之間的搏斗,片方直接對觀眾喊話說:“我們這片好,你來看。”我覺得其實不需要這樣,片方其實只要做好這部片就行了,影院或者媒體覺得這部片好,就向觀眾發出信號邀請他們來影院觀看。但現在片方和觀眾間的關系變得很直接,片方的營銷行為就像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一樣。我覺得這樣的行為很奇怪,為什么我一定要自賣自夸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宣傳或分享性質的媒體就全部失效了。這就變成片方在營銷上自己設了一個賣點,然后將它放在公眾號頭版頭條上招攬觀眾來看。這樣的操作方法對頭部電影來說當然是有利的,但對小電影來說沒有一點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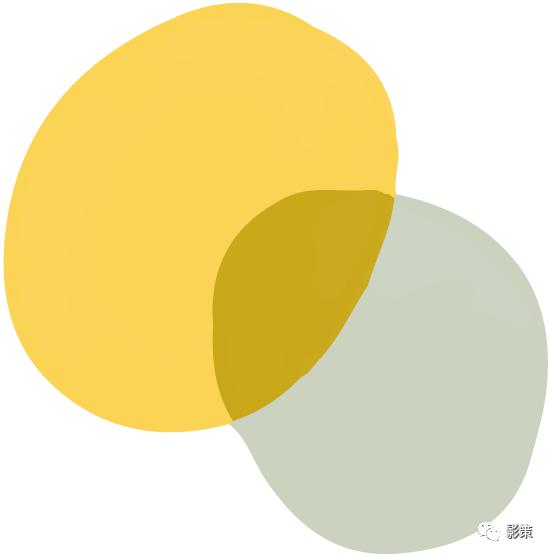
4
新浪潮與審慎未來
七七:那你對我們現在提出“杭州新浪潮”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這個命名其實最早是聽張獻民老師說起的,后來又和深焦的趙晉聊起這件事,覺得它確實是一個可以用來建立描述的命名。
仇晟:我其實還挺開心聽到這個命名的,這個命名其實是帶有期待的,因為目前還沒有真正形成一波強有力的聲音,或者說在創作上有一個明顯的突破,但可能大家,包括我們都需要一點刺激,所以這時候出現這樣一個命名還是挺有趣的。前些年在B站上出現一批潮汕影人拍攝的土味業余電影,時長也就一二十分鐘,我們開玩笑一樣的將這批電影稱為“潮汕新浪潮”,比如《潮汕古惑仔》、《一不小心愛上你》之類的。所以“杭州新浪潮”這個命名我覺得它更多包含的是對這一地區創作者的希望,但至少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足夠的份量。
七七:我覺得目前看到的這幾部長片都很好,但它還是沒能從參與的人數,或者出現的作品數量上達到或掀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運動。比如像法國新浪潮,就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涌現出非常多令人稱奇的作品。但接連不斷地推出作品,在這個時代并不是容易的事。
仇晟:《郊區的鳥》剛拍完,我就有拍《犬父》的想法了。《犬父》這部片主要是講我和我爸之間的關系,我從研究生階段就開始構思了,比《郊區的鳥》要早。但那個時候覺得還沒有想清楚父子間的關系,當《郊區的鳥》拍完后,我覺得自己有力氣去拍這部電影了。當時還是希望可以連續進行創作的,比如《郊區的鳥》拍完過一兩年,我就可以開始拍《犬父》。但實際上沒能接上,13年到17年其實算藝術片的好年景,那時候找錢還比較順利。但到了18、19年,我得更謹慎思考這部片到底應該怎么拍,這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原標題:《訪談 | 仇晟X蘇七七:在回憶與未來的盡頭相遇》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