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國大分裂的前世今生① :極化的起源及其原因
極化(Polarization)作為一個相對寬泛的政治概念,幾乎和美國當代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沾邊,無論是惡性黨爭,國會崩壞,還是民粹主義抬頭/特朗普上臺,乃至民主制度的衰敗/失衡,都能把鍋甩到極化身上。
也正是因此,有關極化的討論和研究在近年來層出不窮,各方大家都試圖從不同角度來探尋極化現象發生的原因經過以及這一現象對當下和未來美國社會政壇的影響。總的來說,學界對當前這一輪極化開啟的誘因和最早出現時間有著比較統一的定論,但對什么因素加劇了極化的程度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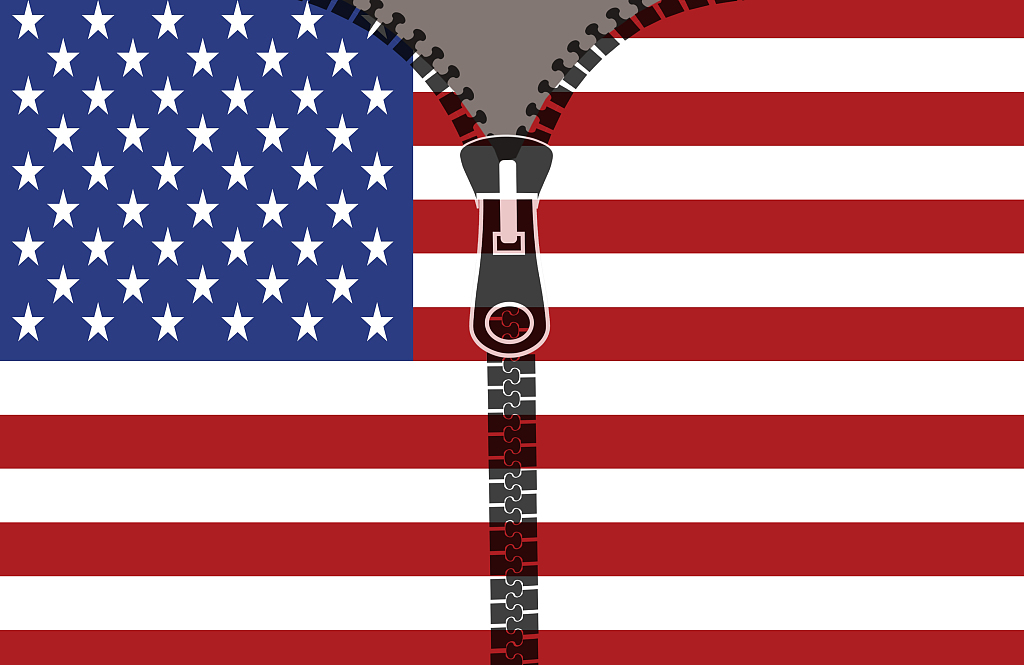
極化的定義及其問題
首先,在講極化現象的起源和發展之前,先要給極化這個概念下個定義。
極化在美國政治的語境中,指的是美國兩黨選民和精英階層在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方面的極端化。在極化的推動下,兩黨均是根據保守和自由主義兩大對立的意識形態立場來引導自身的政治行為。而這一過程自然而然的推動了兩黨選民和精英在重大政策和社會問題的判斷認知上差別越來越大,發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了紅藍兩個美國分裂的局面。
通俗點講,極化,就是民主黨變得更左,而共和黨變得更右。兩黨之間曾經寬闊的中間交際地帶,隨著極化現象的發生變得愈發狹窄,甚至可能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最直觀的數據,就是選民意識形態上的變化。皮尤中心2014年的數據調查顯示,自1994年以來20年的時間中,自認為簡單自由派/保守派的美國人翻了一倍,從94年的10%上升到21%。而兩黨選民的意識形態中間值差異,也有著顯著提升。截止到2014年,92%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要更右,而94%的民主黨人要比共和黨人更左,這一數據在二十年前僅位于60-70%的水平。
而如果稍微了解美國政治的話,都知道90年代的美國遠非什么兩黨認同一致的和諧年代。在1994年金里奇革命掀起的焦土式政治大行其道20余年之后的今天,美國的政治極化比90年代還要嚴重得多,足以說明極化現象在美國社會現在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與此同時,作為政黨精英的兩黨國會議員,也同樣伴隨著選民的極端化而自我調整。兩黨意識形態極化的一個重要外在表現,就是兩黨國會議員開始變得愈發和黨派主流靠攏團結,使得六七十年代規模龐大的兩院中間派勢力在幾十年后幾乎完全銷聲匿跡。
兩黨的黨派團結率分(Partisan Unity Scores)均從70年代的60%左右,上漲到21世紀初的90%水平,而奧巴馬特朗普兩任總統更是進一步加速了這種黨內同化的趨勢。一黨多數必定反對另一黨的多數,于是奧巴馬任內的重大立法成就奧巴馬醫改沒有一票來自于國會共和黨人,特朗普的稅改,也沒有任何民主黨人支持。
雖然單就極化問題本身來說,極化所帶來的影響并不完全是負面的。但由于美國民主制度實行的是福山所稱之為“否決政治”(Vetocracy)的復雜機制,國會兩院實權還同時三權分立,使得政治機制的正常運作需要多個環節的配合工作和廣泛的跨黨派民意支持。
在兩黨選民和精英都因為極化而缺乏共識,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情況下,美國政治幾乎無法以正常的方式運作。隨著而來的政治僵局和政府低效,導致了長期社會性問題頻頻得不到解決,民眾對政府和體制失去信心,進而產生了濃厚的反建制和民粹主義情緒,給特朗普登場搭建了舞臺。
而兩黨意識形態的對立,很快演變成了兩黨選民對彼此的怨恨和敵視,負面式競選成為了政治選舉中主要采取的方式,而黨同伐異為反對而反對,則成了兩黨選民思考問題時所最先思考的因素。在政治極化登峰造極的2020年,美國一切的事務都要通過政黨和意識形態的濾鏡來篩選。事實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凡事先要看立場,站隊要緊。
極化固然不是美國獨有的政治現象,但目前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治極化比美國更嚴重,影響更深遠。即便是呼吁團結的拜登取代推動分裂的特朗普成為了總統,美國政治極化也沒有出現絲毫好轉的跡象。1月6日國會山暴亂的陰影,仍將長期籠罩著美國的未來,畢竟,能發生一次的事情,肯定還能再發生第二次。
當然,美國當前的現狀,肯定不是簡簡單單極化一個問題所造成的。未來怎么樣,現在也說不好,與其鼓吹失敗主義杞人憂天,不如先回顧回顧歷史。
極化的起源
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來看,極化在美國并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現象,建國初期,內戰前美國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兩極化和兩黨尖銳對立。但一般來說,當前所指的政治極化,都是建立于美國內戰重建(Reconstruction)結束,第四政黨體系確立以來的語境之下。所謂有史以來政治最極化,社會最分裂,也是從內戰后開始算起。(畢竟,內戰不就是極化/分裂的衍生物嘛)
具體到現在這一輪的政治極化,普遍的認知是它起源于上個世紀70年代。而政治極化誕生的誘因,是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所引發的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崩塌,進而出現的選民遷徙和政黨力量重組。
過去往往有一個常見卻錯誤的坊間智慧,即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在歷史上經過意識形態的換位,民主黨從保守主義為主導變為了自由派的代言人,而共和黨則從左轉右,完美實現和民主黨的對調。顯然,事實并非如此。兩黨意識形態的變化不是簡單粗暴地交換立場,更多像是剔除了黨內原來勢力龐大的意識形態異端/獨立山頭,最終使得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區分變得無比明確。
歷史上,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意識形態較為松散的大聯盟政黨,其選民組成和政策立場往往和美國的人文歷史和社會經濟發展有關,而不局限于單一的意識形態流派。民主黨在內戰后的早期雖然確實是由南方/保守派波旁民主黨人為核心,但也吸收了中西部帶有左翼經濟民粹色彩的農場主作為補充。十九世紀末勞工運動興起后,民主黨更是積極和工會勢力以及大城市中的政治機器所勾結,意圖擴大自己的選民基本盤,和作為第四政黨體系處于絕對主導地位的共和黨進行抗衡。
等到威爾遜和羅斯福兩代民主黨總統上臺,特別是后者的新政,奠定了自由主義作為民主黨主流的基礎。而羅斯福上臺執政帶來的新政聯盟,囊括了包括南方白人、自由派知識分子、勞工勢力、愛爾蘭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猶太人以及非裔美國人,形成了廣泛群眾基礎。于是,憑借著新政聯盟的力量,民主黨在1930年代之后的數十年中取代了共和黨成為了美國政治中的多數黨和霸者,開啟了美國的第五政黨體系。正是1960年代民權運動引發新政聯盟逐步解體,才有了后來70年代極化現象出現的可能。
而共和黨在歷史上同樣也存在著意識形態迥異的內部派系和山頭。重建結束后,共和黨在美國當時的政治體制下有著絕對性優勢,長期把持總統和國會的控制權(一度30年只有一位民主黨總統)。雖然政黨內部的主要話語權由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建制派把控,共和黨內部的保守派力量一直十分強勢。在鍍金時代美國西部諸州逐漸加入聯邦之后,自由意志主義者/保守主義思想在共和黨內部更是成為了主流的思潮。
不過,由于第四政黨體系下政治影響最為深遠的共和黨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是一個進步主義者,他所代言的共和黨左翼勢力在二十世紀初長期保持著相當可觀的政治力量。羅斯福新政之后,共和黨為了突破新政聯盟的包圍,頻繁需要提名溫和乃至自由派的共和黨人來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抗衡,客觀上給共和黨的中間自由派提供了強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必要。
隨著羅斯福新政的高潮退去,二戰結束之后民主黨自由派的政治優勢出現縮水。政治立場通常較為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為了遏制自由派和美國社會中日益高漲的反種族隔離情緒,主動和保守派共和黨人結成了政治同盟,組成了長期實質性控制國會的“保守派聯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
通過對委員會層面的絕對控制,保守派聯盟有效的阻擊了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當政期間的民權法案。然而,民權運動的興起和美蘇冷戰意識形態交鋒的大背景,讓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成為了美國的負資產,變相促使除南方前邦聯州外的國會議員迫于外界壓力,逐步摒棄了放任南方民主黨人單方面否決民權類法案的做法。最終,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敲響了南方種族隔離時代的“喪鐘”,但與此同時,身為民主黨人卻簽署民權法案的林登·約翰遜也親手開啟了民主黨在“穩固南方”的崩盤。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黨和南方的“脫鉤”,并不是一個迅速發生的過程,而是經歷了漫長的半個多世紀時間才宣告完成。重建結束之后在南方一黨獨大長達百年時間的民主黨畢竟樹大根深,長期執政所帶來的穩固政黨組織框架和選民的投票慣性,在民權法案生效之后的幾十年時間起到了對沖作用。雖然絕大部分南方州在聯邦大選層面不再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1976年的卡特例外),但仍穩定選出民主黨籍的國會議員和地方官員,直到1994年和2010兩次民主黨總統任內的轉型式中期選舉才改變了這一慣性。
但不管怎么說,民主黨逐漸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使得原先穩固的新政基本盤出現了本質性動搖。而隨著大部分保守派南方民主黨議員被共和黨人所取代,原先在民主黨內擁有具足輕重力量的保守一翼基本失去話語權和生存空間,使得民主黨自我凈化掉了意識形態的異端,變為自由派為絕對主導的政黨。
與民主黨變化相應的,便是共和黨在吸收了大量南方選民的情況下,逐漸丟失原有的東北部“氣質”。宗教和社會保守主義兩大因素越來越濃的共和黨,不可避免地疏遠了信奉世俗主義的東北部原共和黨選民,把他們推向了民主黨的陣營。
一來一往,兩黨都刷掉了己方陣營中一度強勢的“異端勢力”,完成了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上的整合。實際上,這一變化讓美國政治從1940-50年代的“四黨共治”(自由派/保守派民主黨人,自由派/保守派共和黨人)真正變成了70年代后的“兩黨對立”,從50年代兩黨缺乏本質性差別,變為70年代后的對比鮮明。
如果沒有南方轉型作為誘因,美國政治恐怕不會出現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人口和經濟占比都不顯著的南方,長期在美國歷史上擁有遠超地域本身硬實力外的政治影響力,是一個有趣且獨特的現象。
推動極化的原因
然而,政黨重組只是政治極化現象出現的導火索而已,真正把極化推向到今天兩黨劍拔弩張,事事針尖對麥芒這樣極端局面的“幕后黑手”,另有他人,也不止一個。
在這方面,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各有自己的側重點。為了講得全面一點,順帶避免爭議,這里就把基本被公認和極化有關的因素全部都講一遍。
首先,推動極化的因素主要有兩大類,一種是政治體制內部的改革和變化,另一種則是社會和選民本身所經歷的變動。兩大類原因之間并不互相排斥,時常相輔相成,齊心合力把極化推向高峰。(而究竟是政治精英還是基層選民要為極化負主要責任的有關討論,很多時候和蛋生雞還是雞生蛋之類的辯論沒啥區別
政治體制內部的變化
1970年代以來政治體制內部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政黨權力弱化,國會議事程序的變革,搖擺選區數量減少,和選舉激烈程度上升等方面。
初選制度的出現,極大的削弱了政黨原先對國會議員和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控制力。雖然初選有利于促進黨內民主,把選擇權力返還給基層選民,但權力弱化的政黨無法積極的排除黨內的極端因素。初選相對較小的選民規模,更是有利于黨內的意識形態積極分子掌握政客的生死權,逼迫國會議員必須盡量嚴格遵循黨的意識形態路線,不然將失去重新獲得提名的機會。
不公平的選區重劃(Gerrymandering)則加劇了初選帶來的問題。伴隨著搖擺選區數量的下滑,讓大部分議員都處于穩固的紅藍席位,真正有意義的選舉只是兩黨內部的初選。而由于兩黨選民愈發對反對黨充滿了抵觸情緒,為了政治生存的政黨精英也必須要相應的調整自己,進一步推動極化。
國會議事程序的變革,同樣也對極化起了極大的推波助瀾效果。從60-70年代開始,民主黨自由派不滿于保守派南方民主黨人長期把持重要委員會,開始積極推動參眾兩院權力結構的調整。尤其是眾議院的“削藩”行為,使得立法權力重新高度集中在議長/領導層身上。
金里奇革命之后,更是讓這種大權獨攬的現象登峰造極,基層國會議員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大大削弱。大部分缺乏個人獨特政治形象的議員,在缺乏立法成效的情況下,只能更多遵循黨的基本路線,避免犯路線錯誤丟掉飯碗。
在此期間,直播國會議事程序的電視頻道C-SPAN開播,雖然有利于透明化民主過程,但各類聽證會卻也不可避免地變為了兩黨議員為博眼球的作秀平臺和黨爭工具,進一步壓縮了兩黨可合作的方式和空間。
最后,國會和總統選舉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兩黨之間合作妥協的意愿。1990年代以來兩黨勢均力敵的政治常態,在美國歷史上其實非常罕見。內戰后的第四第五政黨體系都有明確的多數黨/主導政黨存在(先是共和黨,后是民主黨)。
新政之后長達60多年的時間中,國會長期由民主黨把持,共和黨曾在眾院連續四十年在野。相對低頻率的國會控制權換手,反倒有助于兩黨的合作(因為在野黨看不到翻身的希望)。1994年之后,國會兩院控制權頻繁出現更迭,每兩年都有可能出現新多數黨,這大大降低了雙方妥協的意愿。只需要反對黨團結起來一致反對,讓執政黨一事無成,那么就可以等待政治風向推動自己上臺。
也就是說,選舉競爭的愈發激烈提高了政治極化的收益,進入到新時代后,對立更加符合兩黨的核心利益——成為多數黨,也難怪國會成為了政治極化的最大受害者。
社會和選民的變動
政治極化的另一大類驅動力量,則是美國社會和選民自1970年代以來的變化。
冷戰的結束使得美國兩黨失去了共同的敵人蘇聯。缺乏一個清晰明確的宿敵,讓兩黨失去了一個可以一致對外的理由。選民的代際更迭,特別是大蕭條二戰年代成長起來的“偉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逐步凋零退出核心選民隊伍,被沒有經歷過這些重大社會變故、缺乏集體記憶的戰后嬰兒潮和千禧世代所取代,造成了“這屆選民不行”的本質性問題。
美國社會的種族和宗教多元化,給政治黨爭加入了文化和族群斗爭的新變量。兩黨之間斗爭逐漸由從原先利益分配方面的角力轉向了道德和種族層面的話語權的爭奪。雙方的火藥味是越來越濃,所斗法的領域也越來越多。以至于到了2020年,兩黨選民互相之間的看法,都是極度負面的,甚至可以說是互相仇恨的。
而選民互相之間的敵對情緒,自然會折射到他們選出的國會議員和總統(比如特朗普)身上。負面黨派情緒(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另一直接后果,是美國選民愈發不愿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分割選票(Ticket Splitting),參院和眾院選舉結果與總統大選高度趨同。來自“敵人地盤”議員數量的大幅減少,國會內部和總統都缺乏向另一方讓步妥協的政治意愿和需要。
另一方面,兩黨意識形態主流在70年代確立之后,兩黨選民自主的進行黨派選擇行為(Partisan Sorting),進一步固化了兩黨的政治立場和區域性優勢。70年代后,兩黨內部不完全符合政黨主流標準的少數派,除了轉投對立黨派之外,往往會選擇自我調整,積極向黨的主流靠攏,增強了黨內意見的一致性。
選民自主選擇向黨派靠攏的同時,還會根據政治傾向來選擇居住工作的地方。黨派理念相同的人抱團,自然會加速美國政治地理的紅藍分裂。于是,大部分州都是紅區越來越紅,藍區越來越藍,帶來的后果則是國會兩黨的安全選區/州越來越多,中間溫和派選民的政治影響力隨之下滑。
冗長頻繁的選舉周期和競選成本(金錢/政治現金)的激增,則更是放大了黨內愿意花時間經歷去參與初選/其他選舉活動的政黨活躍分子的能量,讓政黨精英不得不受制于黨內的極端勢力。
最后,信息渠道的多樣化和傳統媒體的衰敗,使得美國民眾逐漸在事實認知和基本價值判斷層面就出現分歧。1960-70年代美國選民主要的信息來源還是傳統的紙媒和ABC、NBC、CBS三大電視臺。在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 的約束下,大部分媒體報道是相對客觀可靠的,起碼民眾對事實還是有著比較共同的認識。
但自從里根政府廢除公平原則之后,隨之出現的24小時新聞周期和主觀新聞臺(CNN, FOX, MSNBC)逐漸讓新聞報道變動主觀起來。這些帶有明確黨派傾向的電視臺,滿足觀眾的同時,加固了公眾的黨派偏好。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的碎片化,再加上社交媒體根據用戶偏好推送新聞的做法,更是把大部分美國民眾圈在了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假新聞和陰謀論大肆橫行,兩黨之間現在連基本的事實判斷都不能達成一致,焉能有不極化的道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嵐目”)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