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留學漂流記,15000人的艱難之旅
原創 AI財經社作者 AI財經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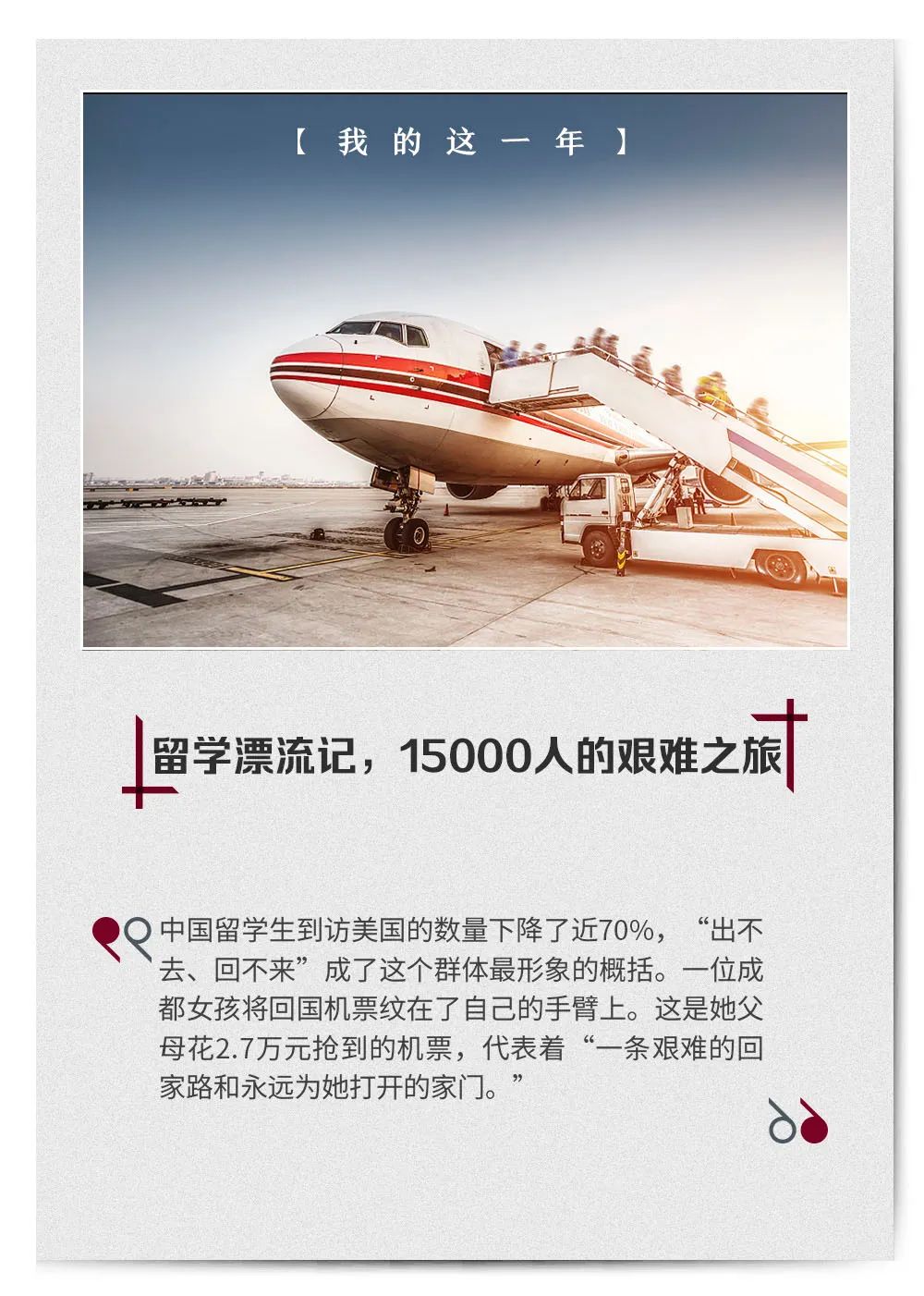
【撰文 | 王雯清】
【編輯 | 周路平】
留學行業的艱難時刻,在2020年被無限放大。
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一位舊金山探店博主的視頻停留在了2019年,一位英國留學生留下了十次歸國機票的購買記錄,超過15000位用戶加入了豆瓣“2020s留學艱難小組”。
疫情徹底打亂了留學生們的節奏,并且在各種意義上重塑了留學生的體驗。有人形容那種綿延的無力感,“你覺得每個月都好長,你覺得總該結束了吧,它卻似乎沒有終點。”
最終的結果是,有些人為了工作留在海外,更多的人回國或者留在國內。而無論留在海外,還是回到國內,背后的留學行業正在經歷著艱難時刻。
堅守還是回國
在美國讀大三的諸葛朗薩起初以為自己是感冒了,乏力、偏頭疼,每天只想睡到自然醒。那段時間,他連續點了三天回鍋肉外賣。他是成都人,想借著家鄉的風味提振一下精神。
到了第三天,諸葛朗薩漸漸發現不對勁了,“越吃這個味道越少”,前兩天尚存的肉味全沒了,只能吃到咸味。
慢慢喪失的嗅覺讓他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2020年11月26日,他在美國確診了新冠,拍了胸片,右肺已經有部分發白,“當時挺絕望,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開完處方藥,回到家,他把門窗以及他接觸的東西都消毒了一遍,通知室友們離他遠點。盡管有些崩潰,但諸葛朗薩的心態很好,“我想什么大風大浪都見過了,不可能因為拿個快遞我就掛了。”居家休息了兩周,他慢慢恢復了健康。
和別的留學生不同,諸葛朗薩很能融入美國社會。他21歲,性格張揚,說話喜歡加上“他媽的”。即便遇到種族歧視,他會舉起花臂,給對方豎個中指,“我覺得我出來就是代表了一個國家,大不了打一架,對不對?”他甚至在中國國慶節當天,組織外國朋友觀看閱兵儀式。
即使在2020年三月份美國疫情開始蔓延的時候,諸葛朗薩也沒有想過要回國。他從小學開始住校,高中畢業后來到美國,一直學電影。諸葛朗薩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放養,媽媽希望他能出去闖一闖。疫情發生后,他媽媽“覺得天又沒塌,該吃吃該喝喝”,沒有想喊他回國的意思。

圖/視覺中國
高中還沒念完,諸葛朗薩就在國內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參與了央視紀錄片的拍攝,在西藏待了一年,進入羌塘拍攝金絲野牦牛。野牦牛在荒無人煙的高原奔騰,他也在自己的人生平原里探索出路。現在,他讀大三,夢想是用美國的手法拍出中國的故事。
但他也很清楚,以他的學歷回國,沒有任何優勢。而他所就讀的美國學校,每年都會有很多制片廠來招畢業生,他至少不用太過于擔心就業。
海外環境和工作機會帶來了很大的吸引力。臨近畢業的衛文新也很喜歡她留學的溫哥華,在這里她不需要坐車去很遠的郊外,就可以見到各種自然景觀。她向往那種一家三口在公園散步、野炊的生活。
薪資高也是這座城市吸引衛文新的地方。溫哥華的最低時薪是65元人民幣。她曾在一家面包店兼職收銀,一天下來,“就可以買一雙球鞋了”。溫哥華的公司對學歷限制也并不嚴格,本科畢業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讀碩士的李一則決定不再返校,她將通過在家上網課的方式讀完研二。
格拉斯哥大學位于蘇格蘭,常年多暴風雨,“我所有帶去的傘都壞了”。秋冬的時候,當地天黑得很早,一個人從學校走回住處,她覺得特別孤單,經常想家。
2020年3月,學校停課,李一在公寓待了一個多月。由于洗手液緊缺、食物斷貨,她經常一天只吃一頓飯。她有自己的臥室,但廚房是公共空間。做飯時進進出出,需要反復消毒。最后她干脆只用電飯煲,只煮速食食品。
恐懼并非僅僅源于疾病本身。剛來英國的時候,李一曾從學校樓梯上摔下來,崴了腳。她擔心會有骨折的可能,但不夠流暢的口語以及未知的看病手續卻讓她更為憂慮。糾結再三,她還是放棄去醫院,托了一個朋友微信會診,所幸并無大礙。類似的處境她不想再經歷第二次。
李一已經對體驗當地文化不再有執念,回國反而是更舒適的狀態:不再焦慮,陪在家人身邊,待在熟悉的語言環境,節省將近10萬元的房租。
紋在身上的機票
但留下或者回國,都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國內的疫情好轉,海外疫情惡化。國內網民開始對這些想要回國的留學生冷嘲熱諷,輿論壓力驟升。
變幻莫測的政治局勢也讓人焦慮。7月6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發布新規,“驅趕”秋季只上網課的留學生。9月9日,美國政府公告已注銷千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一個個出臺的政策就像是一聲聲驚雷,打在這些孤立無援的留學生身上,“教育無國界的理想被打破,就會覺得過去在美國度過的時間好像是一個謊言。”

圖/視覺中國
就讀于舊金山藝術大學的清子,原計劃是畢業工作兩年后再回國。但自從2020年3月9日舊金山封城,學校將課程改為線上網課。母親會每天給她打電話,檢查她是否待在宿舍。有次她出門去韓國超市買東西,突然接到母親的微信視頻。接通以后,母親看她在外面,對她破口大罵。
來自大洋彼岸的牽掛,最終讓她決定提前回來,她買了2020年5月份的機票,踏上回國之路。對于即將畢業的她而言,代價也是沉重的:失去申請美國工作簽證的機會。
湖北女孩衛文新有著同樣的困擾。去年3月份起,她就開始在溫哥華居家隔離。經歷過湖北疫情的母親,對于她的安全狀況非常擔心,無論她怎么報平安,母親還是焦慮,視頻通話的時候常常擦眼淚,“萬一在那邊感染了一個人怎么辦?”
衛文新記起三年前的夏天,母親和繼父去溫哥華看她,她帶著他們去好玩的地方,吃很多奇怪的食物。離別的那天早上,天氣特別好,出了機場就看得到藍天白云。她卻一直在哭,哭了一路。“回到家,一下午都躺在床上,像個死尸一樣,就是被打回了原形的感覺。”
她一下子理解了母親。剛出國的時候,母親送走她后,整個人都呆滯了,看到空著的臥室就會想起她。“生活上什么都沒有變,但是就變成一個人了。”盡管明白分別是成長的必修課,她還是花了一周才整理好情緒。
但隨著航班急劇縮減甚至中斷,回國本身成了異常艱難的旅途。
機票相較于往常漲了5倍,并且一票難求。衛文新不想花這筆錢。父母離異以后,母親帶著她重組家庭,繼父和母親經常因為誰給自己的孩子花了更多錢而產生摩擦。衛文新不想讓母親為難。但母親幾經周折,偷偷給她買好了2020年7月份的機票,“她就說沒事,讓我不用擔心,說她有錢了,可以給我買。”
那時國內已經恢復了正常秩序,“我知道很多人想回去都沒有回去成,當時就非常感動。”衛文新說。
李一前后搶了十次機票,最后買到了4月24日從倫敦起飛的航班。出發的那一天,她穿上雨衣,戴上口罩,不吃不喝飛了十個小時。
去年12月份,衛文新將回國機票紋在了自己的手臂上。她把機票上一些無關緊要的數字,改成家人的生日,對她來說,那張花2.7萬元搶到的機票,代表著“一條艱難的回家路和永遠為她打開的家門。”
困在網上
回國或者留在海外的留學生們發現,麻煩才剛剛開始。他們的課程幾乎都轉到了線上,尤其是對于在國內的留學生,上網課成了一個非常雞肋的選擇。
成星玥是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的大一新生。由于預約不到簽證,她只能在國內上網課,學校減免了住宿費和伙食費,但每學期還是要支付約18萬元的學費。
時差是最先出現的問題。去年8月份,學校開學。凌晨一點,父母準備睡覺,她才在書房上完第一節課。等到她家的狗已經呼呼大睡,她還在撐著疲憊的眼皮聽課。環境漸漸安靜下來,電腦外放音量數值從80降低到50,“孤獨,就好像整個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在上課。”
清晨五點,窗外萬物蘇醒,她鉆進被窩。
學習的體驗感也大打折扣。比如晚上做功課時遇到一些難題,發郵件給教授咨詢,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得到回復。郵箱里塞滿了學校發來的郵件,通知社團招生或者學生會主席競選。其中有一封是宿管發來的,邀請學生周末去摘果子。“如果我在學校的話應該會參加,但我不在那,我就沒怎么關心,看完就刪掉了。”
憧憬中的大學生活,她會交到很多朋友,但實際上她新認識的人十個都不到。“上網課我覺得基本上沒有歸屬感,就像是在交培訓機構的錢。”
為了體驗校園生活,成星玥參與了羅切斯特大學的“中國本地學習”項目,這個項目通過與中國大學合作,保障留學生學業順利進行。成星玥被分配到山東大學,每學期另繳納5200元學費。

圖/視覺中國
在山大,她能享受圖書館、食堂還有雙人間宿舍。一開始,她還是堅持在夜里上網課。往往一覺醒來,食堂已經關門了。到10月份,她實在受不了這種黑白顛倒的生活狀態,“對身體傷害太大”,她開始看錄播,盡量每天十點之前起床。
但線下上課的效果也并未達到成星玥的預期。她在山大選了一門日語課,其他同學都來自一個學院,彼此認識。成星玥明顯感覺自己是個外來者,無法融入,“好像既不屬于山大,又不屬于美國學校,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成星玥是在高二的時候決定出國讀大學。她是江蘇人,高考的壓力很大,她估計以自己的分數考去上海的理想大學很難,就轉去了國際班,全心全意為出國做準備。高二寒假,她要同時備考托福和ACT,還要準備競賽。壓力最大的時候,她會因為填表這樣的小事跟父母吵架,第二天父母帶她去精神病院,檢查出了輕度躁郁癥。
但計劃好的一切努力都被計劃外的疫情擊碎。
成星玥對未來的期待在一點點降低,不得不接受花錢上網課的現實,她沒有參加國內高考,也不可能再被國內的大學錄取。如今,她只希望大學四年能去美國讀一兩個學期,“我也沒有改變疫情的能力。”
蕭條的留學行業
海外疫情的蔓延,讓赴海外留學的學生驟減,也直接讓整個留學行業步入寒冬。
孫洪海是慢慢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他是留學機構青島索引翱申教育公司的運營主管,從業13年。

圖/視覺中國
去年早些時候,同事們還在談論去哪過年,在哪開年會以及做2020年發展計劃。氣氛熱鬧,大家對新的一年信心滿滿。一個月后,他搭乘人數寥寥的地鐵回到位于北京中關村的公司。
辦公室里空無一人,他看到架子上的綠蘿因為長時間無人澆水,幾近枯萎。那是他第一次具體地感受到疫情的破壞力。
熬到了3月份,各種跟留學相關的語言考試取消了。他還抱有期待,“怎么著4月就該好了,你不能不讓人過日子吧。”但事情的走向并未如他所愿。他形容那種綿延的無力感,“你覺得每個月都好長,你覺得總該結束了吧,它卻似乎沒有終點。”
2019年是索引留學的黃金年份。即使在淡季,他每天也能在系統后臺看到三四十的簽約量,如今這個數字變成了個位數。索引留學的營收額下降了20%左右,但退費總金額卻同比增長了8倍。
“目前主旋律確實是全球抗疫,中國又表現得最好。加上機票問題,簽證問題,還有入境隔離的問題,仍然堅定去國外深造并順利出國的人其實連10%都沒有。”孫洪海說。
孫洪海今年34歲,大學畢業后,他就加入了現在的公司。他對公司的歸屬感很強,低迷的行業前景之下,許多同行利用積累下來的人脈,轉去做保險。但孫洪海沒有想過離開,對他來說,這不只是工作,更是他的事業。
他喜歡通過他接觸的學生,去看見個體命運的流轉,接觸更大的世界。比如一個三本學生,在英國讀完一年碩士,通過努力,畢業后在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工作;還有一位澳洲留學生,畢業后移民地廣人稀的澳洲,結婚生子,每天工作8小時,選擇了和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也憂慮自己的命運。“對男人來說,35到40歲是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如果疫情再持續幾年,我可能這一輩子就真的算是浪費掉了。”他預計,要再花兩三年的時間,公司的留學業務才能回到2019年的水平。
他所在的公司只是整個留學行業慘淡的縮影。根據艾媒咨詢的數據,201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已突破70萬。受疫情影響,有接近90%的留學生認為國內更安全,但僅有20.7%的人選擇取消留學計劃,更多是選擇推遲留學計劃或者改變留學國家。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消息。2020年前9個月,持F-1留學生簽證到訪美國的外國人數量比前一年同期驟降61%,其中中國留學生的到訪數量下降了近70%,簽證發放數量驟減了99%。
孫洪海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但仍然對留學行業充滿信心。“無論什么時候,人本身就存在往高處走的欲望。”教育資源差異的客觀存在,使很多家長愿意送孩子出國。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世界也需要國際化人才。
衛文新從溫哥華回國后,經歷了一場手術,父母的婚姻也面臨危機,而以前的鄰居被拉走隔離后就再沒有回來。這一切把她打回了原點,很多努力和記憶被強制清零,但也是疫情讓她收獲了重新出發的勇氣。
她計劃過完春節返回溫哥華。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考量:臨近畢業,有國外工作的經歷利于提高她的就業競爭力,而工作也可以讓她去思考是否繼續讀研深造。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李一、衛文新為化名)
你身邊有出國留學的朋友嗎?他們的近況如何?

我們從《財經天下》周刊出發,以新媒體的形式和節奏、
以傳統媒體求實的精神,致力于傳播真正有價值的報道。
本文系AI財經社原創內容,未經授權,禁止任何轉載
原標題:《留學漂流記,15000人的艱難之旅》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