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舌尖下的中國|在農村,土雞蛋為什么越來越難買到了
“兄弟,你回農村老家,幫忙帶點土雞蛋吧。”
“好的,沒問題,一定幫你帶上一兩百個。”
這樣的對話,大家一定不陌生。鄉村和土雞蛋,一度是聯系最緊密的兩個詞匯。青山綠水,稻田果園,天然成為了土雞蛋、草雞蛋、樹窩蛋等“綠色”、“生態”、“健康”概念雞蛋的出產地。然而,在我的家鄉,情況已在悄然發生變化。
2020年12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出來時,父母想為我的孩子準備點土雞蛋。奈何自己家只剩五六個,便向村里各家各戶去收購。有趣的是,母親從村頭走到村尾,找了二十多戶人家,花了兩個多小時,三塊錢一個,好不容易才湊齊了三十來個。
母親用小籃子帶著“求來”的“百家蛋”回來時,一邊一個個地數著,一邊嘴里念叨著“天嘞,本來想給你買一百個的,結果走遍全村都收不到三十個”。
我問,是什么原因?
母親說:“家家戶戶沒雞了,有雞也生不了幾個蛋,自己吃還不夠,根本不愿賣。”
我又問,為啥不多養一點?
母親說:“養?養一波發一波瘟,發一波瘟,滅絕一波,雞都要絕種了,誰還有蛋賣。”
我接著問,難道把雞關起來,或者放到山谷里,隔絕開也沒用?
母親說:“時風(雞瘟)一來,關到家里幾個月不放出門的雞也會死,放到山谷山窩窩,周邊沒人住的地方的雞也會死。”
母親又補充道,現在村里搞村容村貌建設,怕家里有雞屎,容易臟,不讓馬路兩邊的養,老人家跑山里去養,又走不動,干脆就不養了。
說到這里,我才發現,村里的確看不到什么雞在跑了,早晨的雞鳴聲也稀稀拉拉。開春時,我們家到兩里路之外荒廢的梯田里搭了個小木棚,期待干凈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氣能讓十幾只雞兒免遭瘟疫。

為了躲避雞瘟而藏在山谷里的雞棚。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出于好奇,我又問了豬的情況。
母親說:“豬就更害死人了,像個賊一樣,年年起來發豬瘟,去年就害我們死了四五頭,損失一萬多,氣得我兩三天沒吃飯。現在人人怕養豬,村里一年到頭都沒一頭豬可以殺。”
父親也在旁邊補充道:“好多人都對吃豬肉有點害怕了,干脆多吃點魚,吃點鴨子,有的人肉都吃得少了。”
一開始,和母親的一對一答,我覺得沒什么。因為從小到大,自己親眼見證過村里幾次雞瘟、兔瘟、豬瘟的暴發,家家戶戶扔雞埋豬,河里的動物尸體一層一層地漂著。甚至自己在7歲時也曾因誤食瘟雞肉,而患過急性肝炎,花了將近半年才醫治好。
但細細想想,覺得事情沒有那么簡單。我繼續在村里走了一段,同屠夫、養豬場老板,以及平常喜歡多養些家鴨的人家聊聊,順帶以最近三十年為時間坐標,做了一個比對,這個比對未必完全科學準確,但一些特征卻很明顯:
特征一:雞瘟和豬瘟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高。
經過與多位年長村民的交流發現,從1990年到2015年間,發生雞瘟和豬瘟的次數共有五、六次,平均四、五年一次。而到了2015年之后,僅僅五、六年時間,我自己家就經歷過四次雞瘟、兩次豬瘟:2015年春季雞瘟,2016年春季雞瘟、夏季豬瘟,2018年秋季雞瘟,2019年冬季雞瘟加豬瘟。可以看出,瘟疫有時單獨暴發,有時兩種一起暴發,有時一年發生兩次。這些疫情,深刻地影響著當地人的生活,卻因規模不大,沒有引起關注,只能沉沒在小山村中。
特征二:瘟疫不斷,當地的防治能力和相關機制卻難有提升,農民的損失也沒有降低。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雞瘟和豬瘟發生后,獸醫站有專門人員到家家戶戶去給雞發藥片或為豬打針,也有老農民用一些世代相傳的土方子自救,或多或少總有些效果。所以,瘟疫的速度雖快,殺傷力雖強,但發展到一半時,基本能夠遏制住。
而近幾年,一旦豬瘟或雞瘟發生,三五天之內,從一戶人家到一個村莊,乃至周邊鄉鎮,村民根本無法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只好聽之任之,默默承受集體性的、毀滅性的打擊。村民只能自行處理,很難對發生疫情的雞舍、豬舍做消毒殺菌的工作,而承擔防疫責任的獸醫站也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發布數據顯示,人類現存已知的傳染病中有60%屬于人畜共患疾病,至少有75%的人類新發傳染病源自動物。然而,據媒體報道,鄉村難以留住獸醫,有證的鄉村獸醫更愿意選擇在城市給寵物看病,而不是保障基層的動物疫病防護。
在這種情況下,類似我父母這樣的普通農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一年僅散養家禽家畜上的損失就達幾百至數萬不等。久而久之,對于“種”和“養”這兩大農業支柱之一的“養”,越來越焦慮,越來越失去信心。

2019年豬瘟,我家的幾頭豬全部死后,父親推翻土坯的豬欄,重建了豬圈。
特征三:本地肉的供銷體系在分崩離析。
與此同時,一車車的活禽從養殖場往各個鄉鎮市集上運,或走向餐桌,或成為“種子”被養大。本地從散養農戶家統一收購和定點屠宰的土豬肉,處理好后高價往城市里送,而大型養豬場的飼料豬肉,以更低的價格流入本地市場。
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交易中,本地的自產肉產品占比被不斷稀釋,本地肉食產品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原本相互依存的本地肉供銷體系繼續分崩離析。
農民逐漸從嫌棄工業化養殖系統供應的肉食,到不得不一邊罵“這個飼料養的東西真難吃,騙死人、不健康”,一邊繼續消費和購買,因為,不得不選擇,不得不依賴,不得不放棄抵抗。
所以,當村民到了越來越難獲得土雞蛋、不得不哄搶本地家豬肉的境地時,曾經令父母驕傲的“綠色健康食品”,就變成了“焦慮食品”。
至于豬瘟、雞瘟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賊”,會不會越來越常態化,甚至在本地扎根下來,隨時給農民致命一擊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快要離開村子時,我又發現了另一個現象,村里水塘、稻田、菜地、溝渠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福壽螺和它一坨坨的紅卵,福壽螺被列為首批入侵中國的16種危害最大的外來物種之一,在短短一兩年間像另一種“瘟疫”一樣,入侵了一片好山好水。
看著空空的豬欄,沒有雞屎的村道,以及碩大的福壽螺,不知怎地,我一陣難受,想為家鄉建一道健康飲食和綠色生態的防火墻,但這防火墻該從何建起?誰來主導?誰來共建呢?一時間千頭萬緒,有些喪氣。
(作者李藝泓系中國綠發會良食基金策劃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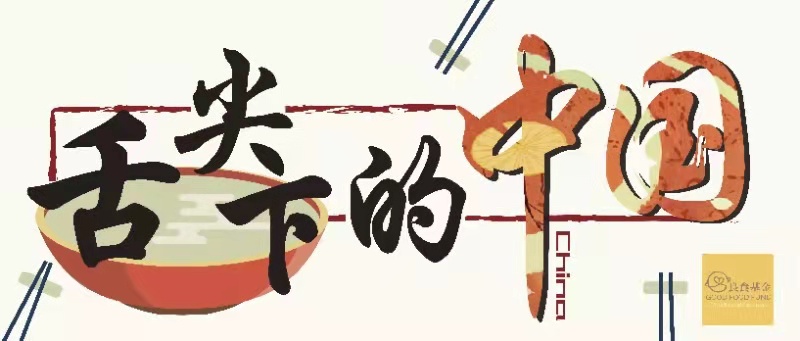
以食物見世界,借舌尖論未來。
"舌尖下的中國"專欄由中國綠發會良食基金策劃及撰寫。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