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未來城市思辨|部落聚會與人工智能寫詩
1950年,計算機科學之父阿蘭·圖靈發表了著名的《計算機器與智能》一文,正式提出了建造智能機器的技術主張。在論述其“模仿游戲”時,有一段設想中的問答尤其引人注意:
提問者:你的十四行詩的第一行為“我可否將汝比作夏日”,是不是同樣可以用“春日”,甚至更好些?
參試者:這樣不合韻律。
提問者:“冬日”怎么樣?這完全合乎韻律。
參試者:是的,但是沒有人愿意被比作冬日。
提問者:你是不是認為匹克威克先生讓你想起圣誕節?
參試者:多少有一點。
提問者:但是圣誕節是一個冬日,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會反對這種比喻的。
參試者:我認為你不夠認真。冬日的意思是冬天里一個典型的日子,而不是一個像圣誕節那樣的特殊的日子。(引自博登編:《人工智能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73-74頁。)
“可否將汝比作夏日”語出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第18首。圖靈設想了這樣一組問答,他認為,如果機器能給出這樣的“參試者”的答案,就可以說它通過了圖靈測試,因為它完全表現得像人一樣。

2020年3月,映在玻璃表面的上海人民廣場。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這個例子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它似乎要求計算機像人一樣懂得詩歌鑒賞,盡管從該篇論文其他部分以及人工智能后續發展看,文學的鑒賞能力都算不上“智能機器”的一個必要條件,起碼不是技術發展的重點。但使用計算機產生文本的歷史,實際幾乎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歷史同樣悠久。

圖靈(右一)與Mark II型計算機的控制臺。 曼徹斯特大學計算機學院/大英圖書館 圖
1951年,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為圖靈器重,加盟后者當時主導的曼徹斯特大學計算機實驗室,負責為世界上第一臺具備存儲程序結構的電子計算機編寫程序。在工作的閑暇,斯特雷奇編寫了最早的文本生成程序之一——“情書”程序。它以這臺計算機的“名義”,向其制造者們打印出“表露衷腸”的短信,就像這樣:
Darling Sweetheart
You are my avid fellow feeling. My affection curiously clings to your passionate wish. My liking yearns for your heart. You are my wistful sympathy: my tender liking.
Yours beautifully
M. U. C.
斯特雷奇所使用的技術,如今看來平平無奇。他預先設定了一些句子“模板”,并編入情書通常會使用的一些名詞和形容詞。計算機運行時隨機選擇詞匯填入模板,由此產生出成百上千種不同組合。但這項工作在當時仍有開創性意義。雖然人們此前就知道,計算機不僅能處理數值運算,而斯特雷奇的工作具體證明了計算機在處理文本時也具有廣闊潛力。
斯特雷奇的程序散失在曼徹斯特大學浩繁的檔案卷帙中,直到2016年才重見天日。但他的方法無疑為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者所廣泛運用,也就是此種采用模板、詞匯等構成的“規則庫系統”進行的研究。事實上,它是早期人工智能技術采用的主流方法。1984年出版的《警察的胡子只造出來了一半》(The Policeman’s Beard is Half Constructed)可謂這種方法的“集大成者”,這本120頁的“詩集”兼“散文集”據稱完全由程序生成。它背后的William Chamberlain等人,自稱編寫了大量的模板和規則,從而讓生成出的文本合乎語法,并具有一定連貫性。但因其從未公開過程序的實現細節,也不清楚書中有多少部分經過額外加工處理,這本書最終也僅被視為一次炒作。
以針砭時弊著稱的科普作家馬丁·加德納,也曾虛構一個類似的故事說,人們對一首由電腦“作”出的長詩追捧有加,最后卻發現,那其實是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一部詩作。(見《矩陣博士的魔法數》,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4頁)
“炒作”或“騙局”恰從另一側面表明,“人工智能寫詩”這件事長久縈繞在大眾心頭。一方面,人們自然要懷疑,計算機所作的“詩”,再多大程度上不同于江湖騙子那般“照貓畫虎”,甚至在批評者看來,這還是一件幾乎涉及藝術“尊嚴”的“大事”;另一方面,對“詩”發起挑戰的人們并不打算止步,其中較為大眾熟知的,當屬清華大學和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團隊,專注于運用當時最新的技術生成古詩和對聯。2011年,杜克大學一名學生編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序,并將其輸出的“詩”投稿到文學雜志,成功“騙過”審稿人而得到發表。2013年以來,隨著計算機并行計算能力的提高和成本下降,“深度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受到熱捧。谷歌團隊在2015年發表的論文中就給出了一種運用這項技術進行作詩的嘗試,他們用RNN技術開發了語言模型,并用它生成英文詩歌。這其中最高調的,當屬2017年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陽光失了玻璃窗》一書。“撰寫”此書的“小冰”一夜間成為了看不見的“網紅”,無數嚴肅的文學批評者爭相辯論這一非人類的“現代詩作者”。
行文至此,有關“人工智能寫詩”的一個問題已十分顯明:指出計算機程序是否具有文學創作、人際交流的能力等,以對其所“作”的“詩”作出評價或解釋,固然是批評者熱衷的一方面;然而,計算機作出的詩,即便能“以假亂真”,與其說是貢獻了詩歌的某種新的形態,不如說其中更值得分析的是催生、孕育、培植了此類“跨界”活動的社會意識。制作一個程序,以產生可以讓人看不出是機械拼湊出的文本,并讓人將它認作一首詩;這種活動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各個階段不斷重現,或許攜帶了更多有關當下時代人文境況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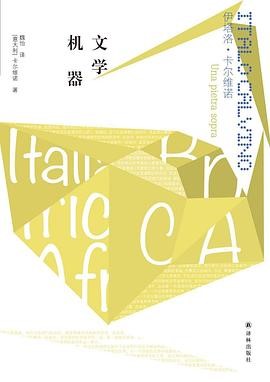
不如將這種視角的轉移,與1967年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一則演講加以比較。卡爾維諾在這則題為《控制論與幽靈》的演講中指出,機器的運作“陌生化”了文學的創作,也使過往種種對文學文本何以產生的原因和動力解釋,遭到新的質疑。
在卡爾維諾看來,不僅程序產生的文本是一種“組合的游戲”,屬于“詩”的范疇,而且程序進行的生成過程具有數學和邏輯的精確和嚴格,這樣嚴密的因果關系正是關于文學創作的種種理論解釋所缺乏的 ——“靈魂、故事,或者社會,或者無意識,如何才能轉化為白紙上一行行黑色的字?即使最杰出的美學理論也緘默不語”。
為此,卡爾維諾提議,不是讓機器成為“作者”,而是將“作者”視為機器——將“作者”這種身份的構成視為多方參與的結果,化約為“寫作(行為)的產品和方式”的載體和執行者。是機器、還是某個人充當這樣的執行者,并不是“文學”的關鍵;這一關鍵在于讀者,因為后者是“一個更有意識的人,他明白作者是一臺機器,明白這臺機器如何運轉。”(《文學機器》,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268-269頁)
恰恰是一名作家提出了一種否定“作者”的文學觀念,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揚棄,亦折射出文學觀念的一種變革或轉折。懸想上古時代,口傳的文學往往不是一人一時之所為,而是歷經數代人層累式的傳承;倘若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所言不謬,注重“作者”身份而不堪忍受其匿名狀態的“文學”乃是17-18世紀西歐的產物,或即便推而廣之到各種帶有署名的文本出現以來,形形色色的“作家文學”也不過是數萬以至數十萬年人類生存歷程中的短暫片段;卡爾維諾所說的“文學機器”,亦即文本(或文學話語)諸多生成原因的組合,的確比有名有姓的“作者”歷史更為悠久。
這樣的文本表達,亦不再與“作者”的“創造力”抑或“主體性”掛鉤,而是在更為根本的層面上,與大眾掛鉤。
卡爾維諾寫道:“想要講述一個神話,僅靠第二天部落聚會時那個講述者的聲音是不夠的,還需要特定的地點和時間,還有秘密的聚會。僅憑詞語是不夠的,還需要一系列多功能符號的共同作用,也就是一種儀式。”(271-272)圍繞口頭文學的程式所進行的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研究已系統揭示了儀式是人類早期文本生成所主要依托的情境,同時也是文本獲得意義的重要契機。
類似地,人們與人工智能的每次交手,都在為“人工智能文學”提供基本的“地點和時間”;正是在它“理論上”仍未能免于機械性的反復運作過程中,獲得人們的認知而被賦予了意義。
從“小冰”的語言風格和吟詠內容中,真正顯露自身的是“文本”中的體裁特征和語言風格,而人們從中辨識出現代詩熟悉而鮮明的特征。要理解這些由程序生成的“詩歌”文本,人們本不必思量“小冰”那樣的人工智能系統是否可以或應被看作現代詩人的合格“模仿者”——它是否具有“主體性”、是否在從事“模仿”,對把握其文本生成過程的意義而言都是無關項。
以此觀之,在“小冰”的“詩作”中,確確實實洋溢著的,是人們對這種體裁特征和語言風格的認可。畢竟,沒經歷過中文現代詩洗禮的人,不認可其文學價值的人,是不可能真誠投入到一項旨在生成現代詩風格文本的技術工作中的;甚至,技術研究者之所以選擇讓他們構建的這一系統“寫詩”,也同樣是因“詩”被認為是“文學”最有典型意義的代表。借用一個技術上的比喻,通過“小冰”系統的不斷“采樣”,人們看到了現代詩的“語言空間”中那些未被觸及的表達,也直觀感知到它具有的局限,呈現出歷史上“現代詩”這一體裁承載的文學觀念和價值譜系,而人工智能“寫詩”,才可能幫助人們探索文學的可能性邊界。

艾達·洛夫萊斯夫人。她在對查爾斯·巴貝奇分析機(Analytical Engine)設計草圖的評注中指出,這臺進行計算的機器還能進行符號操作,從而在音樂編曲等領域發揮作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她是英國詩人拜倫的女兒。科幻小說《差分機》對此有所推演。
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當前面臨諸多挑戰,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學院院長張鈸院士,就對“跟風”式的“人工智能”熱潮提出警告。怎樣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讓它更好地完成某些工作,始終是計算機科學和技術研究者的任務,通常非人文學者所能置喙。
但在被動接受技術的應用之外,人文學科還有一事可為,那就是不斷觀察和體認,既包括那些研究者對“人工智能”這一領域的激情和驅力,也包括社會大眾對人工智能投以的狂熱、盲信或憂懼、懷疑。
從統計上說,人們對未來技術發展的估計,很多時候都是錯誤的;雖然如此,人們還是不斷進行著這樣那樣的估計,用技術發展的未來敘事“預支”出彌補當下之所不足的底氣,這讓人回想起洛夫萊斯夫人評論計算機器時所說的那種“對真理的預期能力”。這樣一種“心理能力”,是否真的是人與非人的根本差異所在,或許難以確認,但可以確認的是想要理解“人工智能”,想要理解并因而獲得安心的意愿。正是由于人們對“文學”何以成為“文學”的原因抱有回答的預期,“人工智能寫詩”才成為我們當下這個時代的一個特殊標志。
(作者朱恬驊供職于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是計算機背景的城市愛好者)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