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幸福的詩學”:在過去與現實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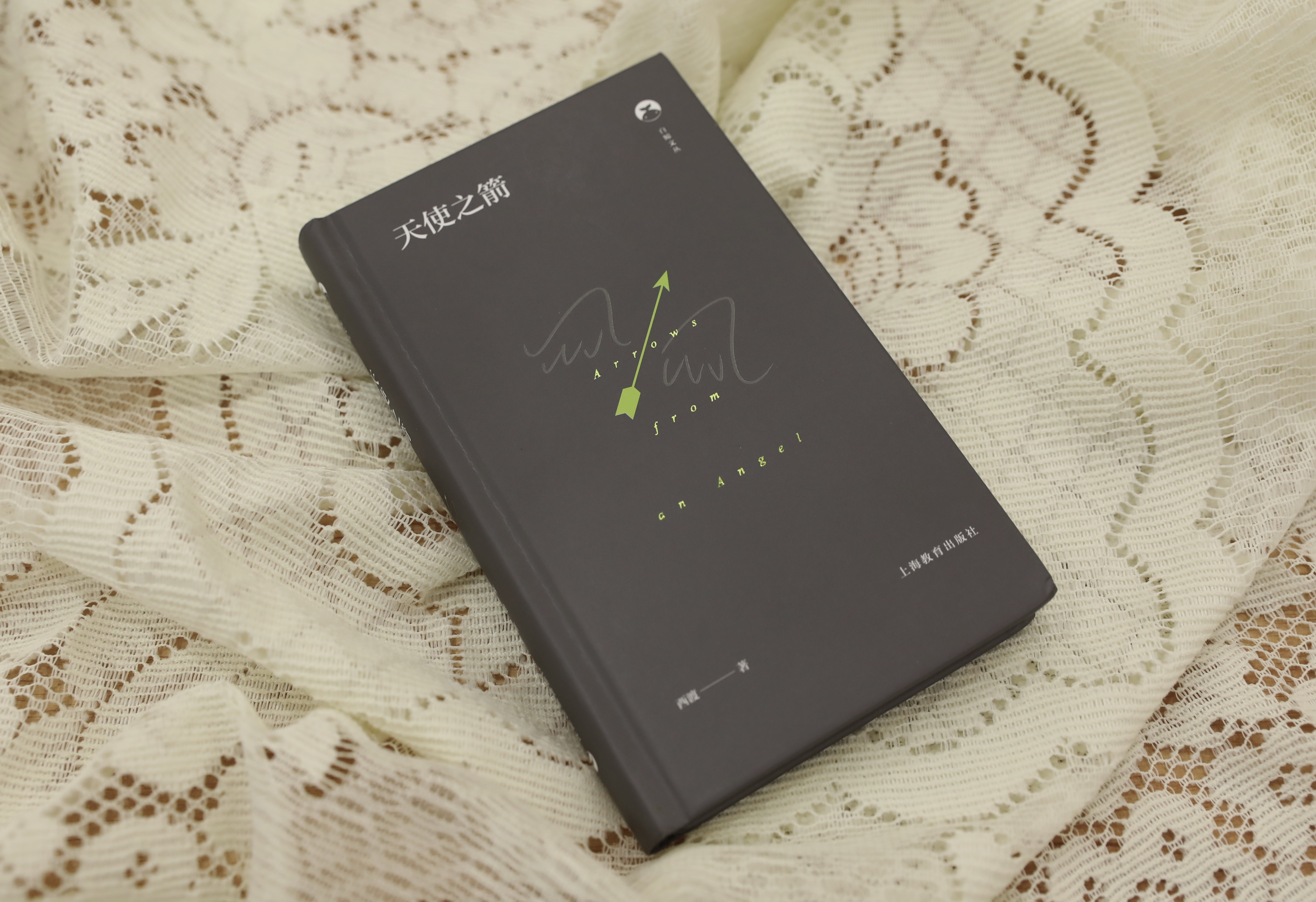
“幸福的詩學”:在過去與現實之間
——西渡詩集《天使之箭》初讀札記
◎王辰龍
上世紀三十年代,借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寫導言的機會,胡適想起了新文學發生期的往事。按照他的說法,當初的文學革命引發最多爭議的文類是詩與戲劇。“這是因為新詩和新劇的形式和內容都需要一種根本的革命。”胡適主張以白話和自由體去置換古詩的文言和格律體,同時也提示出每個歷史階段的“當代文學”與傳統之間可能產生的關聯。百年有余的新詩史上不乏嘗試借用傳統的作者,從較為寬泛的意義而論,他們傾注心力的方向主要有兩個方面:參照古詩的聲音體系和形式感,為新詩設計格律化的方案;抑或在詩藝、文學精神等具體層面上對古詩有所借鑒。暫且不論嘗試者的成敗,他們提出的理論、展開的實踐卻凸顯出另一些值得反復追問的話題:當代詩人是否必須在作品中對傳統進行回應?強調傳統在文學書寫代際鏈條中的延續、變形或轉化,其現實針對性究竟何在?如何有效地回應上述話題,新近問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渡詩集《天使之箭》提供了一些可供討論的例證。
《天使之箭》涵蓋了西渡2010年至2018年間的創作,包括短詩(第一輯)、組詩(第二輯)、截句(第三輯)等不同體裁。其中,第二輯的《故園,心史》《返魂香》等組詩、第三輯的截句與傳統展開了對話。
先談談第三輯中的短章。這些沒有題目、只有編號(從“0”到“101”)的詩作,在文本建制上最多四行,最少則只有一行。詩后附有西渡寫作的《附錄:截句的可能》,追溯了創作的動機——緣自一個夭折的短詩(被策劃者命名為“截句”)選集出版計劃,同時也描述了新詩史上的短詩現象。西渡寫道:“短詩的體制對于詩人的誘惑始終存在——如何在盡量少的篇幅內達成詩歌的震驚效果,面對這種挑戰,多數詩人在一生的某個階段都會有所嘗試。事實上,類似的短詩寫作在當代詩歌中一直沒有斷過。北島的《太陽城札記》是一個起點,顧城寫過《一代人》,海子、駱一禾名之為漢俳的也是。”反觀古詩,在極其簡省的篇幅中精確地做到狀物、傳情與表意,且常有出人意表的奇思,這本就是其長處。在西渡看來,短詩的可能性還遠未窮盡。他不以古今截然對立有別的眼光看待新詩與傳統的關系,他選進詩集的短詩(“截句”)也有著絕句般的勢能:這并不是說“截句”在寫法或情調上充滿舊日的美感,而是指它們能夠以極快的語言速率切入日常生活的某個場景或是生命體驗的某種時刻。具體而言,西渡的“截句”有三個特點:一是精確,在幾個詞句的連綴中便能把境況勾勒清楚;二是主題集約化,沒有在瘦小的文本里做主題的填鴨;三是恰到好處的意義呈現,能貼切讀解出人事風物的意味。
西渡寫作“截句”時不拘一格。比如,他會寫清晨時的氣氛,把對聲音的體驗轉化為視覺上的形象(4:鳥鳴如花/開在早晨的樹上),也會由眾生的形色體悟到命運的流轉(17:農家的少女舉著一樹桃花/走在田間的時候是美的/當一個農人舉著一樹桃花/回家的時候,是悲哀的),還會慨嘆生命不可逆轉的消逝(8:姐姐們都老了/我獨自返回/空無一人的故鄉)。可以說,“截句”與傳統的對話在于寫法背后一種詩歌思維方式的相通。與之相較,第二輯的《故園,心史》《返魂香》則更為打眼地顯示著與傳統的聯系。在詩集“自序”的最后,西渡就這兩組詩發表了一番“傳統觀”。他認為,傳統與歷史并非全然于今有別,它們是鮮活的現實:這不僅是指古詩作者身處的世界與當下的情境或有雷同,更意味著偉大作者應對人事世情時的詩學方案蘊含了有待重現的當代意義。
可以說,《故園,心史》是西渡上述“傳統觀”最為集中的一次呈示。這部由六首詩作構成的組詩,除最后一首《高啟》外,前五首(《陶淵明》《謝靈運》《杜甫》《李商隱》與《蘇軾》)都以“我”作為抒情主體,這些或可命名為“詩人傳”的作品用獨白口吻重現了偉大詩人(同時也是古詩傳統的重要構建者)生涯中的關鍵階段,期間不時穿插著他們作品中為人所知的主題和標志物。比如,《陶淵明》有辭官歸家、躬耕、酒與自然,《杜甫》少不了國破、逃亡與貧病,在《蘇軾》中詩人則寫到梅花、竹林、茶、父親、兄弟與流放。西渡充分調用了詩人們的“本事”,著重敘述“本事”中的困境時刻和艱難情形,向讀者暗示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我”的困境,其成因與表現具體是什么?“我”在面對艱難的狀況時究竟應該作何判斷,又該怎樣抉擇?當人性在某些特殊乃至極端的境遇下顯示其存在,結果往往不可預測,是朝向惡,還是秉持善,或是長久地搖擺于兩難之間?在上述拷問人性的“詩人傳”中,西渡采取舒緩的、充滿耐性的敘述口吻,用豐沛的細節對詩人們的生活境遇做具體的重現。比如,對陶淵明來說,現實是“人應該回到家里,和植物/一起生長,讓雞、狗和牛跟隨我們。/院子里該有一口井,那是人伸向/大地的根;炊煙升到空中,那是/房屋的翅膀””。隨著境遇慢慢清晰,詩人們對何為良好生活的設想、實踐,也因針對性明確而變得雄辯。
所謂針對性明確,是指詩中第一人稱的視角使“我”內心世界的每一次波動和每一回篤定都關聯著具體的現實,對愛和美的堅守,對良善的向往,也都并非空談或玄思。換言之,在西渡講述的詩人往事里,文所載的道,詩所言的志,無一不是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實踐。在詩集自序中,西渡予以的命名是“幸福的詩學”:“詩是對生活的渴望,這種渴望的力量是贊頌的力量。生活所賴于建立的東西才是生活的真實。詛咒不能建立生活,唯有贊頌建立生活。”
《故園,心史》中的《杜甫》一詩正是對“幸福的詩學”的實踐。這首作品在結構上有著設問句式的設計:在文本的開端,“我”追問著“光”是什么;全詩進入尾聲時,“我”找到的答案是“光”是“詩歌”。換言之,整首詩的推進便是答案浮現出來的過程。杜甫的詩歌記錄著“走過的每一個地方”與“那些相互惦念的人”,當他把“春天來了,草木/浴血生長,杜鵑啼血,而農人們/仍在耕作”寫進詩中,便使“偉大的生存意志”有了永恒的文學紀念碑。對西渡來說,傳統是座“故園”,重訪它的初衷和目標并非獵奇、考證或在模仿、借鑒中制造幾首可供賞玩的詩作;傳統最終具化為偉大詩人的“心史”,貫穿其中的則是愛這個世界的能力和責任。西渡在重審傳統的過程中驗證著“幸福的詩學”的可行性,他先描述現實晦暗一面如何成為詩人的日常,繼而揭示出傳統的塑造者如何避免被黑暗、仇恨和暴力同化。他的驗證足夠有理有據,組詩本身也有了詩學反思的品格和深度。
事實上,為偉大詩人作傳與寫作悼亡詩都顯示出西渡書寫“過去”的能力。僅就與過去的詩學對話而言,古詩無疑是一個悠遠的大傳統,而新詩或也在百年演變中形成了些許親切的小傳統。當下的詩人們如何理解胡適時代的白話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形成獨立詩歌聲音的西渡,有時會被寬泛地歸入“知識分子寫作”群落。觀察所謂“知識分子寫作”關涉的觀念、實踐在《天使之箭》中有著怎樣的延展,或許能從中發見“九十年代詩歌”及其涵蓋的詩學意識、詩學方案在新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形和轉換。當然,這已不是本文所能夠承載的話題。
(作者系文學博士,任教于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西渡,詩人、詩歌批評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縣。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并開始寫詩。1990年代以后兼事詩歌批評。著有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草之家》《連心鎖》《鳥語林》《西渡詩選》《天使之箭》,詩論集《守望與傾聽》《靈魂的未來》《讀詩記》,詩歌批評專著《壯烈風景——駱一禾論、駱一禾海子比較論》。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