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游戲中的死亡意味著什么?——再訪“游戲現實主義”問題
“游戲現實主義”論爭(一)——大塚英志的《故事的體操》與《角色小說的制作法》
所謂“游戲現實主義”的論爭,即是大塚英志(1958-)與東浩紀(1971-)這兩位批評家在 2000 年代圍繞文學里的“電視游戲氣”(テレヒ?ケ?ーム っほ?さ)與“游戲一樣的小說”的對錯所展開的一場基于文學評論的論爭。 后者在《游戲現實主義的誕生》(『ケ?ーム的リアリス?ムの誕生』)里對前者在《故事的體操》(『物語の體操』)以及《角色小說的制作法》(『キ ャラクター小説の作り方』)里提出的主張作出了反論,由是展開了一場論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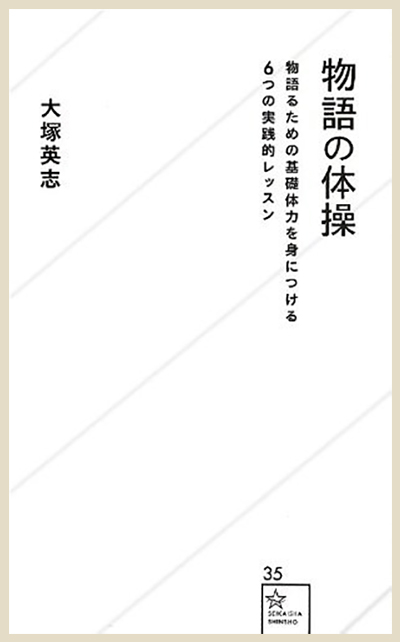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議論雙方在論爭中大量使用了模糊、混亂的術語, 我們很難認為這是一場針鋒相對的、富有建設性的論爭(至少從現時點往回看是這樣的)。因此,本文不會對這場爭論作出總體性的評價,事實上這也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情,更何況要與精通漫畫、動漫、角色小說等現代日本亞文化的批評家們同場競技,這也非是筆者的能力所及,以及本文的主題所能回應的。
然而依據這場論爭——特別是通過東浩紀對大塚英志提出的反論——對故事與世界觀的分離、玩家與角色的乖離(二元性)、元故事性、重層化的死亡表達等這些小說、漫畫、動漫里缺乏的,卻由游戲這樣的文本類型所獨有的經驗進行分析/記述,可以豐富我們的視角,這對于日本的亞文化及其批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此筆者認為,在現在這個時點重新梳理這場論爭里被稱作“游戲現實主義”的術語——它究竟是什么,這對于游戲研究而言意義重大。
1、“電視游戲的創造性”
首先討論的文本是大塚英志的《故事的體操》(2000年)。大塚在該書中使用了“電視游戲的創造性”這一術語,以之批判在特定的文學作品(小說)里所出現的類似傾向,此外他還提出了“動漫現實主義”(アニメ·まんか?的リアリス?ム)這一在此后產生了巨大影響力的獨特概念。
大塚英志就村上龍(1952-)的小說《五分后的世界》(1994)作出了如下敘述:
于我而言,運用村上龍式的手法創作小說,這種奇怪說法的真正意思是創作像電視游戲一樣的小說。而且我認為他至少使用了與迄今為止的“文學”截然不同的偏向于游戲與漫畫的技術論才創作出了他自己的“文學”。 (大塚 2000=2003, 122)
大塚認為這類小說的特征是“故事”與“世界觀”的分離。這里所謂的“世界觀”是存在于“表面的故事背后”的“作為舞臺的世界”。將“架空的世界”與“講故事(storytelling)分離,對其進行個別且縝密的設計,這樣的想法” 雖然在“一般的小說家”與“文學”中比較罕見,但在“科幻小說家與奇幻小說家”那里卻是很普遍的。于是可以說它是“電視游戲的”。要問為何:
用這樣的比喻可能比較容易理解吧。玩家每次游玩都會輸入主人公的名字。這個被賦予任意名字的角色在程序化的游戲世界中代替玩家完成任務、打倒敵人。玩一輪游戲就相當于看了村上龍小說里的一集故事。(大塚 2000=2003, 132)
“每一集故事”都被當成獨立的事物進行“世界觀”設計,“任意的‘故事’在這個預設的‘世界觀’里穿行”,大塚將這樣的事物稱為“電視游戲的創造性”。而且他認為這樣的“世界觀”設計在日本的亞文化里始于《機動戰士高達》(『機動戦士カ?ンタ?ム』),其第一部電視動畫在1979~1980年播出)。
一旦設計好“世界觀”,后面就像玩游戲一般,無論在這個“世界觀”的基礎上玩多少輪游戲都可以(即使并非真的如此簡單),這個系列因此連續不斷地延續下來。盡管《高達》的主人公不停變化,卻依然持續了 20年以上,就是因為有這個“世界觀”的存在。(大塚 2000=2003, 134)
大塚之所以對這個“電視游戲的創造性”予以關注,無非是因為它成為了今日同人志文化的原動力,即成為了所謂的“二次創作”的原理。
比如玩這個游戲時,“世界觀”成為了程序化的游戲內世界的全部。玩家在程序化的“世界”里,按照這個“世界”的規則自由地行動=可以游玩。如此比喻也就很容易厘清剛才所說的“二次創作”問題了。總之,“二次創作”就是與玩一輪游戲完全等同的行為。(......)我是基于上述理由才認為“二次創作”與著作權法上的“二手著作物”在本質上是具有不同性質的。(大塚 2000=2003, 133)
但無論怎么看,大塚對“電視游戲的創造性”的評價——盡管它并非非黑即白這樣的簡單論述——是否定的。他將《五分后的世界》里“故事” 與“世界觀”的分離稱之為“可說是文學的卡拉OK化”,“與我等在這里對‘文學’進行簡單的懷疑相比,它是從根源上使文學的特權性遭到解構的事物(大塚 2000=2003, 132)。

他一度主張“電視游戲的創造性”并非特別新鮮的事物,例如我們也可從江戶時代的歌舞伎那樣典型的“日本大眾文化的歷史”里發現它的影子,不過他最終還是回到了歌舞伎的“二次創作”與今日的同人志具有決定性的不同這樣的結論中。
在歌舞伎的世界里,與“世界觀”相當的事物可以稱之為“世界”,而與玩一輪游戲 =故事相當的部分可以稱之為“趣向”。(......)例如“太平記”或者“小栗照手”這樣的“世界”是由歌舞伎的戲曲家與觀眾們共享后生成的,在這個“世界”中,任何“趣向”=可進行“二次創作”的一集故事都源自戲曲家的創意。可以說,觀眾也能在“趣向”的層次對作者的創意投以評價的視線。但是,歌舞伎里“世界”與“趣向”的關系,跟今日同人志的“二次創作”的決定性不同在于,它不只是由“傳播者”即由制作歌舞伎的戲曲家創作的,也是由它的“接受者”即作為愛好者的同人志作家創作的。(大塚 2000=2003, 134-137)
從至此的議論大致可以推斷出,大塚對“電視游戲的創造性”的批判性態度與他自身對“文學”(或者說“純文學”)這樣的文本類型——也可說是愛恨參半——的偏袒密不可分。大塚在《故事的體操》里以1999年獲得芥川龍之介獎的平野啟一郎(1975-)的小說《日蝕》(1998)的解釋與評價為中心,對東浩紀進行了點名批判。不過,欲就該作品對二人見解與立場的差異作出清楚的梳理——至少在本文中——這仍顯困難。東浩紀是在“表層上”對這部作品的“亞文化的想象力”進行解讀/批判的,而大塚則是在“故事構造”的層次做的解讀/批判,即使梳理本身非常簡單, 但如僅根據大塚自身的論述來下判斷,就欠缺了中立性與客觀性。本文不會從此處介入討論。
大塚采納了同樣著眼于《日蝕》的“故事構造”的萬葉學者中西進(1929-)的批判。中西指出,這部小說給讀者設置了“略顯猥雜的流程”,并“驚訝于如此構思的持續力”——明明早就可以到達視線范圍內的目的地了, 卻還讓讀者不停地繞遠路。大塚對此說道,讀者“很容易進入”《日蝕》, 無非是因為讀者掌握了“這類慢吞吞”的“既視感”,而這個“既視感” 的原形正是“電視游戲”。
吊胃口也沒什么意義了,“既視感”的原形已被清楚地描繪出來,不管如何考慮,這都是在電視游戲上玩RPG游戲時的感受。總之,盡管已大致了解了探索對象,但是在主角到達目的地之前,還是要繞各種各樣的遠路,不斷遭遇許多莫名其妙的人,在進入村莊之后,又必須走遍村莊的每個角落。因此,好不容易以為可與目標人物碰面了,但在此之前仍要忍受森林與洞穴的折磨。中西進緊接著在剛才引用的部分里將之形容為“延遲”的想象力,但我以為它的原形不就是電視游戲一樣的東西嗎?(大塚2000=2003, 153)
大塚基本上以中西的解讀為線索,主張“《日蝕》的故事結構就是RPG 式的,總之是源于電視游戲”(大塚 2000=2003, 154)。他批判東浩紀的著力點在于,他認為東浩紀不過是發現了《日蝕》與亞文化(漫畫、 奇幻小說等)二者在“素材與所使用的術語等表面上的一致”,卻忽略了更關鍵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也揶揄中西進沒能洞悉平野“想象力”的原形“純粹是電視游戲一樣的”事物,中西還是在以往的“文學”觀結構內進行“評價”。大塚的判斷是,《日蝕》——與東浩紀及中西進的主張都不同——是一部站在“文學”一側“收復”“亞文化的”主題與想象力的作品。

在此意義上,《日蝕》是一部學術含量極高的小說,即使是引人矚目的《新世紀福音戰士》(『新世紀エウ?ァンケ?リオン』)式素材的煉金術與基督教神學,它們本來以“知識”的立場出現,最終卻都淪為了亞文化的消費品,換言之,如果把《日蝕》視為重新收復“文學”的作品,我認為它是一部只能生自己悶氣的作品。(大塚 2000=2003, 150-151)
大塚在此明確了對待“文學”的立場。平野啟一郎這樣的小說家,其想象力在“時代氛圍”里“毫無爭議的成立”,他與他的作品沒有絲毫的“價值倒退”。然而問題在于,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之下,批評(家)像是從“文學”與“游戲”的混合物里一齊推出的。
如果不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好好考慮游戲體驗復興“文學”與文壇 感覺的意義,我認為東浩紀還會再次胡鬧,果然還是應該做些什么吧。(大塚 2000=2003, 153)
后面(本章第三節)將在《角色小說的制作法》里繼續考察大塚對“文學”(或者說“純文學”)的講究以及他對越界的“游戲一樣的小說”的批判。
2、“動漫現實主義”
《故事的體操》是引入了大塚獨特的“動漫現實主義”概念的重要著作。東浩紀后來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游戲現實主義”這一術語。
大塚指出,戰后日本的漫畫與動畫孕育出了“與近代小說的現實主義完全不同的現實主義原理”(大塚 2000=2003, 211)。“私小說”里極端的“近代小說的現實主義”指向的是——經常與作家自身重合——從作為主人公的“我”的視角來“寫生”“現實”這樣的“自然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なリアリス?ム)。大塚就出道以后的新井素子(1960-)在訪談里提到的“想寫《魯邦三世》(『ルハ?ン三世』)一樣的小說”的發言作出了如下言論:
總之,她不是對“現實”而是對“動畫”這樣的虛構進行“寫生”的作家。換而言之,新井素子可說是最早運用非“現實”的,即運用“動畫”的自然主義手法的小說家。在那一瞬間,與日本近代小說傳統全然不同的小說問世了。(......)戰后漫畫史、動畫史是非現實主義的故事表達。“寫生”這樣的漫畫與動畫,意味著仍然是在創作非現實主義的小說。(......)當新井素子爽朗地說出“《魯班三世》這樣的小說”的瞬間,這個國家的小說中的動漫性,即與自然主義傳統迥異的現實主義就被帶入了小說之中。 (大塚 2000=2003, 209-210)
這就是大塚所說的“動漫現實主義”。“非現實主義”可以就這樣偷換成“現實主義”嗎?先就此打住這樣的疑問吧。此外我們也繼續保留“現實主義”的定義,承認它的字面意思。采用“動漫現實主義”的代表性文本即是“角色小說”。
用“角色”替代“私小說”里的“我”、用動漫現實主義替代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說被稱之為角色小說。可以說,Cobalt文庫的少女小說、Sneaker文庫的奇幻小說全都是“角色小說”。(大塚 2000=2003, 210)
此處還不能明確(在本章第四節里會明確)大塚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對“角色小說”作出了什么樣的評價?。他提醒讀者注意,“對于文學而言,小說的角色小說化并非是隔岸觀火的事態”,“文學的角色小說化是隨處可見的現象”。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從此以后打算寫小說的人們——這些書預設的讀者是“中小學生”——“于充分理解自己的小說在近代小說史里占據什么樣的地位的情況下去創作‘角色小說’”。
3、作為小說創作模式的TRPG
接下來討論的文本是大塚的《角色小說的制作法》(2003)。本文從中提取了兩個論點,即以新的三分法為基礎的二次創作的模式化,以及對作為“漫畫”的比較類型的“游戲”(或者是“游戲一樣的小說”)批判的尖銳化(但兩者在本文里的討論順序是相反的)。
如前所述,盡管二次創作在《故事的體操》里被定義/解釋為“故事”與“世界觀”的分離狀態,但該書又將其再定義為游戲設計者、游戲主持人、玩家這樣的桌上角色扮演游戲(TRPG)三方角色分擔模式。這可以說是從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轉換,從“歌舞伎模式”到“TRPG 模式”的位移。
大塚采用這樣的模式是受到了將TRPG引入日本的安田均(1950-)的啟發。安田認為 TRPG里游戲主持人的任務包括兩方面:“1. 事先考慮故事的背景、設定與重要情節;2. 把握TRPG的規則”(大塚 2003,176)。
大塚繼續寫道,在創作“角色小說”時特別考慮“描寫玩家的小說的立場” 與“描寫游戲主持人的小說的立場”是很有益處的。具體而言,前者的立場是徹底成為“角色”,通過“臺詞”來活生生地表現角色;后者的立場是置身于小說中的“非對話部分”,引導跑偏的角色回到事先考慮的情節之中,最后使故事毫無破綻地順利進行下去。大塚還披露了水野良(1963-) 把TRPG《羅德島戰記》(『ロート?ス島戦記』)的錄像小說化為《羅德島戰記——灰色魔女》(角川Sneaker文庫,1998 年)時運用了所積累的TRPG游戲經驗的軼聞。
而且大塚在安田的解釋之上——TRPG的兩種角色分擔方法包括作為玩家的方法與作為游戲主持人的方法——進一步追加了新的立場,即“游戲主持人與游戲玩家參加的架空‘世界’與游戲進行時制作規則”的“游戲設計者”。
總之包括三類人物,即制作游戲世界觀與規則的游戲設計者,管理其中具體的一句句對話的游戲主持人,在游戲主持人的引導下所扮演的角色。 (大塚 2003, 180)
大塚說道,實際上水野一個人靈活運用“上述三種迥異的立場”再現了《羅德島戰記》的小說。這就意味著他在漫畫創作過程中對這三種角色進行了“分工化”處理。
總之包括三種角色,即創造世界觀的人、創作并管理故事的人、具體操作角色與畫漫畫的人(......)因此,《MADARA》雜志在刊登時列示了“世界設定”“原作”“繪畫”這三種名頭。(大塚 2003, 182)
與《故事的體操》不同,這本書雖然未將“二次創作”主題化,但很明顯這里的“三種角色的分工化”是與前著里——“故事”與“世界觀的 分離”——所解釋的二次創作原理相當的事物。而且大塚不但在這本書里反復使用了“游戲一樣的小說”這一術語,還提出有必要常常留意這里所謂的“游戲”模式就是指 TRPG。他如此強調 CRPG(電腦RPG游戲)與TRPG的區別:
CRPG將游戲主持人委派給電腦程序,玩家只能控制與“故事”相關的事務。角色的臺詞已被預先程式化了,不可以即興發揮。總之,CRPG的自由度與TRPG相比是特別低的。因此,即使是相同的RPG,CRPG 比起TRPG,是不太可能實現“小說”創作的基礎訓練的。(......)況且電腦游戲與桌游在RPG方面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即在“前者里”,游戲設計、游戲主持人、游戲玩家三者之間無法相互影響。(大塚 2003,184)
被(再)定義得如此周到的“游戲一樣的小說”,其價值被作者本人輕而易舉地摧毀了。而且與此相關的討論從一開始就率先被收錄在該書前半部分的創作TRPG模式里了。
4、“動漫一樣的小說”Vs“游戲一樣的小說”
大塚在《角色小說的制作法》里重申了自己在《故事的體操》中的主張, 認為新井素子是動漫現實主義的元祖,并解釋了“寫生”動漫的小說輕而易舉地克服迄今的文學里“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傳統的過程。《故事的體操》里被稱為“角色小說”的事物在《角色小說的制作法》這本書里——取自對這個文本類型的誕生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角川書店的商標名——也被稱作“Sneaker文庫一樣的小說”。
我認為,如果將站在自然主義立場描寫“我”的“私小說”作為日本近代小說的一極,那么把根據漫畫的非現實主義描寫角色的“Sneaker文庫一樣的小說”稱之為“角色小說”,大概就是對這類小說本質的最正確的表達。(大塚 2003, 28)
根據大塚的說法,長年累月發展起來的“Sneaker文庫一樣的小說” 作為作家世代交替與類型改編的結果,在今天分化出了“動漫一樣的小說”與“游戲一樣的小說”兩種類型。前者是當初就存在的事物,后者是新近出現的事物。他寫道,后者的代表正是“《羅德島戰記》一樣的奇幻小說”, 這些小說對于角川的Sneaker文庫而言就是“救世主”。他表示,現在的 小說家也沒有深思熟慮自己在寫什么,而是隨便去寫“動漫一樣的小說” 或者“游戲一樣的小說”,在這種情況下就變成了相同題目的動畫、漫畫、 游戲,這所謂的“二次元融合(MediaMix)”造成了越來越多的混亂。
然而,大塚在此處主張“游戲一樣的小說”與“動漫一樣的小說”“雖然是相同的角色小說,可仍然具備決定性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能否描寫“戰爭”與“人的死亡”這樣的“現實”。
大塚尤其重視漫畫史里的手塚治蟲(1928-1989)。特別是晚年的手塚秉持了“漫畫文本在本質上只是對人類存在進行符號化的表達這樣的自我警惕”,并把這份警惕傳遞給了下一世代。但“手塚以來的戰后漫畫史一邊采用‘符號化’的表現手法,一邊用這樣的技術描寫具備非符號化的真身的人類存在及社會現實”,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接受那樣的努力”(大塚 2003, 126)。大塚著眼于手塚在停戰之前的1945年初夏所畫的《直到勝利之日》(『勝利の日まて?』)這部作品。手塚在這部作品里動用了自己所習得的全部技術——即符號的手法,最后“奇妙且真實”地刻畫出主人公流著血向后仰倒的場面。大塚說道,手塚在最后的數格繪圖里“使用了隱藏戰爭這樣的‘現實’的漫畫技術,卻反而刻畫出戰爭這樣的使人死亡的‘現實’”。
盡管手塚“自覺”到作為“符號化”表達的漫畫其所刻畫的“死亡中的身體”與“戰爭”的“現實的側面”有不相稱之處,卻仍然積極地把它們作為自己的表達對象。戰后漫畫史繼承了手塚這樣的態度,即“努力用與現實主義相對立的符號化手法刻畫只能用現實主義手法描寫的事物”。
大塚回想起他自己在描寫小說《多重人格偵探 MPD-PSYCHO》(『多重人格探偵サイコ』)里的主人公雨宮一彥時,也“自覺地”承擔了“盡管是角色,但也有身體性”這樣的“表現技術與表達對象的矛盾”。這就是強調漫畫與“漫畫一樣的小說”的“責任”。他認識到恢復“使角色流血” 的意義,不止是角色小說,更是今天日本“文學”的“最大問題”。
那么“游戲一樣的小說”是怎么一回事呢?漫畫與“漫畫一樣的小說”、或許還有推理小說,它們通過提問如何運用符號化的表達來刻畫“現實的死亡”,“并在所屬文本類型的可能性與邊界里頑強戰斗”,與此相對, 具有“游戲一樣的小說”的一面的角色小說卻缺乏那樣的努力。如果考慮到“游戲的表現手法對人的死亡的描寫”本來就是“顯示為一節數值,且是可以重置的事物”,那這就是理所當然的表達了。
電影、漫畫、推理小說只是對人的死亡進行符號化的刻畫——我們在自覺到這樣的限度的基礎上探索它們與“現實”的相互關系,與此相對,我不由得認為“游戲”與以“游戲”為出發點的“游戲一樣的小說”卻缺乏這樣的努力。在運用“游戲一樣的死亡”的表現手法之前,(這個作為小說的一個范疇的文本類型的)作者必須考慮如何刻畫真實人類的死亡(這也是真實的生存的對立面)。作者進行了這樣的努力,就會對“因為漫畫而殺人”“因為游戲而殺人”這樣的批判從一開始就抱持堅決的態度。(大塚 2003, 143)
盡管大塚承認 TRPG模式對角色小說的創作方法有助益,但同時也寫道“不應忘記‘游戲’這樣的模式也有絕對無法刻畫的事物”。“‘自覺’本領域的方法所不能描寫的邊界”后,他注意到游戲與“游戲一樣的小說”還未臻至進化了所有表達的階段。角色小說應該是“文學”,這是該書的結論——倒不如說大塚是在表明自己的決心——但是,“游戲一樣的小說”暫時還不能包含在這樣的可能性里。
“游戲現實主義”論爭(二)——東浩紀《游戲現實主義的誕生》
《游戲現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后現代2》(2007年)是東浩紀在《動物化的后現代——通過御宅族考察日本社會》(『動物化するホ?ス トモタ?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會』,2001 年)里所獨家分析/理論化 的“后現代的數據庫消費”環境里,追問“故事”是如何幸存下來,其中又蘊藏了什么樣的可能性的著作。
“數據庫消費”是與大塚所謂的“故事消費”相對的概念,它是東浩紀新提倡的消費形態,在《動物化的后現代》里它被定義為“既不是消費單純的作品(小敘事),也不是消費背后的世界觀(宏大敘事),甚至不是消費設定與角色(大型非敘事),而是消費存在于深處的、更大范圍的御宅族系文化的整體數據庫”(東 2001, 77-78)。總之,“并不是故事而是作品的構成要素本身成為了被消費的對象”(東 2007, 40)。
東浩紀指出——其實不必等他指出,這也已是眾所周知的了——盡管“宏大敘事”在后現代里已然衰退這樣的話流傳甚久,但現代世界中依舊“物語”橫流。東浩紀如此設問:“與其認為現在是宏大敘事衰退了,不如將其理解為是故事的過剩與泛濫才更為妥切吧?”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之下, 東浩紀在該書中對“故事”進行了考察與分析。不止如此。被東浩紀描寫成“動物的”后現代消費者——所描寫的正是他自己——為了像“人類一樣” 生存,還是具有如何才能好好與世界相處這樣的頗為“普遍化的存在主義問題意識”。這就是為什么他在分析亞文化的過程中必須處理“生”與“死” 這兩個議題的原因。
1、作為“游戲一樣的存在”的“角色”
盡管東浩紀積極接納了大塚所謂的“角色小說”這一類型化的概念, 卻反對大塚在其中設置“動漫一樣的小說”與“游戲一樣的小說”這兩個下位概念的區分,以及大塚以欠缺“描寫現實的努力”為由,否定后者“如文學一樣的魅力”的論述。
東浩紀質疑的是大塚的如下假設,即“動漫一樣的小說”可以描寫死亡,“游戲一樣的小說”卻不能描寫死亡。何以如此呢?其原因在于,前者講述的是“一次而終”的故事,而故事在后者里卻經常是“可以重置的事物”,換言之,后者只是提示了“所有可能性”中的一個。東浩紀認為,“角色”是以數據庫為環境的存在,它使平時“一次而終”的故事解體,呼喚著“其他的故事可能性”。從此就出現了消費者也參與其中的“無數的二次創作”。 總之,無論是小說、動畫、漫畫還是游戲,從一開始“角色就是游戲一樣” 的存在。
如此狀況下,現在市場上流通的——無論是在“動漫一樣的小說”中使用,還是在“游戲一樣的小說”中使用——角色,其本質都是元敘事的,換言之,是游戲一樣的存在。”(東,2007,127)
2、“元敘事性”
“元敘事性”是從“游戲性”置換而來的術語,它是該書最重要的概念, 實際上這一概念也是受大塚啟發而來的。誠如所見,大塚在《角色小說的制作法》里,一邊參考 TRPG的游玩經驗,一邊論述了“游戲作為創造復數故事的元敘事系統對制作故事所產生的影響”(東,2007, 122)。總之, 大塚意識到了游戲在本質上擁有“元敘事性”。但與此同時,大塚在考察角色小說時排除了“游戲一樣的小說”。因此,他不僅限制了自己的考察范圍,同時也使自己的理論出現了“巨大的矛盾”。東浩紀如是指出:
因此,可以認為大塚把角色小說劃分為“動漫一樣的小說”與“游戲一樣的小說”的主張在理論上是不成立的。在如今讀者的美學里,“角色的出現”意味著由游戲的=元故事性的解讀所打開的可能性最終等同于“一次而終”的解體。“動漫一樣的小說”在角色出現的那一瞬間就發生了向“游戲一樣的小說”的轉變。(......)大塚的角色小說論懷抱著巨大的矛盾,他一方面認為角色的引入使得文學的可能性(半透明性)第一次得到了實現,另一方面他又嘗試將其他特質(元敘事性)排除在外。在言及TRPG與“游戲一樣的小說”時,這就成為了表現他論述中所存在的矛盾的異常點。 (東,2007,130-131)
再者,此處所謂的“半透明性”,即賦予角色小說以文體特征的“動漫現實主義”,盡管它否定了近代的私小說與自然主義文學“透明”化的現實描寫,卻不是簡單地向近代以前的“不透明”話語回歸,“它身為不透明的非現實化的表達,卻抱有想要將現實透明化的矛盾,是漫畫表達以及作為對漫畫表達的‘模仿’而被創造出來的術語”(東,2007,95)。它“使近代的理想反射在在前近代的媒體里,并收獲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如此曲折的歷史過程,才被稱之為‘半透明’。”(東,2007,96)
3、“游戲現實主義”
東浩紀認為,由于“元敘事性”的存在,一切角色小說都是“游戲的”。 那么根據這樣的“元敘事性”,我們自然就須重新討論與更新角色小說的“現實主義”概念。盡管大塚自覺到“符號的”表達方式的界限,但仍然用它來刻畫“真實的人類存在與社會現實”,并將之稱作“動漫現實主義”,且用它來表現“使角色流血”。與此相對,東浩紀提倡的則是“游戲現實主義”。
此外,在提出“游戲現實主義”這一術語時,東浩紀事先坦承該概念未必適用于“所有游戲”,他所關心的“始終是故事與文學”(東,2007,123)。事實上,成為他在第2章作品論里的分析對象的游戲作品 ——《ONE》(1998 年)、《Ever17》(2002 年)、《 寒蟬鳴泣之時》(『ひく?らしのなく頃に』,2002~2006年)三部作品——全都屬于多線劇情 AVG(adventure game)游戲下位類型的“美少女游戲”,無可否認這些游戲在類型方面太過偏倚了。東浩紀認為,游戲的本質是創造 “復數可能的敘事”的規則集合,他一邊引用弗拉斯卡的研究(弗拉斯卡1999=2000),一邊嘗試將自己的論述與歐美的游戲研究結合起來。
除了“時死時傷的身體”的動漫現實主義之外,不是應該認為角色的元敘事性打開了另外一種現實主義的可能嗎?(......)本文暫且把這另外一種現實主義命名為“游戲現實主義”吧。這是角色元敘事性的想象力闖入只有一個開始與一個結束的小說形式時,在其接觸點上生成的“現實主義”。 (東,2007,140)
“游戲現實主義”為了“實現故事的復數化、角色生命的復數化、死亡之后可以重置”,解構了“作為‘動漫現實主義’的課題的使角色流血的意義”。如此說來,角色的生與死無論如何都不具備現實性嗎?并非如此。游戲當然可以用其獨特的方法來描寫生與死的“現實”。
4、角色與玩家的乖離
那么,“游戲現實主義”獨有的而其他文本類型所欠缺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角色與玩家的“二元結構”或者說“二元性”。簡而言之即是這樣的事實:與其說角色的死亡對于玩家而言并不意味著游戲的終結,不如說是玩家必須反復操作角色的死亡——當然也有一些游戲是例外。而且可以發現,游戲玩家的經驗也對今天的小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東浩紀將櫻坂洋(1970-)的輕小說《All You Need Is Kill》(2004年)當作“游戲現實主義”的作品進行了解讀。

《All You Need Is Kill》是所謂的“時間循環”(ルーフ?もの)小說, 主人公桐谷啟二一邊操作時光機、一邊重復“同樣的戰斗”,不得不在其中數度經歷同伴及自己的死亡——盡管他嘗試過自殺,但仍然會陷入循環之中。桐谷與其他出場人物明顯是被描寫成存在于同一世界內不同次元的角色。把這部小說“當作‘游戲的比喻’進行閱讀時,并非是把桐谷與‘游戲中的角色’進行比較,而是將他與‘我們’,換言之是與游戲玩家進行比較”。東浩紀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可以說,櫻坂在此處將小說世界分割為故事層與元故事層,桐谷以外的人物全部是故事層的角色,只有桐谷被刻畫為游戲的,換言之被刻畫為元敘事層的玩家。通過引用這一二元結構,櫻坂試圖把游戲玩家在電腦游戲里所體驗到的故事形態——反復“重置”“重玩”獲得的元敘事經驗——融入到小說的形式之中。(東,2007,166-167)
通過玩家與角色的“二元化”,生與死這樣的古典主題就被重新改寫了。 櫻坂的小說使讀者體驗到的不只是“一輪的”生(與死)的重要性,而是“可以重置”的生與“不可重置”的生之間存在的鴻溝。如東浩紀所言,《All You Need Is Kill》描寫了“兩種類型的死”,“它們分別與角色的悲痛以及玩家的悲痛對應起來”。第一種類型的死——包括桐谷自己——是出場人物的死,它是“可以重置”的。第二種類型的死,是達成既定目標(對擬態的勝利)后,循環遭到終結,又重新恢復了“通常的時間”流逝,換言之,它是游戲結束后由游戲世界(時間)的外部所帶來的事物。與其他所有戰斗的死者不同,“最后一戰”的死者是絕不會生還的。總之,與其說這部小說描寫的是“死亡的一次性,還不如說它描寫了由生的多樣性消失所伴生的選擇的殘酷性”。
與其認為櫻坂在這里排除了將死的一次性相對化的元敘事的想象力,不如說他活用了這個相對化來刻畫死的重要性。而且在這部小說中使這樣的反轉戰略成為可能的是,他區別、刻畫出角色層與玩家層,即在感受到死的殘酷性的位置上,換言之是在讀者向痛楚移情的位置上,使故事=角色層向元敘事=玩家層發生了位移。(東,2007,180)
東浩紀認為讀者所體驗到的“痛楚”表現了“使玩家流血”。當然這里的意圖是要與大塚所謂“動漫現實主義”里的“使角色流血”的稱法相抗衡。東浩紀表示,我們或許不止一次地依照這樣的“反現實的假想”來認識“只有一次”的生命。因此,“游戲現實主義”“通過使角色流血”把“如何使玩家流血”變作課題(里重要的一部分),它通過“可以重置” 的生(及死)與“只有一次”的生(及死)之間難以填補的鴻溝打開了有關死亡表達的新的可能性——換而言之,它反手取得了所屬文本形式的媒介條件。
大塚認為死是一次性的,所以在對死亡的描寫中故事的一次性就是必須的。與之相對,櫻坂認為,假設死亡是一次性的,那么正是為了感受那樣的一次性,復數的故事——總之玩家的視角就是必要的。在前者那里,讀者將移情入只有一次生命的角色的無力感里;而在后者這里,盡管讀者遍歷了復數的生命,結局卻是他們移情入所有角色都只被賦予一次生命的玩家的無力感中。(......)游戲現實主義引用了角色層與玩家層這兩個層次的區別,鐫刻出人類與世界。(東,2007,180)
“游戲現實主義”立足于以角色與玩家的“二元結構”為前提的“玩家視角的現實性”,是一種新型的現實主義。
如果在此進行回顧,盡管大塚早早地指出了游戲設計者、游戲主持人以及游戲玩家這三個角色之間的區別,但以他們的“分工”為趨向,讓一人分飾多重身份,是無法設想出新的可能性的。他的討論也表現出他的主要著眼點是“作家”如何組織故事。與之相對,東浩紀自始自終是就“讀者=玩家”這樣的視角與想象力來展開論述的。此外必須抓住如下差異的重要意義,即大塚采用的“游戲”模式是多人玩的——游戲主持人與玩家各有分工——TRPG游戲,與之相對,東浩紀所謂的“游戲”基本上是為 了單個玩家游玩而被制作出來的電腦游戲——尤其是“小說一樣的游戲”。 對于大塚而言,電腦游戲對“小說”創作訓練是毫無幫助的。因此,他對有志于成為小說家的學生們說道“你們只玩游戲的話是沒有出路的噢。”(大塚,2003,184)
然而,如果在這里挪用古典的對比法作出簡單的結論,認為大塚的理論是“創作論”,東浩紀的理論是“讀者論”,那就犯錯了。東浩紀的理論也——只是未被強調——具備了充分且合理的“創作論”面向。當然在另一方面,大塚所提倡的小說制作法也可以用于徹底地解讀/批評同時代的小說與漫畫。此外,也應將他們二人所討論的“橫跨文本類型的”作為基本的態度予以合理評價——理解因此而產生的不少的混亂與錯位。他們二人都實現了個別領域的專家無論如何也無法模仿的理論抱負。我想再次指出,他們二人無論誰的理論都是對二次創作與成為二次元融合原理的現代(日本)亞文化具有無比說服力及整合性意義的理論,且這些理論仍然沿用至今。
死亡作為故事的終極矛盾
1、“瀕死意識”的描寫與現實的界限
截至上一章,我們重訪了“游戲現實主義”論爭的整個過程,可以說我們通過理解/斟酌該論爭里所提出的概念與見解,基本達成了本文的目的。本章在此基礎上,嘗試對這次的爭論作出補充考察。
首先,大塚英志與東浩紀都將對“死亡”的刻畫(表現)放置在故事的“現實主義”評價標準之上。
正如在考慮繪畫與文學的寫實主義時所明了的,大概現實世界里一切為知覺所感知的事物都可以成為“現實主義”——本文大致定義了何為據實描寫/再現現實——的對象。但大塚與東浩紀在使用這一術語時各自夾帶了獨特的限制。首先,大塚把描寫人受死、遭受折磨這樣的“嚴酷的現實”稱之為“現實主義”。其典型代表即是戰爭與人的死亡。如果考慮到他所謂的“動漫現實主義”是從戰前的現實主義文學(特別是遵從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的私小說)里繼承而來的課題,其含義就很好理解了。另一方面,東浩紀認為近代的自然主義文學與后現代的角色小說里的“文學的想象力其被放置的社會環境完全不同”,他是在嘗試考慮基于后者的“現實主義”,即角色小說的讀者與游戲玩家“感受到了什么樣的真實”這樣的“社會學的現實性”——那就是(東浩紀再定義的)動漫現實主義以及游戲現實主義。因此,盡管同樣以“表達死亡”為問題意識,二人論述的前提與目的的分歧卻是巨大的。大塚所考慮的“死亡”徹底屬于被“描寫”的對象,而東浩紀則是在追問“敘述”層次所表現的“死亡”。既然他所考慮的“游戲”在本質上是“元敘事性”,那么存在這樣的差異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然而無需由擁有東浩紀所分析的“時間的循環構造”的近來的小說與游戲來提出表述“死亡”的困難性,這樣的困難性本可從全部文學作品里觀察到。而對此給予特別關心的就是小說理論家。
在文學理論與語言哲學的領域里,是如何使得小說(虛構的故事)與非虛構(歷史書、日記、傳記,等等)的區別成為可能的?就這個問題交織著長時間的復雜討論。其中存在著這樣的立場,即小說的正文里包含了成為小說目標的語法論特征。本文所關注的是,由死亡描寫帶來的發現該特征的典型場面。例如文學理論家科恩(Dorrit Cohn,1924-2012)在《小說的識別》(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1999 年)里就傳記(biography)與小說(novel)的差別作了如下說明:
在人生的所有瞬間里,傳記(biography)與小說(fiction)的類型差異,以及傳記作家的受限與小說家的自由的差異,并不比死亡與瀕死(death and dying)的差異(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更加顯著。這是因為小說可以再現任何樣態與形式的“自然的”敘述都無法傳達的經驗。恐怕就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小說家——偉大的現實主義者與偉大的反現實主義者都一樣——給予我們的才是毫無進步的對瀕死意識的模仿(the mimesis of a dying consciousness)吧。(科恩,1999,22)
描寫“人類瀕死意識”的故事的確是“小說”。作為歷史記錄的文獻依據而被書寫的“傳記”,它是不可能包含那樣的描寫的。這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在瀕死之際將自己的所思所感記錄下來留給后世。換言之,任何 “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都無法“真實”地描寫“瀕死的意識”。那樣的描寫并沒有給予我們任何判定“真實”的標準。那是字面意思的現實主義的彼岸。對于小說的表達而言,“死亡”就是那樣的特異點。
然而,小說經常使用“自由間接話法”來表述“瀕死意識”。“自由間接話法(free indirect speech)”在形式上是非對話的部分(敘述人的陳述), 它把出場人物的內心活動像當事人在講話一樣詳細地描述出來,且通常使用了間接話法與直接話法的折衷形態一般的文體(清塚,2009,29)。第三人稱視角與第一人稱視角的區別就這樣消失了,且敘述人與出場人物的聲音、思考也發生了混淆。而且,自由間接話法把敘述人用作對出場人物的——柏拉圖(Plato)將“模仿”與“敘述”對峙起來——“模仿”(中川,1983)。前文所引用的科恩的“模仿瀕死的意識”這樣的說法也是如此。即使是貫徹“從外部觀察”的現實主義作家,如欲有說服力地描寫瀕死,也須借助“模仿”的手法。
按照死亡這樣的特異點,科恩的論述呈現出——講述的主體與被講述對象的若即若離——故事(敘述)本身的困境。而且,如果故事本身是內部具備多層性的事物的話,那么它與作為“游戲現實主義”最大特征的“角色與玩家的二元性”到底保持著什么樣的相同性與關聯性呢?這是在考慮到故事與敘述的基礎上,于今后必須探求的主題吧。
2、作為故事的絕對外部的死——作為“規則”的生與死
接下來我想在“游戲現實主義”論爭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游戲的“死”所被賦予的角色與地位。
盡管可以用“游戲所表現的死”一言蔽之,但其中還是存有一些區別。 游戲“描寫”了死亡,那么玩家是在“觀察”死亡呢,還是游戲迫使玩家去“體驗”死亡?于是“死亡”的是玩家角色(玩家自己的分身)呢,還是其他角色?在后者的情況里,死亡的是支持玩家的角色呢,還是與玩家敵對的角色?而且,如果玩家角色死亡了,那么我們失去的只是復數生命里的一條呢, 還是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換言之,玩家角色死亡之后,有重玩游戲的可能嗎,還是游戲就此結束了?
大塚與東浩紀的論爭里幾乎全未涉及這些很快就能想出來的區別。而且這些區別也給兩人的論述帶來了混亂及錯位。例如,大塚的現實主義針對的主要是“死的描寫”,而東浩紀追問的卻是“死的經驗”的現實性。
與之相對,井上明人從弗拉斯卡的論述(Frasca 2001)中獲得靈感,區分了在游戲戰斗系統內的死(比賽中的死)與游戲故事意義上的死(故事中的死)。井上認為,前者以“生命的復數性”為前提,而后者的前提則是“生命的天然性”。不過,即使兩者再怎么高明地(再)結合,對于存在于“游戲外部”的玩家而言,“游戲內部”角色的死亡都是“可以重置”的。 盡管認識到了這一點,井上仍然“在存在于游戲外部的玩家層上”發現了以《皮克敏》《合金裝備 3》等為代表的“使玩家感受到死的天然性”的手法。 但是,在前者里“死亡”的是玩家角色(奧利瑪)操縱無數的皮克敏,而在后者里“死亡”的卻是玩家角色(斯內克)自己。井上忘了指出兩者的死并不具有同等的“天然性”。此外,《皮克敏》里的“日志”系統與《合金裝備 3》里回避不可避免的死——盡管作為故事的手法,它們的優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可以說是在“游戲的外部”嗎?其中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由于井上在論文中沒有考慮到“故事”與“游戲”的包含關系, 使得上述考察均不可能實現。

一如開篇所言,溫茨把玩家所體驗到的替身(玩家角色)的死亡,稱之為電腦游戲中死亡的“象征機能”。這樣的“死的經驗”是在讀小說、 看漫畫、觀電影時體驗不到的,只有在電腦游戲中才能有所體驗。
再稍微思考下“死的經驗”這一實在有些奇妙的表達。毋庸置疑,我們受限于真實的生活,是不可能在現實世界里體驗到“死的經驗”的。有鑒于此——這里令人想起科恩的主張——應該誰也無法回答游戲中“死的經驗”究竟是在模仿或者感應什么吧。死亡存在于一切“故事”絕對的外部。可與玩游戲過程中“死的體驗”相類比的事物是什么呢?筆者認為, 正是“故事絕對的外部”,即拒斥一切“故事化”領域——也包括“元敘 事”在內——的經驗。此處應該參照一貫堅持游戲是“規則與故事(虛構)相沖突的場域”的杰斯珀·尤爾(Jesper·Juul,1970-)的研究。尤爾認為, 正是“規則”在故事的外部隱瞞了虛構世界中的“空白”與“矛盾”。游戲中的規則常常無法從游戲內部的故事(小說)處得到解釋與依據。反過來,玩家又經常把無法從故事中得到解釋的事物視為“規則”而加以體驗。他舉出《大金剛》(『ト?ンキーコンク?』)里馬里奧(玩家角色)擁有“三條命”的例子,如此說道:
基本問題是這樣的——為什么馬里奧擁有三條命?可以如此作答:我們在體驗虛擬世界(fictional worlds)時,是被掩埋于瑪麗 - 勞爾·瑞安(Marie-Laure Ryan,1946-)稱之為“最小脫離法則”的空白(blanks)里。在虛構里沒有解釋發生了什么的時候,我們就會對自己給出最簡單的解釋。就《大金剛》而言,我們可以故意技術性地聲稱馬里奧之所以擁有三條命,是因為該游戲是一款與靈魂轉世說緊密結合的印度教游戲。但實際上——根據我的采訪——玩家自己的解釋是,三條命與游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相關。“規則就是那樣的”“不是三條命的話就太難了”,等等。在許多游戲里都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很難解釋游戲中大量的事物與游戲虛構之間的關聯。在此情況下,我們就會將其解釋為游戲中的事件是與游戲中的規則相關聯的。(尤爾 2005a)
游戲世界里并沒有給出馬里奧不是一條命,不是兩條命,也不是四條命,而是“三條命”的理由。在游戲中也好,在我們的現實世界里也罷, 虛構與故事總是“不完整”的。而且,玩家把虛構里的“空白”部分作為“規則”加以理解、體驗。它們是在現實世界里無法加以合理說明的事物——生與死就是其中的代表——對于我們而言,它們似是作為“命運”與“自然” 的事物而被我們感知的。
大塚是如此批判游戲的——“可以重置”的游戲不能“表達死亡”。因此, 游戲與動漫相比并不具有“現實性”。而東浩紀對此提出了如下反駁——正因為游戲“可以重置”才引起了角色與玩家的乖離,創造出“玩家視角的現實性”。而且以“元敘事性”為本質的游戲可以通過玩家的視角實現新型的“死亡表達”,這正是“游戲現實主義”。但本文既不認可(大塚)所言“因為游戲無法表達死亡,所以游戲就是非現實性的”,也不認可(東浩紀)所說“因為游戲可以表現死亡,所以游戲就是現實性的”。這不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已,我認為這并不正確。作為“虛構與規則的沖突” 場域的游戲現實性,它可以通過死亡預兆故事世界的界限及其外部性。
其實不僅僅是游戲,本來就不可能用任何媒體及手法去實現“死的經驗”的“現實表達”。現實世界里具有說服力的、可以使人感受到“真實”的“死”都是虛構的。假如游戲中有“現實性”這樣的事物,不如說它是對“真實的死的表達”這樣的虛構的拒絕,故事——即有關“世界”的合理解釋—— 總是指向不完整的事物。而我們的人生也正是這樣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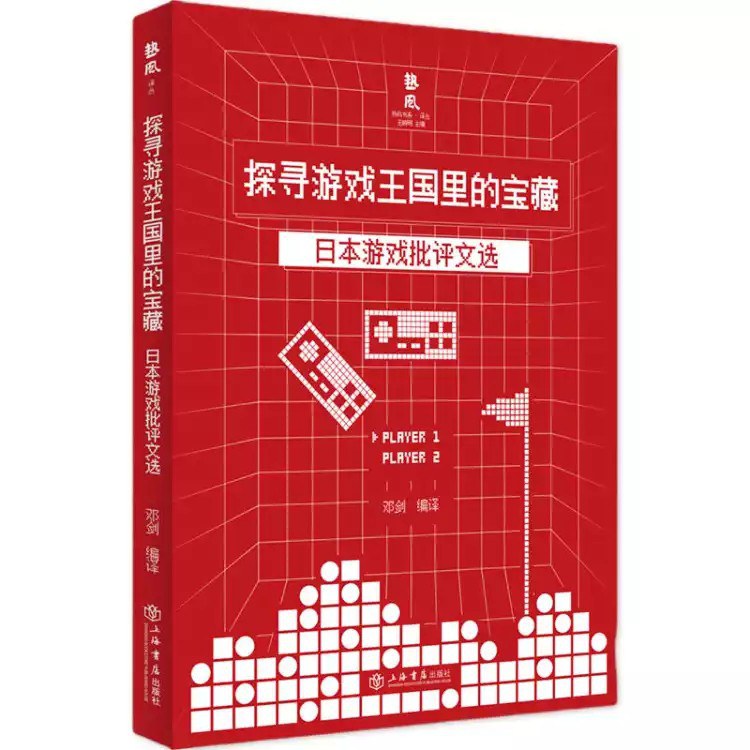
《探尋游戲王國里的寶藏》,鄧劍 編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文經授權選摘自《探尋游戲王國里的寶藏:日本游戲批評文選》一書)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