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白水《八首歌》:“它的詩意和暴力直截了當,還算得上精彩”
電影落幕以后,音樂響起。白水新專輯《八首歌:豐收前夜路過的人》分兩部組歌,第一部的三首琴音清澈、溫柔繾綣,歌詞閃著寒光,適宜的出場地點正是片尾字幕滾動的漆黑影院。觀眾的心潮還在起伏,聽覺在黑暗中達到最敏銳的程度。此時聽到謠曲,不懂川南方言的人也具備夢里的超能力,仿佛能從只言片語中領會歌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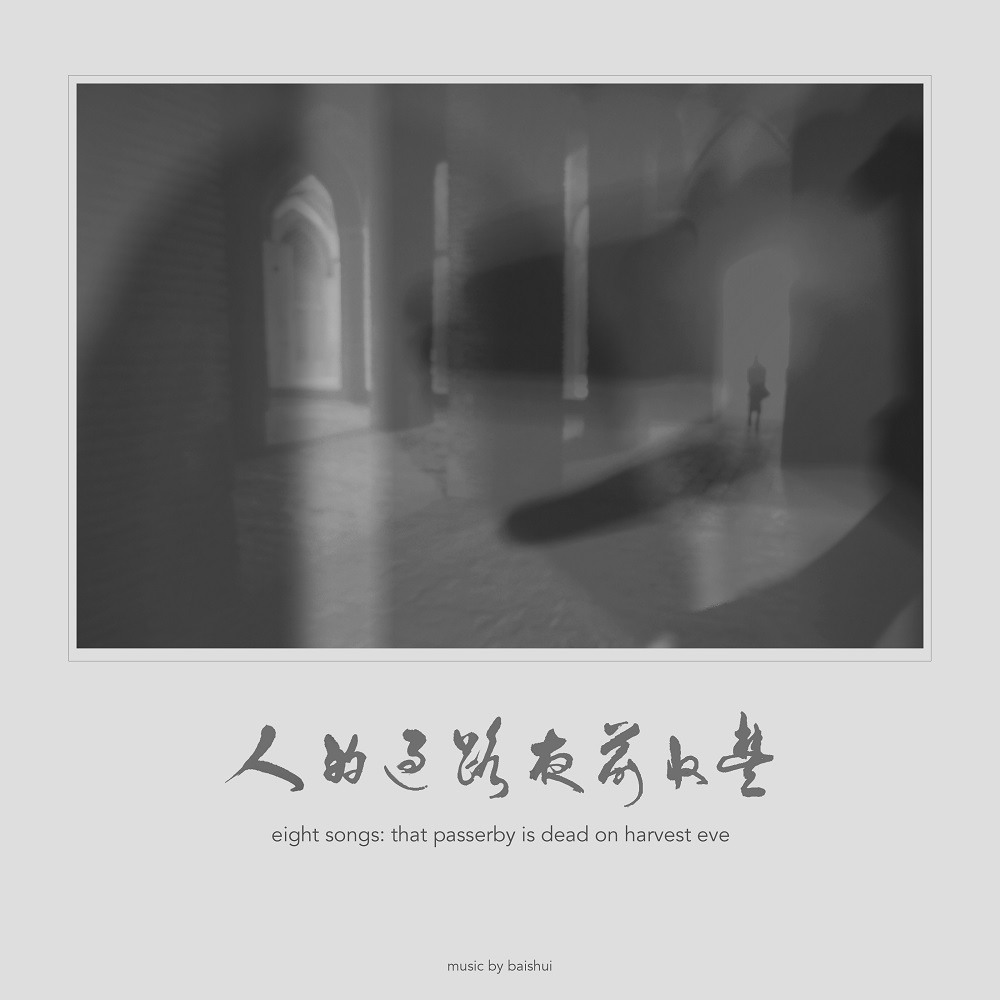
白水新專輯《八首歌:豐收前夜路過的人》
粵語人聲誦詞《豐收前夜路過的人》之后,空氣變了。鄉村布魯斯從幕后跳出來,樂隊載歌載舞。燈光閃爍,觀眾把電影情節和復雜情緒忘得一干二凈,立即投入到銅管的光輝和各種惟妙惟肖的戲仿中。
最近幾年,蜀地音樂人白水定居“北美荒野”。他無法說出環境對音樂的具體影響,但清楚地感覺到青年時期生活不會磨滅的影響,“那種氣氛早已經融入到那個年輕自己的骨血里”。距離會產生奇效。他身處荒野,生活清簡,卻被遠方撩撥得驚顫。這樣產生的作品既有放大扭曲的情緒,又有格外冷靜的色澤,像一顆冰天雪地里的凍梨,風味獨特。
他形容從前生活是“潮濕,陰郁,水色與霧氣,秋日第一場雨后那致命的悲傷”。一路聽白水的人,贊嘆他變色龍般閃耀的音樂色彩。黑暗民謠、蜀地民歌、各色實驗、電影配樂,無不在水澤蒸騰中隱現傷感的貝殼。
新專輯連序帶歌,構成一座難解的迷宮。兩篇序相當于兩部微型小說,人物一個銜出下一個,霧中還有許多人影憧憧。他說序和歌并無實際的交匯,“它們即使有交點,都會離觀聽者很遠”。歌里的諷喻和狂亂容納想象空間,它們對聽者有要求。但白水相信,“它蘊含的詩意和暴力都直截了當,且還算得上精彩”。

白水
澎湃新聞:一共九首,為什么叫《八首歌》?
白水:這本專輯實為兩部組歌,《抒情歌三則》與《漁夫之死詩五首》。前后加在一起,正好八首。當中有一首人聲誦詞為《抒情歌三則》之后記,算不得歌。
澎湃新聞:《序》里的故事讓我想到《金枝》里形形色色的仲夏夜儀式。關于食人和娛樂,研究人類酷刑史的人確實可以得出和“卡羅娜”不同的結論。說說這些故事以及這張專輯開始的創作動機吧。
白水:卡羅娜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我猜想她一定是讀過這本弗雷澤的名著。只是和弗氏主要沉浸于圖書館文獻不同,卡羅娜更多的是在游歷中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所以,同樣的事件,工具和方法的不同,結論自然就千差了。
兩部組歌的創作動機實質和覆蓋于其上的故事或文字描述幾乎是無關的,就像接近于平行的線。它們即使有交點,那交匯之處,都會離觀聽者很遠。
歌的緣起分別來自2018年到2019年持續發生的多起事件。無論你選擇如何表達,我想,合適且別致的載體一定會為你的述說增色。那“食人”與“殺神”恰好在現實與表達之間搭建起了有趣的支撐。它蘊含的詩意和暴力都直截了當,且還算得上精彩。
澎湃新聞:創作過程是怎么樣的,先有詩歌再有音樂的嗎?哪個部分磨人、具挑戰、有樂趣?
白水:從上一部作品《兒童樂園》開始,我的音樂基本都是先有文本再有聲音。而文本的內容來源也雜亂,如書信、詩歌、筆記、文摘。這部《豐收前夜路過的人》也基本如此。所有的詩歌都改寫于我平日的雜文散記。
音樂對我而言,已談不上所謂樂趣。而更是生活、工作與研究。想想,如果真的要說讓人喜悅的點,我想還是錄制過程。具體如何,我會結合后面的問題稍微展開。挑戰與磨人的部分其實也鑲嵌在這快樂中。
澎湃新聞:“拋棄節拍器與分軌的同步奏唱錄音的方法,不給后期編輯與處理留下余地” ,解釋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白水:自人們開始分軌錄音以來,近幾十年,八成以上的音樂作品都不是即時(real-time)錄音完成的。就如大多數流行音樂,都是分軌錄制好器樂部分,再錄制人聲。更隨著錄音技術的發展,這種方法被從錄音室到家庭工作室廣泛采用。因為它便捷,簡易,后期的編輯與修改空間很大,這讓錄音對樂手歌手的技術要求也大大降低,甚至有一些人一首歌要一個小節一個小節去彈,一句一句地去唱。唱得不準沒關系,軟件來幫忙。并且,以上這些過程都是在一個穩定的節拍下進行的。
可這是音樂自然的樣子嗎?一定不是。對我而言,音樂迷人的地方反而是那些穩定中的瑕疵,無可替代的人性動態,還有表演過程中被情緒所干擾的失誤,及其導致的音準問題。另外,機械性的分軌錄音讓錄音過程越發無味,多了機會,自然就少掉了對自己我的苛刻。
于是,在2017年《歌選》開始,我就開始嘗試用一只麥克風或者一個便攜式錄音機在心理節拍的指揮下進行彈唱錄音。盡力回到演奏和錄音原始的狀態。但這無疑對演奏技術和表演狀態的要求都是極高的。過程雖艱難,但效果明顯。并且在如此情景里,更能找到奏唱的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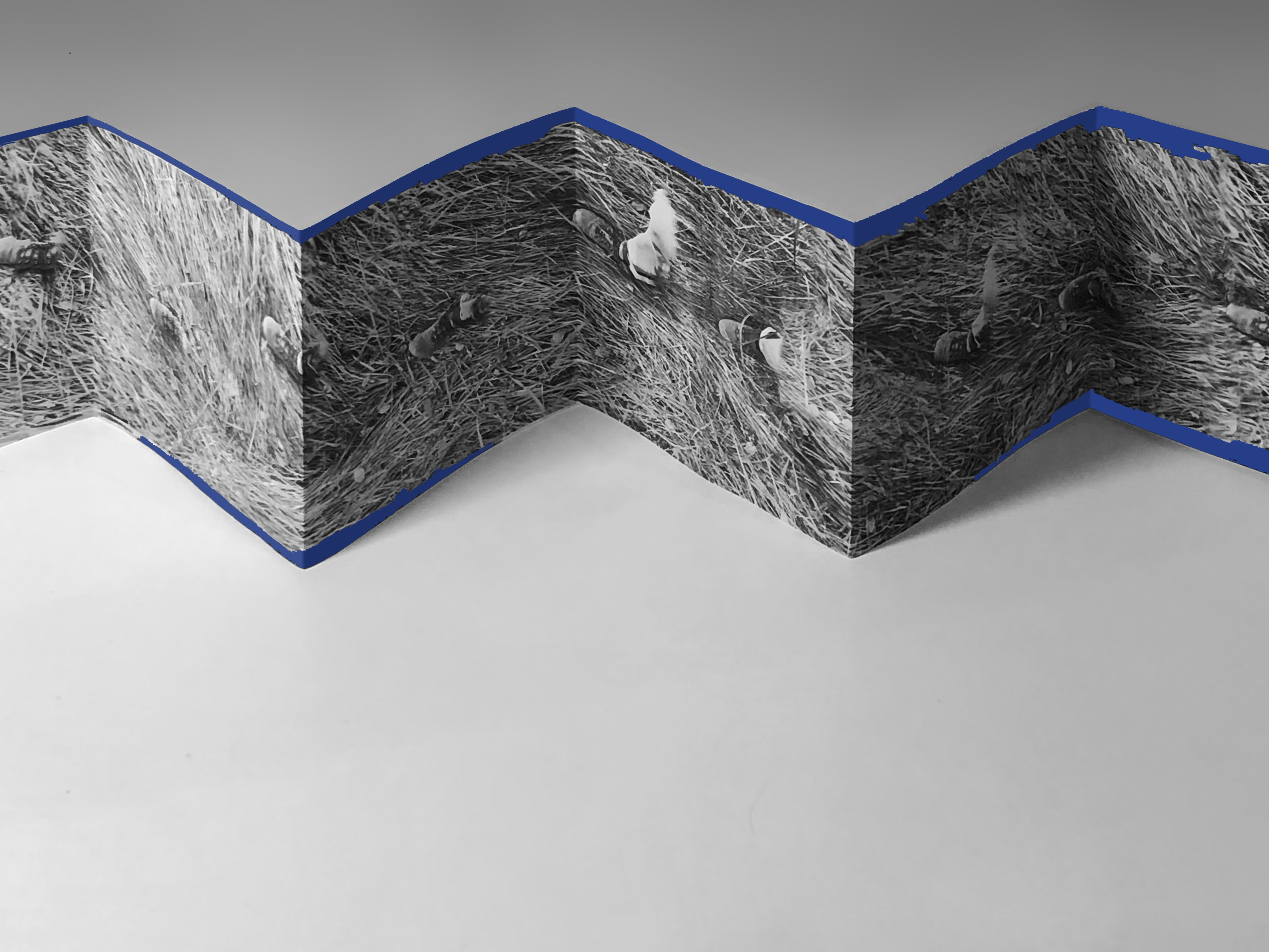
白水新專輯《八首歌:豐收前夜路過的人》
澎湃新聞:你唱歌的聲音和早期很不一樣了,越來越清晰明亮,和一般人自然發展的過程似乎是相反的……怎么會這樣?
白水:從音域的角度來看,我的聲音其實越發低沉了。雖然我依然還能發出那些尖利的高音。不要太看重時間對人聲塑性的影響,合理且嚴格的訓練或許才是駕馭自己聲音的好之途徑。
澎湃新聞:對這張專輯來說,文學性的考慮在音樂性之上嗎?
白水:既然是歌曲,我認為詞曲奏唱都不能有軟。所以,我并沒有考慮誰在之上的問題。如何把這些部分在邏輯中合理有序地架構起來,才是我優先會去考慮的。
澎湃新聞:這張作品的音樂非常清澈、通俗,是有意識地這樣處理音樂部分,中和歌詞內容的苦澀難懂嗎?
白水:有意算不上,更多還是自然吧。另外,我的聲音一出來,如何通俗易懂的旋律都會分崩瓦解,暫時不需要詞來助力。
澎湃新聞:這張的感覺好像又回到neo-folk的時候,那是很多年之前了。興趣一直都在 ,還是淡去又拾回?早的時候怎么會被neo-folk吸引?
白水:有嗎?neo-folk是真的一點興趣沒有了,但無疑它的那種氣氛早已經融入到那個年輕自己的骨血里。而我們的表達中八成以上的東西都逃不過那無意識的牽絆。
喜歡neo-folk,我想喜歡的還是它的那種特別容易被具象且抓得住的氣。這種氣和我所生活的川地有種臆想的聯系。潮濕,陰郁,水色與霧氣,秋日第一場雨后那致命的悲傷。以上這些描述,無一不讓被荷爾蒙控制的且喜歡浪漫的年輕人好奇與著迷。
澎湃新聞:詩歌/歌謠若可以脫離語境存在,為什么還要寫這些故事并和專輯一起發表?
白水:沒有人能逃脫語境的困局,就如我們的創作如何也避免不了事件本身緣起的第一因和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干擾。回到這本專輯來說,這些故事其實就是音樂發展過程中的干擾,決定了終呈現的模樣,你無法不去面對他們或她們。
澎湃新聞:《漁夫之死》里那個沒頭沒腦的怪誕故事很迷人。人都喜歡怪誕故事,所以才會有那么多本《怪誕故事集》。平時就喜歡這些神秘的故事嗎?為什么你筆下的都不發生在現在,是因為有意要和日常拉開距離嗎?
白水:我喜歡這樣的故事,像愛倫·坡與勃朗特姐妹那樣藏在里面的,也像雷蒙德·錢德勒那種露在外面的。
其實我寫的東西都是實實在在的當代故事,它們真真實實,只是理所當然被隱了名。你覺得嗎?在日常里我們已有太多的觸目驚心,何不讓他們扭曲一些,說不定這種變形還多少能帶給作者和觀聽者一點虛情假意的撫慰。
澎湃新聞:《小丑預言之瘋王來了》很街頭,它有即興的成分嗎?這張專輯是怎么錄的,你給它多少即興的空間,給了樂手多少發揮的空間?
白水:《小丑預言之瘋王來了》是受到free jazz影響的一首作品。吉他與演唱部分是奏唱同步,而貝斯部分是我寫好交給樂手演奏。精彩的銅管部分是即興的,但這種即興也建立在事先和樂手的一些討論和安排上。所以,嚴格講,它不算是絕對的即興。

白水
澎湃新聞:對真正的詩人來說,真的有好的和不太好的時代之別嗎?
白水:對詩歌來說,沒有好壞時代之別。而對人個體來說,我認為是有的。靠向內尋找靈感的創作方式畢竟是有限的,它被局限于年齡和感知能力及知識結構。更多的時候,詩人不得不向外去尋找素材與沖擊。
澎湃新聞:東西方混雜的地名和人名像迷宮,唱歌的語言又是很古雅的川南方言,這種感覺很奇怪且危險,它是你現實生活、或是內心的反映?是怎么成形的?
白水:我一直都受到東西方文學音樂藝術的雜糅影響,而且相對東方,西方可能還稍多。從前,這影響建立在一種異域想象上,而如今它成了我的生活。無論是聆聽、閱讀和寫作,兩種截然的語言,多種完全不相關的表達,卻在同一時空中漂游延續。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你的思考和審美,在不知覺間就霸占了你的想象。
澎湃新聞:目前還是定居國外嗎?異國生活對創作的影響一定不止這些人名和地名,還有什么?
白水:我搬到北美有好些年了。對創作的影響得你來說,因為創作終的呈現是在觀聽者那邊,我答不上來。我只能談對個體的影響。我所在的荒野讓我的生活更加清簡。這種寧默的生活在抵抗荷爾蒙的運動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心里的妄想不會因此而減少。嶄新的視聽讓人的表達也有了些許的不同,但絕不是重生,因為我們如何也擺不托那些早已注入你身體的牽絆與困擾。
澎湃新聞:能不能簡單描述一下你現在的生活狀態?你對音樂的態度和從前有無變化? 比如它是必要的表達發式,情緒出口,謀生的方式之一,享受/痛苦的東西 ,努力去找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的珍寶?……
白水:生活依然,養育子女,吃穿住行油鹽柴米。音樂好像也是一如既往,你說的所有詞它都可以搭得上。只是它們越發過期,連保質期都被忘掉了。這很殘酷,卻是毋庸置疑的理所應當。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