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才導演,情色大師,厭女標志,性侵嫌犯……誰是金基德?
如果2020有最魔幻事件的評選,他的離去肯定會有一票。
韓影史上,甚至在世界電影范圍內都極負盛名卻充滿爭議的導演金基德,因新冠感染在拉脫維亞意外離世。最先發出這則新聞的是一家拉脫維亞語媒體,一個多小時后,韓國媒體才“姍姍來遲”地最終確認。
那一個小時,就如同大多數影迷在看完他電影的最直接感受——遲疑,震驚,錯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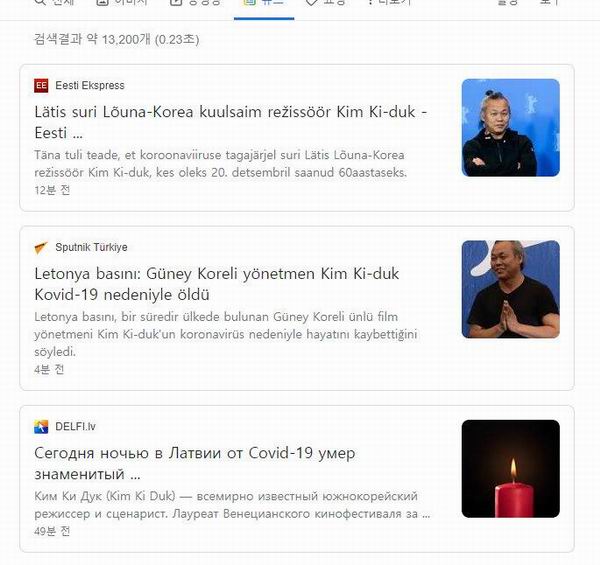
與大多數中西方媒體都發出了悼文不同,韓娛圈只有釜山電影節執行委員長全陽俊(音)發文“韓國電影界無法挽回的損失,以及巨大的悲痛”以作悼念,無論是他合作過的電影人還是大部分電影圈人士都選擇了沉默。
天才導演,情色大師,厭女標志,片場暴君,性侵嫌犯……用任何一個詞都無法簡單概括的金基德的爭議人生,無論從哪個角度展開,都會成為正反雙方的戰場。但歌頌與聲討都不是以下文字的本意,無論是從他的為人還是作品去剖析,都并非為了表明立場。某種程度上,無論是金基德這60年的人生,還是金基德的電影,都是窺探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第三只眼”。

韓國著名影評人鄭圣一甚至這樣說過:“是金基德電影的出現,才使得韓國電影開始能從整體上描繪以往時代所經歷的真實生活。”但金基德的底層視線是如何形成?他與其他1960年代出生的韓國導演們又有何不同?他的爭議背后以及后來的韓國電影界,發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變化?
絕望的底層觀察者
60年前的冬天,金基德出生于韓國慶尚北道奉化郡的一個山村。貧窮的出身和扔到人海里也不突出的相貌,似乎早就為他顛簸的人生定下了基調。
金基德的父親是經歷朝鮮戰爭的退伍軍人,雖然當了20年的村長,但由于在戰爭時期受過很多槍傷,所以患有嚴重的神經痛。即便戰爭已結束多時,他的父親每年都會給國務總理寫信索賠,但寫了幾十年,得到的回復就只有四個字:無據可查。
飽受身心折磨的父親能做的,就只是把憤慨和傷害轉嫁到兒子身上。每天在餐桌上上演的震耳欲聾的咆哮謾罵早已是固定節目。因為在課本上涂鴉,小腿各被抽打100多下的暴力行徑對金基德來說也不過是家常便飯。

小時候的金基德敢做的,就是迅速逃離。寧可逃到后菜園偷白菜充饑,甚至躲進農家土屋屎坑,也不愿和父親多待一分鐘。即便父親后來逢人就炫耀自己有個當導演的兒子,金基德也依然沒有與他和解。
為了逃離父親的魔掌,20歲時金基德主動加入了訓練最為酷烈的海軍陸戰隊,但軍隊的經歷不僅沒有緩解他的憤怒和悲傷,甚至讓他第一次感受到令身體顫抖的殺意。金基德所在的小隊駐扎在雷達基地,是專門負責捕獲間諜的尖端部隊。他的上級在某一天值勤的時候,沒有及時發現疑似間諜船出沒的痕跡,更沒有向上級報告,但因為韓國根深蒂固的上下級關系,金基德“理所當然”地成了背鍋俠,被關進了南漢山城監獄。
顯然,這次逃離以失敗告終。
服役了足足5年以后,他用盡所有的積蓄買了單程機票逃到法國,憑著小時候喜歡的,承載著他自我的對涂鴉畫畫的癡迷,開始以畫畫為生。在法國也沒有過得多好,因為沒錢所以只能跟流浪漢蜷縮在塞納河邊,一起饑寒交迫地度過了最開始的時間,甚至連黑人清潔工都是他羨慕的對象。

認識和跟隨的朋友形形色色,有來自東歐和阿拉伯國家的小偷和騙子,有跟著他學畫畫并教他法語的越南少年,經歷了七次兩伊戰爭的逃兵,還有韓國流亡家庭。《野獸之都》便是再現這些像是野生動物般活著的人們的記錄。
就這樣在法國度過了2年,依然無法獲得成功的他回到了韓國,但這段經歷對他來說卻是“最值得珍惜的時光”(金基德《于我,電影即斗爭》),后來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帶有這部分經歷的影響。
事實證明,無論他怎么逃,也逃不出父親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
父親對于金基德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暴戾和憤怒,還在于剝奪了他在韓國社會立足,也是韓國社會最看重的根本——學歷。
年僅9歲的金基德,為了哥哥的學業隨著家人搬到首爾居住。但后來哥哥因頑劣被學校開除,金基德也受到了牽連,父親認為他們都不是讀書的料,一怒之下迫使他們進工廠賺錢。就這樣,金基德的學歷只停在了初中。能接觸的人群,也只剩粗鄙的工廠糙爺們和騷擾他的街頭混混。
要知道,同代的韓國名導,包括李滄東、奉俊昊、樸贊郁、許秦豪、康祐碩,都幾乎出自韓國高校甚至SKY三大名校(首爾大、高麗大和延世大),洪常秀不僅生于電影世家,是科班出身的正統電影人才,甚至還是韓國第一批留學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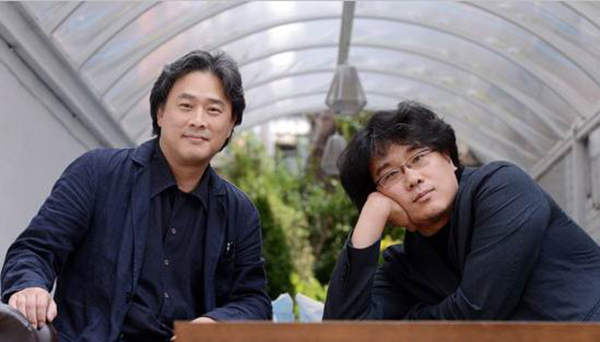
與金基德類似學歷卻同樣成為名導的,最為人熟知的大概就初中畢業的林權澤和高中畢業的李晚熙了,但這兩位的所經歷的時代和環境顯然又無法直接與60年代生的導演們進行比較。難以復制的早期經歷,令金基德無論是在觀察還是表達上都與眾不同。即便是幫同學和戰友寫情書,他能想到的開頭都是些諸如:“某個人忽然在街頭仆倒,生死未卜,血流如注”,“一片花葉被摘下”,這種一般人未必能想到的極端表達。
但這樣的“才華”并沒有讓他被唾棄,反而讓他抱得了美人歸。甚至后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在法國交往的筆友。金基德對于文字和表達的信心以及講故事的欲望,便是從這里開始的。這些在普通人看來根本不算什么的小小“成功”,對于在底層的泥潭里掙扎多時的他來說已是最大鼓舞。而這樣的經歷種下的種子便是,原來成功的途徑之一可以是講故事,無論故事本身有多么的極端。遇到電影這種能承載他的故事和肆意表達的載體,便有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拍電影便成了我與這個世界對抗的手段,同樣也是我輕視自己不堪重負的無力內心的一種表達方式。”(金敬《羸弱男子的駭人之力》)
于是,他一面瘋狂地創作以求獲得更多的肯定和成功來填補極度的自卑,一面又以更加極端的故事來滿足觀眾的窺探欲和他的表達欲,同時為獲得的關注和成績沾沾自喜。

因出身產生的自卑和通過電影獲取成功的自傲成為纏繞金基德一生的矛盾。這或許也是為什么,同樣經歷韓國高速的經濟發展卻文化貧瘠的樸正熙時期以及民主抗爭最為激烈的全斗煥時期走過來的金基德,會走上與同代導演截然不同的路。
面對憤怒,他無法像李滄東一樣用詩意去表達;面對現實,他也無法像奉俊昊那般精雕細琢;面對暴力,他沒有樸贊郁那樣的控制力;面對愛情,他也無法像洪常秀一樣拍得如此有沉浸感……這是他的成長環境和經歷所導致的。
女性崇拜VS女性厭惡?
自卑和自傲的矛盾不僅存在于金基德的言辭和對作品的態度上,也在于他的電影里。特別是成為眾矢之的的,對女性的角色的描寫上。
評價金基德電影時使用最多的標簽就是情色,大尺度,19禁。他電影中的女性大多都是以妓女和被欺凌者的形象出現,而男性往往是制造這般狀況的人,或是窺探其中的旁觀者。但通過這樣的設定是否就能二元地判斷他的電影就是在表達對女性的厭惡?

個人更傾向于,在電影里,他處于一邊自卑地對女性進行“母性”崇拜,一邊自傲地在他創造的世界里對其進行“凝視”的狀態。因為他的作品里,總是欲望先行,主人公們總是為了本能心甘情愿地成為欲望的奴隸,而這顯然是在普世價值里不容易被接受的,甚至是違背道德的。就如他在訪談里提到的對愛與性和妓女的看法:
“愛情或許是動物本能的一種回歸,它應該是在消滅類似理性、道德性、社會地位和階級之后,才開始的一種純粹感情。”
“我電影的重心在關系上,而不在性愛上。但是,我認為所謂性能夠通過火花釋放出能量,是這個社會的重要驅動力。”
“‘制度圈’教我們要靠大腦謀生,而不是靠身體。但有些人是無法靠大腦謀生的,他們只能靠身體謀生。流氓靠身體謀生,妓女也是。這其中涉及的是道德和倫理,還有生活方式的正確與否。出賣肉體雖然看似和在建筑工地上汗流浹背地辛苦勞作沒什么區別,但在當今社會中這卻被視為社會底層人物的謀生手段。我們社會有這樣一種傾向,即人們可以接受利用自己的身體去搬運物品,但卻無法接受利用自己的身體去接觸別人的身體。二者看起來的確存在著很大區別,但我卻不這么認為。如果有靠大腦謀生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存在利用身體謀生的生活方式。事實上二者沒有所謂的誰對誰錯。”
如果放下道德的條框,在這樣的作品觀下再去看金基德電影會發現,女性并非完全是他厭惡的對象,甚至是他自己的一種投射。
《欲流教室》的主演徐情也曾在訪問中提到“他(金基德)甚至把自己想象成女子”,“與其說是對女性的一種壓迫,不如說是遭到漠視和疏遠的人想跟抱有偏見的人之間進行交流和溝通。”
他電影里的女性形象,就只有受壓迫和凌辱的單一反映嗎?顯然不是的。
若是遵循金基德的作品時間線看,他作品中的女性反而逐漸在覺醒的,甚至某些女性角色在他的電影里擔當的是一種客觀上的“救贖者”功能。




《雛妓》貞與惠美,美好的妓女與冷酷的女大學生的對比,表現出女性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甚至成為溫水青蛙的境況,即便是具有反抗意識,也只停留在對這個現象產生敵視的階段,并未作出行動;《漂流欲室》的熙真有了掌握命運和愛情的意識,但她的反抗仍然停留在獲得男權庇佑的前提條件下;《收件人不詳》的恩玉則更加明顯地打了同族男性的臉,因為她不愛任何人,也拒絕任何男性的俘虜和控制,無論是選擇美軍還是享受歡愉,甚至傷害,都是自主決定的;《弓》在船上與老人生活的未成年女孩,在遇到大學生之后開始反抗和覺醒,但即便是身體達到了自由,卻依然無法擺脫倫理的束縛;《呼吸》的妍得知丈夫外遇后以超乎常人的舉動(去監獄探視囚犯)進行報復和獲得解脫,在此過程中不僅達成了自我救贖,甚至令死囚也獲得了解脫和救贖;《圣殤》里美善對殺人者(男性)精心設計的成功報復……
女性形象在金基德電影里的變化過程,某種程度上是金基德用拍電影來反抗生活的一種投射,也從側面反映出隱忍的傳統女性到自主把握命運的現代女性轉變過程,只不過實現的方式總是慘烈的。
金基德也在早期的訪問中提到,他其實并不明白“男性主義”這個詞的確切含義,而且他自己“也是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再去重復那些衰敗的、令人不悅的東西?……如果沒有女人,作為男人的我便失去了一切機能。于我而言,女性便是可以用尺量的,某種精確分明的晝與夜的對照(即男性的對立面)。就像沒有黑何言白,沒有夜晚何謂白天?”
如果籠統地把他的作品分為三個階段的話,《鱷魚》到《海岸線》為第一階段,《海岸線》至《阿里郎》為第二階段,《阿里郎》之后為第三階段。以上的分析更適用于前兩個階段的金基德,第一階段大多都是從他的過去生活中取材的;第二階段雖然是以想象展開的,但仍然能看出他的矛盾和掙扎;但到了第三階段,經歷了差點導致女演員死亡和弟子們的“背叛”,《阿里郎》后的金基德,在自卑和自傲的矛盾的牽扯中漸漸走向了失衡,變得更歇斯底里和驚世駭俗。
畢竟,他的作品一直是在男性“凝視”的角度下進行表達,而且在極端環境下的性與暴力這種“喧賓奪主”的標簽早已成為他的先入印象,女性自身的轉變顯得非常微弱。加上如今在社交媒體時代,女性意識的覺醒,擺脫男性“凝視”和對于性暴力和性安全等問題高度關注,他的表達顯然更無法被接受。特別《圣殤》之后,他的作品除了在隱喻并批判韓國社會現狀,更多地變成了波蘭斯基般的“我控訴”。

事實上,在《阿里郎》最后槍響的那一刻,那個在掙扎邊緣徘徊的金基德就已經可以說是“死去”了。
無以為家的“犯罪者”背后
可以說,電影既拯救了金基德,也反噬了金基德。電影彌補了他年少時被踐踏的尊嚴并給予了他大多數導演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榮耀,為他提供了出口的同時,也模糊了世俗約束的界限。
實際上,金基德一直都對自己的矛盾和欲望直言不諱,無論是暴力的因子還是對女性的追求。
“我自從海兵隊退役后就沒跟人打過架,因為我開始相信能夠自我克制,便已經是—種勝利。
過去的我要是對誰生氣發火的話,常會無法克制自己憤怒的殺意。因此有兩次我差點失手將人打死。”

合作過《收件人不詳》和《壞小子》的作曲家樸浩俊也曾說:“《壞小子》里強吻第一次在大街上邂逅的陌生女子,或者千方百計地接近她等,這都是金基德導演自身的經歷寫照。他在酒桌上講了很多關于女人的故事,雖有些獵奇之嫌,但故事本身不同尋常。任何人都可以那樣想,但幾乎很少有人能夠直率地講出來并付諸實踐……他喜歡拈花惹草,這在電影界已經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
時而發生的緋聞,或許還能令他的影迷“人和戲分開看”,畢竟金基德也曾好幾次提到過他的家庭以及絕不原諒流言蜚語對女兒造成的傷害。然而這種模糊和混沌到了2018年完全消失殆盡。

韓國電視臺MBC在時政節目《PD手冊》播出了一期“電影導演金基德,大師的真面目”的節目。三名女演員控訴遭受到金基德及演員曹在顯的暴力對待和性侵。
而在此之前,金基德就已經在片場扇女演員A某耳光被判罰賠償500萬韓元。A某起訴金基德以演技指導為由扇耳光,未經演員同意迫使其拍攝床戲,而金基德施暴的真正理由是其要求發生性關系被拒絕。B某控訴金基德單獨約見她的時候,連續2個小時不停地在聊性話題。C則指控金基德、其御用演員曹在顯和他的經紀人每天都去敲她的房門,三人像是比賽一樣每天嘻嘻哈哈地聊著,“因為執著于性關系,好像相比電影,這件事才是目的。”金基德的御用演員曹在顯不僅在這次節目中被控性侵,他還涉及性侵17歲未成年人的丑聞,5位受害者站出來指證他的暴行。

隨著曹在顯寫下“我懷著真心向那些因我而受到傷害的人謝罪的心情,放下一切,繼續贖罪。”的親筆信并退出娛樂圈,即使對于金基德的指控因時效和證據不足令他未獲處罰,他在韓國也已經被宣告“社會性死亡”了。再加上他后來反告女演員誹謗卻敗訴,更為他的辯解再添上了一把火。
聯系他那些總是挑戰道德邊界,尺度驚人,混沌不清的作品,“人和戲分開看”無論是對于普通觀眾還是影迷來說,其實都不太可能了。畢竟連他自己都說,“原來的我只要看到某種美麗就可能引發身體欲望,而現在,我需要的是更切實更強烈的心靈感應。其實,直到現在我還時常忍受著欲望和表達的壓抑。人們常愛說‘道’,而且也期望人人遵從其‘道’。可就在某一瞬間,我們會不自覺地翻越‘道’,甚至超越無法控制自身意識的界限。我自然也在所難免。忍耐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甚至可以讓‘罪’意識暫時消滅。”
實際上金基德等電影人的隕落,在韓國電影圈造成的影響其實比想象中更大,甚至可以說是推動韓國電影界往一個新方向發展也不為過。在2018年Me Too事件爆發后,不少電影劇組都在開拍前集體進行防止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教育;而電影界也設立了幫助受害者的相關機構,去跟進事件并為受害者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但更突出的表現在于,在男性手握最大話語權的韓國電影圈,女性電影人和以女性為敘事中心的作品有如雨后春筍般冒出。要知道,2009年到2018年10年間,每年排名前50的韓國電影中有一半女性角色有名有姓的或不超過兩個,或幾乎是背景人物,或是在全部由男性構成的集體中充當配角。連女演員都那么艱難,就更別說女導演了。
但明顯地在MeToo事件之后,越來越多的潛力女導演們開始涌現,如《我們的世界》的尹佳恩,《蜂鳥》的金寶拉,《鯰魚美琪》的李玉燮,《我們的身體》韓佳嵐,《燦實也多福》的金初熙,《82年生的金智英》金度英等。

韓國電影圈沒有了金基德算不算是種損失?算。
畢竟他的作品確實為了解韓國社會和探討極端環境下的人性作出了貢獻,打開了一扇從未見過的門,但受害者的傷痛和聲音也不應該被磨滅。
韓國電影圈在失去金基德之后是不是就黯然失色了?顯然也不。
李滄東奉俊昊樸贊郁等人依然能在海外舞臺用完全不一樣的作品大放異彩。事實上,有了創造歷史的奉俊昊,金基德幾乎就被人拋諸腦后了。
毫無疑問,分析和批判金基德也并非是為了辯解,而是對不斷前進的行業進行反思。韓國電影圈是否在失去金基德和富有爭議的電影人之后變得更好?這或許在你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在金基德難得接受的一次韓媒訪問后,沉思已久的他,最后緩緩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希望即使沒有我,這個世界也可以講述其自身的問題。”
現在可以回答他了。
會的。
但不會再有與你一樣的方式。

部分參考資料:
[1] 《野生金基德》,金基德、鄭圣一,(譯)范小青
[2] 《金基德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的自省意識》,潘騁
[3] 《金基德電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馮志英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