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方文史︱科大衛:我與地方文獻
2020年12月5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學科大衛教授以線上的方式進行了一場題為“我與地方文獻”的講座。講座由華東師范大學黃阿明副教授主持。

科大衛
回到“地方文獻”
科教授回顧他年輕的時候,在香港和國外,只能接觸到非常有限的地方材料。他上大學的時候(20世紀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清史學界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清實錄》等官方編纂的記錄,所以很多學者都是研究清政府的制度而不是地方社會。跳出政府制度,他們最有興趣研究的地方是對清政府財政最重要的地區——江南。
臺灣地區成文出版社從1960年代開始,相繼翻印了一系列的中國地方志。在這之前,地方志也不容易找到。當時,大家以為可以利用地方志探討地方史,但是,很快,不少學者已經認識到地方志其實也是非常官方的材料,而不是民間保存下來的地方文獻。當然,地方志繼續對歷史學者很有幫助,不過要先明白地方志與鄉村(“地方”)已經距離很遠了。
當年,通過閱讀傅衣凌先生的《明清時代永安農村的社會經濟關系》,知道地方文獻的存在。傅先生提到他在永安縣黃歷鄉無意中發現一批土地契約,令學者一窺使用從地方人士手中拿過的文獻做研究的興奮。當時,出版的徽州文書數量很少,直到葉顯恩先生《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一書出版,科教授才知道徽州文書里面的內容如此豐富。

傅衣凌
那個時候,不僅能看到的地方文獻十分有限,就是到中國大陸的機會也不多。1973年科教授第一次來大陸,但是根本沒辦法到鄉村行走。當時,歷史學者中,很少有人想到要研究地方上的歷史,反而都是一些人類學者在香港的新界和臺灣做田野考察,所以當時他們研究中國依賴的其實是中國邊緣地帶的材料。歷史學者用江南研究明清中國,人類學者用新界、臺灣研究中國,這種方法在今天看來可能有一些難以接受,但是鑒于那個時代的種種局限性,這已經是學者們最接近中國農村的方法了。
不是收集“文獻”,而是在地方學習
科大衛1976年畢業,1977年到香港中文大學工作。香港中文大學位于當年還有農村氣氛的新界。在新界學習鄉村的歷史,才碰到地方文獻。
科教授強調在農村學習歷史最大的優點,是可以注意到每一段文獻材料的出土背景。他以新界一個偏僻小島吉澳發現的《奉兩廣總督閣部堂大人批行給示勒石永遠遵照額例碑》為例,說明為什么出土背景資料對歷史學者重要。碑文的內容是兩廣總督在嘉慶七年的批示,回應“疍民”即水上人的申請,禁止岸上人向他們增加租用土地的租金。按照碑文所述,這些在偏遠小島的水上人,向要走兩天才可以到達的新安縣,呈交了呈文,縣政府認為事情的重要性值得傳到兩廣總督批示,然后,批示刻在碑上,放到當地的小廟。我們要知道當時這些水上人或許普遍都沒有讀書識字。這個過程,需要怎樣了解?大概當時還是有書吏替他們寫狀子的吧。但是寫狀子的人,真的需要替他們跑到新安縣衙門嗎?誰知道總督有沒有這個批文,誰知道新安縣有沒有判過這個案子?誰知道碑是否嘉慶七年立的?我們并不知道事實到底是什么樣的,唯一能知道的是有這么一個碑出現在這里,作為歷史學者,我們需要抱住這些疑問去解讀。
地方文獻包括族譜。但是科教授從一些老照片和田野所見的祠堂、祠堂里分豬肉、牌坊、碑刻、古鐘銘文顯示族譜需要放到宗族的生活里面解讀。地方文獻也包括土地文書。在香港新界,土地文書甚至可以連貫到非常詳實的殖民地時代的田土登記記錄。科教授在他發表的有關新界歷史的書(《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香港新界東部的宗族與村子》)有一章就是利用這些資料重構一個村子發展的歷史:祖宗到來住在哪里,哪些房子是哪一房的后人建筑,為什么宗族的規模就印刻在村落房屋的分布之中,其發展與村前的防潮堤壩的修建有什么關系。當然,地方文獻還包括賬本。他以一本租簿為例,說明為什么解讀賬本還是需要對地方有所了解。賬本中有一個把兩兄弟名字合并的名字。村子里面的人一看都知道這個名字代表兩兄弟,但是外面的人就會以為這個名字代表一個人。解讀地方文獻也需要懂得地方的禮儀活動。他認為他在新界的研究,其中一個最大的收獲,是可以從宗教活動中了解鄉村聯盟。宗教禮儀需要道士先生的參與,道士先生應用的科儀本,很慷慨地讓我們學者復印。但是,學者需要可以把科儀本放回宗教儀式的現場才可以明白宗教活動在鄉村生活的核心性。歷史學者在田野的目的,不是在收集文獻,而是學習村民文獻、口述傳統、儀式演繹,把歷史存留下來。科老師強調,文獻其實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專門為歷史學者而留下,因此歷史學者們要讀懂一個文獻,需要把文獻放回生活去。
在新界發現的地方文獻,只是學習的副產品。但是,在新界也實在發現不少文獻。他在新界研究找到的文獻,都是復印后把原本交還村民,同時也存一份在圖書館。現在香港的大學圖書館都藏有《新界文獻》的復印本或膠卷(20多卷)。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界大埔海下村找到的一家人三代的藏書。需要明白,到現在,學者沒有在多處發現一整批的鄉村讀書人的藏書。其中有印本,有抄本。有看風水、看相的書,也有鄉村的日用手冊,常用的禮儀文書(例如三書六禮)。有地契、有賬本、有醫書、有課本,有普及的到處可見的四書五經,也有清末民初廣東這一帶的新課本(例如民國元年的《婦孺三四五字書》,用廣東話寫的),也有單張的文件(例如《那奴及澳順島舢板水手合同章程》)。這些都是很寶貴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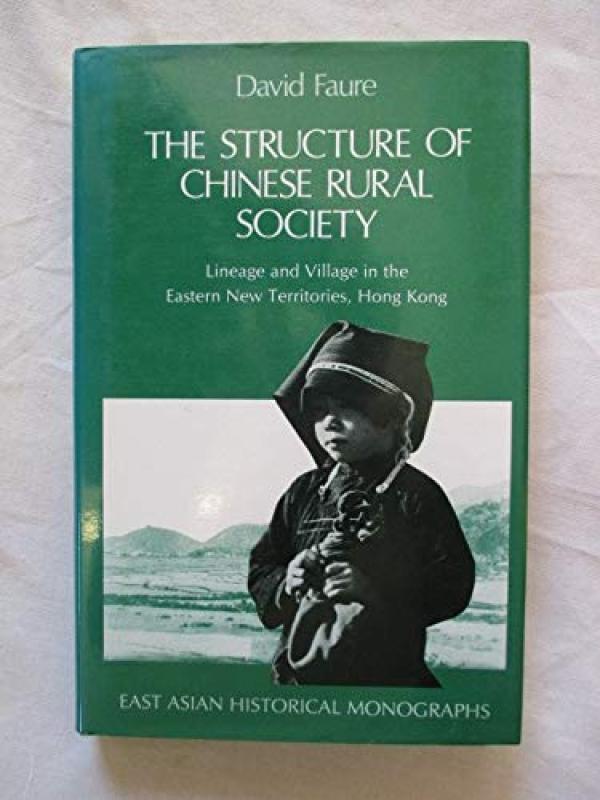
《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香港新界東部的宗族與村子》
文獻收藏:收藏者、圖書館、舊書店
研究了新界的歷史以后,科教授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繼續研究宗族的歷史。他雖然有機會跑田野,但是更多的時間其實是在廣東省圖書館。對于他而言,地方志、譜牒、碑記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除了碑記,在地方上找到的文獻不多。在番禺沙灣,地方辦公室收藏的《留耕各沙總志》和《辛亥年經理鄉族文件草部》非常寶貴。后者標題的“辛亥年”就是辛亥革命這一年。可能因為珠江三角洲在近代開發比較早,很多地方文獻流失到別處。但是,地方學者給他們很大的幫助。小欖何仰鎬先生讓他們讀他寫的《欖溪雜輯》手稿,楊寶霖教授與他們分享他收集到的東莞族譜,佛山博物館也非常慷慨地讓他看到他們當年還在整理的文物志的材料。他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是得到很多地方上的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甚至中山大學、廣東省社科院的同事種種幫忙的。
村子的文獻流失,去了哪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部分葉靈鳳先生后人捐獻的材料,其中包括一本光緒丙申修的《靈應祠田鋪圖形》,一幅一幅地紀錄佛山祖廟(就是靈應祠)的房產。很明顯,有部分流失的材料去了收藏者的手里,然后再從他們手里轉到圖書館。所以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文獻,需要在圖書館里去找。在廣東省圖書館從1930年代,已故羅鄉林教授已經有收集族譜。圖書館還有一些魚鱗圖冊、家用賬簿等等資料。他特別有印象的是新會縣景堂圖書館,收藏了好幾份行會的資料,也從改革開放開始收集當地的族譜。當時比較意外的,是在國外的圖書館找到重要的珠江三角洲地方文獻。在英國大英圖書館,找到道光十年編的《佛山街略》。這本小冊子把佛山每一條街的商業活動記下來。另外有一本《廣東名人故事》木刻版的小冊子,以趣味形式記錄例如霍韜、方獻夫上大禮議其中兩人的微妙關系。其實也不應該奇怪這些十九世紀出版的小冊子收進了國外圖書館。以前,這些印刷很粗略的小冊子在地攤上可以買到,藏書家看不起,但是外國人感興趣。另外一個有豐富廣東地方文獻收藏的地方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尤其是收藏一批廣東巡撫衙門的文書抄本。這類材料,他只見過三種。另一種收藏在廣東省圖書館,第三種香港許舒先生在舊書店找到。
有關舊書店和許舒先生,科教授說許先生是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政府官員,長時間在新界服務,對鄉村歷史很有研究,也多年來跑香港的舊書店,收集了不少有關廣東的資料。許先生很慷慨,找到資料提供給學者參考,他是受益者之一。科老師在“告別華南研究”已經提到黃永豪先生把許先生買到的地契配合到廣東省圖書館收藏的族譜寫出一本有關沙田開發的歷史。許先生還買到過一批從民國初年到四十年代的潭岡鄉鄉會董事局議案薄。這個單姓村在新會,但是在民國初年因為械斗毀掉,通過在外地生活的族人(在廣州、香港、東南亞)的協助重建,建立了鄉會。所以村子雖然在新會,鄉會卻在香港開會,新會的事務交予當地一名“司理”,長時間不斷地向鄉會報告地方情況。在這個架構之下,鄉會的會議記錄就是一份非常詳細的地方檔案。剛巧,這批文件差不多完全有正副本。許先生收藏了正本,后來捐到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科老師得到副本(沒有的,以復印本補充),副本后來去了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他用這批材料寫個一篇文章。順帶一提,他在香港的舊書店也很幸運找到好資料。《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給他很大的啟發,《葉光大堂世守書》顯示家族祖嘗過渡到有限公司的變化,《承辦廣州市糞溺大生公司息摺》他認為應該放在博物館,最后捐了去廣州博物館。
告別華南與怎樣利用離地的地方文獻
2000年以后,科老師帶著八十年代的問題,跑到華南以外的各處。比較注意的材料仍然是地方志、碑記、族譜。再沒有機會做像在新界那樣的深入研究,去過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走馬看花,但這個經驗還是非常重要的,令他知道中國各地社會的異同。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山西,所記錄的碑文對他的研究很有啟發。在當地讀碑與在出版品里讀碑的經驗就是不一樣。在山西代縣鹿蹄澗村所見到的元、明碑記,不只看到族譜刻在碑上,還見到有一行被鑿掉。為什么要鑿掉,最后連貫到一個離奇的故事,這里不多說。地方還是有文獻:江西村子的人很幫忙地拿出族譜,西南一帶的道士們也提供科儀書,但是2000年以后,隨著經濟高度的發展,村子變了,文獻也變了。這個是一個地方文獻工作者一定需要面對的問題。
近些年來學者在地方上發現大批文獻,陸陸續續把文獻在很大部頭的文獻集出版。比如貴州清水江文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徽州文書、上海交通大學石倉契約、浙江大學編的龍泉檔案。還有很多還沒出版的文獻收藏,例如中山大學的徽州文書、廈門大學與地方政府開發的永泰縣文獻、浙江師范大學的民間文書等等。對科教授影響比較大的尤其是家譜網,主要是上海圖書館與猶太家譜學會的網頁。這些在以前看來不可思議的發展,對歷史學者來說,無疑是一種享受。科教授發現,尤其是現在疫情期間,自己更多的是坐在電腦前做研究。有多少以前不到北京、東京、紐約就看不到的族譜,現在可以隨手通過電腦鉆研,更可以把族譜連貫到地方志、甚至這些最近發現的資料。這些發展把地方文獻的利用帶入另一個平臺。科教授現在正在寫一本總結這十多年來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書,這些材料對他非常重要。

上海圖書館的家譜數據庫
但是,這些資料的出現,也有它的隱憂。歷史學者從田野學習到利用現成(例如圖書館)的收藏,再到依賴出版的資料集,歷史學者與他們/她們所研究的地方之間距離拉到越來越遠。盡管可以研究的文獻越來越多,但其實歷史學者對文獻的背景了解越來越少。地方文獻脫離了地方社會,變成一種空泛的“制度”,我們很容易走回頭到建構一些誰都不知道在哪里發生過的“制度”史。
科教授說需要知道讀文獻為什么要跑田野。1,跑田野可以啟發研究者對地方的感情。2,可以增加研究者對地方的環境的敏感。3,因為會碰到在一些長時間有人連貫定居的地方,人們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知識和認同。4,因為在田野還可以看到文字資料,只有田野中才能看得懂文字資料里面有些話的意思。
接近講座尾聲,科教授對于文史機構如何幫助學者了解歷史提出幾點建議:首先,他十分感謝技術發展下,在電腦上就可以看到材料。但是請一定要保持文獻的完整性,收集資料,需要用考古學的態度,考古學者往往在研究報告中寫清楚文物如何出土,在哪里出土。文獻需要從“制度”回到“地方”,越細致越好,具體到哪個村子,村子的哪個部分。面對今天這樣一種變化,科教授對年輕學者也有一些提議。他認為帶著田野的經驗讀文獻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有了現在更充實的材料,年輕學者應該開發新的研究問題。科教授說,假如他現在還年輕,絕不會陪上一代的學者去討論那些什么國家與地方,唐宋變化之類的問題。上一代學者為沒有史料發愁,這一代的學者應該為怎樣面對讀不完的數量的史料發愁。沒有新的問題,新的資料是沒有用的。我們要通過新的問題發現新的田野,因為只要一直有人在活動的地方,歷史就沒有停止過。
黃阿明教授認為,這是科教授對他的經驗分享最為完整的一次,并認為提出新的問題其實是科教授對新一代學人提出的要求。文史研究班的成員,分別以線上、線下的方式,就如何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保存音樂等特殊體裁的文化等問題與科教授進行了交流。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