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個叫做“分水嶺”的小鎮,藏著關于油紙傘的故事
江子
【編者按】: 一把油紙傘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作者江子在四川瀘州發現了一個叫做“分水嶺”的小鎮。它位于云貴川三省交界之處,以盛產油紙傘聞名。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這里擁有大大小小上百家油紙傘生產廠,從業人員多達上萬人。然而,當機器生產開始普及時,手工制作開始失去了活力。
雖然油紙傘業已經蕭條,但在作者眼里,油紙傘已經成為了另外一種存在——它的文化意義沒有消失,它是文明的使者,是中國千年古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它改變了瀘州的氣質,讓瀘州風情萬種。
瀘州只是作者江子行走的其中一站,在《去林芝看桃花》一書中,他步履不停,前往浙江、廣東、四川、新疆、云南、西藏、福建、臺灣、江西9個地方,以自然風物為切入,娓娓道來與之息息相關的奇聞軼事,如浙江的“雙龍六帖”“梅雨潭”、新疆“賽里木湖”、西藏“林芝的桃花”、福建“五店市的馬”、江西“瑤里的月亮”“豐城的窯”等等。
作者筆觸細膩柔美,內容豐盈飽滿,不止是單薄地吟哦風景,而是以風景為線索,尋訪其背后隱著的人、物與事,讀來引人入勝。
經出版社授權,本文摘錄書中“瀘州的油紙傘”一章,一起走入這個神秘的邊遠小鎮,了解油紙傘的前世與今生。
瀘州的油紙傘
同大多數中國當代鄉村集鎮一樣,位于瀘州江陽區東南部的分水嶺鎮,是個看起來人氣并不旺的地方。據說它曾是川、黔、云三省間的商貿中心和物資集散地,可我到達時,看到的是一條長長曲折的老街兩邊,店鋪要么店門緊閉,要么懶洋洋開著的光景。街上既看不見人問價,也少有人走動。只有幾家飲食店,門口的爐子冒著熱氣,爐子上的大鍋里都煮著大塊的豆腐。正是中午時分,店里三兩人吃著,也不太說話。
我們走在街道上,總算讓街道有了點人氣。可這街道上僅有的本地人對我們的到來并不訝異,我們經過時,他們只是向我們投去匆匆一瞥,依然低頭做著自己的事。偶爾有一兩條狗躺在地上,似乎連睜眼看看我們都覺得費神。
這個集鎮給我最強烈的印象,就是植物長勢兇猛。街道兩邊常常是巨型樟樹,枝葉豐饒如巨大傘蓋,樹干要八九人才能合圍,以為是長了五六百年才有的規模,一問才只有一二百年的樹齡。從集鎮往四周望去,青山環抱,色如新漆,似乎生命的喧響無所不在,再悲傷暗淡的靈魂都會如沐春風。
然而寂靜的山溝可能是鳳凰的故鄉,表面如此冷寂的分水嶺鎮也會有風流妖嬈的一面。當當地朋友領著我們轉入了一個逼仄巷子,走進一座有著百年歷史的老宅子時,我們看到了與老街完全不一樣的景象:

分水嶺鎮不一樣的風景。 視覺中國
許多人在忙碌。他們有的在用機器把木頭裁成棍條狀,有的忙于在木棍上鑿細小的洞,有的在木棍上裝上木條,形成傘骨,有的在傘骨上纏上絲線。有的呢,往傘骨上拼貼有圖案的紙。還有的,往紙上涂上糨子……我不能詳盡地敘述他們的工作,因為我的目光所及,他們工序復雜,分工精密,指間的動作細微謹慎,有著與機器生產完全不一樣的節奏和耐心。
他們都是一些中年男女,與我在老街所見的本地人有著一樣的樸素穿著。他們也與老街上的本地人一樣無聲,可他們有著同老街上的人們的慵懶閑散不一樣的專注、靜穆。他們的表情是深遠的,好像在他們的心里裝著一個遠方。那個遠方,叫作傳統。——那是一種叫作油紙傘的古老制作傳統。
你該知道了,云貴川三省交界的邊遠小鎮分水嶺鎮,是中國漢文化符號之一——油紙傘的故鄉。
那個面積巨大的百年老宅,就是全世界矚目的瀘州油紙傘的制作工廠。

瀘州分水嶺鎮,以生產油紙傘聞名。 視覺中國
相傳傘是魯班的妻子發明的。
木匠魯班每天都要出門工作,常被雨淋。魯班妻子從門外的亭子造型得到啟示,就用竹條做成了一個像亭子一樣的東西,用獸皮搭在竹條上面,下面用一根棍子撐住。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傘。后來經過魯班改造,傘成了收攏如棍、張開如蓋的物件。
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人們借此改進了造傘技術,發明了在傘紙上刷桐油用來防水的油紙傘。
傘是尋常之物,可做傘卻是個對原料和技術要求都十分高的活計:要能撐數千次不損壞,油紙被雨水反復浸泡能不脫骨,傘頂在暴風中行走能不變形。從選原材料到成傘,要一百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嚴格的技術嚴格的質量標準。

制作油紙傘 視覺中國
位于云貴川三省交界的分水嶺鎮是個天然適合做油紙傘故鄉的所在。那里植被豐茂,到處是適合做傘托的通木,深山里的老楠竹韌性大,彈力強,非常適合做抗大風不變形的傘骨。竹木又是做油紙傘的紙最好的材料。桐油呢,印刷精美圖案的石墨呢,都可以在山上取材。
早在明末清初,分水嶺鎮的人們意識到自己的資源優勢,開始研究油紙傘的制作技術。幾乎是同時,瀘州人開始生產日后讓瀘州聞名遐邇的瀘州老窖。
分水嶺鎮人上山挑選最好的木頭和老楠竹。分水嶺鎮人在經過防腐處理的木頭和竹子上鉆孔、拼架、穿線,精心布置用于抵擋雨水的各種小小的機關。分水嶺鎮人在紙上畫上最好看的圖畫——在這張圓形的、與天空對話的紙上,分水嶺鎮人展開自己的想象,畫上臉譜、山水、花鳥,畫上對生活的贊美與祝福,并給紙涂上最好的桐油……

分水嶺鎮人上山挑選最好的木頭和老楠竹制作油紙傘。 視覺中國
天然的資源優勢,和分水嶺鎮人的勤奮刻苦,也許還包括分水嶺鎮有十分好的地理優勢——處于云貴川交界,是三省物資集散地,分水嶺的油紙傘迅速游走四方,盛開在中國雨水橫斜的天空下。
無法再現400年前瀘州分水嶺鎮家家生產油紙傘的盛況。有一組歷史數據可以窺見一斑: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靠近瀘州小市碼頭的珠子街是當時瀘州的“油紙傘一條街”。極盛時期,瀘州境內共有大小油紙傘生產廠家100多家,從業人員上萬人,年產紙傘2000萬把。無疑,瀘州最先制作油紙傘的分水嶺鎮是其中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分水嶺鎮人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把滿山的草木做成了美的產業,讓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原本處于三省邊緣地帶的瀘州管轄下的蕞爾小鎮。

珠子街是當時瀘州的“油紙傘一條街”。 視覺中國
可以說,瀘州,是油紙傘天然的T字舞臺。
被長江和沱江滋養的瀘州,植被豐茂,萬木蔥蘢。我去的時候正是9月,在瀘州坐車沿途所見,田野,山林,街頭,巷尾,到處是水潤潤、油汪汪的綠色,天地間似乎一片枯葉也沒有。
瀘州地處四川盆地南緣與云貴高原的過渡地帶,是個地勢空間上高低落差不小的地方。無論山區城鎮,地面俯仰峭拔、轉彎抹角、變化無窮。我所住的酒店為江陽區南苑酒店,滾滾的長江就在不遠處,卻如谷底之豹,與酒店的地勢有百米的落差,需低頭才見。從長江到酒店,中間好幾條路蜿蜒曲折,車流人流輾轉攀升,有著平原地帶難得一見的崎嶇與宛轉。
如此的地形地貌,加上一把油紙傘,瀘州就風情萬種了,就如詩如畫了。想象著雨水橫斜的日子,有人撐著油紙傘從低處緩緩走上高處,仿佛是一朵彩云徐徐出岫。那駕著彩云的人,肯定就仿佛妙曼的仙子,她的面孔在傘下隱沒,她撐傘的手涂著蔻丹。或者,遠遠地看著一個人撐著油紙傘,從高處徐徐走下低處,山坡橫斜,四周皆綠,彩色的傘與綠色的環境,撐傘的人與山坡,構成了色彩和幾何意義上的視覺之美。街頭的拐彎處,古老的巷子盡頭,陡然出現一把色彩飽滿、雨水在上面唱著圓舞曲的油紙傘,連天空都會為之迷醉。
沒有油紙傘,長江邊的瀘州就只是一座酒城。的確,瀘州老窖的名聲太大了。走進瀘州,到處是瀘州老窖為主角的店鋪和廣告,到處是飲酒的雕塑。那些雕塑里叫不出名字的飲者,或側臥或斜立,手里舉著向天的酒盞。一旁的長江和沱江,感覺也步履趔趄,醉態百出。
酒讓瀘州充滿了陽剛之氣。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瀘州就是一座雄性十足又浪漫風流的城市,一座容易讓革命家、浪子與詩人流連忘返的城市。20世紀20年代,劉伯承在瀘州發動了起義及朱德在瀘州駐節,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是油紙傘改變了瀘州的氣質。她告訴世人,瀘州除了散發著白酒的迷香,還有油紙傘的風情。油紙傘,讓瀘州在擁有了酒的灑脫陽剛之后,透著古典的陰性之美,充滿了女性的柔情與蜜意。

家庭作坊,制作油紙傘。 視覺中國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瀘州的油紙傘業開始冷寂起來。漫天的雨水澆灌,分水嶺鎮的人們開始發現自己無所事事、內心虛空。看著雨水中鋼架傘擁塞了街道,分水嶺鎮人的心是迷茫的。許多人心懷著失落離開了油紙傘制作現場,去了遠方。仍有人堅守原地,守護著這祖宗傳下來的手藝。
機器生產使油紙傘失去了實用的那部分市場,可是油紙傘還有另一部分堅韌的存在。油紙傘除了是使用的傘具,還是文明的使者,是千年漢文化的重要部件。試想,如果沒有了油紙傘,旗袍會不會覺得孤獨?那些淌著雨的江南小巷子,會不會過于空曠?《白蛇傳》里許仙與白蛇娘子西湖斷橋邊的愛情,怎么開始?戴望舒的經典詩歌《雨巷》,會不會變得平庸?
在漢語的中國,油紙傘含義豐富。它意味著繁衍。客家方言中,“油紙”與“有子”同音。從字形來看,繁體的傘里有五個人字。故過去女性婚嫁,女方通常會以兩把油紙傘作為陪嫁,以祝福新婚夫婦早生貴子。它意味著平安。它是進京趕考的書生或走馬上任的官員的護身符,在中國古代,趕考的書生與上任的官員背上包袱里除了衣物與書籍,一定會帶一把紅油紙傘,即“包袱傘”,又稱“保福傘”,以求仕途平安、獨占鰲頭。即使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有親朋、家長、同學給高考的學子送一把油紙傘,預祝成功。它意味著圓滿。傘面張開是一個圓,是人人喜歡的象征人生圓滿的祝愿之物。它意味著吉祥。在許多地方的習俗里,油紙傘所用桐油有著驅鬼、辟邪、納吉的功效。所以,家家要用傘來保風水、驅邪氣。油紙傘還用于道教典禮及祭祀等方方面面……
分水嶺鎮人重新審視了油紙傘的文化意義。他們紛紛回到了油紙傘的生產工地。他們上山采來了上好的楠竹,重新開始在通木上挖孔鉆洞,精心布置一個個機關。他們在傘面上描花繪朵:畫一棵黃山不老松,祝有德行的人壽比南山;畫一個龍鳳呈祥圖,祝福新婚的人們恩恩愛愛;畫一個雙龍戲珠圖,祝福那新生的人兒快樂幸福。他們在分水嶺鎮的上空掛滿了油紙傘,這是他們的野心:他們要讓天空也變得生動與吉祥。

瀘州的油紙傘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視覺中國
分水嶺鎮從事油紙傘制作的人從手藝人變成了文化人。——他們的油紙傘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國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一個叫畢六福的鄉黨,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油紙傘制作技藝國家級唯一法定傳承人。
——穿行在那座被當作油紙傘制作工廠的百年老宅之中,我立即成了有福之人。我看到的每一個人臉上都寫滿了靜穆和良善——那是被傳統浸潤日久的靜穆和良善。我得到了無數的祝福:那油紙傘上面的牡丹、龍鳳、花鳥、山水,都在祝福我幸福平安健康美滿。我有理由認為這里的每一個人都叫畢六福——對傳統畢恭畢敬,愿人生六六大順,福氣滿滿,這是一個多么好的適合于所有油紙傘從業者的名字。
走出那座作為油紙傘生產基地的百年大宅,外面是用數十把大大小小色彩圖案各異的油紙傘串起的天空。天上的光在傘間如同嬰兒,躲閃雀躍,仿佛做著快樂的游戲。我可以發誓,那是我見過的最美的彩色天空。

瀘州油紙傘 視覺中國
離開瀘州回到家后不久,瀘州的朋友給我寄來了禮物:一個紙箱子里有兩瓶瀘州老窖,還有瀘州的特產蓮子、桂圓干,然后是一把油紙傘。
那是一把很小的傘。它是紅色的,傘面繪的牡丹,牡丹旁用行書寫著“天香國色”。這把傘太小了,傘面比八開的報紙還小,小得就像是一個傘中的嬰兒。那些紙面下細細的傘骨,仿佛初生的嬰兒細細的骨骼。
我立即撐開了這把傘。分水嶺鎮聞到的桐油味道撲鼻而來。我立即被分水嶺鎮乃至瀘州的山水及400多年分水嶺鎮制作油紙傘形成的傳統所裹挾、包圍。我的宅子似乎被吉祥的霞光鋪滿。
我把這把小傘放置在我家的電視機旁邊,希望它護佑和祝福屏幕內外所有的人。我無端地認為,這小小的嬰兒是有生命的,它會長大,會在我們出門的時候,獨自在家旋轉、跳躍、翩翩起舞,把祝福灑滿我家的每一個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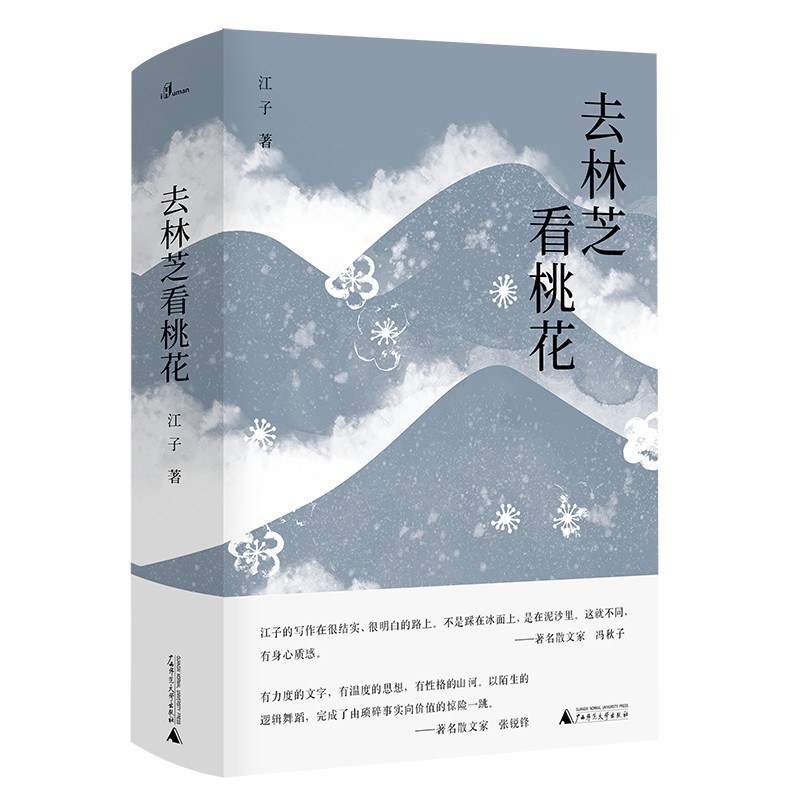
《去林芝看桃花》,江子(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