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張生: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內部分層
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難民失去了中國政府保護,面對屠殺、強奸和搶劫,只有少量歐美人士可以依賴,南京國際安全區最多時收容了約25萬中國難民。而日軍在“屠殺令”存在的前提下,其犯罪是普遍而蓄意的。所以就整體而言,中國難民都是日軍制造的浩劫的受害者,無論貧富貴賤。
然而,南京國際安全區是南京淪陷后“空位期”特殊的空間區域,其存續,一依賴僑民的人道精神和與中國人民休戚與共的決心;二依賴當時處于中立地位的歐美各國及其設定的條約利益;三依賴日軍方面措辭含糊的默許。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同于和平時期的政府,也不是正式意義上的“國際組織”,沒有國際條約賦予其合法性和權力,沒有司法、行政能力和資源來保護平民生命財產安全,也沒有實際力量制止日軍暴行。它發揮作用,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認可和合作,包括日本對英、美、德等國耐人尋味的忌憚。也就是說,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有一定的能力,然而有限。有限的能力投射到安全區管理中,使得中國難民就個體而言,在死亡威脅和戰爭暴行面前,處境不完全相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生命和財產安全受日軍威脅的程度不同,受歐美人士庇護、救助程度不同,居住環境不同,食物結構不同,劫后際遇不同,等等。處境不同,結果也不同,中國難民在死神面前,并不“平等”,內部由此出現分層,并影響到南京大屠殺的具體歷史面貌和結果。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壁畫
一
造成中國難民命運不平等的因素,一是身份,淪陷前擔任官方職務或系社會精英的,得到特別關照;二是與南京歐美人士的關系,與他們存在傳教、教育、商務、主仆等各種關系的,視密切程度,得到相對好的安排;三是所處空間,安全區占當時南京市區面積的八分之一,其中歐美人士只有二十幾人,無力進行全覆蓋、實時性的庇護,結果在歐美人士比較方便顧及的地域,難民受到更多照顧;四是難民自身與教育程度、認知水平、生活經驗等有關的自我保護能力和具體作為;五是難民自身的財產狀況。
這些差異因素,是歷史的客觀,由此而造成難民中的“特殊群體”。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位于小粉橋1號的住宅,是安全區的一個難民收容所。其中住著三名特殊的難民。一位是中國空軍機長,化名羅福祥,真名汪漢萬(音譯),曾擊落日機,南京淪陷時生病,未能過江,翻城墻進入安全區,住到拉貝家里,平時并不露面,甚至在拉貝日記中長時間未出現。1938年元旦,露天住在拉貝家院子里的602位難民逐一簽名向拉貝表示感激,該機長也未出現。拉貝乘英國“蜜蜂”號炮艇離開時,將其偽裝成自己的仆人帶出南京,才在日記中點明其身份。另外兩位是國民政府方面的官員龍先生和周先生,他們攜帶巨款,捐給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南京國際紅十字會5萬元。他們經常給拉貝仆人小費,還向拉貝個人捐出5000元,拉貝轉交給了國際委員會。拉貝住宅由其親自照拂,日軍雖多次闖入,但止于院中,上述三人幾乎沒有遭遇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脅。另有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和軍醫蔣公穀,因照顧傷員,來不及撤退,先是在美國駐華大使館躲避,身份外泄后,得貝德士和金陵大學徐先生幫忙,入住漢口路9號,“上面掛著是美國旗”,并有安全區總稽查施佩林關照,雖時日日警惕、一夕數驚,到底未受傷害。他們少數幾人的處境,屬于最好的一類。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女士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負責人美籍人士魏特琳的主要助手之一,她整天跟隨魏特琳,沒有受到日軍屠殺搶劫的直接威脅,而從其食物結構可以看出她的處境不同于一般難民。1938年1月18日程瑞芳日記寫道:“昨日大使館(筆者按:指美國大使館)送兩只雞、十二個雞蛋,是送華(筆者按:指魏特琳,魏特琳中文名為華群)的。學校的雞蛋只夠華他們吃的,我的小孫子一天有一個,其余的鄔(筆者按:指鄔靜怡,金女大生物學教師,參加金女大難民收容所工作)留下養新雞。我們有這些東西也算不錯,不算是真難民。”正因為如此,程瑞芳在日記中坦承:“我們做難民很不錯,較別的難民好幾陪〔倍〕。”1938年2月1日,程瑞芳收到了從上海寄來的青菜以及蘋果、橘子、糖,她十分滿足地說:“做難民還有這三種東西吃,不是特別難民嗎?”處境類似程瑞芳的,還有魏特琳的助手陳斐然,拉貝的管家和助手韓湘琳,拉貝家的司機、廚子等仆役,各難民收容所的中國負責人,等等。
當然,“特殊”難民的安全也不是普遍、絕對的,像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的負責人齊兆昌就險遭日軍殺害;而曾得到貝德士親自照拂的會日語的劉文彬,最終在貝德士家中被日軍抓走殺害。
“特殊”難民通常是有文化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被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重視,被委任在各層次的分委員會中,或擔任西方人士的助手,他們的事功或多或少地被記錄在案。他們自身也具有記述和表達能力,蔣公穀、程瑞芳有日記體記述留世,韓湘琳有口述歷史,住房委員會的許傳音戰后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這些人不僅記錄了個人親歷、目擊的南京大屠殺歷史,而且不同程度地剖析了面對大屠殺時的心路歷程。他們在歷史中有一定的顯性度,其經歷已經被自覺、不自覺地設定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標識”。相比于他們,“普通”難民是歷史中面目模糊的“常人”,而其境遇整體上更形竭蹶。
二
難民收容所中的“普通”難民,處境更為凄慘。殺戮司空見慣,性暴力無處不在,搶劫隨時隨地。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1938年1月21日向南京美國使館通報了得自英國方面的秘密情報,情報稱,“緊隨日軍進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館的官員們,看到日軍在難民營內外公開地酗酒、殺人、強奸、搶劫,感到十分震驚。他們未能對軍官們施加影響,后者漠然的態度很可能出于把放縱士兵作為對這座城市的懲罰,而且由于軍隊的控制,他們對致電東京要求控制軍隊感到絕望,日本大使館官員們甚至建議傳教士設法在日本公布事態真相,以便利用公眾輿論促使日本政府管制軍隊”。德國駐南京大使館政務秘書羅森報告說:“每晚都有日本兵沖進設在金陵大學院內的難民營,他們不是把婦女拖走奸污,就是當著其他人的面,包括當著家屬的面滿足他們的罪惡性欲。”美籍教授貝德士報告說:“在全市范圍內,無數家庭不管大小,不管是中國人的還是外國人的,都同樣遭到了掠奪。下面的強行掠奪的例子尤其無恥,收容所和避難所的眾多難民在遭到日軍的集團性搜查時,從僅有的攜帶物品到錢和貴重物品都被搶走了。”
同時,即便是“普通”難民內部,亦有分層性的具體狀況。據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1938年3月到6月的調查,“在3月份的經濟條件下,‘食物’和‘僥幸’幾乎成了同義語。窮一些的人家實際上已經吃不到蔬菜和食油,肉和水果就更談不上了。除了少數人家能弄到面粉外,其他人家都靠大米生活”。“就這個城市的所有地區而論,居民中17%的人是從施粥棚里取得大米的(免費或是象征性地收一些錢);64%的人是從小商販那里買米;14%的人在自治委員會(Self-Government Committee)經營的商店買糧;5%的人是通過‘其他方式’,所謂‘其他方式’,是借助于朋友親戚接濟,……在難民營里平均有82%的人從施粥棚里取得食物,這些人很明顯處于城內的最底層。”
安全區為“普通”難民提供食物的具體狀況,見諸多位親歷者的記憶。李景德回憶說,當時美國人“一天給我們吃三頓老米粥,老米粥厚得很,大鍋煮的,是美國人救濟的,每個人還發幾個蘿卜干子”。孫東城亦回憶說:“金陵大學里面發放稀飯,很稠,一天兩頓,上午九點半,下午四五點,一個銅板可以打一小鍋,夠五六個人吃的。”陳桂英當時避難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因怕被日本兵強奸,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她說:“這里一天管兩頓粥,大家各自拿著碗去操場領粥,領了粥馬上躲進屋子。”
安全區內“普通”難民的苦難,超出和平時期人們所能設想的程度。拉貝1937年12月30日日記記載:“在我的收容所(所謂的西門子難民收容所)的草棚里,在污泥垃圾中,過去的兩個夜晚出生了兩個嬰兒:一個男嬰和一個女嬰。不能為產婦提供別的棲息之地,我真感到慚愧。沒有醫生,沒有接生婆,沒有護士來幫助這些婦女;沒有包扎用品,沒有襁褓,只有幾塊骯臟的破布,這就是父母為新生兒留下的全部東西。”
窮苦,摧毀了一些貧苦難民的道德感。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三聯隊第一大隊的鬼頭久二說:“有的女人是自己從難民區走出來,用自己的身子換大米。”1938年1月2日,日本婦女國防后援會三人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那三個女鬼走時拿出幾個霉蘋果和[一]點糖,那些中年難民都圍著要、搶著要,她們手上拿著幾個銅板,在她們手上搶,簡直把中國人臉都丟完了”。貝德士為此論述了難民們在生存和道德之間的兩難,他說:
有大量普通勞工從事軍需與運輸服務,還有滿足士兵各種需要的社會不正當行業。我早已不愿譴責一個苦力,他替祖國的敵人服務只是為了養活自己的孩子,或是一個姑娘為了免于饑餓而做任何事情,只要他們不給別人帶來太多直接的傷害(譬如參與武裝劫掠或販賣海洛因、嗎啡等)。因為高尚的道德難以抵御生活本身的基本需要,戰爭早已給我們帶來數以百萬計的經濟的與社會的破壞。我們現在偶爾可以看到官方報紙刊載的規模很大的公開妓院的廣告。一個全新的厚顏無恥的少女人群,在餐館當女侍,開了南京“風氣”之先河。
三
在一般的哲學和文化意義上,人類在死神面前是平等的。而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難民面對死神的“不平等”,不僅存在,而且與條約體系下的外國權益存在關聯,其內含的歷史痛楚和諷刺是多重的。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使用的房源主要是作為美國產業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離開南京的外國公司和外籍人士的房屋,戰前建成、主要供國民政府要人居住的“新住宅區”,等等。在歐美人士眼里,外國產業和住宅有國旗、保護通告等加持,事前由各國使領館通知了日軍,安全度要高一些。德國人士對其國旗的象征意義尤其自豪,克勒格爾就說:“德國國旗比美國的更受尊重。”所以,與各國有著各種關系的中國難民就被優先安排進這些房屋,他們的處境,開始時是優于那些“普通”難民的——據程瑞芳日記記載:“今晚由國際委員會回來,在路上許多人由城南搬到安全區,有的人找不著房子,在路上睡。”但日軍并不以難民們身份和關系上的差別為標準而有選擇性地實施暴力。
施佩林報告說:“德國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著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還有他們的妻子。日本士兵幾乎每天都闖進去,對德國人的財產進行洗劫和破壞,以極其卑鄙的方式強奸他們的妻子,公司代理劉先生的妻子哭泣著喊救命,她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她們跪在地上請求我幫助她們擺脫這些野獸的魔爪。——我把這兩個家庭收容進了我的房子里。”安全區1937年12月19日的檔案記錄了另一個案例:上午8點30分,美國傳教士費吳生的司機李文元一家被日軍搶劫,他們家8口人住在珞珈路16號德國人的房子里,門上有納粹卐字旗,仍被搶走7箱衣物、2簍家庭用具、6床羽絨被、3頂蚊帳、吃飯碗碟和50元現金,陷入一貧如洗的境地。
德商代理,傳教士司機,在當時確屬“特殊”身份,也意味著他們本屬南京的小康之家(李文元家的有些被劫財物如羽絨被當時甚至可以說是“奢侈品”),但日軍暴行,抹平了他們與最貧苦者的“不平等”。侵略者的犯罪造成異樣的“平等”,構成了另一重諷刺。

約翰·拉貝(John Rabe)在南京大學校園里的故居。
四
無論如何高度評估當時南京歐美人士的重要性都不為過,時人刀尖下倉促寫成的文字已褒揚了他們的歷史性貢獻。程瑞芳說:“所幸還有兩個德國人在此,光是美國人不行。現在幾個美國人也無法可想,也累死了,換一句話說,若不是幾個美國人在此,中國人也只有死路一條。”也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南京歐美人士的睿智和高尚,正如美國教會人士引用《波士頓環球報》對南京美國人士的評價所稱:“日本人進攻南京時,一小群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組織了安全區委員會,希望創建一個非軍事人員可以免遭攻擊的聚居地。委員會成員是大學職員和差會成員,他們是教授和教區牧師。這是一個非常理智的組合。正是這些舉止優雅有修養的人,出現在文明遭到破壞的地方和當口。”
但是,比較當時南京的中國難民和歐美人士,其中的“不平等”同樣存在,而且如果與中國難民內部的“不平等”對照,更能映照出當時中國悲劇的深刻和蒼涼。
食物是不大被論者注意的環節。1937年12月23日美國傳教士馬吉在致夫人函中,詳細描述了他們的食物,他說:
每天我們都吃稀飯,以節省些大米,一個大問題是蔬菜和肉非常少。日本人幾乎把一切都搶走了。……我們還有一盤咸肉,咸肉是范家在我們搬到市區時從下關帶來的。另外還有一些白菜。……我們各自的存貨都帶去了。福斯特家有許多存貨,夏天,他們的廚師貯存了許多壇水果和豆子。……
今晚我們吃了稀飯、花生、腌菜、大白菜和豆腐乳。這對我還行,因為我偶爾還能吃到西餐,但對這里的中國人來說真夠嗆,幾個星期來他們一直吃這樣的食物,但能有吃的我們已是感恩不盡了。
歐美人士顯然同樣面臨食品短缺,魏特琳在這一天也記錄道:“現在食品越來越少,我們已有好多天沒有吃到過肉了,現在街上根本買不到任何東西,就連雞蛋和雞也買不到。”腥風血雨中,他們對能夠有食物可吃已經心滿意足。1937年圣誕節,他們舉行了一次有燒豬和甜土豆的盛宴。偶爾也有驚喜,1938年1月15日,日本大使館舉行了一次“便宴”,邀請留寧的部分外僑參加,希望他們為日軍“說好話”。出席這次宴會的外僑有拉貝、魏特琳、鮑恩典、貝德士、米爾士、史邁士、特里默、克勒格爾、馬吉等。宴會上的食物十分豐盛,魏特琳說:“晚餐與這些客人一樣,也具有各國的風味,有中國菜、日本菜和西餐。”拉貝在日記中也寫道:“便宴上的菜肴是第一流的,有中國美味可口的牛肉、雞蛋、粉絲火鍋等食品,有歐洲式的蘆筍,還有米酒和紅、白兩種葡萄酒。我們很久沒有吃過這些好東西了,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番。”
歐美人士救助中國難民,也經常冒著生命危險。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美國傳教士麥克倫和鼓樓醫院醫生威爾遜都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骨干,均曾被日軍持槍威脅,麥克倫脖子還被日軍用刺刀扎傷。基督教青年會干事美籍人士費吳生因為目睹暴行和身體勞累,一度失憶。魏特琳女士因為日軍暴行,抑郁癥反復發作,最終自殺……中國難民記憶中的他們,始終是救命菩薩的形象。所以,對于南京歐美人士相較平時已屬簡單、對比難民仍屬豐盛的伙食,他們較好的住宿、交通條件,當時南京大屠殺中國親歷者們留下的所有資料中,沒有任何人進行道德審查,過事苛求。作為中國難民心目中的英雄,他們相對優越的生活顯然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對中國難民來說,歐美人士是更“高”的存在——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在文化、精神上亦如此——他們面對日軍和日本外交人員的不卑不亢,日本人對他們的敬畏,給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中國難民向西方人士提出請求時,往往跪倒在地,哀聲慟哭,西方人士是被中國難民仰視的對象。日軍暴行甚至都沒有抹平中西人士同時面對死神時的“不平等”,這是另一個層次的悲劇。
余論
需要指出的是,大屠殺中,中國難民處境的優劣是相對而言的。正視難民內部分層的存在,有助于我們更加精細地觀察大屠殺時期的南京;而過分夸大其間的分別,則會低估日軍作為全速開動的獸性機器的普遍性摧毀力。戰時客觀存在的難民內部分層,不同于和平時期社會分層導向人口社會流動、公共產品提供、政府政策調控等問題的討論,它主要揭示了戰爭環境下人之存在的豐富側面。
大屠殺期間的難民內部分層,可以作為觀察整體歷史的透鏡。宏觀者,其時中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低下,條約體系在中國近代國家演變、整合過程中的復雜作用,作為未完成近代化、動員程度低、管理能力差的國家,國民在戰爭中承受不能承受之重時政府之缺位,等等,被放大呈現。微觀者,南京大屠殺慘烈程度在空間、時間上的相對不同,住房、食物等久被宏觀敘事忽略的細節,和平時期“先在性”社會分層在戰爭環境下的“帶入”,等等,被顯微“凝視”。對難民內部分層的關注,可以作為切入南京大屠殺史更深層面的楔子,并為以社會史、人類學、環境史等跨學科方法進入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開辟路徑。
(本文摘自張生著《發現歷史:范式轉換與路徑選擇》,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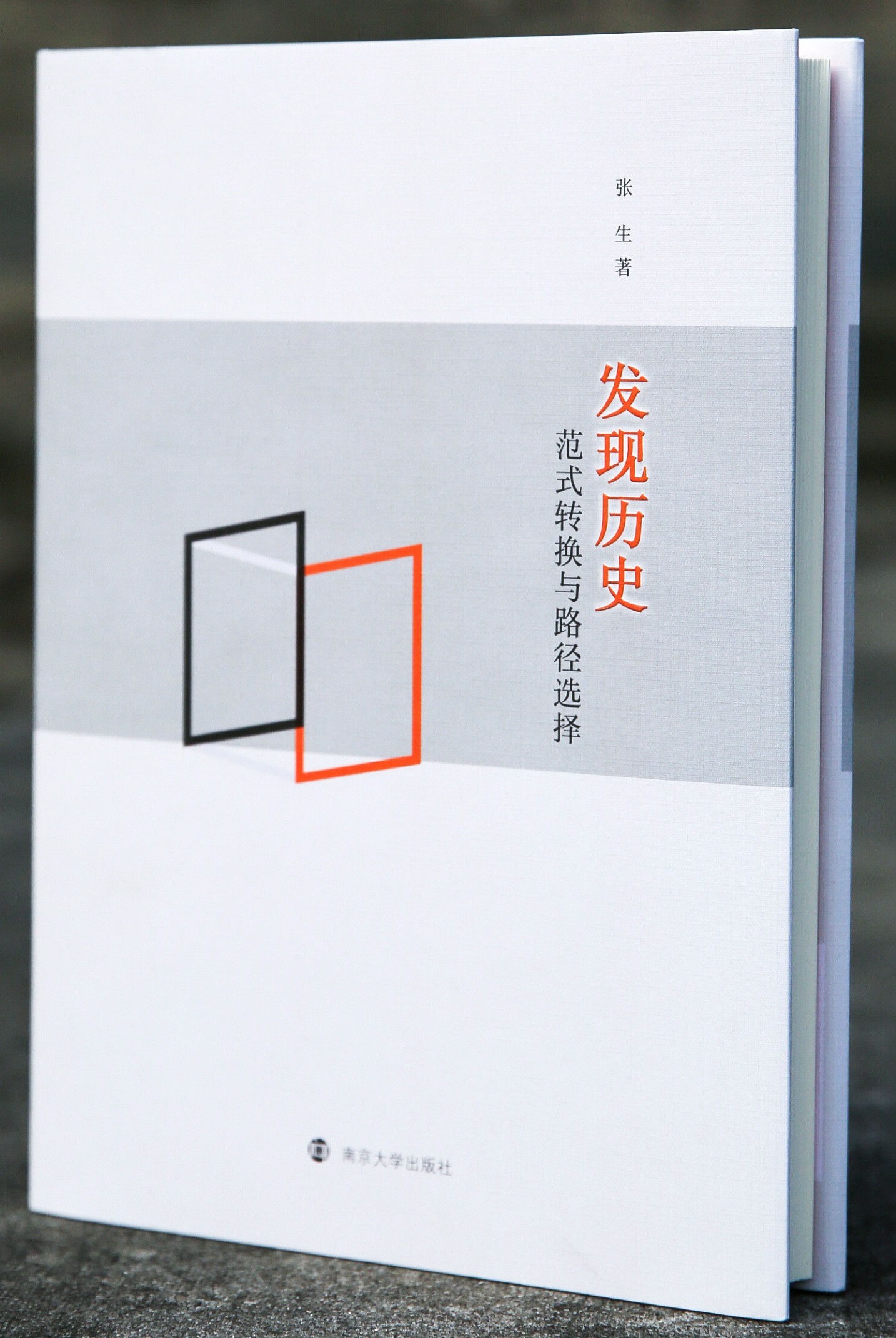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