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影像民主化時代到來?手機之于電影的意義
男人正在洗臉,急促的敲門聲響起。男人漠然地擦完臉,開門。他并未走出門去,身著防護服的醫護人員拿著體溫槍為他測量體溫。此時正值疫情爆發期間,男人與妻女都在酒店隔離,這已經是隔離的第十天……這是疫情期間常見的故事,它來自青年導演陳碩執導的5分鐘手機電影《慢車開來》。在今年的第14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下簡稱FIRST影展)上,vivo與FIRST聯合開啟了全新展映單元“超短片單元”。在合作基礎上,vivo與FIRST聯合邀請導演楊慶,通過vivoX50系列手機為超短片單元拍攝開幕片;此外,vivo也向陳碩等一批青年創作者提供設備(vivoX50系列手機)和費用支持,幫助他們完成作品創作。這一系列短片共同組成了以“不虛此刻”為主題的手機短電影,其中,《慢車開來》獲得了“超短片單元”組委會特別推薦大獎。
《慢車開來》沒有復雜錯綜的人物關系,沒有浮夸華麗的布景,沒有夸張刻意的臺詞,一切都顯得簡單質樸,卻意味深長。男人的內心世界清晰展現,他從漠然、封閉、孤獨中一點點出來,一次意外的發生,終于讓他突破內心隔閡。這個5分鐘的短片具備飽滿的情緒和多重解讀空間,或是人的孤獨,或是中年情感危機,抑或是親情故事。而在疫情這個特殊背景下,時代性與個人性交織,讓這部短片的底蘊變得更為豐厚。
如果沒有事先提醒的話,觀眾很難看出《慢車開來》是一部手機電影,因為它的電影感與數字攝像機拍攝的電影別無二致。《慢車開來》全程用黑白色調拍攝。黑白畫面對光線要求更嚴格,人物與場景在最佳光影對比之中達到平衡,得益于X50 Pro定制了專業Color Filter色彩濾光片,對色彩濾光片和傳感器整體做了調整與優化,將黑白影像的精簡洗練和意蘊無窮,體現得淋漓極致。影片全程使用電影人像濾鏡,vivo X50 Pro的智能追焦也引導著觀眾沉浸于主角的情緒之中。
張弛導演的《美神》,則讓我們看到了手機電影的另外一種風貌和可能。美術館中,新老兩個保安在進行工作交接。老保安通過電腦監控視頻看到場館里有一個“闖入者”,一個年輕女性面對著一個雕塑作品輕盈地翩翩起舞。《美神》充滿實驗性、神秘性和多義性,它讓我們感受到手機電影雖然短,卻可能像是李商隱一首精巧的小詩,隱晦迷離、難于索解,又錘煉嚴謹、沉郁頓挫。無論何種解讀,觀眾都能感受到美對人的召喚。無論是神秘的闖入者,看上去呆板的新保安,吊兒郎當、口是心非的老保安,還是新保安心心念念但眼睛看不見的妹妹,美對他們都有吸引力,美不需要階層和門檻。美神面前,人人平等,懷揣真善美的人們,會感受到美的圣光。《美神》同樣由vivo X50 Pro拍攝,在場景轉換和鏡頭調度上,它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并不遜色于大銀幕電影。vivo X50 Pro搭載的超穩微云臺實現“立體防抖”,防抖性能兩倍提升,完美呈現藝術品與人之間的微妙共鳴。
隨著手機攝影功能的不斷進化,手機攝影與數碼攝影機之間的差距正不斷縮小,手機電影日趨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創作實踐。人們對手機電影的另一個擔憂在于:手機電影會否破壞電影的“電影感”?電影感決定了何謂好電影。如果觀眾此前對手機電影的電影感有所懷疑,vivo與FIRST影展聯合呈獻的“超短片單元”,足以讓我們刮目相看。除了《慢車開來》與《美神》外,楊慶為該單元執導的開幕片《當我們決定放棄的夜晚》,整部片子用一部手機拍攝,沒有任何外界的設備也沒有其他附加的東西,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用一個五分鐘的長鏡頭表現,但它在色彩、亮度還原上穩定,焦點的控制準確、快速;青年導演何梓源創作的《傷停補時》,敘說兩個小孩離別前的最后一場足球賽,無論是追逐中的奔跑還是嬉戲時的玩耍,手機在拍攝運動時鏡頭并沒有抖動,反倒因為鏡頭的輕巧靈便,運動場面行云流水。
隨著手機迅速地更新迭代以及5G技術的發展,我們甚至可以想象,手機電影能否充實電影的美學體系,并形成一套屬于移動設備的質感與美學體系?就像德國哲學家Walter Benjamin在《講故事的人》中談到的,神話傳說、講故事的口傳文學以及詩歌,是游牧文明、農業文明以及商業文明的早期階段的代表性文體;小說是從商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代表性文體;影視則是工業文明發展到較高階段以及后工業文明的代表性文體。顯然,傳媒的任何一次變化,都會引起藝術本身革命性的變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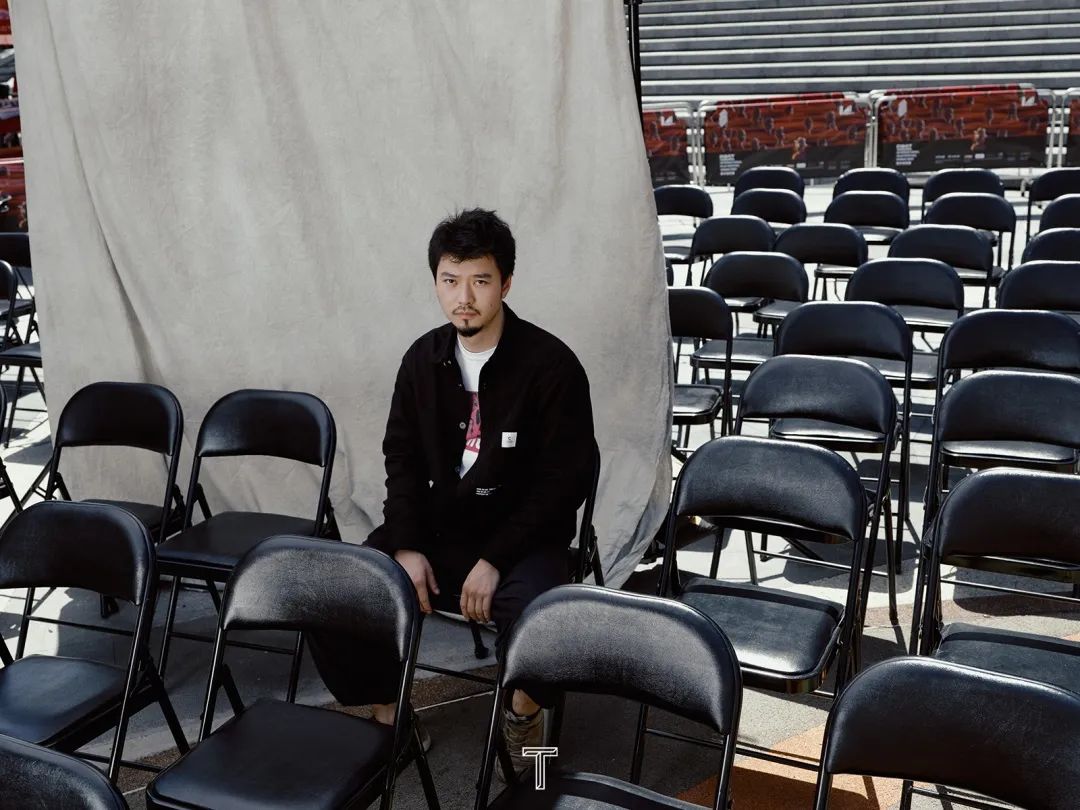
這一次“超短片單元”,很多導演是第一次使用手機拍電影。度過一開始的輕微不適后,他們很快游刃有余,并發現手機電影的別樣精妙。在《美神》導演張弛眼中,手機在他手上就像是一把水果刀,進入之后,特別順滑爽快,給他的即興創作和臨場發揮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什么機位都可以盡情嘗試。張弛說:“因為原來拍的人、機器、設備非常多,突然冒個想法,他們會覺得你不太好實現,手機確實非常放松,非常輕松,這個機位再來一下,那個機位再來一下,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把創作還給導演,讓更多的時間都留在創作上。”由此觀之,手機的邊界性、靈活性,或能讓手機電影的語言更具主觀性和即時性,更為輕巧多樣。
可以說,在技術層面上,手機電影的電影感與傳統電影的電影感并沒有太過懸殊的差距。在內容層面上,手機電影經常遭遇的一個非議來自于它的“短”,手機電影幾乎都是以短片形式出現,今年FIRST影展的“超短片單元”也限時5分鐘。跟長片相比,短片是否意味著內容和深度上也打了折扣?事實上,電影就誕生于短片。“現代電影之父”盧米埃爾兄弟早期在巴黎大咖啡館反復放映的《工廠大門》《火車到站》《水澆園丁》等10余部作品,都是短片。電影誕生之初,囿于技術手段、放映設備等局限,短片是電影的唯一形態。電影長片普及之后,短片創作也依然繁榮,短片是很多初涉電影的青年導演展示才華的窗口,很多知名電影節都有短片競賽單元,很多知名的電影導演就是因為短片而被發掘的。因此短片與長片的差別,近于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的差別,更多的只是篇幅上的不同,就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各有各的精彩。
何況,短片升級為長片的渠道一直敞開著。獲得2018年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的《四個春天》,就是短片的創造性集結。《慢車開來》導演陳碩認為,FIRST影展和手機品牌聯合來做手機電影這個事情,某種程度上是給手機電影正名,就是手機電影是可以出好作品的,而不僅僅是隨手拍或者vlog層面,是可以形成表達甚至思考的。他補充說:“以前用手機拍人家覺得你不專業,要用大的機器拍才專業,這種器材黨,都有一種鄙視鏈,這個被打破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對我自己的創作來說,手機可以形成美學。”

手機之于電影還有一個深遠的意義——手機便攜又平價,它大幅降低了創作門檻,一般人不必特地購買攝像機或單反相機,也不需要擁有一個專業的制作團隊,只要使用口袋里的手機就能拍攝電影。普通受眾都有自我表達的欲望,通過手機這個移動終端受眾可以突破傳統電影工業流程的束縛,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盡情展示自己的作品。這是將創作的權利從少數精英那里下放給大眾,是影像民主化時代的重要特征。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是表達權的一次進步。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普通公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達便利。手機電影讓創作者體驗到自我存在感,激活了個體表現自我、記錄生活的能力。
那么,普通人可以用手機拍些什么?當手機電影成為創作趨勢,它能為電影的內容創作帶來新的表達方式嗎?這屆FIRST影展“超短片單元”的主題“不虛此刻”,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破題思路。誠如陳碩所說:“我自己在做紀錄片創作的時候,我發現當手機來拍的時候,人物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抗拒或者不自然的感覺,因為身邊有太多人拿起手機隨時拍東西,所以自然度,以及進入這個事件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手機電影在記錄日常時更方便、更即時、更自然,我們不會錯過每一個值得記錄的“此刻”。
“不虛此刻”也是電影誕生的初心。Paolo Cherchi Usai在《電影之死》中寫道:“旅行、消遣、歡鬧或醒目的事件,都是活動影像起源時所表現的內容。”我們回望盧米埃爾兄弟最初創作的那些短片,無不與日常有關,其中絕大部分短片反映的就是盧米埃爾兄弟自己的生活,即他們的“不虛此刻”。手機電影的“不虛此刻”,為野心勃勃、忙著開疆拓土的電影工業做了極好的補充,它使人們更多地關注生活中那些極易被人忽視的普通小人物,關注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態,為他們保留住日常中轉瞬即逝的瞬間。如此,人們不僅可以仰慕超級英雄,也能擁抱身邊的普通人。這也正好契合了vivo如今所倡導的人文理念:通過科技與文化的結合,手機影像不僅記錄了人的文化,也能發現人性的美好。
本冊內容由T China: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風尚志編輯部制作,風尚志編輯部是本屆FIRST青年電影展戰略合作媒體
撰文:曾于里
攝影:任三克
Credit
出品人 馮楚軒
監制 李森
原標題:《影像民主化時代到來》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