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話】郭凈:調查之路,參與行動之路(下)

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
郭凈,民族史博士,云南省社會科學 院研究員 , 紀錄片導演、影視人類學家。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西部山地民族文化史、影視人類學。發表的主要專著有《云南紀錄影像口述史》《雪山之書》等9種 ; 合著、主編《云南少數民族新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6種;譯著《宇宙、神諭與人倫》等2種;影視作品《卡瓦格博》等2種;從事公益項目“社區影視教育”等6項;除學術研究外,還與影視界同人發起“云之南紀錄影像展 ”,參與鄉村影像和文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踐。
采訪者 :張婷婷,北京社會資源研究所成員。
文化視角的重要性
張婷婷:就是沒有文化視角。怎么證明文化視角這么重要?
郭凈:我舉個簡單例子:我們和TNC合作,經過長期交流,他們做了一件事情,派了2~3個專家組成調查小組,由村民帶領,在卡瓦博格幾個村子里跑了半個月,調查藏族眼中的整個生態環境系統。在那之后,我們又和藏族學者調查了一年。TNC是來到中國才知道這個事情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才來討論當地人的環境觀是什么。發現這個環境觀不是簡單的一些說法和想法,而是通過一套地方性知識體系來實施的,藏族人劃分了內部空間和外部空間,內外空間都有嚴格的管理方式。如果我們完全不關注這些,怎么開展以村民為主的社區參與式環境保護呢?只有外面的人說了算而已。
張婷婷:這些經驗也有被意識到,但為什么沒有傳播開來,沒有影響NGO?
郭凈: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相對于全球化過程,往往表現為一個漢化的過程。有一個美國學者叫哈里斯,調查青藏地區的野生動物,寫了一本書叫《消逝中的荒野》,書中提出一個論點,說中國政府在西部做的環境保護,通常是以儒家文化為思想基礎。我們把這個概念延伸開來會發現:在西部做的許多鄉村建設,其實都有儒家文化的背景(民國有的鄉建運動有基督教的背景)。這是什么意思呢?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是一種園藝式的農業,是精耕細作的。但是西南地區各個民族的農業,都是多樣化種植而不是單一種植,此外還有畜牧業、狩獵、采集,還有一部分刀耕火種,這樣一些多樣化的文化和經濟體系,都被現代化消解掉了,改造成以漢族為典范的精耕細作的單一種植體系了。關鍵我們還要看到,許多以漢文化為背景的NGO也是同樣的思維模式,那么,在這樣的華夏文化體系下的NGO系統,會輕易接受西部的文化和生態觀念嗎?很多人甚至都看不懂、不關心,也完全沒有切身的體會。另一位美國學者斯科特以一系列著作(如《逃避政治的藝術》)提出了一個佐米亞(Zomia)的文化區域概念,認為在這個區域的東南亞、南亞和中國南部的許多山地民族,歷史上一直在用部落制、刀耕火種、無文字的文化傳承系統抗拒和逃避平地國家體系的收編。而低地國家則試圖用定居農業、人口和土地控制、文字教育把這些山地民族納入體制當中。這提醒我們,在做西部鄉村建設的時候,會不會有意無意地做了后者的推手?
貴州學者楊庭朔研究過很多農村經濟體系,像一塊地里種很多東西,不是作為雜草來消除掉的,不是一個單一的精耕細作的農業體系,而這種體系大規模地向西部擴張的同時,NGO也在擴張。所以我才覺得,有的NGO很可能是在幫助這種一體化的經濟和文化體系的擴張。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輕易改變NGO大環境和思想認識非常困難。只有先去聚集一小批人,以邊緣的立場,重新思考和尋找出發點。

在德欽縣明永村卡瓦格博山下
張婷婷:我感到自己想要保持自己的個性和獨立思考,但在外面的環境下,就會被牽走,獨立性會受到影響。但好的一點是,我會時不時反思,把自己拉回來。
郭凈:你在社會資源研究所,可以同時做一個學者。學者的好處是可以跳出來做事情。做公益很容易沮喪,我見過太多公益人,做到三十幾歲困惑起來了,跑去讀書,太多了。做公益本來需要理想主義,但你會發現理想主義越做越少的時候,你就會困惑,那時候唯一選擇就是去讀書,去學習。如果你一開始就把身份定為同時作為觀察者和研究者,你就會擺脫這種情緒,你會比別人看得更深入,會看到問題的背后,會比別人看得更長遠,不僅是看到潮流,會看到長時段的變遷,這樣子你心里就會比較踏實。我做這么多年下來,很少覺得不踏實和惶恐,就因為經歷過幾個時代,也因為是個學者,學者這個身份挺好,讓你能夠接受規律和變化。一個村莊消失了,很多人很著急,要去拯救它。其實,任何事物都要經歷成、駐、壞、空的階段,沒有永恒的東西。當你真正去了解這種思想和理論時,你心里會比較踏實。和人一樣,生老病死,文化、社會、族群,都有生老病死,公益圈也不例外。今天是這個潮流,再過十年可能變了。
張婷婷:我的有些朋友真的會沮喪,覺得做了那么多事也沒看到變化。
郭凈:有些人擔心自己難以融入當地人的社會,我們學者也有這個問題,人家并沒有把我們當成自己人。而且你本來就是個外人,怎么可能成為當地人呢?人類學家告訴你,你沒必要成為當地人,即使融入當地文化了也不等于你成為當地人。“去欣賞和了解另外一個文化是我的福氣,是我這一生活得有意義的地方,而不是去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樣去想,很多困惑就不會有了。我在藏族學到太多東西,也學到了很多佛教的內容,但我對佛教也會批判性地去看。
“分享人類學”
張婷婷:有人會說,我覺得人類學作為觀察和開展社區工作的基礎很有必要,但它只能是觀察,沒有辦法導向行動。
郭凈:其實我更愿意把研究者和推動者的身份合而為一,這樣退可以研究、進可以行動。說老實話,很多行動都是失敗的,并不基于當地人的意愿,因為最終的行動者應該是人家而不是你。人類學有一個觀點叫分享人類學,攝像機是一個刺激分享的因素,我們可以通過攝像機去交流,這個過程中,他會發現這個攝像機可以為他所用,這時候你的目的就達到了,他會用這個攝像機來行動。而你要怎么行動?這個社區不是你的,你怎么行動?而且你的行動很可能是破壞社區而不是幫助。
人類學不太主張學者去干預研究對象的生活,只是在當前社會思潮下,我們采取了干預行動,這種干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也要明白這種干預的限度。它只是一個刺激,刺激發生后,適當的時候就應該退出,當地人產生自覺后他們自會行動。比如年保玉則,他們有能力請到10多位活佛來講經,你不可能做到啊,你的辦法是你外來人的想法,但這些想法滋生的行動和設想,大多在社區是失效的。
張婷婷:那人類學的干預行動是怎么產生的?
郭凈:有幾種可能,第一,只研究,不刺激也不行動。鄉村影像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是,我研究的資料可以成為他們的資源——原來人類學家的調查成果都是為自己所用,發表、評職稱,而鄉村并沒有得益。那這就是第一步:我的東西可以分享。
第二,你有了人類學的背景,就容易知道在什么情況下,采取什么方式刺激他們去了解和交流。比如他們對旅游不了解,也沒有環保概念,這些東西進入了,引起當地人的惶惑,這些觀念你就可以給他們講明,在被他們接納后,就可以成為他們的武器。比如藏族接受了環保觀念,這就成為他們保護神山圣湖的工具。而他們對環保觀念的理解和運用和你都是不同的,那么你就和他們成為對話者,可以不斷地提問來引發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又會刺激到他們的行動。就是不斷地把他們的自主性和自覺性激發出來。而且不單是激發出來,他們也有自己不了解的東西,也不是做得都對,那你和他們交談過程中,會意識到問題,比如垃圾問題。你還可以給他們搭平臺,比如原來藏族只和藏族交流,現在藏族可以和瑤族交流、苗族交流,而且原來僧人只與僧人平等交流,到了普通百姓那里就端著講經,但通過拍紀錄片,他們和牧民就可以討論、相互討教。這樣做事情,你就會有成就感,是你幫助了他們,而不是你跳到社區中取代他們做事。現在很多代替村民做事的,村民不用動就等著拿錢,建個廁所,再建個豬圈,老處在這樣的循環當中。

德欽縣雪達村馬背上
張婷婷:一個是分享,一個是提出問題促進思考搭建平臺,還有嗎?
郭凈:更重要的是你成為他們真正的朋友,那時候可能立場都轉變了,不做NGO,會用自己的方法參與很多事情。原來在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工作的一個朋友,在青海做了很多項目,后來到德國讀博士,回國后做生物學的田野調查,和當地人一起做。研究也需要參與性,她用她的方式改變了學術研究的方式,相當有趣。這時她不是NGO,也不是單純的學者,她會享受和當地人的相處,并找到新的研究方式,甚至性格、人生都改變了。
所以,拋開任何的社會運動和NGO,我們活著的目的是什么?無非是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有意義。你選擇了一種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它賦予了你新鮮和欣喜,這不就很好嗎?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張婷婷:如果我有一年時間,我要去一個村子待著,我應該怎么更好地理解社區?
郭凈:人類學是一個非常個人的學科,而不是依靠統計數據去做的學科,非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個體交往。我們認為要深入做鄉村,除了深入了解鄉村,沒有任何途徑可走。比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一個根本性的東西。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實踐過呢?如果你沒有時間自己調查,至少你要讓當地人學會自己做調查,而不是讓他作為一個報告人給你提供情況,因為那種提供很多都是假的,人類學家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也會說假話,就像《天真的人類學家》里說的那樣。云南人類學界已經發展出很多調查方法。比如讓村民寫日志,一年一年地寫,有的村民日記已經出版了。我們也讓村民畫過圖,還可以在那個基礎上發展,光是圖也非常有意思,國外也有很好的經驗。總之,方法是可以去摸索的,關鍵是要深入。包括鄉村影像培訓,“鄉村之眼”也有一套完整方法,很多NGO做不到那么深入。
張婷婷:如何看待行動研究?
郭凈:關鍵看你研究什么的行動?是研究他人的行動?還是邊行動邊研究?我們是兩種都做。我自己習慣于把行動過程作為研究過程,你不止做,還會想為什么去做,帶著批判眼光去行動。
張婷婷:為什么我們這么多的項目,很少有從開始到結束的全程跟蹤和研究呢?
郭凈:我覺得中國的NGO,包括早期的NGO,很多都沒有留下資料,這有缺乏經驗,也有缺乏研究意識的原因。我們談到NGO應該建立的體系,每個NGO都應該建立自己的檔案體系,比如“鄉村之眼”,就特別強調建立影像檔案。這個影像檔案不僅是NGO的,也包括我剛才提到的鄉村知識體系,這個體系需要用一套檔案系統作為基礎,為村民也做一套檔案。村民積累了資料,才會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比如藏族人做了那么大一套關于水的書,那就是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料。如果我們給每個村子都做了完整檔案,分類很清楚,真正想要幫到人家,就要留下東西嘛,不能人一走,什么都不見了。NGO的發展,也需要對自己的生命歷程有反思。
張婷婷:最后,請您給我們年輕人寫一段話吧。
郭凈:就寫毛澤東那句吧:“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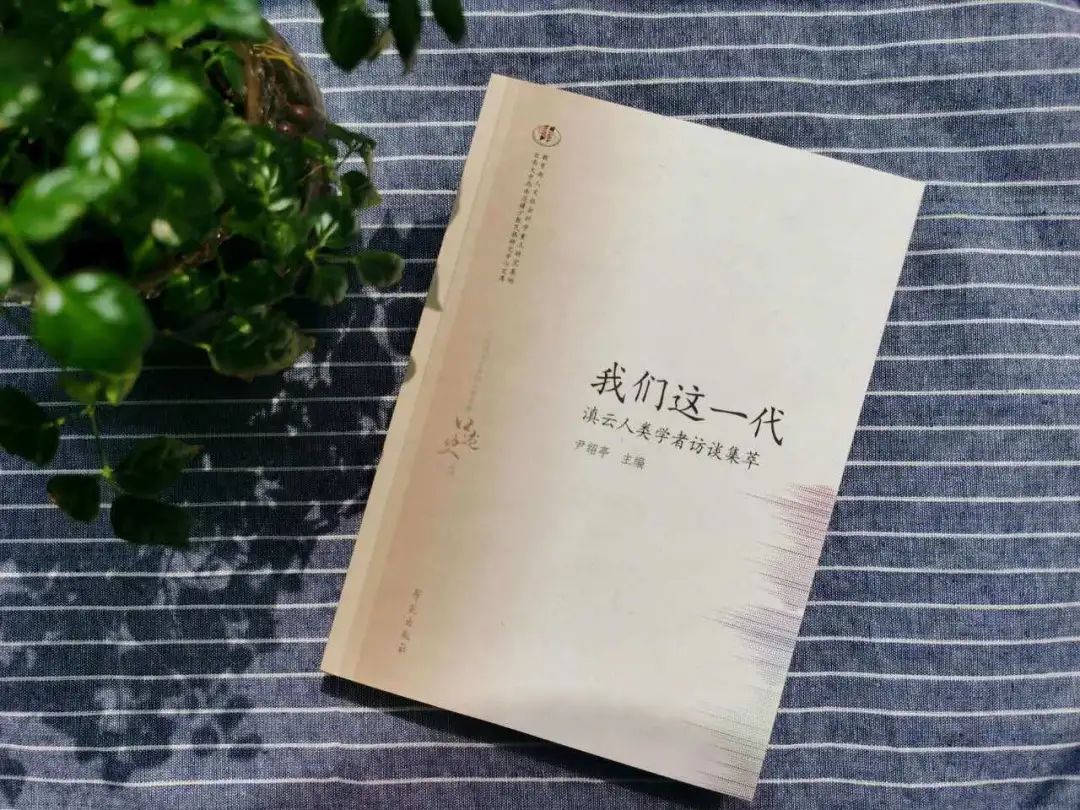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