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生新聞采寫·札記 | 無腳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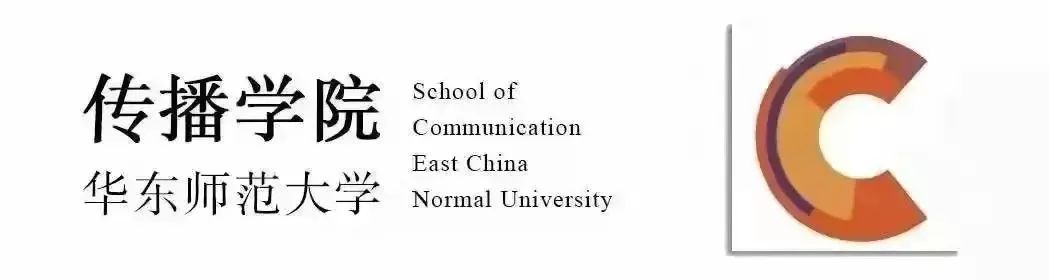
按語
上學期,21級本科新聞和20級本科播音班分別開設《新聞采訪和寫作》和《新聞采訪》必修課,由陳紅梅老師主講。兩門課程以獨立采寫的新聞報道作品作為平時作業,以學期采寫札記和心得作為期末結課作業。
經任課教師推薦,從2023年3月起,本專欄陸續刊發兩門課程的部分結課作業“采寫札記”,講述新聞采寫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給有志于新聞學習的同學們一些借鑒和思考。
無腳鳥
21級新聞學 鄧安之
“世界上有一種鳥沒有腳,生下來就不停地飛,飛得累了就睡在風里,一輩子只能著陸一次,那就是死亡的時候。”
站在車流緩動的路口,抬眼便是參差林立的高樓大廈,穿行在來往行人之中,我們試圖剖開萬物表象,找尋所謂真相,將其呈現,不予置評。在某一瞬間,看見天上掠過的飛鳥,和同伴行走在街頭巷尾,想到可能會從事的行業,會產生一種無法輕易描述的感受,細想起來,可能與無腳鳥相類似。
這學期以前,我從沒認真考慮過從事專業相關行業的可能性。從心而論,專業并不是我的第一選擇,只是為了不浪費高考分數才有的選項,被錄取也實屬意料之外。從被錄取,到來學校上學,了解到一點新聞相關的知識,整個過程,我無法說明是自己的情感更多還是必須去這么做的任務感更多,仿佛從始至終,對這門學科,我沒有很多個人的喜惡在里面,平淡就是最好的回應。
事情開始變得不同,從有人這樣告訴我開始——“你這么喜歡自由,當記者不就挺好的”。新聞這個專業在我眼中逐漸醒過來,一直到接觸新聞采寫這門課,模糊的感覺開始變得愈加清晰。
采寫課從不同的角度構筑了我心中新聞專業的框架,是最重要的一筆,讓它在我心中不再完全無感。第一次不是為了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才去做一些筆記和整理,閱讀和了解更多的新聞,讓我對新聞的認識更加立體和多面——一些報道加深偏見,一些報道打破偏見,未知全貌的時候,一切結論都是不可靠的,在更加了解的同時,我對新聞的一些固有偏見被打碎,另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在不斷生長。
閱讀不同的新聞,對我而言,是在閱讀另一種文學作品,雖然新聞和文學作品在許多特質上并不相同,但在我眼中二者的生命線都是相通的。無論是何種類型的作品,無法打動人心的那一種都是失敗的作品,沒有存在的必要。或許乍見之下新聞客觀得稍顯冰冷,不置可否,客觀事實是其根本,但同樣不可否認,如何呈現事實的方式有許多種,總有一種是可以觸碰人心的存在——我希望看到的新聞都是鮮活有生命的,我希望自己能真心對待手中的每一篇報道。這樣的想法隨著這門課程的深入而不斷明朗起來,我不會稱其為所謂的新聞理想,說到底我并沒有一定要從事這門行業的決心,只是未來如果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我希望自己是自由而又真誠的。
跳出方寸書本與課堂,行走在各個街頭,一個又一個地尋找新聞素材,一次又一次放棄又重拾,踏過許多不知名街道,路過眾多各色各樣的店鋪,每當在如此疲勞奔波依然一無所獲后,不免感受到做新聞真的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僅僅是進入門內的第一步就已經需要耗費許許多多的精力與時間。整個國慶假期的投入,幾乎此后每天都會思考幾次選題方向,周末和隊友一同從早到晚接觸備用選題……很累,一無所獲的時候尤其心累。但不知為何,我有點樂在其中,所有的疲憊都讓我感受到生命的活力——穿梭在高樓大廈之間,為了尋找某種東西,和同伴一起,這樣自由又充實的感覺是具體的。
和同伴尋找素材的那個周末,或許是在所有采寫開始前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天。那是在十多個素材埋沒在手機備忘錄里,“輕型紙”和“中北宿舍”兩個話題都進行不順之后的一次出行,一邊趕路,一邊尋找下一個話題所在地。“古董爺爺”這個選題原本是那一天的主要內容,雖然我們心底都清楚,能邀請到對方做采訪的可能性非常小,也預想過被拒絕的場景,甚至提前給對方安慰打氣,但真正被當面拒絕的那一刻依然不好過。并非是玻璃心,也不是不能接受打擊,當期望徹底落空,失落不可避免。
“也不是全無收獲,他店里的小玩意兒都挺精致的。”從另一個角度自我安慰,可能是必須要有的技能。此前也在互聯網上被許多意向采訪對象拒絕,實際生活中頭一遭而已,我和同伴都深知向各種各樣的人尋求采訪的必要與重要,我們遭遇的拒絕還算十分溫和委婉。
當一整天都陷入囹圄境地,一點意料之外的收獲就足以彌補一天的不順。
能拿到“城市拾遺店主”的聯系方式是那天所有的收獲,卻掃去了之前全部的陰霾。在向他開口詢問之前,我和同伴思考了很長的時間:怎樣才不那么尷尬?怎么做才能顯得更真誠?我承認當時的自己始終缺少一點勇氣,幸得同伴替我補足了缺失的東西。但能拿到聯系方式也并不僅僅依靠于此,運氣占據了大部分因素。
回想所有的采訪經過,幸運是我能想出來最貼切的詞語。沒有很偏激的拒絕,也沒有長久的一籌莫展,仿佛在每一個山窮水盡的地方,都會及時出現下一個柳暗花明之處。
無論做了多久的準備,列采訪大綱、預想答案、猜測可能出現的情況,當我真正與人隔著網絡一對一采訪時,之前的預想都會突然清空,一切準備到最后都只是為了不讓最壞的情況發生。和許松月的采訪過程,與其說是采訪,不若將其稱為聊天。在那些列表問題以外的對話,常常讓我更加了解對方,從另一個角度補全了采訪中時常會遺漏的一些問題,與她聊天、對話,仿佛在和一個經年不見的朋友談及她的往事,總帶給我一種午后唱片機里老歌悠揚的愜意與慵懶感。
一種感受,一個故事,價格是一段時間。采訪于我而言,有點類似于這樣的買賣。和他們對話的過程,或緊張或舒適,都讓我感覺是在隨他們一起回到特定的時間段里,重溫那里發生的人和事,讓原本可能模糊的片段,一點一點地變得清晰起來。
于是在寫下那樣一個故事的時候,會思考很久——怎樣構思和用詞才最貼切——我總是想要將采訪對象帶給我的感受傳達給第三方讀者。在正式動筆之前,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我會偶爾想一想敘事的開頭和結尾,最初只是一些零散的小片段,后來能夠被串聯起來。當整個框架開始清晰明了,《逆時鐘旅人》這篇報道在我腦海中便成為一種暖黃色,報道里的姐姐留給我的印象也是暖黃色的——溫暖而又富有生命的朝氣,她口中的故事同樣如此,因此我的所有遣詞用語都會下意識地偏向于更加溫暖的描述。
從寫稿到定稿,我離不開同伴的幫助,但其實我們的合作比較獨立。她讓我感受到一種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意味,和她一同采寫的過程,仿佛兩種色調的不同碰撞,互相彌補、互相修正。我和她的觀點并不總是相通的,大多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總是各持觀點展開辯論,這樣的經歷讓我對新聞的一些看法更加的完善,總是百家爭鳴才能百花齊放,沖突往往意味著更深入的思考。
和她一起去書店查看各類“輕型紙”書籍的那一天,我們談論過未來的可能性,有關新聞行業的可能性。一般來說,我不是一個喜歡談論不確定的人,也不喜歡討論未來。我不愛想象以后可能的生活,或者場景,那些在我看來都是虛妄,不構成實際的生活價值。因此我沒有具體的可以和別人探討的畫面,和她走在去往下一個書店的街頭,我只能告訴對方此刻的感受——疲憊又自由,無數次提及過的詞語。在她提及的那一刻,我想到了《阿飛正傳》里的無腳鳥,一輩子不落地,落地即是死亡。
我從來不覺得無腳鳥是一個時常與流浪者、邊緣人相聯系起來的意象,“睡在風中”或許也是一種浪漫,我總是由它聯想到所有自由和舒適的感受以及場景。做新聞像是睡在風中的無腳鳥,這樣一句話在我心中卻顯得無比正確又貼切,死亡的那一刻應該是再也感受不到采寫過程中隱藏的快樂的那一刻吧,我無比自然地想到。
無論在何人來看,新聞行業都是日薄西山,而工作在大多數人眼中是謀生的手段,以致越來越多的人不會選擇從事新聞相關的行業,確實如此。我亦沒有鴻鵠之志,不做懷揣高尚新聞理想的人,但只要有某一個時刻,踏入了這個行業的大門,就應該無愧于每一個采訪對象和他們故事中所有的喜怒哀樂。一學期,四個月的課程感受,只有這一點最是烙在我心中,也為這一段的經歷烙下深刻的句號。
我理解了新聞的日落,也理解了同時還有人懷揣理想墜入新聞的日落海中。即使我這樣,對新聞原本無感的人,也會在采寫過程中感受到新聞的魅力,也會想到或許新聞行業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無腳鳥,追求著這個時代的一些無法放棄的東西,自由堅定又浪漫。
鄧安之新聞采寫作品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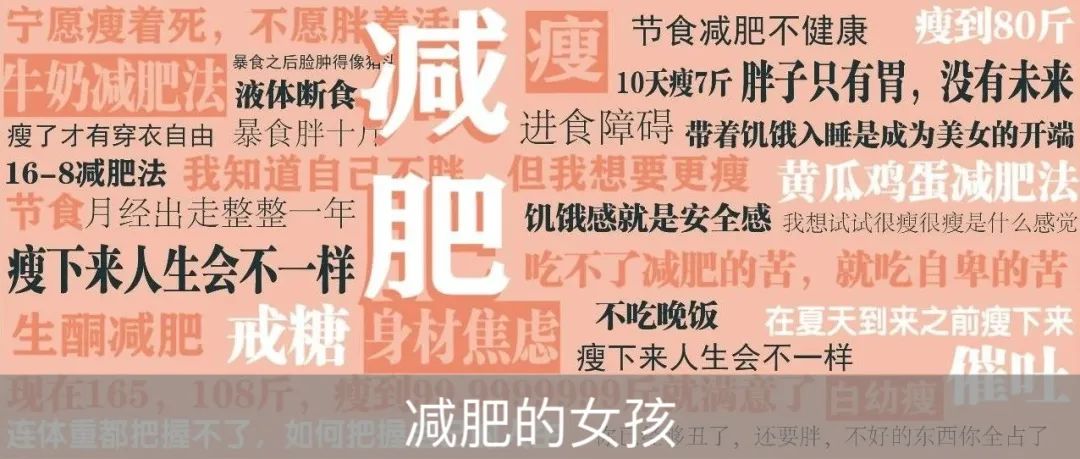

END
圖文 | 鄧安之
原標題:《學生新聞采寫·札記 | 無腳鳥》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