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消失于互聯網時代的100件事


還記得在互聯網時代席卷我們之前,人們是怎么生活的嗎?《消失于互聯網時代的100件事》一書描寫了100個在互聯網時代已經消失或瀕臨消失的生活情景,從日常出發,讓回憶轉身,對現代生活進行了一次細致的審視和反思。作者帕梅拉·保羅認為:“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太多東西,比如說信息、訪問路徑、與外界的聯系、娛樂活動、各種發現、愉悅的體驗、參與感、豐富性,還有少數人偶爾可以獲得的,貨真價實的財富。不過所謂進步,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就像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上述好處,但也拿走了一些其它東西。”
書中提到了許多我們失去的東西:一見鐘情、名片盒、生日賀卡、電視指南、相薄、傳真、家庭聚餐、同理心、耐心……有些東西我們毫不吝惜,有些東西我們萬分懷念。
今天夜讀,回看書中所提及的諸多物品,它們或許帶著懷舊或陳舊的氣息,但并不意味當下時代不需要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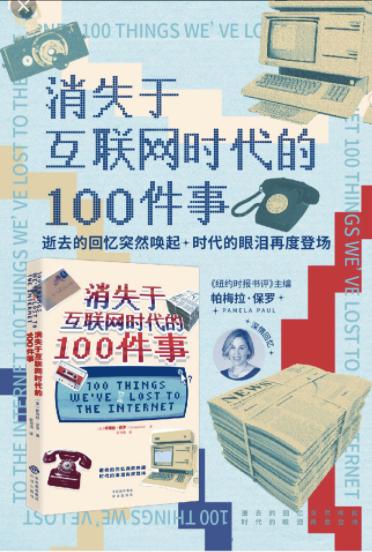
同理心
考慮到我們在線上交流的程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要表達,都有自己的聲音需要被聽到,你會覺得我們所有人都能手牽手站在和平、理解與愛的光輝之巔。哎呀,實際上,人們在線上互動得越多,他們真正聽到彼此心聲的機會就越少。我們可能會讀到其他人的文字,聽到他們說了什么,但我們并不理解他們的弦外之音,也許,我們也不理解他們給我們的感受是什么樣的。
隔離期間,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感受到了與世隔絕的壓抑感,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只能通過上網交流,我們也都只能成為線上的自己,而這種感覺其實是很自然的。當你和其他人在網上互動,而且一直都在網上互動的時候,你會覺得和你交流的人似乎少了點什么。當你們雙方沒有互相理解的時候,另一個人就一直是處于陌生的他者位置,像平面的紙片人一樣,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立體人。

話里有話的文字以靜默符號的形式出現在小小的屏幕之上時,你聽不到話中的語音語調,你也看不到對方的肢體語言。點贊和收藏,都不如眼神交流、深度對話,以及全身擁抱那般具有同樣的情感沖擊力。視頻通話里的大頭像因為與我們沒有共享空間,而失去了某些東西,那些失去的東西難以言喻,是我們同處一個物理空間時,與他人哪怕一句話不說,也能產生的某種聯結。
哦,當然了。當手送信和名片每天都在19世紀90年代的倫敦會客廳之間轉來轉去時,誤會時常發生;當我們和大學時代的朋友在20世紀90年代煲電話粥時,許許多多情感上的微妙之處也消失了。你看不到電話線另一頭的人翻白眼,也不確定對方這次的簽名落款寫的是“真誠的”,而不是“最真誠的”,有什么含義。不過當人們書寫發自內心的長信時,你的確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字斟句酌,而在煲電話粥的時候,人們也會遵守一定的通話規則。
而在數字空間里,這些信件和電話會怎么樣呢?互聯網忽略了,或者說破壞了人類的組成元素,比如同理心、深層次關系、兒童成長、家庭和睦、持續對話、讓步與同情心。互聯網的產品和服務幾乎全是由20多歲的單身男性開發而成的,不管這些人的動機多么單純,都是基于金錢與權力在開發互聯網系統的。各種網絡工具和網站所反映的價值觀,并沒有考慮12歲女孩或75歲老人的優先需求,而人工智能的思想也不是基于他們的想法而建立的(只有12%的頂尖機器學習研究人員,也就是從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是女性)。有些人口統計學信息只是對我們的底線沒有價值可言,而人類產生的情緒,并不完全都是為了賺錢。

同理心,還有許多其他作為人類的基本特征(溝通、友情、暴力),都可以被分為兩類:現實世界的,還有虛擬世界的,而且這兩者往往相互排斥。虛擬的那些特征往往很膚淺,就像虛擬的友情,或者是社會學家所說的“準社會”友情——這種關系純粹存在于腦海之中,而且往往是單向的,比如,14歲女孩和她最喜歡的視頻主播之間的友情,前者會給后者發消息,購買她帶貨的商品,還會對后者產生各種不對稱的、沒有回應的感情。
盡管虛擬關系可以通過喜好和共鳴讓人們團結一致,但也可以通過拉踩和恐懼將人們化為仇敵。社交媒體因為發布抓眼球的帖子而欣欣向榮,尤其是能夠抓住人們情感注意力的帖子——這就是所謂的“情感參與度”,而這些情感也包括負面的情感,主要是憤怒與恐懼,但也有悲傷與驚訝,或者用更直接的說法:聳動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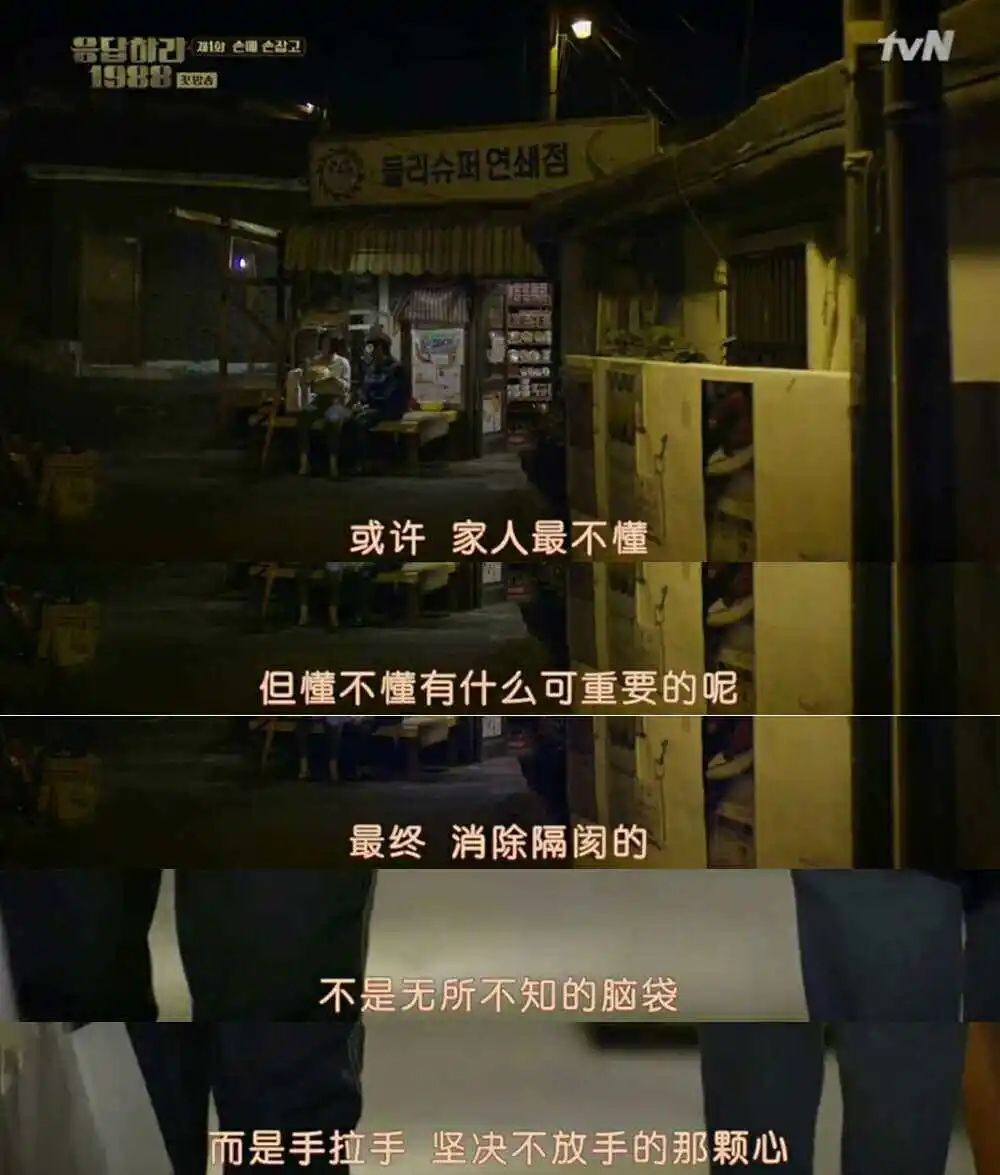
▲ 《請回答1988》劇照
人們還傾向于分享能夠讓他們感覺良好,并且能夠鞏固他們信念的帖子,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永遠在互相肯定的閉環——一個備受關注的網絡同好小圈子,而不是各種各樣探索他人想法,或者告訴其他人應該做什么的帖子。比起闖入別人的情感領土,我們更愿意牢牢穩穩地待在自己的舒適區里。我們反復地鞏固自己的偏見,卻不愿意去探索偏見的另一面。
在網絡世界里,訴說多于傾聽,開放式傾聽則幾乎沒有。線上互動更多的是發現人們對誰誰誰生氣了,或者對什么事情發脾氣了,而不是分享心事和想法。線上互動根本來說就是同理心的反面。在網上,憤怒實現了很好的自洽,而別的情緒則被排除在外。
2010年密歇根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從1979年到2010年,大學生的同理心下降了40%,尤其是互聯網時代,也就是2000年到2010年期間,換位思考和共情關切這兩項能力下降得最多。你可能沒辦法用簡單的科學研究術語把共情能力的下降與變幻莫測的算法聯系在一起,但也很難忽略這二者重合的軌跡。
沉迷演出
劇院的燈光一旦暗下來,外面的世界便消失了,而且會足足消失兩個小時。如果上演的是電影《安娜·克里斯蒂》或《妖型樂與怒》,那便是一種享受。如果你受困于中間一排,看的又是音樂劇《星光快車》,那就更接近于折磨,不過無論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作為觀眾中的一員,意味著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忘記劇院外發生的一切,沉浸于舞臺的故事之中。沒有其他辦法,別人就是找不到你。就算保姆一直抱著孩子沒法放手,就算你的前男友正在醉醺醺地敲打你家大門,就算你奶奶給你寫了封信正在信箱里等著你去拿,他們也都必須等舞臺落下帷幕,等你回家才能找到你。你正在看表演呢。
最糟糕的打擾可能是酸味水果糖包裝紙發出響亮而皺巴巴的聲音,或者座位離過道最遠的孩子在第一幕中途要小便了。有些人可能會不由自主跟著一起唱,或者大聲詢問鄰座觀眾剛才舞臺上發生了什么。在學校音樂會上就更隨意了;很可能有一兩個過分熱情的父母擋住了你的視線,就為了找一個好的角度看到舞臺上他們的孩子。在體育場演唱會上坐你旁邊的人可能會在別人喊安可的時候,反反復復輕擦一個壞了的打火機。

▲ 電影《雨果》劇照
而今天,即使是最嚴肅的劇院觀眾,也免不了呈現出馬戲團的氛圍,與上述一切都無法相提并論。就算所有演出開始之前都會有廣播聲明,直接請求我們把手機靜音、不要錄像、不要使用閃光燈照相、并且要好好尊重演員,劇院里似乎沒有人會真的把手機關機。噢,當然他們還是把手機靜音了,只是不會完全關機,因為——你懂的,因為等會兒重啟要花的時間太久了,而人們僅僅只是無法忍受和別人斷聯而已。所以就算你坐在那里,打算全身心沉浸于演出本身,你還是可以聽到從外套口袋里傳來的低沉嗡嗡聲,你的鄰座也可以聽得到,哪怕是輕微的打擾,也會把你們的注意力從舞臺上拉回來一點點(比如說,你會看手機,看看你老板回復了那份備忘錄嗎?)。我們還能看見坐在三排前的人把手伸進了手提包里,當屏幕暗下來的時候,小心翼翼又心不在焉地嘗試看手機。沒用的,女士。我們看到你在看手機了。
大多數流行音樂演唱會都允許使用手機,不管這對于演出者來說有多少干擾。不過新奇的是,想要把整場演出錄下來以后看的人無處不在。“請問你可以不要再用攝像機錄我嗎?因為我就在這里,在真實的世界里,”這是歌手阿黛爾在歐洲巡回演唱會上對一個粉絲說的話,“這是一場真實的演出。”
句號
還有其他標點符號比卑微的句號更不起眼嗎?這個招人煩的小點,本職工作就是讓你完全停下來。沒人把句號當作話題來討論。有關句號的看法,力挺也好,反對也罷,文學傳統里都無跡可尋。比起圍繞分號、牛津逗號,或者濫用的破折號所展開的熱情洋溢的語法內訌相比,句號和它那即將過時的命運,能引發的莫過于一聲沒精打采的哈欠。不過哪怕是平平無奇的句號,也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句號直接、果斷,而且還不裝腔作勢(絲毫沒有括號的優柔寡斷)。句號恪盡職守,然后朝下一個句子前進。現在,句號沒用了。或者用當下流行的說法:要在線結束話題,句號充其量就是個可選項。在社交媒體上,你不會用句號來結束一個句子,除非你想讓自己看上去不知道在干嗎。句號已經變成了難事和壞事的象征。近期一項語言學研究發現,句號不僅僅是在非正式的文字短信息里變得相當罕見,而且總的來說,它最常見的用途是談論重要事項。

句號意味著人們在斟酌措辭。當你被叫去和老板開會的時候,就得使用句號,表示你不是要閑聊。句號意味著在屏幕的另一邊,有人特別不開心。句號讓你顯老,讓你過時,還讓所有人情緒低落。“只有老人家或煩心人才會在每條信息的結尾加上句號”,這是維利亞·圖克在她的現代禮儀指南《殺死所有回復》中寫到的話。
句號可以給人一種非常有力的強調感,因此聽上去有些諷刺,網絡版的“拜托”,“不,謝謝”,還有“真的嗎”卷成了一個小點,這種趨勢出現在數字時代早期,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得以加強。到2009年,“互聯網語言學家”格蕾琴·麥卡洛克指出,有互聯網用戶把句號定義為“一種炫酷新方法,用來加強(通常情緒化的)嘲諷語氣”。句號還能給人一種被動攻擊的印象,這是麥卡洛克追溯至2013年的一種趨勢。
句號的一部分問題不在于它本身是什么,而在于它本身不是什么:句號不是感嘆號。感嘆號不再局限于孩童般熱情的爆發,或是間歇性的特別強調,而是變成了溫暖與真誠的傳遞符號。所以當感嘆號缺席,你將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當對方郵件里只是寫了“謝謝”或者“酷”的時候,你會發現你腦子里想的是:“他一定不喜歡我的想法。”
這也是為什么感嘆號無處不在。真的是無處不在!谷歌郵箱的自動回復永遠不會只有“謝謝”。就算沒有人工智能輔助,如果你嘗試寫一封不帶感嘆號的郵件,也會聽起來像個混蛋。而感嘆號在郵件里通常出現的位置,以前明明用句號也挺好的。人們收到不帶感嘆號的郵件,讀了之后一定會思考:“我是不是做錯什么?”違背你的直覺,違背你在大學學到的一切,違背你在職場溝通中應當采取的做法,尤其如果你還是個女人,那么你一定會寫“謝謝!”,甚至是“謝謝!!”現在不這么寫就意味著你不夠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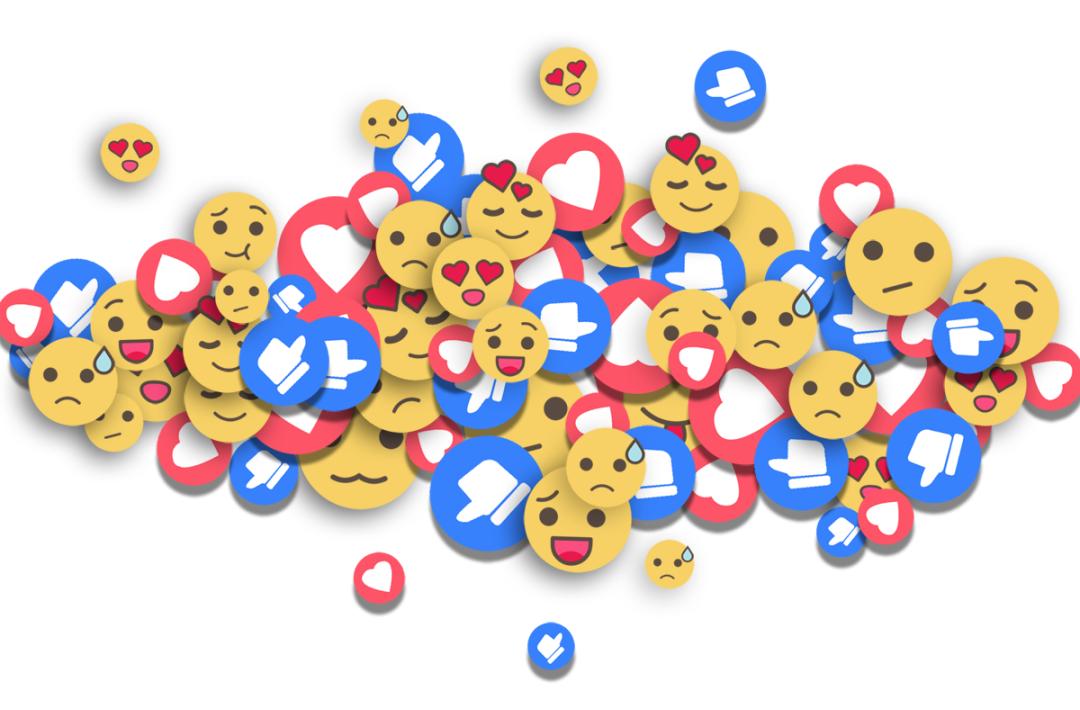
你會發現,你將質疑每個句號。你會發現,你在糾結到底是用兩個感嘆號還是三個感嘆號回復才是最好的。有一天,你醒來后會發現,你在使用表情符號,卻不帶諷刺意味。你在給你的孩子發親吻短信,同時思考哪種顏色的心形和哪種辦公區公告相匹配,另外還會想,如果通過電子形式給你的主管使眼色會不會很奇怪。你或許人到中年,但正在以翻白眼的方式為郵件收尾,然后經過一番自我覺醒,趕緊補上了一個/笑哭。
(《消失于互聯網時代的100件事》帕梅拉·保羅/著,張勿揚/譯,中譯出版社2023年1月版)
原標題:《消失于互聯網時代的不僅是那些懷舊物件,更有專注、沉浸的內心世界|此刻夜讀》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