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本人講抗戰︱操東北話的日本“義勇軍”跟隨林彪過長江
兩年前,我在做“中日戰爭和解的民間運動”相關的研究調查過程中,結識了現年85歲的藤后博巳老先生。藤后先生近年多次作為日本和平團體“紫金草合唱團”名譽團長訪華交流。我與藤后老先生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2012年紫金草合唱團訪華交流的時候。通過日語的簡單交流,老先生得知了我是東北人,于是,開始用熟練的東北話與我攀談。這實在讓我驚訝。經過一番詳談,我了解到老人是當年日本“滿洲移民”政策的親歷者,而且還有著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
接下來,文中直接引用部分來自于我對當事者本人的采訪,其他部分來自于我對老人口述細節及相關史料的綜合整理。直接引用部分中使用了日語中常用的“滿洲”說法。

日本歷史上的“滿洲移民”
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人移民現象早在1931年之前就出現了。1905年日俄戰爭之后,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取了包括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在內的一系列在華特權。當時的日本政界出現了以陸軍大將兒玉克哉和之后的滿鐵總裁后藤新平為代表的“滿洲移民”思潮。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移民鞏固日本在東北地區利益,以防止沙俄卷土重來。就這樣,日本開始了向中國東北地區移民的一些初步嘗試,其移民數量在“九一八事變”時達到了一千五百人左右。這一階段在20世紀日本移民史上被稱為“早期移民”。
“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移民得到了日本軍隊的武力保障。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政界開始籌劃更加詳盡的移民政策。1932年2月的關東軍統治部的《日本移民法案要綱》中,在“政治”、“社會”、“經濟”這三個部分之外,明確提到了“軍事”目的。原文中提到“滿蒙是軍事用地,而且很快會成為我國國防第一線。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從我國內地(指日本本土)動員移民,使他們在滿蒙全境定居。平時可以從事文化以及資源開發,一旦出現特殊情況,可以立刻拿起武器勇敢面對。這是我們國家所希望的……”(《満州の農業移民方策》、1932年2月)如果說日本的“早期移民”是以經濟為目的進行的農業移民,那么這一階段則在保證經濟利益的同時將重心轉向了政治與軍事方面。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1936年,被稱為“武裝移民”。
1936年,日本國內確立了法西斯政權。掌握實權的廣田弘毅內閣在“七大國策”中提到了移民政策,這也預示著移民在日本侵略中發揮更加重大的作用。1937年的“七七事變”爆發后,大量成年農民被征入軍隊或軍工業,導致移民出現人員短缺。為了彌補這種短缺,日本政府開始動員青少年移民,歷史上稱為“滿蒙青少年義勇軍”。這一政策使得日本的移民政策得以在人員短缺的情況下持續到1945年抗戰結束。截至到1945年,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從事農業生產的移民總數達到了27萬人(注:截至1945年,中國東北地區日本移民總數為155萬人。這既包括帶有農業生產任務的移民,也包括了兼有武裝性質的農業移民。)這一階段在再后來被稱作“國策移民”。
15歲日本“義勇軍”來到中國
85歲的藤后博巳老先生當年正是作為“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中的一員進入中國東北。關于自己為何會去中國,老人這樣講道:
我去“滿洲”的時候剛剛十五歲,放到現在也就是個初中生。所以后來人們經常會問我,當時你還是個孩子,為什么會去那么遙遠的地方呢?
在我的少年時代,日本社會中全方位地充斥著軍國主義。我第一次聽說“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以下簡稱“義勇軍”)的消息還是在高等國民學校二年級(相當于現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當時的老師說“我們要和滿洲的人們友好相處。他們建立國家需要我們日本青少年的幫助!”,甚至來到我們每個學生的家里勸我們參加“義勇軍”。后來才知道,當時的老師們接到了“文部省”分配下來的指標,也就是說,一個學校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學生去參加。
我當時天真地被宣傳所說動了,覺得如果為了國家怎么樣都行,就決定去滿洲了。當然,當時的背景是我從小接受的是軍國主義的教育。那時我是以為國家去“滿洲”而驕傲的。另一方面,一直憧憬的“大陸生活”對我來說也很有吸引力。就這樣,我報名參加“義勇軍”,并接受了一年的訓練后,來到了“滿洲”。
那么,在這位親歷者眼中,所謂的“義勇軍”到底是什么樣的組織呢?
這個“義勇軍”其實被稱為關東軍的“虎之子”。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政府把“偽滿洲國”當作國防的第一線,一直在考慮如何才能強化“國境”的防衛。最后想出的方案就是“農業移民”。日本政府認為,無論什么時候,能作為后備兵力出動的武裝青少年團體都是必要的。而這個“義勇軍”就是“開拓”和“侵略”的青年幫手。最開始是作為關東軍的預備隊來設計并實施的。
就這樣,藤后老人作為關東軍的后備力量,在日本國內接受了一年訓練之后,于1943年來到了中國東北。

躲過了“西伯利亞抑留”,成為解放軍
來到中國東北一年半之后,藤后先生就在哈爾濱迎來了抗戰的結束。當時,“義勇軍訓練生”被拘留在牡丹江的日軍收容所。日軍收容所中的人是要被蘇聯軍隊帶去西伯利亞的。由于藤后老人當時尚未成年,才得以被釋放,幸運地躲過了“西伯利亞抑留”。(譯者注:數十萬的日軍成年戰俘在戰后被蘇軍帶到西伯利亞,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下從事高強度勞動。在伙食不能完全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大量日本戰俘死在了西伯利亞,史稱“西伯利亞抑留”。)當時藤后病倒了,被擔架抬回了哈爾濱的“原訓練所”。老人常常感嘆,如果當時被帶去西伯利亞,可能抱病在身的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回到哈爾濱之后,屬于開拓團的糧食已經沒有了。如何熬過哈爾濱寒冷的冬天成為老人面對的又一個問題。很幸運的是,老人得到了善良的中國人的幫助,得以在一家中國飯店里工作。就這樣,藤后老人平安地度過了那個冬天,并且在這個冬天里學會了中文。
1946年春天,“八路軍”(之后的解放軍)取代前蘇聯軍隊進駐哈爾濱。談到對于“八路軍”的印象,老人說:
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的“八路軍”對我們日本人的態度和前蘇聯軍隊完全不同。“八路軍”對我們態度很好,而且軍紀相當嚴明。當時的我對于關東軍之外的軍隊還一無所知,因此很驚訝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軍隊。這也是我后來參加八路軍的一個潛在原因吧。
1946年秋天,包括藤后在內的“義勇軍訓練生”集合在一起,在“居留日本人會”的安排下準備乘最后一班車回國。但由于國共內戰的戰況惡化,日本人的歸國被暫時中止了。就這樣,“訓練生”們繼續留在了哈爾濱。
過了一段時間,解放軍對這些“訓練生”發出邀請,希望他們能作為“擔架員”參軍來配合中國的解放戰爭。當時解放軍的說法是“你們絕不是俘虜。而是為了中國解放而留下的國際友人”。這些參加了解放軍的日本人被稱為“留用日本人”。據其他當事人反映,當時的“邀請”帶有半強制成分。有一些日本人是“被迫留用”,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因為嘆服于解放軍嚴明的軍紀,主動要求參軍。當時,解放軍中的成員以農民居多。比較缺乏醫療和技術方面的知識分子。因此“留用日本人”中也包含了相當一部分護士與技術人員。據藤后老人回憶,當時共有八千到一萬名的日本人留了下來,并參加了解放戰爭和之后的新中國建設。一直到回日本之前,“留用日本人”都受到了和中國士兵完全一樣的待遇,并沒有受到任何歧視。
過長城,渡長江,解放海南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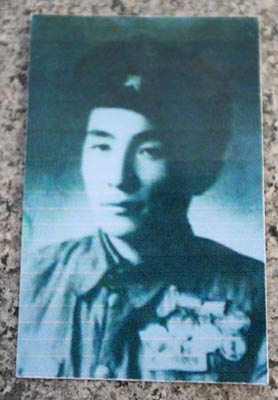
當時作為擔架員被送上前線的我們,其實也是第一次親身體驗槍林彈雨的作戰現場。1946年冬天,在參加解放長春的戰役時,我的腳被凍傷了,之后暫時被送到后方的醫院治療。出院之后,我和之前的軍隊失散了,就暫時在解放軍編制的車隊里工作。那時,解放軍解放了整個東北,受美國支援的蔣介石部隊開始實質反攻。于是我所在的部隊被編入了“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部隊會師之后,我們一路過長城,渡長江,橫跨中國大陸,最后參加了解放海南島的戰役。這對日本人來說是很難得的體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我們還在作戰途中。當時聽到建國消息,我和中國士兵緊緊抱在一起,相擁而泣。那時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解放軍是多么偉大的軍隊,也堅信我們會取得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與此同時,我想到解放軍是人類史上罕見的軍紀嚴明的軍隊。“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種簡潔明了的軍紀,如實地反映了其作為“人民的軍隊”的特質。在解放軍中的多年生活,使我親身體驗到了中國革命一刻都不離開人民的特質。
在解放中國南方后不久,老人所在的部隊就因朝鮮戰爭而移師東北。因為日本人不能參加朝鮮戰爭,老人就被安排在丹東的后方修汽車。1954年,老人離開部隊,被安排到貴州貴陽的機械廠與一般的日本技術人員一起工作。就這樣,老人接近8年的解放軍生涯畫上了句號。
朝鮮戰爭結束后,中斷許久的“日本人歸國”活動經由紅十字會牽頭以及中日雙方的一系列交涉,于1955年重新啟動。藤后在1955年2月從天津塘沽坐上了“興安丸”號歸國船,就這樣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祖國日本。
你能理解他對異鄉的眷戀么?
回顧自己在中國的多年經歷,藤后老人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像我們這樣的,為了建立新中國而被留用的日本人,從抗戰中日中對立的時代一直到抗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與中國人一起生活。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和中國人之間產生了超越國家對立的友情。我想就算把這說成為“日中友好”而播種也并不過分。這是我們廣大留用日本人的心聲。從另一種角度看,對于日本侵略的反省和謝罪,最終不也是為了“日中友好”嗎?
就這樣,藤后老人帶著“決不允許那悲慘的戰爭重現”的信念,在回國后加入了“日中友好協會”,到今年已經快60年了。老人認為,無論是針對歷史認識問題,還是針對“日中關系”可以與歷史分開來看的觀點,都很有必要把類似他所經歷的戰爭體驗傳遞給更多的人。因此,老人近年來也致力于讓更多的日本年輕人知道戰爭的實際情況,并希望以此來喚起年輕一代對戰爭體驗的關注。
遇到藤后老人之后,筆者又在之后的幾次調查中陸續遇到了幾位有留用經歷的日本老人。他們對中國的眷戀之情令筆者感到驚訝。例如擔任日中友好協會東京都理事的三井老人,聽說筆者是中國人后,一邊在紙上畫著地圖和自己的移居路線,一邊興奮地向筆者講述其在中國的經歷。而另一位老人,在一次為中國洪水災區捐款活動的慶功會中,飽含深情地用中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歌唱祖國》和《國際歌》。戰爭年代的體驗,在這些老人身上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在感嘆這些80多歲的老人時至今日仍然活躍在日中友好活動的第一線的同時,筆者也期待這種在正視歷史基礎上致力“日中友好”的信念能在日中兩國后繼有人。
(作者系大阪大學人間科學研究科人類學博士生,主要研究與戰后中日和解有關的民間運動。)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